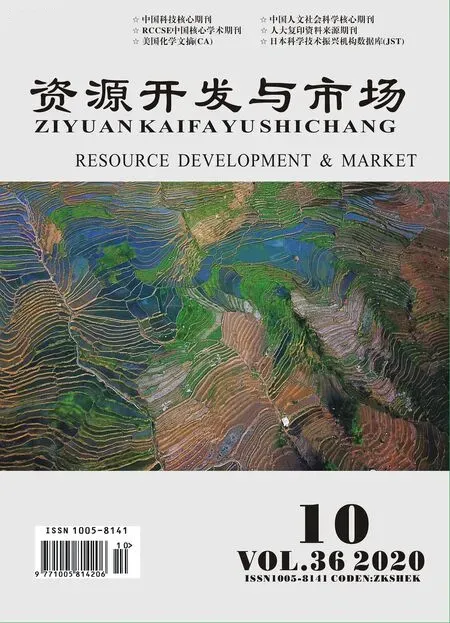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評價研究以湖南省江永縣上甘棠村為例
曾 燦,潘鑫王月1,李伯華,竇銀娣
(1.衡陽師范學院 城市與旅游學院,湖南 衡陽 421002;2.湖南省人居環境學研究基地,湖南 衡陽 421002)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曾指出,“脆弱性是世界面對的一個現實,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首先就要減少發展的脆弱性”。傳統村落人居系統的經濟、社會、生態、文化之間關系錯綜復雜,目前我國傳統村落空心化問題嚴重,文化活性被破壞,人居環境原生空間逐漸解體[1],要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實現傳統村落人居環境可持續發展,同樣需要減少各子系統的脆弱性。脆弱性研究起源于災害學、水資源學等領域[2],20世紀70年代后研究延伸至生態學、社會科學、地學與可持續科學等領域[3],區域(城市)人地耦合系統脆弱性[4]、(旅游)產業系統脆弱性[5]、農村家庭生計脆弱性[6]、傳統村落景觀脆弱性[7,8]等多學科交叉融合的自然—經濟—社會復合系統脆弱性成為新的研究熱點。總體上來看,脆弱性作為一個科學術語被地理學、災害學、資源學、全球變化、社會學、經濟學和可持續發展科學領域眾多專家學者所應用,現已成為現代地理學及其相鄰學科詮釋地球“人—地”系統作用機制,探索人類活動的生態與環境效應的重要科學途徑和具有重大意義的前沿科學問題[9]。
人居環境是環境、社會空間和歷史文化的融合,是人類聚居的基本環境要求。國外學者在人類聚居學的基礎上,對城市及社區、城市邊緣區、鄉村等人居環境進行了系統研究。人居環境評價主要在城市與鄉村兩個層面,城市人居環境評價指標體系較健全[10,11],鄉村人居環境評價研究則相對薄弱,指標的確定也沒有統一標準。傳統村落作為農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遺產,其人居環境的多元價值和現代意義一直以來成為國內外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12-16]。目前對傳統村落人居環境方面的研究很少,有代表性的是李伯華等學者對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轉型發展進行的較為系統的研究[17-20],而以傳統村落人居環境為主要對象的評價研究更是鳳毛麟角,多是把人居環境作為傳統村落整體評價中的一部分,如滿意度評價[21]、適宜性評價[22]、資源評價[23]、保護評價[24]、質量評價[25]等。目前,對人居環境評價的方法大多為層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模糊綜合評價法等,已基本形成了一套評價方法與模型。
鑒于此,本文選取湖南省湘南地區千年古村落江永縣上甘棠村為案例地,從村落整體入手,運用脆弱性理論,探討了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的概念內涵,構建了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研究框架和定量評價體系,揭示了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的形成機理,提出了降低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的調控措施,以促進傳統村落的保護與開發利用。
1 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理論解析
1.1 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緣由
具有獨特地域文化和民族風格的傳統村落成為新時代我國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不容小覷的重要資源和潛在力量,也是當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主要抓手之一[26]。在經濟飛速發展和社會急劇變遷背景之下,依托于千百年農耕文明建立起來的中國傳統村落正逐漸失去其存在的穩固基礎,經歷著令人扼腕痛惜的快速消亡過程。湖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中心對17省的調查數據顯示,頗具歷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藝術研究價值的傳統村落從2004年的9707個驟減至2010年的5709個,平均每年遞減了7.3%,平均每天消失了1.6個[27],而一般性古村落則更是以每天幾十個的速度遞減。專家估計,我國現存古村落僅占全國行政村總數的1.9%,具有較高保護價值的則不到5000個。
傳統村落既是居民的生產生活空間,又承擔著生態環境保護重任和文化遺產傳承使命。傳統村落這一特殊人居系統關系錯綜復雜,在新型城鎮化語境下對我國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轉型發展的演化規律有待進一步探索。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轉型發展過程中容易受到水、火、風等自然因素的侵襲而表現出脆弱性,更易受到人為因素的影響而表現出年久失修、人去樓空、過度開發、設施老化、人為損毀、手藝失傳等脆弱性。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是鄉村地區人—地關系變化的重要表現,而人居環境脆弱性研究不僅有利于找出其轉型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主要驅動力,同時也為鄉村地區人居環境治理提供了必要依據,對傳統村落人居環境可持續發展與鄉村振興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2 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內涵與系統構成
人居環境科學起源于希臘城市規劃學家C.A.Doxiadis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人類聚居學”,是以包括鄉村、集鎮、城市等在內的所有人類聚居為研究對象,著重探討人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人居環境普遍指人類所居住的自然、社會、經濟、文化等環境的總稱,是一個復雜的巨系統,強調從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全面綜合地對人類聚居進行闡釋。而脆弱性在實質上是源于系統內部的一種基本屬性,是在外部特定的干擾下表現出的對這種特定干擾的敏感程度,由系統內部結構和外部干擾的不同特性確定[28]。結合人居環境和脆弱性概念,本文嘗試將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表述為:傳統村落人居環境的內部系統在發揮歷史延續、文化承載與生存和諧的功能過程中,因地形地貌、自然災害、環境變遷、村莊建設、旅游開發等自然和人為干擾活動所引起的,對擾動的敏感程度及其在被損害后復原的難易程度。
吳良鏞先生將人居環境系統分為自然系統、人類系統、社會系統、居住系統、支撐系統等5大系統[29];李伯華、竇銀娣、曾燦等學者在鄉村人居環境研究的基礎上,將傳統村落人居環境引申為人類生活生存必需的自然條件和資源的自然生態環境,地方傳統習俗、文化制度和社會背景的社會文化環境,村民能進行生產生存活動的具象的地理地域空間環境[17-20]。傳統村落的脆弱性研究通常從系統的內部影響與外部威脅兩個維度切入,借助探究其影響因子和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的方式獲取研究結論[7,30]。本文結合人居環境系統和脆弱性的基本維度,分析了兩者間的內在聯系,嘗試從自然生態環境(N)、居住空間環境(L)、支撐設施環境(I)、社會文化環境(S)4大子系統建立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評價體系(圖1)。

圖1 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系統構成
1.3 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因子選擇
結合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四大子系統層次,遵循科學性、目標性、系統性、可操作性、簡潔性等原則,通過對大量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資料深入挖掘、分析和咨詢專家等方法,提煉出適用于人居環境脆弱性評價的具體指標。將對人居環境脆弱性影響較小的指標進行剔除,保留對人居環境脆弱性影響較大的指標,對符合系統特性的指標按照系統層要求進行分類,得到包括32個具體指標的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評價體系,見表1。
具體為:①選取自然環境、人工環境評價村落自然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共計6個指標。其中,村落地形地貌、水體與村落的整體融合度能增加人居環境的適宜度,村莊所處氣候區和該地的氣溫、降水等適宜程度是人居環境重要的考察因素,屬于逆指標;自然災害發生頻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傳統村落的可持續發展,屬于正指標。②選取傳統建筑、空間環境特征共9個指標評價居住空間的脆弱性。其中,傳統建筑是傳統村落中最具代表性和特色的部分,傳統建筑的質量、材質、久遠度是影響居住質量的重要因素,而建筑功能置換率的測算則是為探究傳統村落人居環境更替的特點,為人居環境脆弱性進一步研究做補充。L7—L9對除建筑空間外的其他生活空間進行研究,是人居空間環境的深層次要求,為逆指標。③選取消防設施覆蓋率、衛生設施覆蓋率、電力設施覆蓋率、自來水覆蓋率、排水設施覆蓋率等8個指標對支撐設施系統的脆弱性進行評價。傳統村落擁有需要重點保護的傳統建筑,為維護傳統建筑的環境安全,保證村民日常生活生存的需要,設置消防設施,配備足夠的垃圾桶、公共廁所等衛生設施,配備維持基本生活的自來水、電力等設施,是提高人居環境質量的重要手段。根據傳統村落實際情況,分析其缺少的設施建設也是人居設施環境建設的重要步驟。④選取社會經濟、精神文化、旅游開發等3個方面9個指標評價村落社會文化環境的脆弱性。其中,S2村落人口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民在村落生活的滿意度,而S4—S6傳達了當地傳統民俗活動沿襲情況、舉辦頻率和村民參與度,以及當地歷史性故事久遠度、傳統精神發揚程度等顯示出傳統村落當地民俗文化村民的接受度,更深入反映了文化環境對人居環境的影響。村民的平均收入和村落“空心化”程度從側面反映出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特點。村民收入與人居環境脆弱性呈負相關,“空心化”程度則與人居環境脆弱性呈正相關。S7—S9揭示了旅游開發是傳統村落的普遍開發模式,旅游開發情況從側面的角度反映了傳統村落人居環境的內在要求,旅游開發的程度不同,對人居環境的影響及大小也不同,表現形式也可能隨著旅游開發完成情況出現相反的結果。

表1 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
2 研究區概況與數據處理
2.1 研究區概況
上甘棠古村位于湖南省江永縣城西南25km的夏層鋪鎮,是周氏族人世代聚居之地。上甘棠村作為我國古代建筑遺產中的一份珍寶,具有豐富的歷史藝術價值與重要的科學價值。2006年上甘棠古村落建筑群被列入我國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7年被評選為第三批國家歷史文化名村,2012年被列入首批中國傳統村落,其村落主體建筑群、摩崖石刻與周邊山水環境等物質因子和民風民俗等非物質因子皆為當地珍貴的文化資源,體現了中古時期文化的精華。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上甘棠村的年輕勞動力外流越發嚴重,老、幼年的比例過大,7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和18歲及以下的青少年人口居多。近年來,隨著美麗鄉村建設的快速發展和鄉村旅游開發的持續進行,上甘棠村人均收入實現了大幅增長。當前,上甘棠村人居環境建設面臨著諸多不確定因素,如城市文化的入侵、利益主體的涌現和生活方式的革新等,導致傳統村落人居環境系統演化趨向復雜。
2.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本文依據脆弱性評價的基本思路,參考有關定量方法在脆弱性評價中的應用[31-32],同時考慮方法的技術性與可行性,選用層次分析法的綜合指數方法對上甘棠村人居環境脆弱性進行了定量評價,綜合分析了該村的人居環境脆弱性特征。N1—N2通過實地勘察村莊自然條件環境和訪談獲取數據;N3通過搜集官方統計資料獲取數據;L1—L3、L7—L9、I6—I7都均通過實地調研勘察和訪談的方式獲取數據;S2、S4—S9通過文獻資料查閱和實地走訪獲取數據;N4—N6、L4—L6、I1—I5、I8均通過實地調查和資料查閱獲取數據。
2.3 數據處理
首先,進行定性指標量化處理。建立的評價體系中包含定性與定量指標。其中,N1—N3、L1—L3、L7—L9、I6—I7、S2、S4—S9共18個指標為定性指標。本文主要采用分級打分法對其進行定量化處理[8](表2)。其中,賦分標準能估計百分比的,按照百分比的大小,與相應等級的分值相乘得到該項指標的量化分數;不能估計百分比的,按照其與該等級的匹配度或符合度得到量化分數。
其次,進行定量指標量化處理。定量指標在評價中也需要制定分級量化的標準,同上述定性指標一樣,將N4—N6、L4—L6、I1—I5、I8、S1、S3等14個定量指標劃分為5級。為使評價體系能適用于其他傳統村落,結合研究地考慮在全省或全國更大范圍內尋找指標信息,搜集各指標數值的最大值、最小值和眾數值,根據眾數值來校正各指標的平均數,最終計算各指標的分級標準(表3)。

表2 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評價定性指標賦值

表3 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評價定量指標賦值
第三,確定指標權重。本文采用層次分析法(AHP)計算各指標的權重和一致性指標,依照具體計算步驟[33]得到32個指標權重(W)與一致性指標,結果見表4。經計算,人居環境脆弱性評價體系中系統層的一致性指標CR=0.044<0.1,通過一致性檢驗,自然生態環境系統(N)中的指標層一致性指標CR=0.018<0.1,居住空間環境系統(L)中的指標層CR=0.041<0.1,支撐設施環境系統(I)中的指標層CR=0.080<0.1,社會文化環境系統(C)中的指標層CR=0.016<0.1,均通過一致性檢驗。將各指標的指標權重與系統層的系統權重相乘,得到各指標對人居環境脆弱性評價的貢獻度,即綜合權重。

表4 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評價指標權重
3 結果及分析
3.1 上甘棠村人居環境脆弱度
本文根據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評價體系的量化分級賦分標準,利用專家打分法對上甘棠村人居環境脆弱性各項指標進行打分,采用加權平均法將獲得的分值與各指標權重進行計算,利用公式(1)得到上甘棠村的人居環境脆弱度(HSEHVI)。
(1)
式中,Si表示各評價指標因子原始數據經過量化處理后所得數值;Wi為各因子相對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的權重系數。結果數值越大,人居環境脆弱度越高;數值越小,脆弱度就越低。數值大小保持在0—100之間。
本文根據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評價體系各分值標準,將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度與量化指標分值相對應,分為5級:0—19分為不脆弱,20—39分為微脆弱,40—59分為中脆弱,60—79分為強脆弱,80—100分為極脆弱。由此,得到江永縣上甘棠村各指標的得分和人居環境脆弱度,評價結果見表5。

表5 上甘棠村人居環境脆弱性評價結果
從表5可見,上甘棠村人居環境脆弱度的得分為34.533,為微脆弱,各系統之間得分差異總體差距不大,較為協調均勻。說明盡管上甘棠村地處湘南腹地,與外界交流閉塞,但村落的保護也存在著許多不足。上甘棠村人居環境部分系統雖然呈現一定程度的脆弱性,但是自然、社會、經濟、居住等綜合條件良好,整體人居環境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和諧,總體上較理想。
3.2 自然生態環境脆弱度最低
氣溫適宜度、降水適宜量、合理風速等要素對傳統建筑和村落部分設施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自然條件惡化,人居環境的脆弱性會相應增高;自然環境條件越理想,人居環境的脆弱性會越低。根據評價結果(圖2),自然生態環境(N)對上甘棠村脆弱度貢獻度最低,脆弱度得分僅3.656,說明上甘棠村人居環境的自然生態系統較為穩定。上甘棠村自然條件獨特,村落的開發也并未建設完全;同時,自然生態環境有其獨特的穩定性,不會輕易受到外界干擾影響,故上甘棠村自然生態人居環境脆弱度顯示為微脆弱。其中,氣候適宜度(N3)是對上甘棠村人居環境影響較高的因子(圖3),脆弱度得分為2.312,這是由于氣候對上甘棠村人居環境的影響較為綜合造成的。
3.3 支撐設施環境脆弱度最高
根據各子系統脆弱度統計結果(圖2),傳統村落人居環境四大系統中,支撐設施環境(I)對上甘棠村脆弱性的貢獻度最高,占38.5%,得分為11.958。說明在上甘棠村人居環境系統中,支撐設施環境較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不夠;同時,休閑娛樂設施的缺少也進一步限制上甘棠村人居環境的發展。由圖3可知,自來水覆蓋率(I4)、公共服務設施完整度(I7)、未建設設施率(I8)是支撐設施環境中脆弱度得分最高的3個因子,分別為3.200、5.520、2.025,說明上甘棠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較為缺乏。

圖2 上甘棠村人居環境各子系統脆弱度 圖3 上甘棠村人居環境脆弱性指標分值分布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研究在于明確系統脆弱性的脆弱度及其動力機制,并提出切實有效的調控對策或應對措施,以增加應對各種不利影響的能力,降低脆弱性,實現傳統村落人居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由上述評價結果可以看出,構成上甘棠村人居環境脆弱性體系的因子較多,表現方式也不相同。上甘棠村的整體開發力度不大,雖然某些指標的脆弱度較高,但是村落的基本平衡并未打破,呈現出總體的和諧;自然環境有其自身的穩定性,同時上甘棠村的建設活動并沒破壞整體生態結構,故脆弱性較低。4個子系統并不是單一作用于整個人居環境脆弱性系統,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人居環境系統受到內外驅動因子的影響而呈現出一定的脆弱性,自然條件、農戶行為等內在驅動因子的變化直接影響傳統村落人居環境子系統脆弱性變化,政府政策、市場變化等外在驅動因子間接影響傳統村落人居環境的脆弱性;同時,人居環境系統的發展又將反饋于各驅動因子(圖4)。

圖4 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性形成機理
4.2 建議
本文基于對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脆弱度評價和脆弱性形成動力機制的分析,從自然、政策經濟、社會等多角度提出以下脆弱性應對措施建議:①遵循自然生態的內在機制,營造和諧宜居環境。首先,保護當地現有的植被,鼓勵人工造林;其次,對謝沐河加強管治,嚴禁向水體里排放廢水和亂扔垃圾,保障人們日常生活環境的整潔。②提高建筑及人居設施的利用率,完善設施建設弱項。依照村落發展重點,對現有設施的位置和未建設的設施種類和名稱進行統計;通過政府的力量,整合現有設施情況,進行專項規劃,彌補建設漏缺,對被破壞或存在故障的設施進行修復。③明確村落發展基本目標,促進人口轉負為正。上甘棠村“空心化”問題較突出,缺少建設動力,村落建設停滯不前,影響了人居環境的發展。因此,當地政府應合理增加就業機會,提升就業質量,全方位提升上甘棠村的居住質量,如修建文化館、休閑娛樂廣場等,以豐富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④創新村落旅游開發模式,確定開發建設底線。利用“政府+企業”聯動的方式,保證更多的資金與政策投入;建立監管與協調機構,在政策、資金條件充足的情況下,加大旅游開發力度,打響知名度。同時,確定上甘棠村的旅游開發限度,保證旅游開發與人居環境的融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