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病毒,好病毒
王亞宏
“來自熱帶雨林的危險病毒,可在24小時內乘飛機抵達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航空線路連接了全世界的所有城市,構成網絡。病毒進入網絡后,一日之間就能來到飛機抵達的任何城市:巴黎、東京、紐約、洛杉磯。”在紀實作品《血疫:埃博拉的故事》里,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頓描述了一個讓人心驚膽戰的事實。
在2020年過去的大半年時間里,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讓人們對病毒的認識又深了一層。病毒似乎一直在給人類社會帶來威脅,甚至奪去了無數人的生命。
在人類歷史上,我們一直對病毒進行反擊。對抗病毒的戰爭不見硝煙,但同樣艱苦卓絕,且伴隨著巨大的犧牲。
在這場戰爭中,人類一直處于被動防守的一方。但是,如果形勢逆轉,人類獲得全勝,將病毒都消滅掉,那么世界是否會更美好呢?
病毒都有害嗎
當病毒這個詞一出現,先入為主就會覺得應是一個處之而后快的對象。但其實雖然病毒對人類健康的威脅客觀存在,但對其評價的標準卻是完全以人類為中心進行的。
現在全世界到底有多少病毒存在,我們還不清楚。實際上,人們對病毒的認識還只是冰山一角,盡管目前已經有數千種病毒被正式分類,但可能還有數百萬病毒未被分類。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病毒生態學家瑪麗蓮·羅斯辛克認為,人類目前只發現了一小部分病毒。由于對病毒的認識有限,科學家也不清楚有多少病毒對人類有害。
其實在病毒眼中,人類只是諸多宿主中的普通一員。如金黃色葡萄球菌噬菌體、棉鈴蟲核型多角體病毒、斜紋夜蛾核型多角體病毒、菜青蟲顆粒體病毒等病菌,其宿主是雜草,以及害蟲、害鳥、害獸等。尤其是對一些害蟲來說,相關病毒對其殺傷性極強,但卻人畜無害。因此,從人的價值來考慮,也存在“好病毒”這種生物。
更好的病毒則是對人類健康有益的病毒,這打破了一般的刻板印象。比如GB病毒C型是一種常見的人類血液病毒,是西尼羅河病毒和登革熱的非致病性遠親,它與HIV陽性人群的艾滋病延遲進展有關。科學家們發現,GB病毒C型似乎可以降低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死亡率。
也有名聲不大好的病毒會成為治療某些疾病最有希望的藥物之一。噬菌體療法在上世紀就有大量的研究,使用病毒進行靶向細菌感染。病毒靶向治療應用前景廣闊,因為這種療法可以在治療中消滅特定的細菌種類,其作用類似于微型制導導彈,即進入并炸毀不想要的細胞,而不是像抗生素那樣不加選擇地消滅整個細菌種群。比如溶瘤病毒,現在就越來越多地被作為一種毒性更小、更有效的癌癥治療方法。
生態平衡的重要一環
如果所有的病毒都消失了,人們丟掉的不僅是發展下一代療法的希望,可能整個世界都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大概率是朝壞的方向變化。
美國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的流行病學家托尼·戈德堡認為,如果所有的病毒都突然消失了,世界的美好將持續約一天半,然后人類都會死亡,因為病毒在這個世界上的重要性遠超過讓人類感染某些疾病之類壞事。絕大多數病毒并不會讓人類染病乃至致命,而且許多病毒在支撐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還有一些病毒可以維持生物有機體的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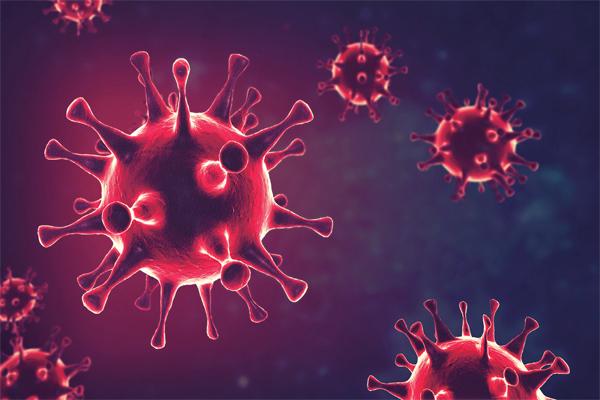
如果沒有病毒,目前熟悉的地球將不復存在。在地球的生態平衡中,病毒占據著不可或缺的一環。缺少這一環,生態系統可能會迅速崩塌,身處其間的人類也會無處安身。
比如地球上70%的面積由海洋構成,而在海洋中90%以上的生物都是微生物。這些微生物產生了地球上大約一半的氧氣,這一過程是由病毒促成的。這些病毒殺死20%的海洋微生物和50%的海洋細菌。通過淘汰微生物,病毒確保產氧浮游生物有足夠的營養進行高速率的光合作用,最終產生足夠的氧氣,以供給地球上的大部分生命。
因此,沒有病毒,人們會很快窒息——而這只是缺少病毒的災難性后果之一。
自然的節拍器
托馬斯·馬爾薩斯很早就在其《人口學原則》中指出,疾病和戰爭一樣,是自然控制人口數量的方式。
在過去一個世紀中,人類已經蓄積出足夠的力量去征服海洋、高山和星空,但面對壞病毒的襲擊依然失敗連連。
雖然在生存的壓力下,人們一直在極力澆灌醫學的科技樹,但卻始終沒有擊潰病毒。在過去一個世紀中,人類已經蓄積出足夠的力量去征服海洋、高山和星空,但面對壞病毒的襲擊依然失敗連連。比如1918年大流感導致至少5000萬人死亡,在整個20世紀,天花估計奪去了2億人的生命。
病毒作為自然節拍器,并不只在人身上發揮作用。研究昆蟲的研究人員發現,病毒對昆蟲的種群控制至關重要。如果某一物種數量過剩,一種病毒就會出現并消滅它們,這是生態系統中非常自然的一部分。這個過程在其他物種中也常見,當種群數量非常豐富時,病毒傾向于快速復制并削弱種群,為其他物種創造生存空間。
如果病毒突然消失,有競爭力的物種可能會在損害其他物種的情況下繁榮發展。而生態平衡容不下“勝者通吃”,病毒“節拍器”的功能就會顯現。
沒有病毒的世界會不可阻擋地滑向坍塌,不過,至少以目前的技術條件看,即使人類想要消滅地球上的每一種病毒,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