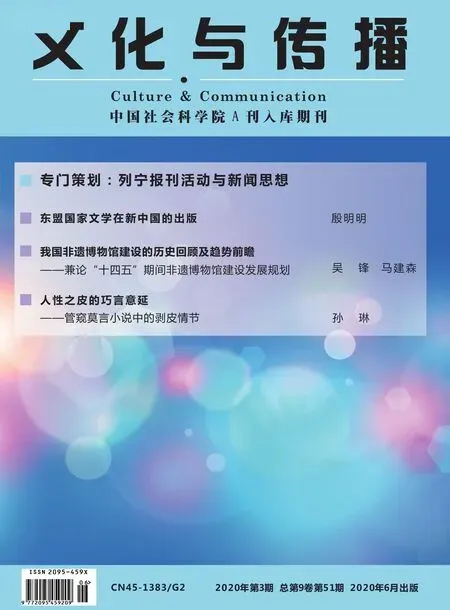東盟國家文學(xué)在新中國的出版
殷明明
東盟諸國與中國地理接近、文化關(guān)聯(lián)性強(qiáng),且有不少華文作家,但對于東盟文學(xué),中國的了解和譯介并不算多。20世紀(jì)初至新中國成立,東盟諸國文學(xué)在中國翻譯出版的作品僅4種,其中3種是民間文學(xué):《馬來情歌集》(上海遠(yuǎn)東圖書公司,1928)、《南亞戀歌》(上海華通書局,1930)、《南亞童話集》(上海教育研究社,1944);文人創(chuàng)作1種:朗新的《愛的喜劇》(時(shí)標(biāo)為暹羅朗新著,陳毓泰譯,馬來亞書店,1931)。
所以東盟國家文學(xué)在中國的翻譯出版,基本上是從新中國成立后才發(fā)展起來的。本文將依據(jù)《全國總書目》等資料,對新中國成立以來至2010年東盟文學(xué)在中國的出版情況進(jìn)行梳理和論析。
一、東盟文學(xué)在新中國出版概況
1949年至2010年,東盟10國中,文萊無單行本在中國出版,另外9國有486種作品在華翻譯出版。按國別分類情況見下表:

新加坡 越南 泰國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緬甸 柬埔寨 老撾 新、馬合集 印、馬合集 合計(jì)178 93 58 55 43 31 16 6 4 1 1 486
從數(shù)量上看,分布很不均衡,柬埔寨和老撾的數(shù)量很少,越南和新加坡的文學(xué)則占到了55%。新加坡文學(xué)是東盟文學(xué)在華出版起步最晚的國家,1987年才有第一批作品譯入,但卻是出版量最大的國家,有178種,占總量的36.6%。尤其是1980年之后,東盟文學(xué)在華翻譯出版有358種,新加坡作品接近總量的二分之一。越南文學(xué)在華的出版開始于1954年,有93種,接近總量的五分之一,遠(yuǎn)不及新加坡文學(xué)。但在1980年之前,越南文學(xué)在新中國的譯介有著絕對優(yōu)勢,這一時(shí)期東盟文學(xué)在華出版有128種,越南文學(xué)有86種,占到這時(shí)期總量的66%。但1980年之后,越南文學(xué)在華出版急劇衰退,20世紀(jì)80年代1種、90年代5種。2000至2010年間未見越南文學(xué)作品在中國出版。
從體裁上看,小說是數(shù)量最大的類型,散文數(shù)量也較多。此外,民間文學(xué)有約23種、戲劇13種、詩歌37種。民間文學(xué)的數(shù)量相對于總量來說不大,但對于老撾、柬埔寨和緬甸文學(xué)的在華出版來說,其占比很高。老撾的4種中,2種是民間文學(xué);柬埔寨的6種中,3種是民間文學(xué);緬甸的16種中,4種是民間文學(xué)。
從題材上看,突出的是反殖民題材的作品,有83種,體裁涵蓋小說、戲劇、詩歌、報(bào)告文學(xué)、回憶錄等多種類型。以反法、反美題材的作品為多,尤其是在越南文學(xué)中十分多見;老撾有1部、柬埔寨有3部反美作品,雖然量不大,但由于這兩國譯介量小,所以占比高。此外還有印度尼西亞阿布都爾·慕依斯《蘇拉巴蒂》(少年兒童出版社,1958;作家出版社,1962)是抗擊荷蘭殖民者題材的小說,緬甸吳登佩敏的《旭日冉冉》(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2)是抗擊英國殖民者題材的小說。
從年代上看:20世紀(jì)50年代東盟文學(xué)在華出版的共有55種, 60年代63種、70年代10種、80年代78種、90年代191種、2000至2010年89種。年度出版量最大的是1993年,有44種;不過這一年的數(shù)量雖然高,但來源國僅有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且分布不均,新加坡37種,緬甸僅1種。最先在新中國翻譯出版的是菲律賓的詩文合集《最后書懷》(華南人民出版社,1951),包含詩6首和小說2篇。該書的書名取自菲律賓民族獨(dú)立運(yùn)動的先驅(qū)何塞·黎薩爾臨刑前夕寫的詩《最后書懷》,當(dāng)時(shí)將何塞·黎薩爾譯為扶西·黎剎。他的名聲與詩文早在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便傳到了中國,最早傳入的是他臨刑前夕寫的詩《最后書懷》。該詩1897年1月便由其好友馬里亞諾·彭西發(fā)表于香港;1904年,在清末革命者戢元丞所編的《教育必用學(xué)生歌》的附錄中有該詩的漢譯,名為《菲律賓愛國者黎沙兒絕命詞》,譯者不詳。此后,梁啟超、林林、王世昭、李霽野等多人翻譯過該詩,目前“共有17種中文譯本,其中中國的譯者(包括香港的王世昭)共有6位。”[1]
二、東盟主要文學(xué)國家在新中國出版情況及特征
從東盟文學(xué)在華翻譯出版的概況可以看到,其出版非常不均衡。柬埔寨和老撾等國的作品譯介很少,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國雖然有一定的出版量,但它們的出版量放在這幾十年中依然薄弱。越南與新加坡文學(xué)在華翻譯出版的作品不僅數(shù)量大,而且有很強(qiáng)的階段性和代表性,有些作品,如越南的《南方來信》《象他那樣生活》在中國的出版量極大、其影響遠(yuǎn)超文學(xué)本身。
(一)薄弱的菲律賓等國文學(xué)譯介
菲律賓作品的譯介有31種,其中約一半是菲律賓華人的創(chuàng)作,大多屬于鷺江出版社的“東南亞華文文學(xué)大系”和中國華僑出版社的“海外華僑華人文庫”。其他作家大多只有一部作品出版,只有何塞·黎薩爾要多些,有3部小說。
馬來西亞文學(xué)方面,按照《外國文學(xué)著作目錄和提要1949—1979》的收錄,第一部譯入的作品是勒斯雷·理查遜《為了我們的母親——馬來亞》(新文藝出版社,1957)[2]。該劇本譯自1954年倫敦Lawrence & Wishart出版社的戲劇集《關(guān)于馬來西亞的戲劇兩種:土地上的陌生人和為了我們的母親馬來亞》,作者是兩個(gè)英國的反殖民主義者。所以這個(gè)劇本是關(guān)于馬來西亞,但不是馬來西亞的作品。
第一部真正來自馬來西亞的作品是阿·薩瑪?shù)隆べ惲x德的長篇小說《莎麗娜》(北岳文藝出版社,1985)。該書原版于1961年,寫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給馬來西亞人民造成的傷害,被視為馬來西亞第一部有影響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賽義德1979年獲得東盟文學(xué)獎,是第一批獲該獎的作家。其他出版的馬來西亞作品主要是華文文學(xué)。
印度尼西亞作品的譯介從1955年開始,直到1957年的3種作品都是民間文學(xué)。第一部作品是阿布都爾·慕依斯的《錯誤的教育》(作家出版社,1958)。這部小說寫的是荷蘭統(tǒng)治下殖民教育給當(dāng)?shù)厝嗣駧淼男撵`毒害和民族矛盾。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9年再版了該書,花山文藝出版社1984年出版了白云譯的新版本。作品譯入多的是普拉姆迪亞·阿南達(dá)·杜爾,有6種。
印尼在中國出版的作品中亦有不少華人作品,約有15種。其中以黃東平數(shù)量為多,有5種。黃東平對印尼華人的生存狀態(tài)進(jìn)行了深刻全面的描述,著有《僑歌》三部曲:《七洲洋外》《赤道線上》和《烈日底下》。其中前兩部分別在1986年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年由鷺江出版社出版。
泰國第一部譯入的單行本是女作家克開·達(dá)云的中篇小說《黑暗的生活》(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8)。這篇小說原載于她1952年出版的同名小說集,寫的是一對姐妹的悲慘遭遇。20世紀(jì)80年代泰國開始譯入的作品呈現(xiàn)了新的主題。如吉莎娜·阿索信的作品,她僅長篇小說就寫了二百多部。她的《夕陽西下》(外國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1982、1988)、《曼谷死生緣》(中國工人出版社,1991)描寫的已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時(shí)期的泰國,有明顯的通俗文學(xué)色彩。
(二)政治性突出的越南文學(xué)譯介
越南文學(xué)在中國出版最突出的特征是政治色彩濃厚。其題材主要是抗法和抗美。越南第一部在中國出版的作品是何明遵以抗擊法國殖民者為題材的報(bào)告文學(xué)《在血火的日子里》(新文藝出版社,1954)。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二部在中國出版的東盟作品。從原作時(shí)間上看,大部分是當(dāng)代作品,除了民間故事,只有一部阮攸(1765—1820)的《金云翹傳》(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9)是古典作品。
這種內(nèi)容上的時(shí)事性和政治性也影響到了體裁。報(bào)告文學(xué)是越南文學(xué)在華出版的重要類型,至少有24種,如果加上書信集、回憶錄,有約31種,占到了越南文學(xué)譯介總量的約三分之一。詩集19個(gè),短篇小說集約14個(gè)、中篇小說8個(gè)、劇本5個(gè),長詩1個(gè),民間故事6個(gè)。長篇小說數(shù)量少,主要有阮功歡《黎明之前》(上海文藝出版社,1957)、阮輝想《阿陸哥》(作家出版社,1963)、阮庭詩《決堤》(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1965)、吳必素(1892—1954)《熄燈》(1938年原版,文津出版社,1996)。這種體裁格局符合當(dāng)時(shí)越南的社會形勢,這類短小的文學(xué)形式能更為及時(shí)反映斗爭情況,也方便讀者閱讀。
作家方面也有明顯的政治性。從數(shù)量上看,有作品在中國出版的以阮庭詩4種最多,胡志明、阮輝想、素友等皆為3種。這些作家都同時(shí)是越南政治人物。阮庭詩1941年參加抗法斗爭,曾任文化救國會總書記,1958年任越南作家協(xié)會主席。胡志明是越南黨和國家的領(lǐng)袖,為中國所熟悉。阮輝想是越南文化救國會創(chuàng)建人之一,1954年在越南作家協(xié)會任執(zhí)行委員。素友1947年起在越北負(fù)責(zé)文化工作,1948年越南文藝協(xié)會成立,任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1955年任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后曾任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等職。
越南作品在中國的傳播帶有極強(qiáng)的政治意味,一些作品得到高規(guī)格的對待。典型如《南方來信》。該書1963年在越南出版,1964年越南外文出版社將其譯為中文于1月出版。同年4月27日,北京作家舉行了座談會討論該書,時(shí)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席的茅盾主持會議、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邵荃麟、曾訪問過越南的作家張光年、袁鷹等人,越南駐華使館參贊黃北參加了會議。
1964年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的第一集(1964年7月四川人民出版租型出版了包含22封信的選集)、7月出版了第二集;1965年5月,1965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還出版了《南方來信選(農(nóng)村版)》。它被改編為多個(gè)劇種的戲劇、木版畫、連環(huán)畫,如1965年9月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木刻組畫《南方來信》。多位中國和越南高層領(lǐng)導(dǎo)、國際友人觀看了該書的改編戲劇:1964年10月5日,越南總理阮文同、老撾副首相蘇發(fā)努馮親王在李富春陪同下觀看了話劇版;1964年10月21日,周恩來、朱德、董必武、彭真等人觀看了話劇版;1965年4月20日,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帶領(lǐng)武元甲等人與康生、羅瑞卿等人共同觀看了話劇版;1965年4月30日,來參加“五一”活動的各國工會代表觀看了話劇版;1965年7月14日,越南副主席黃文歡與彭真、郭沫若、謝富治等人觀看了京劇版。
潘氏娟口述、陳庭云整理的報(bào)告文學(xué)《象他那樣生活》(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65)同樣影響很大,這本書印了超過350萬冊,數(shù)量驚人。此書講述的是阮文追烈士的斗爭事跡,在當(dāng)時(shí)的越南非常受重視,胡志明為該書題詞,越南勞動青年團(tuán)號召青年學(xué)習(xí)該書。1965年8月1日的《人民日報(bào)》介紹了該書,《工人日報(bào)》《北京日報(bào)》《中國青年報(bào)》等全載或選載了該書,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進(jìn)行了播送;文藝團(tuán)體將其改編為舞蹈、戲劇、曲藝等多種形式。
越南文學(xué)在中國的出版集中于20世紀(jì)50-60年代,其中50年代34種、60年代50種;20世紀(jì)80年代起開始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新加坡文學(xué)。
(三)都市趣味與新加坡文學(xué)譯介的興起
中國與新加坡1980年互設(shè)商務(wù)代表,1990年建交。1987年新加坡文學(xué)有第一批作品在中國出版,是作品在華出版的東盟國家中最晚的,數(shù)量卻最多,且最為連續(xù);2000年至2010年,東盟諸國共有87種,新加坡的就有49種。東盟各國作家在華出版種數(shù)居前的也全為新加坡作家:尤今51種;詹姆斯·李16種(兒童文學(xué));黃孟文(8種,其中獨(dú)著6種)。
新加坡文學(xué)總體上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都市的閱讀趣味,表現(xiàn)的多是閑情逸致,風(fēng)格多為優(yōu)雅空靈,描寫的多是現(xiàn)代都市人在利益、感情等方面的苦惱沖突。
這種傾向從新加坡文學(xué)初入中國就表現(xiàn)了出來。最早譯入的新加坡文學(xué)有三本,賀蘭寧的詩集《石帝》(鷺江出版社,1987)和姚紫的小說集《咖啡的誘惑》(鷺江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都出版了該小說集,且所收篇目相同)。前者寫的多是愛情、鄉(xiāng)愁,構(gòu)建的是“情的世界、景的天地”;姚紫寫的也多是女性、以愛情為題材,當(dāng)時(shí)就有人批評姚紫“在愛情上有過份的描寫和渲染”,他的《窩狼拉里》甚至被視為“黃色文藝”,楊越為其寫的長序《追求和追求中的懊惱——姚紫小說簡論》還針對這一批評進(jìn)行了辯駁,認(rèn)為姚紫“對愛情的描寫是十分嚴(yán)肅的,掌握也有分寸”。此后很多小說也是都市情感類,如余麗莎《情陷北京城》《陷入紅塵》(花城出版社,1999)、林秋霞《非常難女》《性感都市》《玩九朝五》。重大歷史題材的小說已經(jīng)不多,新加坡建國后的小說創(chuàng)作質(zhì)量“沒有超過建國前的水平”,流軍是該時(shí)期為數(shù)不多“大家公認(rèn)的最優(yōu)秀的小說家”。[3]他的《海螺》出版后在新加坡文壇引起了爭論,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4年還出版了一本《<海螺>評論集》。
散文方面,在華出版的新加坡文學(xué)也是以體現(xiàn)有品質(zhì)的現(xiàn)代生活作品為主。如尤今就以善寫游記而著稱,她本人去過90多個(gè)國家,出版的游記有30多本。還有美食類的小品文,如蔡瀾《只吃半飽》《絕不擇食》(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旅行、美食,這都是解決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才能有的追求,這類作品的流行,既體現(xiàn)出新加坡的發(fā)展水平,也折射出當(dāng)時(shí)中國人對于悠閑自在的生活的向往。
雖然東盟國家中,新加坡文學(xué)翻譯出版的量最大,但就其社會影響而言,已經(jīng)不再有越南的《南方來信》那樣的作品。
三、東盟文學(xué)在新中國出版重心之變遷及原因
東盟文學(xué)在中國的出版總體走勢是:在20世紀(jì)80年代之前,從題材看反侵略類的作品占主體,從國別看越南文學(xué)占絕對優(yōu)勢。20世紀(jì)80年代之后,反侵略類的作品急劇減少,越南文學(xué)在華的出版銳減,民間文學(xué)還有一定量的出版,華文文學(xué)大量出版,新加坡成為東盟文學(xué)在華出版的主力。
(一)時(shí)局變化與東盟文學(xué)在華出版的變遷
這一變化的主要外部驅(qū)動力是時(shí)局的變化。“十七年”時(shí)期,中國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主要成員,和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處在全方位對立之中。對于東南亞地區(qū)的反殖民反侵略運(yùn)動非常關(guān)注,此類文學(xué)作品也就自然成為譯介重點(diǎn)。這種以服務(wù)于國家政治斗爭的出版導(dǎo)向在當(dāng)時(shí)的中國是一種常態(tài),當(dāng)時(shí)的歐美俄蘇文學(xué)也有這樣的狀況。不過歐美俄蘇經(jīng)典作品豐富,所以當(dāng)政治化的出版浪潮消退后,歐美俄蘇文學(xué)依然是經(jīng)典作品不斷再版、新作品能及時(shí)引進(jìn)。而東盟各國的古典文學(xué)往往不發(fā)達(dá),政治關(guān)注褪去后,其出版量便會迅速消減、以至于出現(xiàn)斷層。所以20世紀(jì)90年代之后柬埔寨文學(xué)在華便無出版,緬甸、老撾文學(xué)僅有幾部民間故事;印尼文學(xué)則基本上只有十余種華文文學(xué)。
這種消長最為典型是越南文學(xué)。在當(dāng)時(shí),越南是中國重要的外交對象,有著同志加兄弟般的情誼;對越南時(shí)局,中國有著長期和直接的介入。1950年,中國不惜影響與法國的關(guān)系,支持以胡志明為首的越南抗法斗爭;1950年1月18日,中國率先承認(rèn)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抗法戰(zhàn)爭勝利后,1955年在美國支持下吳庭艷在南部成立了越南共和國政府,越南又陷入了南北對立。1960年12月,中國宣布承認(rèn)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支持越南北方對南方的解放。
所以20世紀(jì)50-60年代,中國高度關(guān)注越南時(shí)局的變化,《人民日報(bào)》頻繁刊登諸如越南軍民擊落了幾架美軍飛機(jī)這類新聞。盡管越南古代文化和文學(xué)受中國影響很大,但越南古典文學(xué)并沒有因此更多進(jìn)入中國;在中國大量出版的是越南抗法、抗美題材的作品。1964年8月“北部灣事件”發(fā)生、越戰(zhàn)升級,中國在軍事、政治等各方面做出了迅速反應(yīng),8月8日北京近百萬人民上街游行支持北越;1965年中國正式宣布“援越抗美”,該年就出版了至少24種越南作品,是品種數(shù)最多的1年。
這一年中國作家也創(chuàng)作了大量相關(guān)作品支援越南,如詩集《獻(xiàn)給你,戰(zhàn)斗的越南》(百花文藝出版社,1965),刊載了郭沫若、臧克家、袁水拍、袁鷹等人的詩歌;《越南,我們和你在一起》(作家出版社,1965),刊載了郭沫若、賀敬之等人的詩歌;《我們和越南人民的戰(zhàn)斗友誼》(作家出版社,1965),中越友好人民公社集體寫作;《越南人民一定勝利》(上海文化出版社,1965),包括對口詞、彈詞、單口詞、相聲、山東快書、說唱、唱詞等形式。
20世紀(jì)60年代中期,中國對外關(guān)系發(fā)生重大變化,中美逐漸和解、越南則不斷向蘇聯(lián)靠攏,20世紀(jì)70年代中期以后中越關(guān)系進(jìn)一步惡化,直至1979年發(fā)生戰(zhàn)爭。在文學(xué)譯介上,1965年越南文學(xué)在華的出版達(dá)到最高峰后,猝然下降,1966年尚有4種,1967至1971年間則是空白。有學(xué)者指出,“北部灣事件”后蘇聯(lián)政府也加大了越南的援助,特別是提供了很多當(dāng)時(shí)中國沒有或很少的先進(jìn)軍事援助,這就導(dǎo)致“越南在借助外力提高自主安全能力時(shí)日益明顯地倒向蘇聯(lián)一邊,中越之間在政治上的合作趨向冷淡”[4],所以聲勢浩大聲援的1965年,卻也是中越內(nèi)部裂痕擴(kuò)大的時(shí)候,“從 1965年始,中越關(guān)系漸漸蒙上了一層陰影。雙方之間的不信任感增強(qiáng)”。[5]
20世紀(jì)70年代初,情況又發(fā)生了變化,中國加大了對越援助,“1971—1973年是中國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6]。此時(shí)越戰(zhàn)到了最后的階段,也是中美關(guān)系有了實(shí)質(zhì)性突破的時(shí)期。越南對中美關(guān)系改善是十分反感的,中國當(dāng)時(shí)加大了援助,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穩(wěn)住與越南的關(guān)系。與此對應(yīng)的是,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在1972年和1973年分別出版了一部越南的短篇小說集。
1973年巴黎協(xié)定簽訂,越戰(zhàn)結(jié)束,北越進(jìn)一步向蘇聯(lián)傾斜。1975年越南統(tǒng)一后,越南開始反對中國,從那時(shí)起到20世紀(jì)90年代初兩國正常化,越南文學(xué)在華出版的只有團(tuán)文遂《獄中生活》(群眾出版社,1982)。這本書是內(nèi)部發(fā)行,而且該書是反越南當(dāng)局的報(bào)告文學(xué)。團(tuán)文遂1975—1978年被河內(nèi)當(dāng)局關(guān)押,獲釋后,流亡法國。本書是他在西歐各國舉行記者招待會或報(bào)告會上的一些發(fā)言。揭露了河內(nèi)當(dāng)局對越方各界愛國人士,包括原臨時(shí)革命政府和民族解放陣線成員的殘酷迫害,也介紹了有關(guān)越南的“再教育營”和監(jiān)獄的情況。[7]
20世紀(jì)90年代開始連續(xù)出版的兩本作品都是胡志明的,《<獄中日記>詩抄》(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0)和《胡志明獄中詩注釋》(廣西教育出版社,1992)。即使在中越關(guān)系惡化的20世紀(jì)80年代,胡志明依然還是受到中國的肯定,如1980年《胡志明同志關(guān)于中國的友好言論》(東南亞研究資料、1980年第2期)、《回憶胡志明主席的戰(zhàn)斗生活片斷》(世界知識,1980年第10期),都還是把胡志明視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至于中越關(guān)系的惡化,是因?yàn)樵焦脖撑蚜撕久鞯穆肪€,“在投靠蘇霸的黎筍集團(tuán)瘋狂反華仇華的今天,重溫胡志明同志的生前有關(guān)言論,更有助于我們看清黎筍集團(tuán)怎樣背叛胡志明同志的教導(dǎo)。”[8]胡志明的詩集《獄中日記》是其在中國被國民黨關(guān)押時(shí)所作,與中國很有淵源。1990是胡志明誕辰100周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為此再版了《<獄中日記>詩抄》。
雖然20世紀(jì)90年代越南文學(xué)在中國的出版恢復(fù),但除了《絕對機(jī)密:越戰(zhàn)第一大間諜案內(nèi)幕》(軍事誼文出版社,1999)外,已沒有越南新的作品,像吳必素的《熄燈》(文津出版社,1996)是1939年的作品。直至2010年,對于越南文學(xué)20世紀(jì)8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國基本上沒有單行本;到了2012年才有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越南當(dāng)代短篇小說選》,其中部分作品也與戰(zhàn)爭相關(guān),但終于有一些作品反映的是越南戰(zhàn)后的社會。
當(dāng)越南式的政治化作品淡出后,體現(xiàn)現(xiàn)代都市趣味的作品大量出現(xiàn),典型如新加坡文學(xué),馬來西亞戴小華、李憶莙,泰國吉莎娜·阿索信等人的作品也都是以都市生活、感情糾葛為題材;還有一些兒童文學(xué)作品也譯介進(jìn)來,如新加坡詹姆斯·李的多部作品。此外,越南、泰國、老撾、緬甸等國的民間故事也不時(shí)有翻譯出版。
(二)新時(shí)期華文文學(xué)譯介的興起
新時(shí)期以來東盟華文文學(xué)在中國出版的發(fā)展很快。東盟文學(xué)出版的另一個(gè)特點(diǎn)正是華文文學(xué)非常受重視,出版量大、并有多個(gè)系列叢書。專門出版東盟華文文學(xué)的叢書有海峽文藝出版社的“東南亞華文文學(xué)叢書”、鷺江出版社“東南亞華文文學(xué)大系”。其中“東南亞華文文學(xué)大系”規(guī)模較大,分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五卷,每卷10種,從1995年至2000年出版了50種。在海外華人叢書中也有大量東南亞華人文學(xué),如鷺江出版社“海外華文文學(xué)叢書”、中國華僑出版公司“海外華僑華人文庫”、遼寧教育出版社“華人書林”、百花文藝出版社“海外華文散文叢書”等。像在菲律賓的31種中,有約一半是菲律賓華人的創(chuàng)作,大多屬于鷺江出版社推出的“東南亞華文文學(xué)大系”和中國華僑出版社的“海外華僑華人文庫”。
全球華人同根同源,重視華人文學(xué)非常必要。但譯介的文化使命之一便是拓寬視野,東盟諸國雖然或多或少受到中國文化影響、也有不少華裔,但它們也還有除華文文學(xué)之外的文學(xué),需要通過譯介以促進(jìn)了解。如新加坡文學(xué)就是由華文、英文、馬來文和泰米爾4種文字的寫作構(gòu)成,截止2010年在華出版的新加坡作品絕大多數(shù)是華文文學(xué),其他語種的重要作品極少漢譯出版。如季羨林先生主編《東方文學(xué)辭典》收錄的新加坡35名作家中,僅3名非華語作家:艾溫·譚布、馬蘇里、哈倫·阿米努拉錫,他們3人都沒有單行本引入。艾溫·譚布(Edwin Thumboo),現(xiàn)在常譯為唐愛文,新加坡最重要的英文詩人、第一屆東盟文學(xué)獎得主,創(chuàng)作了被譽(yù)為“新加坡史詩”的《魚尾獅旁的尤利西斯》、該詩被雕刻于新加坡的標(biāo)志魚尾獅身像旁邊。馬蘇里和哈倫·阿米努拉錫則是重要的馬來語作家,前者獲得了1980年第二屆東南亞文學(xué)獎。至于泰米爾語作家,不僅沒有作品出版,連《東方文學(xué)辭典》中也沒有收錄。
結(jié) 語
東盟文學(xué)譯介薄弱的現(xiàn)狀,其客觀原因是東盟文學(xué)的發(fā)展程度確實(shí)不如歐美俄蘇,在亞洲也比不上印度、日本、韓國等,它的確缺少世界級的作家作品;非洲文學(xué)雖然在華翻譯出版的總量還不如東盟文學(xué),但由于阿契卡、馬哈福茲、索因卡、庫切、戈迪默等大家的涌現(xiàn),其影響還是要大于東盟諸國。
從主觀上來說,東盟國家在20世紀(jì)80年代之前雖然也有一定量的出版,有的作品出版量還特別巨大,但那主要是受到政治的推動,當(dāng)這種推動力減弱和轉(zhuǎn)向之后,其出版量便急劇下降,典型如越南,甚至到了接近消亡的程度。中國自新時(shí)期以來,文學(xué)視域主要聚焦于歐美,其他地區(qū)并不受關(guān)注。當(dāng)年中國文壇對于拉美文學(xué)的熱情,也還是因?yàn)轳R爾克斯、博爾赫斯等人在西方獲得了聲望,才被中國所注意;在中國有影響的非洲作家,大多也是如此。中國似乎難以越過西方視線,直接去了解他國文學(xué)。
這不免是一種缺失。錢理群曾說,當(dāng)他提出“20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的概念后,其導(dǎo)師王瑤和他進(jìn)行了一次嚴(yán)肅的談話,王瑤先生對他說:“你們講 20世紀(jì)為什么不講殖民帝國的瓦解、第三世界的興起,不講(或少講、只從消極方面講)馬克思主義、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俄國與俄國文學(xué)的影響?”[9]王先生這番話固然指的是中國文學(xué)史的書寫,但也可以引申到文學(xué)譯介上。這種偏重歐美而忽視東方、關(guān)注發(fā)達(dá)國家而無視第三世界的態(tài)勢在21世紀(jì)甚至是愈加嚴(yán)重了。這不利于我們了解世界文學(xué)的整體面貌,也不利于“一帶一路”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