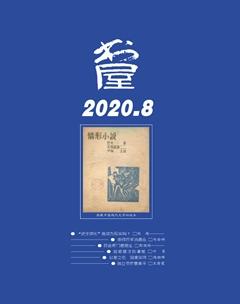詩讖與文讖
甘建華
說起這事兒真有點玄乎。之前,我從不知道李成錄何許人也,更沒有讀過他的什么文章。偶然在網上見有紀念他的一篇小文,稱其生前曾任青海省海西州茫崖行委主任、冷湖工委書記,在多家報刊發表過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等。茫崖、冷湖兩地乃我舊時工作、生活的地方,暗中思忖,是否為其在《柴達木文事》一書中留個名字。因其文名并不大,其間諸事纏身,但他好像知曉我的心思,非要擠進這本書,冥冥之中竟以各種方式闖入視線。
2015年5月20日凌晨,李成錄忽然托夢于我,將海西州群藝館館長烏席勒微信指點一下,倏忽不見蹤影。猛然驚醒,想那蒙古族人烏席勒我也不曾見過,只是早幾天應邀給即將創刊的《德都蒙古》雜志發去一篇文章,州文聯負責人告訴我烏席勒主編的手機號碼,雙方微信隨之開通,但怎么就會這么巧呢?打開烏席勒微信一路查找,見其清明那天有一首短詩悼念李成錄,并有李的詩集書影。
李成錄生于1963年,海北藏族華熱部落人,藏名華瑞·漠然尖措,畢業于青海民族學院漢語系,民族學在職研究生,青海省作協會員,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進入柴達木盆地工作。2007年出版詩集《瀚海深處孤屋的燈盞》,收入八十六首詩歌及十一篇散文,網上有其《黑夜里我給你寫詩》,指明寫給其愛人。書名及詩題均為不祥之語,“瀚海深處孤屋”那是什么地方?“黑夜里寫詩”那是什么情景?不是墳墓、陰間又是什么?
驀地想起歷代“詩讖”之說,這一中國古代詩歌中特殊的文學現象。詩讖最早出現于魏晉,到宋代已有專門的整理、記錄詩讖的詩話、筆記和小說,其內容主要為詩人的生死年壽和仕途窮達,可分為吉讖、兇讖、自讖和他讖四種。《世說新語·仇隙》之一記載的便是最早的詩讖:“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后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始知必不免。后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最著名的一則詩讖則與隋煬帝有關。傳說他成功開鑿大運河,乘彩舫龍舟下揚州,某日忽得一詩:“三月三日到江頭,正見鯉魚波上游。意欲持鉤往撩取,恐是蛟龍還復休。”又作《索酒歌》曰:“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焰奕紅輝。”雖然詩寫得一般,煬帝卻自鳴得意,即刻交付樂工譜曲,令隨行的宮女們合唱。然而識者卻暗訝為不祥讖語,因為李淵其時已漸成勢,“鯉”、“李”二字同音,而前首詩中有李淵化龍之隱喻。后來李淵大軍攻入京師,煬帝躲入迷樓自殺,唐兵將迷樓付諸一炬,正應了后詩之句。
唐朝詩人崔曙早歲孤賤,曾在終南山隨道士邢和璞學法術,后淪落定居宋州(今河南商丘),曾在少室山讀書。殷瑙評其詩“多嘆詞要妙,情意悲涼,送別、登樓,俱堪淚下”。開元二十六年戊寅科(738),殿試時作《奉試明堂火珠》詩,玄宗看后大為贊賞,取為狀元,官授河內縣尉。可惜翌年病歿,唯遺一女名星星者,世人皆以為“夜來雙月滿,曙后一星孤”是其自讖。
《唐名媛詩小傳》載:“薛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女。父鄖,因官寓蜀。濤八九歲知聲律。一日,父指井梧曰:‘庭除一古桐,聳干入云中。令濤續之,即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薛濤后來流落蜀中,為一代名妓,兩句詩無意中成了她一生的真實寫照。又有《春渚紀聞》載:“建安暨氏女子,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詩,云:‘多情樵牧頻簪髺,無主蜂鶯任宿房。觀者雖加驚賞,而知其后不保貞素。竟更數夫,流落而終。”
五代楚王馬殷、馬希范時,江西廖融避亂不仕,與兄廖凝卜隱南岳衡山,號衡山居士,與逸人任鵠、潘若沖、王正己、凌蟾、王元、楊徽之等為詩友,互有唱和。晚年作詩云:“云穿搗藥屋,雪壓釣魚船。”自解曰:“屋破而云穿其中,無人也;船為雪壓,無用也。”遂以為不吉之兆,“病之,六十日后果卒”。
北宋紹圣年間,秦觀坐元祐黨籍,先是發配湖南郴州編管,后貶謫廣西橫州(今橫縣)。途經衡州(今衡陽),太守孔毅甫見過他,便對人說:“秦少游氣貌大不類平時,殆不久于世矣!”秦觀曾寫一闋《好事近·夢中作》,內有“醉臥古藤陰下”,僅此一句中讖,后來果真卒于藤州(今廣西藤縣)。
再說近現代以來各種故實。1926年4月19日,徐志摩發表散文《想飛》,內中有句“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并描述了飛機爆炸的幻想。1931年11月19日,他乘飛機從南京前往北京,途中在濟南南郊遇難身亡。郭小川于1975年寫了一首《秋歌》,內有不祥的讖語:“我知道,總有一天,我會化煙,煙氣騰空/但愿它像硝煙,火藥味很濃,很濃。”次年10月18日,在河南安陽招待所一樓房間,郭小川服安眠藥后入睡,因未滅的煙頭點燃衣被窒息而亡。1996年夏天,汪曾祺給云南紅塔集團原董事長褚時健畫紫藤并題詩:“瓔珞隨風一院香,紫云到地日偏長。倘能許我閑閑坐,不作天南煙草王。”本是一時戲言,孰料兩年后,年已古稀的褚時健因經濟問題系獄。北大教授、著名學者金克木有本專著叫《書讀完了》,意思是說無書可讀了,不久遽爾離世。他的臨終遺言倒是有趣:“我是哭著來,笑著走。”
我將藏族人李成錄托夢這則筆記發到微信,引起海內外諸多師友驚悚駭異。青海知名作家王文瀘嘆息道:“你說的事情確實罕見。為了青史留名,竟然托夢于生人,實在可嘆!文人之重名,一至于此乎?而‘詩讖一說,自古屢見不鮮,難以用‘巧合二字做簡單解釋。清代雍正時期文壇泰斗、吏部尚書尹繼善去世前一月,讓他的幾個兒子做送春詩,幕友解吉庵寫的是:‘也知住已經三月,其奈逢須隔一年。遺愛只留庭樹好,余暉空托架花鮮。尹尚書大加嘆賞,動筆加圈加點。尚書歿后,眾人再讀,方知無意中寫的全是讖語。不管怎么說,既然李成錄如此執著,你就滿足他的愿望,讓他進入《柴達木文事》一書吧!”又接現居海南島的大學同學凌須斌來電,說是在柴達木盆地工作期間,與李成錄是酒友兼文友,熟諳其人其事。李身高一米八○,長相看似粗獷,內心卻很柔婉,喜愛詩歌到了癡迷的程度。每當與朋友相聚,浮一大白后必定朗誦自己的新作,以“官員詩人”自矜。2008年夏天赴省城西寧開會,在橡皮山往青海湖之間遭遇車禍身亡。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海西文學現象”一時領青海風氣之先,“帶頭大哥”即是高澍。高澍出自山東曲阜大宅門,祖輩遷居天津衛,叔父即外交部副部長周南。他于1968年畢業于清華大學汽車發動機專業,因為家庭出身不好,發配到柴達木汽車修理廠,介紹信上寫著“按工人使用”,于是再次發配到車間當車工。他利用業余時間搞文學創作,短篇小說《琴心》發表于《瀚海潮》1978年創刊號,是青海省“傷痕文學”出現最早的幾篇作品之一。改革開放以后,擔任海西州文聯副主席、《瀚海潮》雜志主編,1987年5月調任州委宣傳部副部長、州廣播電視局局長。在那個偏遠落后的地方,他發下了宏大的誓愿:“辦中國地州一級第一流的臺站。”孰料新官上任剛滿百日,酒后騎自行車回家,剛好撞在一個也是酒后駕車人的汽車上,當場死亡,據說那個司機也畏罪自殺。
青海作家井石告訴我,高澍生前出版短篇小說集《活佛》,內收《活佛》、《新荷》、《急轉彎》、《琴心》、《風起了》等九篇,此外發表過中篇小說《漠上》、《隱憂》、《帶血的玫瑰》、《淡水湖,咸水湖》等,1986年加入中國作協。還有兩篇中篇小說的名字,現在看來極不吉利,中了文讖:一個是《最后的紅薔薇》,在他臨去世前發表;另一個趕發出來時人已離世,名為《死亡之吻》。
文讖、詩讖是什么?是所有作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的宿命。試想一下,如果你寫了什么,你的命運也注定發生什么,那是不是很恐怖?戰國時代,荀子發出“言有招禍也”的警告,其高弟韓非竟以《說難》名篇,首創“逆鱗”之說,指出“因言致身危者七”。秦王嬴政為了得到韓非而出兵攻打韓國,李斯因妒其才而將其謀害,《說難》遂成文讖。《三國演義》第三回寫道:“先是洛陽小兒謠曰:‘帝非帝,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邙。至此果應其讖。”南宋狀元文天祥曾有一篇文如其人、在某種意義上猶如文讖的經義——《事君能致其身》其中說:“委質而為人臣,當損軀以報人主。”似乎看到了若干年后自己的結局。即便元世祖忽必烈親自勸降,許以宰相之職,文天祥依然大義凜然,寧死不屈。民國時期,章太炎、劉師培與黃侃,三個大學問家,卻因行為怪僻而被稱為“三瘋子”,其中黃侃是章太炎的弟子。章太炎勸黃侃及早著書傳世,黃侃卻非要堅持“五十之前不著書”。1935年4月3日,黃侃五十歲生辰,章太炎書贈壽聯:“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成好著書。”黃侃見聯中有“絕命書”三字,大為驚詫。是年10月6日,黃侃由于飲酒過度,胃血管破裂,搶救無效,兩天后下世。章太炎因聯語成讖,余生痛悔不已。丁玲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風云人物,瞿秋白曾預言她“飛蛾撲火,非死不止”,后來的人生果然幾度坎坷榮辱相伴。
1988年7月下旬,詩人海子途經柴達木盆地,寫了一首詩《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籠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草原盡頭我兩手空空/悲痛時握不住一顆淚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這是雨水中一座荒涼的城//除了那些路過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我把石頭還給石頭/讓勝利的勝利/今夜青稞只屬于他自己/一切都在生長/今夜我只有美麗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關心人類,我只想你。”詩中兩次重復“唯一的,最后的”這種極端的表達,意味著海子在這一天失去了一切,失去了詩歌和情感,也失去了創作的天才,剩下來應該干什么,還用得著我們費神猜想嗎?果然,翌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關臥軌自戕,從而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符號。
再說吾鄉衡陽先賢、世界華文詩壇泰斗洛夫先生,也曾有過文讖和詩讖,而許多研究者迄今都未感覺到。還在十五六歲讀初中的時候,洛夫在衡陽《力報》發表散文處女作《秋日的庭院》,卻取了“野叟”這樣一個老氣橫秋的筆名。大約是2011年秋天,借其回鄉省親的機會,我曾當面詢問他筆名的來由,他笑呵呵地說:“可能是受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啟發,也有韋應物‘野渡無人舟自橫的影響。‘野叟就是四野流浪的老漢——可不就是嗎?先是從衡陽到臺灣,再從臺灣地區到加拿大,我現在成了一個失國的老頭了。”在洛夫所有的詩歌中,《邊界望鄉》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曾無數次被兩岸的詩評家點評過。1979年3月16日上午,訪問香港的洛夫在詩人余光中的陪同下,去關界落馬洲遙望內地。“當時輕霧朦朧,我從望遠鏡中望過去,見到……河山猛然出現在我的眼前,就好像狠狠地被打了一拳。這就是數十年不見、日思夜想而又回不去的……家園嗎?耳邊響起鷓鴣鳥的啼叫,聲聲扣人心弦,我當時激動得熱淚盈眶。這時才體會到什么叫‘近鄉情更怯,什么叫‘有家歸不得”。同年6月3日寫下詩歌《邊界望鄉》,表達游子懷鄉咫尺天涯的傷痛、落寞和無奈。名句“喏!你說,福田村再過去就是水圍/故國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來的仍是一掌冷霧”,“當距離調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遠山迎面飛來/把我撞成了/嚴重的內傷”,后來不幸成了詩讖。2009年10月底,省、市、縣三級在衡南縣城云集鎮,轟轟烈烈地舉辦了首屆洛夫國際詩歌節,并為洛夫文學藝術館、洛夫文化廣場奠基,天下咸知,歡欣鼓舞。孰料“蕭何們”各貪天功,互相拆臺,暗中使壞,致使建好的洛夫文學藝術館被挪作他用,門前的洛夫文化廣場也被強行更名,“成了一場盛大的騙局,令我無顏回鄉再見父老鄉親”(洛夫語)。
孫蓉蓉《詩歌寫作與詩人的命運——論古代詩讖》一文認為:“詩讖其實不是讖,是讀者在對詩歌的別解字句的過程中形成的,其中一些看似偶然的巧合又帶有某種必然因素,反映了古代文人對于生命與仕途問題的關切與焦慮。而對詩讖的評論和觀點,又構成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古代詩讖的形成有著復雜的原因,體現了傳統天命論的思想、語言禁忌的影響和‘微言大義的說詩傳統的深層積淀。”說白了,詩讖、文讖的主觀意識十分強烈,不無偶合、附會和推論,曾經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被學界視為“旁門小道”和“怪力亂神”。
在高科技非常發達的今天,人們接受信息更加全面,也愈來愈清醒理智,對于任何事情都能辯證地看待,已不再一味地相信和盲從。《孟子·盡心下》就說過:“盡信書,不如無書。”宋代文學家洪邁《容齋隨筆·詩讖不然》亦云:“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家往往以為讖。白公(白居易)十八歲,病中作絕句云:‘久為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白公壽七十五。”衡南洛夫文學藝術館和洛夫文化廣場,經過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在洛夫先生去世一年多以后,終于被新任縣委書記提上議事日程,已經進入裝修設計階段,詩城云集與洛夫先生的名字再度聯系在一起。這也印證了清初傅山題畫梅詩句——“人力能補天地缺”。
因此,我特別推崇湖湘書法名家何滿宗倡導的“寫吉祥,頌吉祥”,以“德”“福”“壽”弘揚我們的美好愿景。為了詮釋這“吉祥三字”,何滿宗又作《吉祥三頌》,分別為《大德頌》、《萬福頌》、《長壽頌》。《大德頌》:“君有德,志高潔,仁愛惠恩澤。敬老尊賢禮天下,心鏡如秋月。”《萬福頌》:“家和諧,人親切,祥瑞喜相接。歡暢心海長波涌,福源永不竭。”《長壽頌》:“慈悲懷,清風節,善行圣于雪。德潤眾生無量壽,時空恒飛越。”并有副歌:“壽比南山久,天風頌大德,洪福萬民悅。”但愿吾友的《吉祥三頌》,能給天下文朋師友一點啟示,并給千家萬戶帶來幸福美滿——扎西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