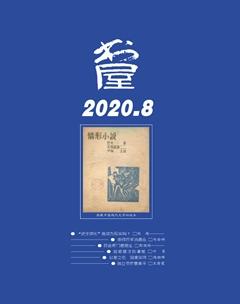閱讀,為善留下空間
蔣書麗
《朗讀者》女主角漢娜在自縊身亡時,電影導演給觀眾留下了一個意味深長的鏡頭:漢娜赤腳踩在一摞書上,完成了自己的自殺行為。在這一情節上,小說中的描寫顯得有些過于簡單和蒼白,作者只用了一句話:“在天色微明時分她上吊死了。”就電影這一改編來說,導演和編劇顯然比原作者更懂得女主角的選擇。書籍賦予了漢娜新的生命,盡管這一賦予是通過死亡來完成的,但這并非悖論。有多少文學經典名著里的死亡,賦予了人物永恒的生命!比如說于連,比如說安娜,比如說苔絲。
如果沒有學會閱讀,漢娜絕不會自殺。從這一角度來說,不管小說還是電影都無關乎愛情、無關乎戰爭,而是關乎成長。而漢娜的成長,直至將近古稀之年,她才得以完成。或者說,學會了閱讀,才標志著她完成了自我意識的確立,才獲得了靈魂。而她的成長,是從遇到中學生米夏開始的。在這個意義上,米夏實際上是漢娜的精神引路人。這種精神上的引導,從二者結識開始,直至漢娜自己學會閱讀為止。
中年女性漢娜和中學生米夏的結識,純屬偶然。放學途中發病的米夏碰巧走到了漢娜的樓下,而漢娜幫助了米夏。情竇初開的青春期男孩和獨守空房的中年女性漢娜就這樣發生了一段不倫之戀。而貫穿于他們戀愛生活中的重要活動則是米夏給漢娜朗讀經典文學名著,漢娜甚至給米夏定下了規矩:“先朗讀,再做愛。”
但毫無征兆的,漢娜不辭而別。因為她即將升職——從電車售票員到司機,而她不識字,只能一走了之,沒有告別,沒有留戀。而當米夏再次遇見漢娜時,卻是在法庭上,一個是法學專業大學生,一個是階下囚。而通過法庭審判,米夏才對漢娜的過去有所了解。原來,漢娜曾是納粹時期集中營的看守,而對于自己的職責,漢娜可謂是兢兢業業,一絲不茍,唯一不同之處是,她經常會挑選小姑娘給她閱讀,直到最后不得已才將小姑娘送走(送到毒氣室或焚尸爐)。而她站上被告席的原因,則是在轉移所謂囚犯的過程中,夜宿的教堂突發大火,為了保持她所謂的秩序,看守們選擇寧可讓這些所謂囚徒活活燒死,而不是打開教堂大門放她們一條生路。
對于漢娜來說,聽從命令、堅守職責和維護秩序比生命更重要,就這一點來說,漢娜身上恰恰也體現出一種阿倫特所說的“平庸的惡”。有意思的是,在米夏為漢娜整理遺物時,的確有那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以及其他一些“描寫集中營幸存者的書,還有赫斯的罪行錄和阿倫特關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判處絞刑的報告,以及一些有關集中營的學術文獻,全都擺在一起”。由此不難相信,法庭審判并不足以讓漢娜對自己的罪行有深刻的認識,恰是閱讀,讓她對自己在納粹橫行期間的行為產生了愧疚和贖罪的意識,這才有了將自己的積蓄送給教堂大火幸存者的一幕。
很顯然,漢娜的生命中存在著嚴重的缺失,那就是對生命的敬重。而這種缺失,與她生活中的缺失密不可分。無論在小說還是電影中,漢娜都是一個孤獨的存在,沒有家人,沒有朋友。更可怕的是,她不識字。在她的生命中,唯一與她發生過緊密聯系的就是中學生米夏。對于她的出生和成長背景,讀者和觀眾不難揣測,那一定是一個缺少愛和關懷的所在。也因此,她在與米夏的交往中,才顯得格外地生硬,她的情感世界里幾乎是一片荒蕪。作為一個生活在現代社會的成年人,一字不識,這一缺陷將她與外在隔絕開來,使她既不能融入現代社會,更不能融入他人的情感世界。更為重要的是,不識字,不會閱讀,讓她的內心世界單一而幽暗,這也就可以理解她何以能夠眼睜睜地看著那么多鮮活的生命被大火吞噬。
其實,對于自己與米夏之間的距離,漢娜內心是非常清楚的。小說中一個耐人尋味的情節是,借助家人外出度假的空隙,米夏帶漢娜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也是一個大學哲學教授的家中,米夏敏銳地感覺到了“她感到在我家是個闖入者”。這種格格不入的闖入者身份在漢娜進入米夏父親的書房時顯得格外明顯,“只見她的目光掃在每一排齊著天花板的書架上,就像是在翻閱書頁一樣。然后,她走到一排書架前面,把右手的食指舉得齊胸那么高,輕輕地劃過書脊,接著又走到第二排書架前,仍舊用食指劃過書脊,就這樣,書脊聯翩著書脊,她劃著劃著,穿過了整間書房”。這一場景遺憾地在電影中消失了。小說作者把這一幕當作關于漢娜不多的幾次寫照留存在記憶深處,而這一場景把漢娜對于書籍、對于自由閱讀的渴慕表現得淋漓盡致。
一次偶然的事件,也讓米夏看到了漢娜的另一面。在兩人出游的一天早晨,米夏給漢娜留了字條就出去了,而回來時,漢娜發瘋似的拿皮帶抽了米夏,并放聲大哭起來。讀者很清楚,漢娜因為看不懂米夏留的字條而懊惱、窘迫、憤怒、羞愧,這些情緒使得她喪失了理智。而米夏也是束手無策,因為“在家里沒人會嚎啕大哭,在家里沒人會用皮帶抽人,連打人都不會,更別說是用一根皮帶。在家里我們是君子動口不動手。可是,現在讓我說聲什么好呢?”這是一次野蠻和文明的短暫相接。從漢娜這一行為中,讀者也不難理解,后來在納粹集中營工作的漢娜何以如此冷漠。
米夏和漢娜顯然屬于不同的世界,將二者聯系在一起的,不過是一種肉體關系。但即便是一種肉體關系,對于米夏也還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注定了他今后的兩性關系是以失敗告終。而在法庭上不能公開漢娜不識字的真相,更讓他產生深深的無力感和愧疚感,而為漢娜朗讀成為米夏自我救贖的一種方式。
美國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在《如何讀,為什么讀》中有過這樣一句話:“只有深入、不間斷的閱讀才能充分地確立并增強自主的自我。除非你變成你自己,否則你又怎會有益于別人呢?”這句話仿佛就是說給漢娜聽的。的確,漢娜只有在最后學會了閱讀,才成為她自己,而在那之前,她只是一具軀殼。而名為《朗讀者》的電影和小說,其實際所指卻是從聆聽者向閱讀者的一次華麗蛻變。抑或,原著和電影本該被翻譯成“讀者”,故事表層的朗讀者無疑是米夏,而真正的閱讀者實際上是漢娜。對于受過系統人文主義教育的米夏來說,閱讀是他生活和學業中必要的組成部分,但對于漢娜卻不是,那是她付出了半生的時光才掌握的技能。也因此,學會閱讀是她生命中的一次質的飛躍,為她荒蕪的生命底色里增添了一絲生機。
一個細節再次證明了電影改編對于小說原著的超越。無論是荷馬的《奧德賽》,還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或者席勒的《陰謀與愛情》,都不過體現的是米夏的課業安排,或者是作為文學經典的代表出現。但電影中出現的一篇契訶夫的小說《帶小狗的女人》,卻是別有深意。一方面,漢娜從聽了這篇小說后,開始根據錄音和書籍對照著學習單詞,邁開了她學習閱讀和識字的第一步,也是她確認自己的第一步,也是她走向死亡(同時也是新生)的第一步。另一方面,契訶夫的這篇小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讓漢娜學會了什么是愛情。電影里對契訶夫這篇小說的反復強調,其隱喻之意十分明顯。小說《帶小狗的女人》,原本講的是兩個萍水相逢的中年男女諸多艷遇中的一次而已,不想當他們在莫斯科某劇院里再次相遇,卻發現彼此產生了一種可以稱作愛情的情愫。回頭看漢娜和米夏當年的相戀,他們彼此肉體的迷戀明顯多于思想情感的交流,而這樣一種交流,實際上是由朗讀和聆聽來完成的。
可以說,作為漢娜的精神導師,米夏是通過朗讀帶領漢娜完成了精神上的成長;而漢娜作為米夏身體欲望的對象,從肉體上引領著米夏從少年轉變為男人。也從此,漢娜的氣味、漢娜健壯的肉體橫亙在米夏與其他女性之間,注定了他的婚姻生活的不幸。而漢娜,當她看到米夏從她手中抽回自己的手,并問她對自己的過去(納粹時期)怎么看時,漢娜明白了,她和米夏之間永遠結束了,而米夏是她在這個世間唯一的留戀。死亡,于她是最好的選擇,對于小說或者電影來說,也是最恰當的結局。
無論是作為戰后成長起來的一代,還是大學法學教授、法官的身份,作者本哈德·施林克都賦予了該小說極強的真實性,加上他返璞歸真的寫作風格和獨特的兩性關系,更使得小說耐人尋味,使得它超越了一般的兩性書寫——如《洛麗塔》之流,也超越了大多數關于二戰的文學敘事,這里集中營、納粹等被簡化為法庭上的一種陳述。這樣的作品,成為暢銷全球之作,實在是不足為奇。而改編的同名電影更是斬獲奧斯卡金像獎,女演員凱特·溫絲萊特也因此獲封影后,一切都是皆大歡喜。
一位評論家曾這樣評價過該小說:“人們會一遍又一遍地讀它,為了找出自己到底能夠做些什么。”古今中外,數不清的大文學家為人類社會留下了數以千萬計的文學經典名著,但卻依然阻擋不了有那么多愚昧、愚蠢的家伙將戰爭、災難帶給人類。可是,倘若沒有書籍,沒有閱讀,這個世界豈不是會更糟糕?也許還是哈羅德·布魯姆說的對:“我們如何讀和為什么讀:在你的生命中保持警惕,了解和認識善的可能性,幫助它忍耐,給它空間。”
是這樣的,閱讀是為了在人世間給善留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