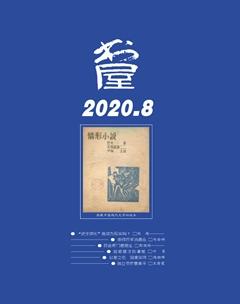“逆全球化”能成為現實嗎?
劉超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全球環境發生巨大變化,許多海外華人紛紛歸國;與此同時,對中國留學生的錄取則大幅收緊,許多國家高校的國際學生招生數縮減,這無疑造成了種種疑惑。這個世界將向何處去?高等教育將伊于胡底?在此情勢下,有人認為國際格局重新洗牌,世界已開始或即將開始“逆全球化”,世界高等教育格局及其國際化進程亦將發生大逆轉。
正如著名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所言,疫病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自古以來,疫病就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一個個歷史轉折的重要推手。人類當下正在經歷的這次流疫亦復如此。毫無疑問,疫情或已改變了原有的世界,人類社會在許多方面很可能是再也回不到從前了。
高等教育是一項國家事業,同時也已然是一種國際事業、全人類的事業,知識及教育的國家化、國際化已成為當今社會的普遍現象。二十世紀以來,尤其是二戰之后,教育“國家化”成為普遍趨勢,高等教育越來越成為國家的事業。克拉克·科爾認為,在美國,“巨型大學不僅是社會利益的接收者,而且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它本身就是美國高生產率的成分之一”。正如布魯貝克所言:“就像戰爭的意義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給將軍們決定一樣,高等教育也相當重要,不能完全留給教授們決定。”二戰以后,多元巨型大學漸成常態。大學職能和角色多樣化使其結構與功能日趨繁雜,需要盡可能平衡學術與行政、大學與社會、國內與國際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大學的決策,往往不是大學所能主導的,不是社會所能主導的,甚至也往往不是主管部門所能完全把控的,它受制于各方博弈所形成的復雜合力。
從歷史上看,大學創建以來就幾乎始終是國際性機構。古代印度的高等教育機構,曾吸引了許多國家的學生和學者前往學習、研究,其影響所及遠遠超過印度本國。歐洲中世紀大學更是如此。意大利的博洛尼亞、法國的巴黎大學等,都有著來自各國各地區的大批學生和學者,近代史上的法國巴黎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以及二戰以來的美國哈佛大學,莫不如此。那些名校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名校,不僅僅是因為可以為世界貢獻全球性知識和思想,而首先是因為能夠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前來學習、工作、交游和參訪。正是人員的國際流動和交往,促進了其影響力的國際傳播,提升了其世界聲譽和貢獻度。可以說,世界名校的這種國際性和開放精神,即便在各國和世界局勢最困難、最艱苦、最動亂的條件下,也沒有完全改變過。
全面抗戰時期,曾留學牛津大學的知名學者羅忠恕,在與西方學者密切合作的過程中指出:“人類對自己創造的燦爛古代文明必須珍視、傳承。東、西方對于自己創造的古代文化必須彼此加強交流。”1939年,他赴日內瓦參加國際問題研究社時指出:“在現在的世界,科學已將地球縮小,使世界任何處所皆已成比鄰,以一個渾圓的地球,任何一處,皆為其他處之東,亦為另一處之西,故可謂東即西,西即東,東、西是處處相遇的。”誠所謂“東西一體,風月同天”。1939年11月,在東、西方都戰云密布的時候,牛津大學諸多學者推動成立了“英中文化交流合作委員會”;12月,劍橋大學也緊隨著成立了“英中學術合作委員會”,李約瑟博士任書記。劍橋方面致函中國:“為促進人類之進步計,東、西學者及科學家似有密切聯絡之必要,使各民族之知識與傳統之精神有適當之聯絡。”中國的燕京、齊魯等五所教會名校聯合致函牛津、劍橋,強調:“雖在戰爭中,亦應盡最大之努力,謀密切之合作。……如能交換教授,對兩國皆有利益。”后來,該目標得以部分實現。1947年,羅忠恕在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哲學顧問時,提出了“世界大同”的理想,表示:“世界是一個整體,需要人民之間的合作;每一個人都應有目的,只有社會機構才是為人人服務的手段。個人與民族應互相尊重,讓每個人都能充分發揮個人的才華,為人類做出最大的貢獻。”
在戰火紛飛之際,這些東、西方名校學者的精誠合作與不懈努力,結出了碩果,至今令人感佩,這無疑是高等教育的國際性的高度彰顯。而今人類文明和高等教育事業發展又到了一個新的岔路口,先賢的努力和智慧尤為今人提供豐富的啟示。
大學的另一項重要職能是學術研究,是知識傳承、貢獻與創新。大學科研工作意在傳承已知、探索未知、創造新知。“作為這個世界一部分的知識”,知識“從來都不是固定的或既定的……不論多么困難,它總是開放的,時刻接受挑戰與改變”。創新無終點,求知無止境,知識是沒有國界的。外部的強力手段可以干預知識生產和傳播,但并不足以改變知識本身的存在和內在發展與固有邏輯。而現代社會中,公權部門對知識的過度干預和國際管控,無疑將制約知識創新與傳播。就此而言,為保障知識創新和科技教育水平及綜合國力的提升,為了保持國家的實力和創新力,相關各國也不得不遵從知識創新、學術發展的這一固有特性。為此,繼續保持開放,與其他國家交流共進,是發達國家的不二之選。而中國作為人類社會的重要一員,作為擁有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國,是西方國家教育開放、學術交流過程中無論如何無法回避的存在。
默頓在其名作《科學的規范結構》中對科學的特性做出經典論述。他認為,科學精神有客觀性和創造性兩大標準,科學共同體應具有四大特征:普遍性、公有性、無私利性和有條理的懷疑精神,而科學“比其他的大多數社會體制更接近于普遍主義的理想”。因而,現代學術被認為是最具普遍性、最具公正性的國際化特質、最具國際主義精神的事業之一。十九世紀著名化學家門捷列夫曾智慧地預言:“認識無止境,科學亦無止境。科學將成為全世界的科學。”日后的學術進展確實印證了這一預言。一般而言,現代科學已成為一個無國界的知識體系。
這一時期學術和學術專業(職業)的發展,同樣呈現出鮮明的國際化特征。“學術專業”遲至十九世紀晚期才出現,“然而一旦出現,它對研究的強調不可避免地表現出世界性而非地方性特征”。而當學術發展到二十世紀末期的時候,人們進一步認識到:“社會科學是近代世界的一項大業,其根源在于,人們試圖針對能以某種形式獲得經驗確證的現實而發展出一種系統的、世俗的知識。這一努力自十六世紀以來逐漸地趨于成熟,并成為世界建構過程中的一個基本方面。”從十七世紀六十年代起,“科學開始被界定為對于超越時空、永遠正確的普遍自然法則的追尋”,華萊士(Walter L.Wallace)指出:“不論科學曾經是什么,科學就是關于人類世界經驗命題的一般化與真假檢驗的一個方式。”科學在本質上具有普遍主義取向和普遍的解釋力,而這種解釋力顯然是超越民族—國家之邊界的。自然科學就如此,知識在本質上仍具有超越民族邊界的普遍化(世界性)追求,世界主義、普遍主義是其本能的訴求。
阿爾君·阿帕杜萊(Appadurai)表示,“文化同質性與文化異質性之間的張力”,是“當今全球性互動的中心問題”。許多學者明確反對單極化、同質化和一元普遍主義。羅蘭·羅伯森提出了“普遍主義的特殊化和特殊主義的普遍化”的方案,通過“普遍主義的特殊化”和“特殊主義的普遍化”雙向推動來解決問題,前者實現“全球本土化”,后者實現“本土全球化”,如此則避免了多種不良傾向,消除了將全球化(普遍性)與本土化(特殊性)作為文化兩極而產生的對立,使它們作為一種“互相貫穿的”原則而存在。因此,各國的社會科學也就是一種“地方全球化”知識,其所尋求的地方性、本土性,應該是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性、本土性,即全球“本土化”。本土化與全球化構成對立統一的張力,二者相生相克。
當然,現實的全球化事實上依舊是不平等的,當今的全球化依然是西方主導的進程。不僅僅在知識生產和話語表述中,即便是在知識分類、評價、傳播、獎勵等諸多環節中,西方也明顯體現出其西方霸權主義(西方中心論)傾向。這當然是歷史所逐步形塑的。
美國科學史家喬治·巴薩拉(George Basalla)在其經典論文《西方科學的傳播》中提出:十六至十七世紀之間,一個由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荷蘭等西歐國家構成的小圈子提供了近代科學的最初家園,并成為科學革命的中心,隨之而來的是征服了全世界。及至十九世紀,“社會科學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地區:英國、法國、日耳曼國家、意大利半島諸國以及美國。大多數學者、大多數大學(當然并不是所有的)都云集在這五個地區,其他國家的大學無論是就數量而言還是就國際聲譽而言都無法與這五個地區的大學相比肩”。可以理解,上述地區的重知識群落的工作,在整體上形塑了近代西方知識體系,而它們也成為近代世界學術體系的母體和主流范式。按照本-戴維的研究,德、法、英、美四國長期是相對自給自足的學術體系,是現代學術的中心(Centers of Learning),其他地方不過是外圍(peripheral)。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萌生于十九世紀,但真正的社會科學向世界擴展,并在國際體系中形成明確的知識權力結構始于二十世紀。1945年前后,社會科學的全部學科的制度化在世界范圍內完成,至此西方主要國家知識體系中基本確立了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三大學科分類模式。
整個十九世紀,西方幾乎征服了全世界,隨之而來的是二十世紀社會科學在全球的擴散。這一擴散最終形成了今天既成的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中的知識權力結構。伴隨著社會科學在西方的形成及其制度化,特別是西方大學教育模式二十世紀向全球的推廣,社會科學所隱含的知識-權力結構,最終演化成為世界體系中的知識權力結構。知識體系并不完全是中立的,它的背后隱含著權力。而學校正是促使主流意識形態合法化的文化再生產的重要機構。正是通過學科在大學中設立院系和教席,促成相關圖書的分類等制度化,西方的知識體系才得以以一種貌似科學化、合理化與合法化的過程,參與到世界范圍內社會建構的過程中。
沃勒斯坦在1996年出版的《開放社會科學》中認為,社會科學的學科界限沿著三條中線而分開,其中之一就是西方的(歷史、經濟、政治、社會學)對非西方(人類學和東方學)。顯然,按照這種力圖最大限度地彰顯世界性的學科分界,東方仍是作為西方的對立物而存在,仍是西方世界之外的難以類歸的存在,這無疑暗含著西方“中心”對非西方世界的歧視。對應于沃勒斯坦提出的“社會科學研究的西方和非西方軸線”,二十世紀國際體系在政治和經濟史上也出現了一些核心區(國家)和邊緣區(國家)的結構。這些“核心區國家”正是那些社會學制度化形成和確立的先進國家,即所謂“西方”,它們創造了今天全球通用的社會科學主要概念、范疇、命題、理論和范式;而“邊緣區國家”則對應于“非西方”,這些國家和地區被動地接受了西方社會科學知識體系。
自然,國際化是多向度的互動行為。它一方面意味著大量非中心國家的人才流向中心國家學習和交流,也意味著中心國家的知識、技術、制度向非中心國家滲透。在這個過程中,中心國家的文化成果完成擴張,而非中心國家分享了先進國家的文化成果,同時也無形中被前者所文化殖民和精神統攝。有時候,它“越是學習他人,就越是依賴他人,難以擺脫邊緣的地位,背離了最初的目標”。任何事物都是作為矛盾統一體而存在的,矛盾就是對立統一:一方的存在構成了另一方得以存在的前提。在世界學術體系中也是如此,若“東方”(非西方)不存在,“西方”的概念就毫無意義;若無“非中心國家”,也就不存在“中心國家”。這種不平等的國際化,正是依賴于西方與非西方、中心國家與非中心國家的密切互動。國際化是西方國家“中心地位”得以實現、維護和鞏固的前提。沒有國際化和人員-文化的國際交流,中心國家不可能實現其價值和技術的推廣,不可能更好地維護和強化其中心地位。錢穆指出:“唯人類文化世界,乃為千百年之根本之大計。”各民族文化的發展常需“去腐生新”。為達此目的,則需創新文化源頭,同時吸收外來優良之文化。相關各國為了維持自己的文化活力,為了增進自己的文化影響力、鞏固自身的學術中心地位、維護自身文化霸權,也不可能完全阻止文化的交流合作。因此,哪怕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西方國家都不可能主動終止國際化,它所希望做、能夠做的,大概僅僅在于調整國際化的方向、步驟和策略。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是人類共有的財富和共同的事業。學術無國界,近代以來的學術更是超越國界的、國際性的事業,是人類共同的大事業,它不僅僅為個別人的利益服務,也應該為全人類全世界的利益而服務。高等教育的非功利屬性和科學的相對超越性(普遍性),是不以任何人、任何國家的意志為轉移的。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它能夠而且必須跨越國家邊界,在全球范圍內傳播和再生產。即便在國家間關系高度緊張的時候,學術文化交流也沒有停止過。具體到美國的大學,也是在二戰中由于大量延攬了歐洲(包括德、意等國)杰出人才而憑借戰爭紅利迅速發家的。由此,在世界的大動蕩中,國際學術中心完成了從歐洲到北美的洲際大轉移,世界高等教育的歷史由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馬克思認為,人類歷史經歷了“從民族歷史到世界歷史”的轉變;人類的歷史一旦進入全球歷史,就已不可逆轉。全球化因此向縱深推進。在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考察,以深遠的洞察力揭示出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趨勢。通過生產、生活和交往,人類歷史越來越“成為世界歷史”。而今,世界已成“地球村”;人類社會已不僅僅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文化共同體,而且實實在在地融合為一個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人,也許是“大地上的異鄉者”,但“沒有人是一個孤島”,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與大地相聯系。沒有人能長久地逍遙于桃花源,沒有人能自外于社會而遺世獨立。歷史發展到今天,人類的相互融合、交錯纏繞已到了空前的高度。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的全球性擴張是不可避免的;資本將從發達地區擴張至經濟文化落后地區,并對全球各國都產生深刻影響。顯然,知識、教育的國際化與資本的國際化是緊密相連、相互作用的。與知識經濟相伴生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必然借助國際平臺,吸收新知識、傳播新知識、應用新知識和創造新知識。因此,世界各國都在想方設法推進本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這是大勢所趨。
高等教育是人類共同的事業,學術事業尤其如此。因此,它是不可能被完全孤立的。要在西方與包括中國及其他國家之間實行徹底的人為切割或隔離,顯然并不現實,這完全違背了高等教育和學術事業的本質屬性。同理,此種意圖注定不可能得逞。因此,在當今及稍后一段時間內,高等教育的快速國際化步伐可能會有所收縮,方向會有所調整甚至發生局部的逆轉,但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大趨勢難以改變,大的格局亦不可能逆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也許會將操縱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進程作為政治伎倆,但是這些國家本身的教育發展和學術事業仍有其自身需求。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教育學術交流合作雖然將受到某些影響,但也不可能因此終結跨國交流。當今的一些亂象,亦只是特殊形勢下的階段性的停擺、收縮或回退,不可能長久如此。
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早已時時、處處經歷著“流動的現代性”,知識、技術、產品和人員等方方面面的高密度流動早已成為常態。高等教育早就不以國界自我設限。此外,人類經濟活動的全球化也在更深層次上推進著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態勢。經濟活動和資本流動的全球性,從經濟基礎的層面進一步強化了人類交往的全球性,以及科技、教育、文化活動的全球性,而這又內在地要求人員流動的全球性。這一大的趨勢,在可預期的將來是不可能根本逆轉的。對此,我們理應有充分的信心。
和很多國家一樣,中國既是全球化的建設者,也是受益者。今后,只要我們準備充分、應對得當,完全可以更好地為世界的繁榮進步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