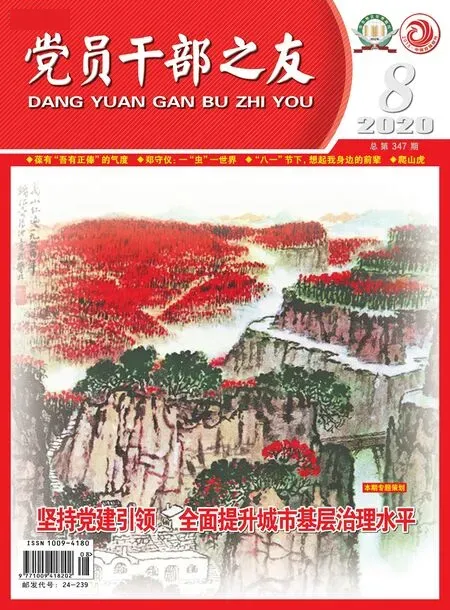“八一”節下,想起我身邊的前輩
□ 逄春階

黎 青/圖
出身寒微,沒有名門望族的詩禮簪纓傳奇,也無光耀史冊的先輩榮光。忽一日,收到安丘市政協編輯的文史類刊物《渠風》,看到一篇文章《我的革命生涯》,作者楊誠錫。名字咋這么熟呢?打眼一看,這不是我的堂舅嗎?沒看文章,先看黑白照片,果然是他。他有啥革命生涯?等我讀完,大吃一驚。趕緊打電話給我的表弟楊貴澤,表弟說:“楊誠錫是老革命,他兒子叫建軍,你想起來了吧?”建軍,我兒時的玩伴,當然熟悉。
“我1930年7月生于安丘市景芝鎮前院村,即將迎來90歲。1945年,我參加村民兵組織,1948年初參軍,先后參加濟南戰役、渡江戰役和解放上海,駐防福建前線,其間參加了東山保衛戰,歷任戰士、班長,1957年復員回籍,次年到景芝酒廠從事保衛工作,1981年退休。”我小時候,住在姥爺家,與堂舅楊誠錫為鄰,他的兒子建軍個子高,領著我們一幫小孩到處亂竄。從來沒聽堂舅講過故事,印象中,他說話聲音不高,愛笑,走路腰桿挺直。
看了文章,我才感覺,他給兒子起名“建軍”,是有寄托的,他懷念他的戰爭歲月。我記得,建軍有頂軍帽,戴在頭上很威風,還有根皮帶。我很羨慕他。
“參軍后不久,部隊改編,成了三野陳毅的兵,團長是以作戰勇猛著稱的‘宋瘋子’宋家烈。我先在機槍班扛了五年的機槍,在部隊總共十年,干了九年班長。解放大河口,十個人的一個機槍班,一仗下來,只剩下一個老班長和兩個新兵,還算囫圇。每次戰斗,機槍陣地自然是敵人重點打擊的目標,曾有一發炮彈飛過來,我班當場傷亡四人,我傷了腳,硬是咬著牙堅持,直到發起戰斗沖鋒,最后把俘虜帶下陣地,指導員在戰場上宣布,楊誠錫是輕傷不下火線,提議我火線入黨。”堂舅的敘述,簡約樸實,沒有夸張,一句一個事,都是實事兒。按我們新聞記者的職業來說,就是用事實來描述事實。
后來,堂舅轉業到酒廠當保衛,盡職盡責,年年先進,口碑很好。后來為讓兒子建軍接班,他提前退休。我找到同學馮金玉,他現在是景芝酒業的工會主席,他說,對楊誠錫老人當然熟悉了,他兒子建軍大名叫楊術澤,好兄弟。馮金玉說:“去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還是我代表景芝酒業給他送到家的呢。這是黨和國家送給一個軍人的最高榮譽。”真是巧合。
堂舅很有意思,本來可以有殘廢待遇,但他拒絕了。他有個“活思想”:“按我的傷殘,當年在部隊上至少應該評‘三等殘’,轉業時衛生員提出給整理一下檔案材料,好辦正規手續,但我沒有申請評級。現在少這一塊撫恤補助,要怪當年有種‘活思想’,本身已經是大老粗了,擔心自己二十多的歲數了,成了‘殘廢’,回家不好找媳婦就沒辦。再后來,就根本沒這些想法了,也沒回部隊去找待遇。你想,國家給咱安排了正式工作,日子越來越好了,比比犧牲的戰友,咱夠幸運、幸福了。”我突然覺得我這個堂舅太可愛了,為了找媳婦,故意隱瞞了殘廢身份。
“建軍”這個名字,還包含了這么多的內容。我佩服我的堂舅。我還佩服一個人,是我五姥爺。
五姥爺楊仲祥如果活著,是97歲,他參加過抗美援朝。我聽他親口講過,他當兵時,我舅楊海仙兩歲,我姨楊梅仙出生僅兩天。我五姥爺聊天繪聲繪色,但好多人說他吹牛。他就坐在炕上抽著煙,說:“愛信不信啊。”
五姥爺愿意跟我聊,他當時跟我不停地說,但我沒記住。要是記住,我就能把他的經歷整理出來了。五姥爺復員后一直在家務農,他去世十年后,他的革命軍人證書從老房子里翻出來。他1949年2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復員前在某軍141師警衛第四連。抗美援朝紀念章是1954年10月26日頒發的,紀念證書是這樣寫的:“茲有本部楊仲祥同志系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四日入朝,于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回國,應發朝鮮祖國解放紀念章一枚……”祖國解放紀念章是朝鮮政府贈送的。
五姥爺給兩個孫子起的名字是“平等”“和平”,他給外孫起的名字叫“運輸”,這些名字,都跟其他人不一樣,很明顯有軍人的風格。
過去農村為晚輩起名字很隨意,但有在外面闖蕩經歷的人,他們孩子的名字都有講究。在農村人眼里,走出村莊的人,見多識廣,所以,我的這個五姥爺應該為好多人起過名字,可惜無法考證了。2000年農歷2月17日,老人家去世。我很后悔,此前那么長的時間,我都沒有關注他。按我五姥娘的話是:“聽他扒瞎話!”一臉不屑。但我五姥爺依然故我。我也就跟著我五姥娘和我的親戚,一起把五姥爺的價值忽視了。因為發現了五姥爺的獎章和證書,五姥娘享受了幾年補貼。
被我忽視的先輩還真不少。我妻子的大舅王木鐸,也是1949年前參軍入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在鎮上擔任民政助理。他給晚輩起的名字更有意思了。長子大聚,二子人民,三子紅喜,四子紅旗。給侄子起的名字有銀行、國營、新華、全國、愛國、建國、衛國、衛東、英文等等,每個名字都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標準的軍人風格。
我的鄰居堂兄逄春經,也是從抗美援朝戰場下來的,他是殘廢軍人,身上被燃燒彈燒了,耳朵、鼻子都是后來植皮做的。他給晚輩起的名字有“槍”“炮”“軍”等,但是晚輩嫌不好聽,都放棄了。有個叫“擁軍”的,是不是春經哥起的,我沒問,他也去世四十多年了。
這樣一數,我發現我的身邊人也是有故事的傳奇人物。比如,我的堂舅說的他參加1953年的東山保衛戰,這是他駐防福建時參加的,被稱作“國共兩黨最后一場酷烈戰爭”。我原以為,全國都解放4年了,跟國民黨還打仗?我堂舅說,打啊,他親自參加了。
東山保衛戰發生于1953年7月16日,當時國民黨軍隊出動軍艦13艘,兵力1.3萬人,在飛機、坦克的掩護下和傘兵部隊的配合下,叫囂要在四至八小時之內占領福建省東山島,我駐島部隊以一當十痛擊來犯之敵,經過激烈戰斗,共殲敵3379人,擊落敵機兩架,擊毀坦克兩輛,繳獲大量軍用裝備。對這些信息,我的當班長的堂舅當時是肯定不知道的,他就負責往前沖,但他的感受是真實的。他說:“這次戰斗中,我們三天三夜就喝了一壺水,頭一天吃不上飯還能堅持住,第二天肚子燒得辣熱,第三天連嗓子都干得沒味了。”這有多難受,我們常人是無法體味的。但是他們挺過來了。
我敬佩軍人,他們在祖國和人民最需要的時候總是挺身而出,沖在最前面。我很幸運地,在我的親戚里找到了軍人的身影,我的身邊也就有了英雄氣息,有了傳奇。比如,叫建軍的表哥楊術澤,我再見他,就會有更多的話題,關于我堂舅的,關于英雄的,關于戰爭的。跟我的前輩比起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輕微的,所有的困難都是不值一提的。我要記住他們,從他們身上汲取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