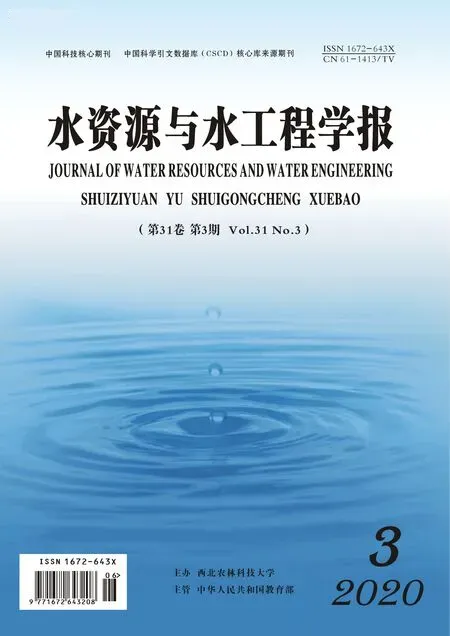岷沱江流域徑流對氣候和土地利用變化的響應
聶 超,倪福全,鄧 玉,馬 捷,張 洋
(四川農業大學 水利水電學院,四川 雅安 625014)
1 研究背景
如今,流域水文循環及水資源研究已成為水科學發展的熱點方向[1-4],而影響流域水文循環和水資源的因子主要有氣候和土地利用方式的變化[5-6]。氣候和土地利用變化在很大程度上交互影響地表徑流的時空演變[7-8],模擬和預測兩者對流域徑流的水文響應,對保護流域水生態、治理流域水環境十分必要。
目前,國內對氣候和土地利用變化引起的水文效應綜合研究較為廣泛,研究主要集中在長江、黃河、海河、黑河等流域[9-12]。例如,馮暢等[13]、黃鋒華等[14]、林嫻等[15]分別在漣水河、北江、武江流域研究了氣候和土地利用變化對徑流的影響,并取得了較好的研究結果。這些研究大部分都將各自研究流域作為一個整體,沒有考慮流域的空間異質性,不能確切地描述出徑流對氣候和土地利用變化的響應情況,而流域徑流的空間變化對水文循環及水資源研究尤為重要[16],因此,有必要將流域劃分為多個分區研究氣候和土地利用變化對徑流的影響。
岷沱江流域是四川省成都平原經濟區、川西北生態經濟區、川南經濟區等主要經濟區的重要水源[17],水生態環境條件十分復雜。“十四五”期間,隨著岷沱江流域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農業現代化、城鎮規模化的不斷推進以及氣候的區域性變化,岷沱江流域水資源供需矛盾必將日益加劇,水資源、水生態承載力、水環境容量作為剛性約束而產生的諸多水問題必將日益凸現[18-19]。因此,積極探究岷沱江流域徑流對氣候和土地利用變化的響應十分迫切。為了辨析岷沱江流域關鍵生態水文過程,建立適合復雜條件的分布式流域生態水文模型,定量評估氣候及土地利用變化對徑流的影響,本研究以岷沱江流域為研究區,構建SWAT模型,探討模型在研究區的適用性,并將岷沱江流域劃分為青衣江、大渡河、岷江和沱江4個子流域,定量分析各子流域的徑流對氣候與土地利用變化的響應規律,對岷沱江流域內“十四五”水資源優化配置、水生態保護、水環境治理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和現實意義。
2 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2.1 研究區概況
岷沱江是長江上游的一級支流,為四川盆地腹部區重要水系,岷沱江流域介于99°~106°E、28°~34°N,面積16.30×104km2。其中,岷江發源于岷山,流經阿壩州、成都、眉山、樂山、宜賓等地,在宜賓市城區匯入長江,流域面積4.6×104km2(不含大渡河、青衣江),長735 km,多年平均流量600 m3/s,多年平均水資源量189×108m3;岷江主要支流為大渡河和青衣江,大渡河發源于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內阿尼瑪卿山脈的果洛山南麓,東行至蕭公嘴與松潘流來的岷江干流相匯,長1 074 km,流域面積7.72×104km2(不含青衣江),多年平均流量1 490 m3/s,多年平均水資源量459.17×108m3;青衣江發源于邛崍山脈巴朗山與夾金山之間的蜀西營,在樂山市水口鄉草鞋渡注入大渡河,距大渡河入岷江口僅7 km,長285.2 km,流域面積1.28×104km2,多年平均流量499 m3/s,多年平均水資源量157.25×108m3;沱江發源于四川西北部九頂山區域,經德陽、資陽、內江、自貢、瀘州等地,于瀘州市城區匯入長江[20],流域面積為2.78×104km2,干流長634 km,多年平均流量454 m3/s,多年平均水資源量143×108m3。
岷沱江流域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夏季高溫多雨,冬季溫和少雨,多年平均氣溫約14℃,多年平均降雨量約900 mm,汛期(5-9月)雨量約占全年雨量80%,土地利用類型以耕地、林地和草地為主,流域人口、城市多聚集于岷江中下游和沱江流域。岷沱江流域水系、子流域及監測站點分布見圖1。

圖1 岷沱江流域水系、子流域及監測站點分布
2.2 數據來源
本研究采用全球30 m分辨率DEM數據集、1980和2015年土地利用數據以及2010年土壤數據,氣象數據來自研究區12個標準氣象站點1979-2014年的逐日氣象數據(降雨、日最高氣溫、日最低氣溫、風速、相對濕度、日照時數、太陽輻射),水文數據來自研究區7個主要水文監測站,其中,岷江干流水文監測站分別為沙壩站、紫坪鋪站、高場站;岷江支流青衣江水文監測站為夾江水文站;岷江支流大渡河水文監測站分別為瀘定站、石棉站;沱江干流水文站為瀘州站(見圖1)。數據來源見表1。

表1 數據來源及特征
3 研究方法
3.1 SWAT模型的建立及校準與驗證
本研究采用SWAT模型,根據收集的土壤數據、氣象數據分別建立土壤數據庫、氣象數據庫,并根據研究區DEM生成流域河網水系、劃分符合模型要求的子流域,再利用土地利用數據、土壤數據劃分水文響應單元(hydrologic research units,HRUs),進而構建岷沱江流域的SWAT模型。
利用SWAT-CUP,基于序列不確定性擬合算法(sequential uncertainty fitting algorithm,SUFI-2)對SWAT模型進行校準和驗證。選取研究區7個主要水文站點的實測月徑流數據用于模型的校準與驗證,并選用決定系數R2和效率系數NSE[2-3]來衡量模型模擬值與實測值的擬合度。
3.2 影響因子變化分析
3.2.1 氣象因子變化分析 采用 Mann-Kendall非參數統計方法及線性趨勢法分別對1979-2014年的降雨和氣溫氣象數據進行突變和趨勢檢驗[21],以分析研究區各氣象因子的變化情況。
3.2.2 土地利用變化分析 土地利用轉移矩陣能反映研究區某一時段初期和末期各地類的面積變化趨勢以及相互轉化的動態過程[22],因此,利用土地利用轉移矩陣分析1980-2015年土地利用變化特征,通用形式為:
(1)
式中:Sij為轉移前的第i類土地利用轉移后的第j類土地利用的面積,hm2;i和j分別為轉移前和轉移后的土地利用類型(i、j=1,2,…,n);n為轉移前后的土地利用類型數。
3.3 情景設置
3.3.1 氣候和土地利用變化共同影響下的徑流模擬情景 為了區分氣候和土地利用變化對徑流的貢獻大小,結合現有資料和岷沱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情況,選取1980、2015年土地利用數據和1981-2014年氣象數據(1979-1980年作為模型運行的預熱期)為基礎,通過將各時段的土地利用和氣象數據相互交叉設計出情景[23],詳細情景設置見表2。

表2 綜合模擬情景設置
3.3.2 氣候變化情景 為了探討氣候變化對岷沱江流域水文特征的影響,以2015年土地利用和1981-2014年氣象數據為基準期,在未來氣候變化的預估范圍內,設定氣溫不變,降雨量±10%、±20%情景以及降雨量不變,氣溫+1.5℃、+2.0℃情景[24],具體設置情況見表3。

表3 氣候變化情景設置
3.3.3 土地利用變化情景 為了探討土地利用變化對水文特征的影響,以2015年土地利用數據和1981-2014年氣象數據為基準,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嚴禁在坡度25°以上的耕地進行農耕操作,必須全部退耕還林,對于坡度在15°~25°之間的耕地,采取保護措施,可適當耕作。考慮研究區土地利用類型主要為耕地、林地、草地,設置3種情景,即在保持其余土地利用類型不變的情況下,分別將研究區坡度25°以上耕地轉為林地、坡度15°~25°之間的耕地轉為草地以及將研究區全部林地轉為草地[25]。具體情況見表4。

表4 土地利用變化情景設置
4 結果與分析
基于ARCGIS加載整理好的研究區DEM數據,參照流域實際河網情況,將流域劃分為89個子流域,載入處理好的土地利用數據、土壤數據,設定合理的土地利用類型面積閾值(5%)和土壤類型面積閾值(5%),進而將研究區劃分為1929個HRUs,隨后加載氣象數據,進行模型的運行以及參數的校準與驗證。
4.1 模型的校準與驗證
在岷沱江流域2015年土地利用情況下,基于SUFI-2算法選用岷沱江流域7個水文監測站的月徑流數據進行SWAT模型的校準和驗證,由于已有的各水文監測站實測徑流資料年限不同,致使各站點的校準和驗證期有一定差異,但不影響校準和驗證的準確性。根據水文監測站實測數據進行參數敏感性分析,選取敏感性強的參數進行調參校準,具體見表5。

表5 SWAT模型敏感性參數及其率定
本研究選用R2和NSE來衡量模擬值與實測值的擬合度,一般認為R2>0.7、NSE>0.6時模型的擬合精度令人滿意[26-27]。表6為模型校準及驗證結果,由表6可知,經模型參數校準和驗證后,研究區7個水文監測站SWAT 月徑流模擬效果較好,各個站點的R2和NSE均高于模型評價標準,表明SWAT 模型在岷沱江流域徑流模擬中具有較好的適用性。流域出水口水文監測站高場站(GC)和瀘州站(LZ)的月徑流模擬值與實測值的對比情況見圖2、3,由圖2、3可以看出,兩個站點月徑流模擬值與實測值基本吻合,差異較小,說明模型模擬精度較高,能夠使用模型模擬值代替實測值。

圖2 1982-2013年高場站月徑流量模擬結果

表6 模型校準及驗證情況結果
4.2 影響因子變化趨勢
4.2.1 氣象因子變化趨勢 本研究中氣象因子主要考慮平均氣溫和降雨量。圖4為1981-2014年研究區年平均氣溫和降雨量的M-K突變檢驗圖,根據M-K突變檢驗結果,曲線UF和UB的交點為平均氣溫和降雨量的突變點。由圖4可見,年平均氣溫和年降雨量的UF和UB曲線均在1995年相交,且位于顯著水平置信線(±1.96)之內,通過95%置信度檢驗,表明年平均氣溫和年降雨量在1995年發生突變,其主要原因是1995年后大量修建水電站[28],對氣溫和降雨量產生影響,從而引起突變。

圖4 1981-2014年研究區氣象因子M-K突變檢驗
圖5為1981-2014年研究區年均氣溫和降雨量變化趨勢。由圖5可知:(1)研究區1981-2014年平均氣溫呈整體波動升高的趨勢,1981-2014年間平均氣溫升高了約0.6℃,1998年年均氣溫最高,為14.14℃,1992年最低,為12.67℃,1981-2014年平均氣溫為13.33℃,年平均氣溫與年份之間的線性相關系數為0.47,通過95%顯著性檢驗(T=2.93>T(0.05/2)=1.64),表明年平均氣溫的升高趨勢是顯著的;(2)研究區1981-2014年年均降雨量呈整體波動減小趨勢,34 a間平均降雨量減少了約51 mm,1990年降雨量最大,年降雨量1 073.18 mm,2006年降雨量最小,年降雨量767.19 mm,1981-2014年平均降雨量為911.19 mm,年平均降雨與年份之間的線性相關系數為0.21,降雨量減小趨勢比較緩慢。

圖5 1981-2014年研究區年均氣溫和降雨量變化趨勢 圖6 1980和2015年研究區土地利用類型空間分布
4.2.2 土地利用變化趨勢 按照SWAT 模型要求,將研究區土地利用類型分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設用地、未利用土地6類,圖6為分類過后的研究區1980和2015年土地利用分布圖。

圖3 2011-2014年瀘州站月徑流量模擬結果
由圖6可以看出,研究區以耕地、林地、草地為主,耕地主要集中在沱江和岷江中下游,林地和草地大部分位于大渡河和岷江上游。
表7為1980-2015年研究區土地利用變化轉移矩陣,它能反映出研究區1980和2015年各土地利用類型組成以及相互轉化情況。
由表7可以得出,耕地轉出面積為9 052 hm2,主要轉化為林地和建設用地,轉化面積分別為4 847和2 087 hm2,分別占耕地轉出面積的53.55%和23.06%;林地轉出面積為17 948 hm2,主要轉化為草地和耕地,轉化面積分別為12 655 hm2和4 661 hm2,分別占林地轉出面積的70.51%和25.97%。草地轉出面積為14 505 hm2,主要轉化為林地,轉化面積分別為12 511 hm2,占林地轉出面積的86.25%。總體來說,2015年較1980年耕地減少了1.01%,林地減少了0.10%,草地增加了0.47%,主要是因為2003年前大量砍伐植被,林地被大肆破壞,林地被轉化為耕地、草地等其他土地利用類型,2003年后退耕還林、植樹造林等政策地實施,耕地、草地等轉為林地,林地面積有所增加。

表7 1980-2015年研究區土地利用變化轉移矩陣 hm2
4.3 情景模擬分析
4.3.1 氣候和土地利用類型共同影響下的徑流模擬情景 表8為研究區各子流域在氣候和土地利用變化共同作用下的徑流變化以及氣候和土地利用變化分別對徑流變化的貢獻量情況。
由表8可見:(1)基于情景2和情景4的氣候變化引起了研究區徑流量減少,青衣江、大渡河、岷江、沱江分別減少26.04、86.49、50.01、42.49 m3/s,其中大渡河受氣候變化影響程度最大,徑流量減少最多;(2)基于情景3,情景4的土地利用變化也引起了研究區徑流量減少,減少程度較輕,青衣江、大渡河、岷江、沱江分別減少0.42、0.66、0.75、0.91 m3/s。可見,研究時段內研究區氣候變化對徑流的影響強度較土地利用變化大,氣候變化對研究區徑流變化起主導作用。(3)情景4與情景1比較可見,氣候和土地利用變化的共同作用引起研究區徑流量減小,青衣江、大渡河、岷江、沱江分別減少26.46、87.15、50.76、43.40 m3/s,減少的徑流量分別占研究區各子流域多年平均流量的5.3%、5.8%、8.5%、9.5%。目前,岷江、沱江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分別高達55%和40%,青衣江、大渡河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分別僅為15.7%和4.4%。顯然,在氣候變化和土地利用的共同影響下,岷江、沱江水資源剛性約束力將進一步增大,從青衣江、大渡河向岷江、沱江引調水資源是必要的。根據目前規劃,通過“引大青濟岷”工程將從青衣江、大渡河引調水資源25.9×108m3/a、平均流量82 m3/s進入岷江、沱江。因此,即使考慮未來氣候變化和土地利用的共同影響,青衣江、大渡河引調水后其開發利用率僅平均增加4.4%,分別增至20.1%和8.8%,亦遠小于目前岷江、沱江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因此,從青衣江、大渡河向岷江、沱江引調水資源是可行的。

表8 研究區各子流域在氣候和土地利用類型共同影響情景的模擬結果
4.3.2 氣候變化情景 表9為氣溫或降雨量變化情況下研究區各子流域徑流變化情況。
表9模擬結果表明:(1)保持氣溫不變,當降雨量增加10%、20%,研究區徑流量均增加,降雨量增加20%時引起徑流量增加較大。當降雨量減少10%、20%時,年均徑流量均呈減少趨勢,且降雨量減少20%情況下徑流量減少趨勢更明顯,可見徑流量變化與降雨量變化呈正比,降雨量直接影響研究區產流;保持降雨量不變,當氣溫增加1.5℃、2.0℃時,研究區徑流量均減少,在氣溫增加2.0℃時,徑流量減少幅度較大。氣溫升高,導致研究區潛在蒸散發增加,徑流量減少,且氣溫升幅越大,蒸散發增幅也越大,而徑流量越小,可見徑流量變化與氣溫變化呈反比。這一結論與馮暢等[13]、李帥等[25]的研究結果一致,即流域內徑流量與降雨量呈正相關關系,與氣溫成負相關關系。(2)在氣候變化情景下,研究區內大渡河徑流量變化最明顯,青衣江徑流變化較緩和,降雨量增加情景下大渡河徑流量增加最大,降雨量減少或氣溫升高情景下,青衣江徑流量減少最小。在通過“引大青濟岷”工程從青衣江、大渡河將水資源調入岷江、沱江過程中,豐水年主要從大渡河引水至岷江和沱江,枯水年主要從青衣江引水至岷江和沱江。

表9 研究區各子流域氣候變化情景模擬結果
4.3.3 土地利用變化情景 基于1981-2014年氣象數據,以2015年土地利用數據為基礎,土地利用類型變化情景下的研究區各子流域的年均徑流量變化情況見表10。
由表10可看出:(1)與基準期相比,情景11將研究區坡度25°以上耕地轉化為林地,導致研究區徑流量略有減少,青衣江、大渡河、岷江、沱江分別減少0.04%、0.12%、0.09%、0.05%,可見林地相對于耕地具有截留作用,主要是由于耕地變為林地,植被增加,流域蒸散發加強,綠水量增加,藍水量必然減少,因此徑流量減少,而研究區坡度25°以上耕地主要集中在大渡河流域,因此研究區內大渡河徑流量減少最大;(2)情景12將研究區坡度15°~25°之間的耕地轉化為草地,也導致研究區徑流量減少,青衣江、大渡河、岷江、沱江徑流量分別減少0.26%、0.19%、0.30%、0.17%,可見草地相對于耕地也具有截流作用。主要原因是相對于耕地而言,草地提高了土壤的涵養水源能力,減少了產匯流,研究區內岷江徑流量減少最大,主要是由研究區坡度15~25°之間的耕地主要集中在岷江流域引起的;(3)情景13將研究區全部林地轉化為草地,導致研究區青衣江、大渡河、岷江、沱江徑流量分別增加0.48%、1.81%、1.11%、0.43%,可見草地相對于林地具有增流作用,這種增流作用是由林地的冠層截留以及林地蒸散發能力大于草地而引起,其中,大渡河增流最大,主要原因是研究區林地主要分布在大渡河流域。這與祖拜代·木依布拉等[23]、竇小東等[29]的研究結果一致,林地相對于耕地具有截留作用,草地相對于耕地也具有截流作用,而草地相對于林地具有增流作用。

表10 研究區各子流域土地利用類型變化情景模擬結果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以岷沱江流域為研究區,基于SWAT模型,利用情景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了研究區土地利用和氣候變化對徑流量的影響,結果表明:
(1)SWAT模型在岷沱江流域適用性較好,可用模型模擬流域徑流。
(2)1981-2014年間岷沱江流域內的氣候和土地利用變化均引起徑流量減少,氣候和土地利用變化分別對流域內大渡河和沱江徑流量影響最大。其中,氣候變化對徑流量的影響程度較土地利用變化強,岷沱江流域徑流量變化由氣候變化主導。
(3)以1981-2014年氣象數據為基礎,僅考慮氣候變化,岷沱江流域徑流量與降雨量呈正相關,與氣溫呈負相關。氣候變化對流域內大渡河徑流量影響最大。
(4)僅考慮土地利用變化,將岷沱江流域坡度25°以上耕地轉化為林地和坡度15~25°之間的耕地轉化為草地,均會引起流域徑流量減少,分別對流域內大渡河和岷江徑流量影響最大,而將流域全部林地轉化為草地則會導致流域徑流量增加,大渡河徑流量增加最大。林地和草地相對于耕地而言有截流作用,草地相對于林地有增流作用。
5.2 建議
氣候和土地利用變化情景下,從青衣江、大渡河流域向岷江、沱江流域引調水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針對研究區岷江和沱江流域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分別達到55%和40%,水資源生態環境壓力大等問題,通過“引大青濟岷”水系連通工程,連接大渡河、青衣江與岷江、沱江,豐水年主要從大渡河引水至岷江和沱江,枯水年主要從青衣江引水至岷江和沱江,可從根本上解決岷江和沱江生態環境用水不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