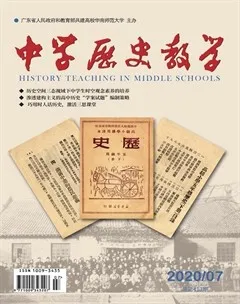基于史料實證核心素養的“二重證據法”的運用
陳兵

一、“二重證據法”在教學過程中的必要性
歷史學科核心素養中的史料實證是指對獲取的史料進行辨析,并運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現歷史真實的態度與方法。[1]要言之,高中歷史學習需要以扎實可靠的史料作為還原史實的媒介。
郭沫若曾說:“無論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鑒別是最必要的基礎階段。材料不夠固然大成問題,而材料的真偽或時代性如未規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還要更加危險。”[2]有鑒于此,史料實證核心素養特別強調對史料“去偽存真”。中學歷史教學過程中卻往往出現“史料/證據”流于“技巧化”與“機械化”、“只見史料,不見證據”的情況[3],因而精擇史料呈現在教學中顯得尤為必要。
對于中國古代史而言,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補正紙上材料——能夠克服史料片面性、主觀性的弊病,是檢驗史料是否可以作為證據的有效方法之一。 [4]下面試以“玄武門之變”的教學為例,略談教學過程中基于史料實證核心素養的“二重證據法”的運用。
二、“二重證據法”在教學中的運用
玄武門之變是唐初歷史的轉折點,但因涉及到皇位的非正常更迭,官方正史對此事的記載存在諸多隱晦。隨著出土文獻的刊布,玄武門之變的另一個面向也浮出水面。傳統官方正史是否仍可作為還原該事件的主要依據?它與出土文獻的關系應如何處理?基于此,我們圍繞著“二重證據法”,將玄武門之變的教學內容分解為四個環節:(一)“成王敗寇”的歷史書寫——傳統官方正史的檢討;(二)當事人的“證言”——出土碑志對官方正史的補正;(三)旁觀者的“記憶”——《唐太宗入冥記》對官方正史的補正;(四)歷史反思——體悟歷史進程的復雜性。在每個教學環節,設計若干層次遞進、指向史料實證核心素養的關鍵問題,有效引導學生。
導入部分:
大郎、二郎在路,一同義士,等其甘苦,齊其休息。……至西河城下,大郎、二郎不甲,親往喻之。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1大業十三年六月甲申條
問題1:義兵初起時,西河一役主帥為誰?表現如何?
設計意圖:我們平時接觸到的大部分文史類讀物甚至史籍,凡涉及李唐創業歷程時,李世民的形象往往英明神武,李淵、李建成的形象則是昏聵無能。溫大雅作為李唐開國的見證者,在《大唐創業起居注》中記載了迥異于正史的李建成形象。這則史料帶來了認知沖擊,進而激發學生深入探討的興趣。
教學環節一:“成王敗寇”的歷史書寫——傳統官方正史的檢討
檢討正史的理由:對于玄武門之變著墨較多的傳統官方正史《舊唐書》,常被用來研究這段隱晦的歷史,但它并非令人信服的“證據”。劉劍橫曾說:“史料的真實與虛偽,在常人所最信任的部分,其偽和誤更多……因為在常人所最注意的部分,亦為當時的統治者或其學者為其自身利益而要加以做作以至捏造的。”[5]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太宗將左右九人至玄武門自衛。……建成、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即回馬,將東歸宮府。……俄而東宮及齊府精兵二千人結陣馳攻玄武門,守門兵仗拒之,不得入……太宗左右數百騎來赴難,建成等兵遂敗散。
——《舊唐書》卷64《隱太子傳》
問題2:《舊唐書·隱太子傳》(下簡稱“舊傳”)關于事變當日建成、元吉與世民的行為記載有無矛盾之處?
設計意圖:舊傳關于玄武門之變的記載頗多抵牾,一方面說李世民帶九名隨從入宮是自衛,變亂發生后秦王府人馬又趕來救援,似乎是太子一系突然發難;另一方面又說太子、齊王到了臨湖殿,發現情勢有異立即勒馬回府,這又暗示他們對宮變并不知情。將這段史料呈現給學生,學生會從字里行間發現史事邏輯的錯亂。
學生發現了可疑之處,接下來就要解釋為什么可疑,這就要從史源學入手。《舊唐書》的史料來源主要為“從高祖到武宗的實錄,從高祖到肅宗乾元時的紀傳體國史,從高祖到憲宗元和時的編年體《唐歷》”[6]。也就是說,舊傳玄武門之變記載的源頭在唐實錄和起居注。
貞觀九年十月,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曰:“今欲親自觀覽,用知得失。……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
——《唐會要》卷63《使館雜錄上》
(貞觀十三年)太宗問曰:“……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貞觀政要》卷7《文史第二十八》
(貞觀十四年)太宗曰:“……今欲自看國史者……卿可撰録進來。” ……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貞觀政要》卷7《文史第二十八》
問題3:以上三則材料反映了太宗什么意愿?最終結果如何?
設計意圖:太宗再三要求翻看起居注,終達目的,對于玄武門之變的記載,頗多微詞,并命令房玄齡等人“改削”起居注。通過史源學的分析,學生能夠了解到傳統官方正史史料來源有被篡改的可能性。在懷疑精神的基礎上,揭示孤證不立的原則,引導學生另尋它證。
教學環節二:當事人的“證言”——出土碑志對官方正史的補正
使用出土碑志補正官方正史的理由:碑志的史料來源是成于私人之手的家傳、譜牒、行狀,雖不免有隱惡溢美之詞,但內容較少受到官方的干涉。特別是墓志,因埋于地下鮮為人見,往往保存了正史諱言的細節。
(武德)七年,封太宗令追入京……令于北門領健兒長上……趨奉藩朝……九年六月四日,令總北門之寄。
——《常何碑》
尋(秦王)奉教留住,除右二府護軍。九年夏末,二兇作亂,太宗受詔,宣罰禁中。公任切爪牙,效勤心膂。
——《程知節墓志銘并序》
(武德)五年,授帳內旅帥。于時儲闈階亂……公奉睿略于小堂……二兇式殄,諒有力焉。
——《鄭仁泰墓志銘并序》
武德五年,奉秦王教,追入幕府,即授右庫真。……二兇構逆,公特蒙驅使,委以腹心,奉敕被甲于嘉猷門宿衛。
——《安元壽墓志銘并序》
問題4:以上四人在玄武門之變前在哪里任職?在事變中發揮了什么作用?
問題5:根據《通鑒》以及《唐宮城圖》(見下圖),找出玄武門、嘉猷門以及臨湖之殿,并分析三者之間的聯系。
太極宮中凡有三海池,東海池在玄武門內之東,近凝云閣;北海池在玄武門內之西;又南有南海池,近咸池殿。
——《資治通鑒》卷191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上方泛舟海池”條
設計意圖:史料實證要求堅持全面運用史料的能力。四方碑志提供了一些不為正史所載的歷史細節——事變參與者進入秦王幕府的時間、所任職務以及在事變發生時所起到的作用(借助地圖呈現),將之與舊傳對比,能夠發現秦王集團之強大及事變中李世民的主動性。要言之,這部分內容借助碑志,用當事人的“證言”,將正史的“選擇性失憶”予以部分地恢復。
教學環節三:旁觀者的“記憶”——《唐太宗入冥記》對官方正史的補正
比照《唐太宗入冥記》的理由:敦煌文獻雖然以佛教典籍為主,但也包括公私文書、寫本書籍、典籍以及其他雜寫。《唐太宗入冥記》殘卷即是一例。這部小說成書于“武周代唐之初”,“是一篇在佛教果報掩護下譴責唐太宗的政治小說”[7]。這部小說成書時間距離事變發生時代近,處于擁唐政治氛圍比較淡薄的武周時期,且在民間廣泛傳播,它傳遞的信息極具參考價值。
催子玉奏曰:“二太子在來多時,頻通款狀,苦請追取陛下對直。稱訴冤屈,詞狀頗切,所以追到陛下對直。……陛下若入曹司,與二太子相見,怨家相逢,臣亦無門救得。……自出問頭云:“問大唐天子……為甚殺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宮?仰答!” ……(皇帝)把得問頭尋讀,悶悶不已,如杵中心,拋問頭在地,語子玉:“此問頭交朕爭答不得!”
——《唐太宗入冥記》
問題6:唐太宗為何會進入冥界?對于為何殺兄弟又做出怎樣的回應?
設計意圖:史料實證要求注意挖掘史料的社會背景含義和特定的微觀情境,上引《唐太宗入冥記》雖涉鬼神之說,但絕非空穴來風。小說往往是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這部分內容通過廣泛流傳于民間的小說,從同一時期旁觀者的“記憶”中復原部分歷史本相。
教學環節四:歷史反思——體悟歷史進程的復雜性
李唐開國,建成以嫡長子的身份居太子之位,而世民則以平定天下之功居秦王之位,一時間皇帝的“詔、敕”、太子的“令”、秦王的“教”并行于世,形成了一君兩儲三方的格局。這種多元政治格局也為玄武門之變埋下了禍根。本課利用“二重證據法”盡可能地還原玄武門之變的面貌,目的不在判定孰是孰非,而在于掌握辨析并批判運用史料的方法,進而體悟歷史進程的復雜性。
問題7:請同學們根據以上史料提供的信息,客觀論述玄武門之變。
學生:李唐建國之初,李建成作為儲君坐鎮中央,秦王李世民則作為天下兵馬元帥征討四方。在戰爭中,世民的身邊集聚了一批謀臣猛將,天下底定之時權勢已堪與太子比肩。朝堂之上,兩大集團的勢力互相角力,明爭暗斗。武德九年,黨派政治愈演愈烈,略處下風的李世民先發制人,在玄武門、嘉猷門安插親信,在臨湖殿預設埋伏,最終以兵變的形式襲殺了太子李建成及其黨羽。
三、“二重證據法”的教學效果
在“玄武門之變”的教學過程中,我們通過列舉與唐實錄同源的《舊唐書》、出土碑志、敦煌石室遺書,多角度地呈現了玄武門之變的面向。此法為教學過程中史料實證核心素養的落地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史料實證意識養成的路徑,其效果也是令人欣喜的。首先,通過閱讀多種類型的史料,學生能夠概括、凝練史料的不同維度信息,進而明確史料的立場。其次,通過多種史料的對比、勘驗,學生能夠對材料進行適當取舍。再次,通過對多種類型史料的辨析與批判,學生能夠體悟“孤證不立”內涵,從而逐漸養成“多重證據”相補證的意識。最后,通過各種史料信息的排比、歸納,學生能夠客觀地論述玄武門之變的始末,進而做到“了解之同情”的歷史書寫。
【注釋】
[1]教育部:《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2017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5頁。
[2]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2頁。
[3]陳冠華:《中學“史料/證據”教學的困局:以教師與課堂教學為中心的分析》,《清華歷史教學》(中國臺灣)2017年第25期,第7頁;陳新民:《“史料實證”素養的教學誤區與培育路徑》,《歷史教學》(上半月刊)2019年第6期,第55頁。
[4]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后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頁。
[5]劉劍橫:《歷史學ABC》,上海:ABC叢書社、世界書局,1930年,第62—63頁。
[6]黃永年:《唐史史料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6頁。
[7]卞孝萱:《唐人小說與政治》,廈門:鷺江出版社,2003年,第6、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