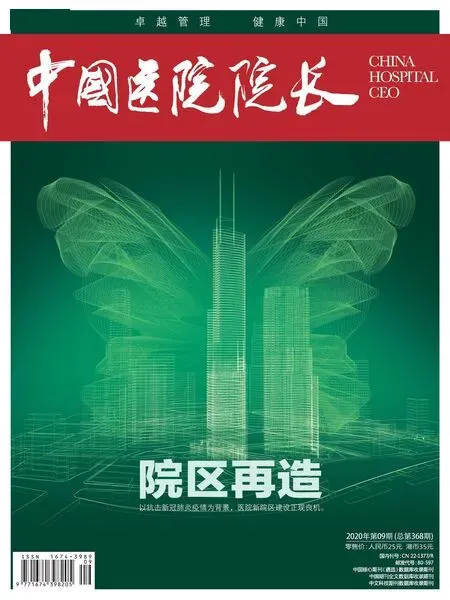我國分級診療秩序難形成的體制機制原因
分級診療未達制度改革初衷,與當前我國醫療衛生領域諸多體制機制問題相關。

實現合理的分級診療秩序,是新醫改以來中央著重要解決的醫改難題,形如國家衛生健康委主任馬曉偉所強調的,“分級診療制度實現之日,乃是我國醫療體制改革成功之時”。為把以大型醫療機構為中心的錯位“倒三角”醫療服務體系糾正為“正三角”,中央近年來不斷出臺多項分級診療相關政策。但就目前分級診療的改革效果來看,“倒三角”的醫療服務體系依然呈現固化趨勢。
2015年,我國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人次為77億人次,其中三級醫院、二級醫院、一級醫院和基層醫療機構的診療人次占比分別為19.48%、15.19%、2.72%和56.36%;而到2018年,總診療人次增長到83.1億人次,三級、二級、一級及基層醫療機構診療人次占比為20.82%、15.28%、2.65%和53.31%。
數據反映,現行醫療服務供給現狀與分級診療的制度改革導向相背離。分級診療“徒有其形,而未得其實”,三級醫院仍人滿為患、門庭若市,基層醫院門可羅雀、難以維持;存在“上轉容易、下轉難”現象;優勢醫療資源向大醫院集中,大醫院門診和住院服務發展失控,呈大規模化,甚至集團化發展之勢,產生“改革虹吸”現象明顯;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常見病、慢性病診療功能日漸弱化,醫療設備閑置和浪費嚴重。
而分級診療未達制度改革初衷,筆者認為,這與當前我國醫療衛生領域的諸多體制機制問題有關,總結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公立醫院改革存在“兩大一公”的體制性缺陷
我國合理的醫療服務體系建設和分級診療制度推進,與公立醫院改革是相互聯系和密不可分的兩部分,共同構成了醫療服務供給體制的核心要件。“新醫改”以來,雖然國家著力推動了縣級公立醫院、城市公立醫院改革,但公立醫院改革困境難以取得實質性突破,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國公立醫院改革存在“兩大一公”的體制性缺陷。“兩大一公”的體制性缺陷是計劃經濟行政管制和社會治理不足的結果,具體表征為:一是我國醫療服務的供給模式以大型公立醫院為中心,地方盲目擴大醫院規模和追求床位數量增長,而且絕大多數縣級公立醫院把控不住區域內的大病,導致近年異地轉診就醫人數增加明顯;二是醫療保險保大病理念與大型公立醫院的住院服務結算相關聯,導致80%以上醫保資金進入大醫院,擠壓了基層醫療機構的生存空間;三是把醫療衛生事業的公益性和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公益性相混淆,造成對公立醫院公益性問題的認識偏差,公立醫院不等于公益性醫院,不論是公立醫院還是私立醫院,都只是醫療服務提供的載體而非主體,姓“公”不等于提供了公益性醫療服務,也并非只有公立醫院才能提供公益性基本醫療服務。
這種體制性缺陷導致我國醫療資源供給產生“倒三角”型錯位結構,80%的醫療衛生資源集中在城市,其中80%又集中在大中型公立醫院。但從需求來看,絕大部分的醫療衛生服務需求集中在農村和基層,是“正三角”需求結構。
醫療供給的倒三角和醫療需求的正三角在現實層面的表現是全科醫生、專科醫生和醫學專家診療行為的倒置,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居民前往大醫院就診的行為慣性,加劇了患者的看病可及性和醫療負擔問題。而且這種以大型公立醫院為中心的醫療服務供給模式,導致了改革的“虹吸效應”,不同等級醫療機構之間不是分工協作關系,而是利益競爭關系,強化了其“圈資源”和壟斷能力,2013年以來,基層醫療機構診療量在逐年下降可看作是有力佐證。
“守門人”性質的基層首診制度須強化
實現分級診療的基礎在于如何堅固基層首診,也即“守門人”制度。基層首診能夠規范就醫秩序,促進不同醫療機構間的分工協作,引導醫療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國外實踐表明,越是醫療服務體系發達的國家越不能隨意就醫,凡是嚴格執行“守門人”制度的國家,基本上都形成了分工明確的就診網絡,其基層診所、社區醫院等初級衛生保健場所的醫療服務利用效率高,醫療機構間的分級診療秩序良好。
國家一直在強調“強基層”、實施家庭醫生簽約制度及目前推進的緊密型醫共體建設,但效果不佳的原因在于“守門人”制度缺乏足夠優質的“守門員”。“新醫改”至今,中央和地方財政投入幾萬億元對基層醫療機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醫療設備配置,但大量的全科醫生或家庭醫生缺口限制了首診制度的落實。按國際上每名全科醫生服務5000名居民的低限標準,截至目前,我國合格的全科醫生缺口仍達40萬名(《中國醫院院長》,2019)。而且當前對基層醫師“能上不能下”的人事管理體制、過低的薪酬分配制度,也不利于基層醫師隊伍的穩定和發展。此外,強化基層首診制,還需要國家開展同質性醫學教育改革,推進“收支兩條線”的財務管理和基本藥物目錄等制度改革。
沒有建立合理的異地就醫機制
異地轉診就醫是一項便民政策,滿足患者的優質醫療資源需求,解決分級診療的“最后一公里”問題。但當前的異地就醫缺乏合理的轉診機制引導,表現為無序就醫的“亂象”,導致其流動方向呈現單一地向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南京、武漢、杭州等城市聚集,其流動數量呈現數倍增長態勢。
2018年全國跨省異地就醫住院費用直接結算132萬人次,是2017年的6.3倍(國家醫保局,2019)。無序異地就醫不僅造成了報銷地醫保基金的支付壓力、弱化了當地醫療機構的診療能力,還增加了患者的看病負擔。因此,從異地就醫的人群界定、轉診備案、報銷比例、付費方式、監督管理等方面進行合理的機制建設迫在眉睫。
分級診療需要建立科學的分級付費機制
在基層就診方面,我國大多數地區,通過不同級別醫療機構醫保差異化支付政策,逐步拉開了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和大醫院的起付線和支付比例差距,以助推分級診療。但是這種差異化的付費政策效果并不明顯,沒有分級付費就不能實現分級診療,如何激勵大醫院釋放首診和慢病、如何夯實基層醫療機構服務能力,需要建立科學的分級付費機制。
分級付費不僅要對當前的醫療服務類型分類,針對健康管理-慢病管理-門診服務-住院醫療-康復治療-長期護理-安寧療護等不同屬性的醫護服務,建立多元復合式支付模式,還要對功能定位不同的醫療機構進行激勵償付,綜合和專科醫院建立基于總額預算管理下的DRG-PPS付費機制,把控住院的大病診療質量,而基層醫療機構建立基于健康促進、慢病管理等績效付費機制,提升常見病治療和健康管理效果。
另外,建立促進分級診療的分級付費機制,也需要落實財政對醫療機構的合理補償責任;建立健康檔案、慢病管理、門診治療和住院治療一體化的個人健康信息和診療信息系統;針對家庭醫生、門診醫師、住院醫師和臨床專家,建立基層醫療機構非臨床績效評估、醫院臨床療效評估機制;逐步建立“同城同病同質同價”的醫療服務定價機制等配套機制。
綜上而言,這些體制機制層面存在的現實問題阻礙了“基層首診、雙向轉診、急慢分治、上下聯動”的合理分級診療秩序形成。因此,再構我國分級診療服務體系,著重推進公立醫院改革、強化基層首診制、規范異地就醫、實施分級付費,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