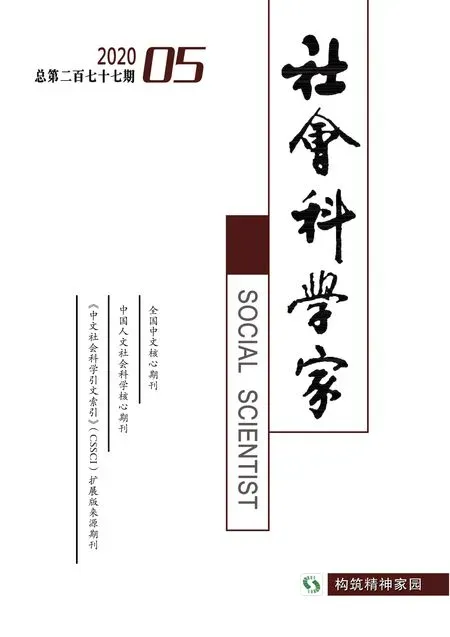審美人類學:構建當代美學與藝術批評新體系
王 杰,孟凡君
(浙江大學 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浙江 杭州 310027)
一、提出審美人類學的現實語境
在文化經濟時代,消費化[1]、網絡化[2]、全球化[3]、娛樂化[4]已經逐漸成為當今社會的重要問題域。它們給時代發展帶來了嶄新內容,同時也如一把雙刃劍為現實生活和學術研究帶來了新的挑戰。這四重變奏式時代主題介入現實生活環境,也影響著學術發展的動態,挑戰著每個學科的發展定力與應對能力。美學也處于其中,面臨著當今時代提供的機遇,也面臨著它們帶來的危機。
消費化將美物與藝術以商品的面貌置入千家萬戶的日常生活中,泛文化物象成為美學研究的基本對象,美學的對象不再局限在對精英藝術的研究和小型社會文化的研究,而是擴大到廣闊生活的各個領域;網絡化的知識傳播方式與審美情感傳遞方式,將美學從傳統的哲學性人文學科,轉向跨學科方法為主體的包含著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甚至包含自然科學的復雜性學科;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相互博弈的過程中,具有當下性的人民大眾的審美經驗仍然是審美認知情感生成的動力源,地方性審美經驗與審美情感融合體相互碰撞,體現了主導地球村民審美情感發展的諸多規律性傾向;娛樂化的日常審美生活給勞動者們套上了新的枷鎖,地球村民們不僅逐漸失去了打破枷鎖的能力,而且沉溺其中,重申“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與平等發展對于當代世界與中國美學研究而言,刻不容緩,與此相對應,悲劇人文主義的研究應該引起中國美學和藝術批評領域的高度重視。
審美人類學的理念和方法有助于美學應對新時代的四重難題帶來的挑戰。具體說來,審美人類學以哲學人類學的觀念和文化人類學的方法為學理依據,以地方性審美經驗為研究對象,在具體的歷史和文化語境中,通過研究具體的審美制度(機制),在地方性審美經驗中找到從現實通向未來的途徑和機制。
二、分析審美人類學的關鍵概念
現代意義上的人類學誕生已經有150多年的歷史。與古典人類學相比,現代意義上的人類學的誕生有著本質性的理念異趣和標志性的方法論差異。下面我們結合現代與古典人類學的理念異趣和方法論差異,介紹審美人類學在構建美學與藝術批評新體系要面對的核心問題。這些核心問題是現代人類學與古典人類學體現在美學領域的區別特征。現代人類學的特色標志性方法更加追求客觀的科學化理念和田野實證操作。在田野調查和語境分析中,確認人類精神的物質基礎及其社會歷史風俗傳統,即較為深入地描摹地方性審美經驗和審美制度。
然而,在精神理念上,審美人類學同時又在某種意義上復歸了古典人類學的價值導向和行動方式,即古典人類學的人文主義理想。在時間和空間域限里,審美人類學是同時指向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對于過去的總結和紀念,對于烏托邦理想的崇敬與追求,訴諸當下的行動方式,既是傳承亦是革新。總體來說,審美人類學以實證材料為基礎,價值導向則是以“人”為中心的人文主義立場。
在討論審美人類學的有關問題之前,有必要對審美人類學的核心問題和關鍵概念作出界定和說明。
1.田野:地方性經驗與中心文化交流的場域
田野調查是現代人類學的標志性方法論。然而,人類學家們迄今還沒有在本體論意義上給出“田野”本身的內涵。“田野是什么?”是人類學和審美人類學的第一個問題。對于人類學及審美人類學之所以成立的第一問題的前提性批判,不僅必要而且無法回避。現代人類學一般傾向于把“田野”作為不言自明的自然而然的存在空間,即“離我遠去”的進行田野調查的地點。從日常經驗角度看,這固然沒有什么原則性錯誤。然而,從建立和完善學科體系角度看,如果“田野”未經過本體化的建構和辯證化的解析,未在最廣泛意義上對它進行共相的歸納總結,未在最特殊的意義上對它進行殊相的屬性分析,則人類學或審美人類學永遠無法獲得學科化體系建設的第一塊穩定的基石,顯然這是無法接受的事情。
基于以往田野調查的空間場域,我們可以給“田野”做出封閉性和開放性兩種定義。封閉性定義:西方人類學家借助“地理大發現”,蜂擁到了大洋洲、美洲、非洲,在這里看到了讓自己驚詫的人類生活方式,他們認為這些區域都是人類學工作的田野;我國的人類學家,從政治經濟中心城市跋涉到東北、西南、西北以及相對偏遠的農村等地域,在這里發現了少數民族偏遠地區的原始生活方式以及古典生活方式的遺存,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和偏遠農村就是田野。從傳統的人類學范疇來看,“田野”是與西方工業文明相對應的散布于各個大洲的原始土著生活空間,是與我國現代化進程發展相對應的少數民族邊疆和偏遠村落的古典生活空間。開放性定義:從當前和未來人類學發展趨勢來看,“田野”概念不是封閉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含義之外,相對于文明的中心地帶,邊緣區域、邊緣空間、邊緣群體的生活場域都可以看作是廣闊的“田野”。比如,城市中的特殊群體空間也屬于人類學工作的田野。《我不是藥神》中白血病患者的城市生活空間就構成某種意義上的“田野”。再如,原來的中心地帶隨著社會發展變遷,滑向邊緣的狀況,也造成了“田野”在空間上的流動性與變遷性。
兩種定義都屬于形而下的經驗歸納,我們需要更進一步從形而上層面進行概念化言說。田野是產生人類原初經驗的第一空間場域,具有原生性、樸素性和相對性,同時還是地方性經驗和中心文化交流的場域。所有的田野調查莫不以獲得原初性經驗為鵠的,原初經驗在感知覺、認知情感方面具有最鮮活的現場感、素樸感。
在地方性經驗與中心文化的辯證關系分析中,我們逐漸剝揭出“田野”的形貌。在原生態的空間中,我們常常認為獲得的地方性經驗僅僅是關于偏遠之地的知識、情感及風俗制度等,實質上其中包含著中心文化的交流與滲透。這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理解:一方面,地方性經驗并非被絕對隔離的文化絕緣體,它是中心文化蕩漾到邊緣引起的漣漪,漣漪撞擊到圍堤返回中央又引起了新的波紋,這便是地方性經驗與中心文化之間的循環互動。例如,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所描述的“長老政治”絕不是單純的封建農村的原生文化,而是在儒家大一統文化傳承方式下,“為政以德”和“為民父母”觀念在農村政治權力的具體表現形態。[5]在中心文化區和鄉村場域上發生的文化觀念,仿佛兩粒品種相同的思想種子,一粒種在廟堂,一粒種在郊野,環境不同,相貌故而略存差異。我們在進行田野調查的時候也發現了這個情況。在廣西壯族自治區陽朔縣福利鎮的一次文化會演中,同時包含了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商品經濟的表現形式,當然還有主流的地域性文化經驗也就是壯族的民間故事文藝演出作為主要載體。民間故事的忠孝觀念與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念在這樣一個民間演出過程中十分自然地融合到了一起。[6]另一方面,對于歐美文化來說,非洲、南美洲等當地土著文化是完全陌生的,甚至可以說絕緣的。這些地方性經驗看似絕緣于世界主流文化,實際上當它們被看見、被記錄的時候,已經成為中心主流文化知識的參照系與構成部分,也就是說,地方性是相對于中心化、全球化而存在的,沒有中心化、全球化也就無所謂地方性。例如,接觸律和相似律看似野性思維的基本方式,換個角度,如果沒有科學化的實驗思維、現代化的分類思維進行比照,怎么能總結出野性思維的規律呢?所以地方性經驗與中心文化相伴相生,共同在“田野”上交流互動。
可見田野雖是富含原生性、樸素性的人類經驗,卻是地方性經驗和中心文化交流的場域。在這種相對流動性的場域文化中,田野不是一成不變的封閉空間,而是流動的空間坐標系。從學理上看,有必要獲得當代意義上的富有流動性的“田野”。田野不僅是第三世界的美洲、非洲、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封閉荒疏的古典村落,它還存在于我們的現代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比如社區、醫院、學校、電影院、商場等都市空間,以及特殊群體所組成的人文地理空間。凡是產生第一原初經驗的場域,凡是存在地方性經驗和中心文化沖突與交流的空間,凡是具有原生性、樸素性和相對流動性的現代地理空間,都具備成為審美人類學工作和考察對象——“田野”的基本質素。對于田野的理解,人類學領域走過了這樣一個從具體蠻荒曠野到現代流動田野的本體化變遷生成歷程。我們提出的“流動田野”的本體論設想,具有人類學學科發展史的歷史支撐。“1979年到1995年費孝通‘三科并列’構想的提出,是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在中國重新恢復和再發展的時期。”[7]他提出“三科并列,互相交叉,各得其所,共同發展”。①胡鴻保:《中國人類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頁。原注:在慶祝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成立十周年暨學科建設研討會(1995年10月31日)上講話時,“三科并列”又表述為“多科共存”。實際上,我們意指的封閉田野概念,與民族學研究對象相近,開放的田野概念則與社會學研究對象相近。
通過對于“田野”的本體化求索,審美人類學的考察對象也就延伸到了現代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既有蠻荒曠野的民族種族地域,也包含都市獨特的生存空間,從而修正了一些批評審美人類學只研究少數民族藝術、邊疆荒野生活的聲音。此時,費孝通先生倡導的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三科并舉的合理性就顯現出來。三個學科的基本概念發生疊合,人類學、民族學的“田野”(field)同社會學的“場域”(field)可以互補性地相互參照。
明確了審美人類學研究本體空間位置及其空間范圍內的地方性經驗,我們還要明確地方性經驗的具體內容,主要包含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質文化生活,以及風俗、藝術和制度等方面的精神文化生活。于地方性經驗的具體解析中,發掘其中的審美經驗,審美人類學的考察對象就堅實具體地呈現在研究者面前,
當代審美人類學的“田野”概念打破人類學初創時期的“中心-邊緣”二元區分模式,進一步打破了文化等級論。當代“田野”是一元本體的空間場域,本土知識與外來知識發生碰撞,產生鮮活原初經驗的場域。
2.語境:審美制度和風俗習慣交互作用的文化空間
與“田野”相比,語境具有循環再生性、文化歷史性和柔性強制性。語境是田野上的文化氣候,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風霜雨露、雷電雪霧,是地域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節氣物候,左右著地方性審美經驗的生成、發展與變化。從微觀層面看,語境的創生以人類的實踐行為和認知情感為基礎。從宏觀層面看,語境生成的雙重動力分別為具有意識形態性的審美制度和日常生活化的風俗習慣。在風俗習慣調研方面,我們以廣西黑衣壯為案例已經積淀了大量經驗性的原始素材,②參看文藝學美學研究書系中范秀娟的《黑衣壯民歌的審美人類學研究》、陳雪軍的《黑衣壯文化的審美人類學研究》等研究著作。也在審美制度研究方面逐步開展了若干研究工作,③審美治理研究參看:本尼特的《文化與社會》《審美·治理·自由》,王杰的《審美習性、文化習俗與自由治理——中國當代審美經驗的理論闡釋》等論著和文章。這兩項工作借助田野調查,特別是語境分析為主要手段逐步開展的。
語境分析在審美人類學中具有重要位置。如果說田野調查面向地方性審美經驗的物質文化基礎,語境分析則比較側重地方性審美經驗的精神文化氛圍。圍繞著地方性審美經驗及其與中心文化的辯證關系,田野調查和語境分析分別指向了客觀實證基礎和人文價值基礎。兩者相輔相成,成為審美人類學理論體系的方法論支撐。
3.地方性審美經驗:作為審美人類學的核心概念
審美經驗是任何一位美學家和任何一個美學流派無法回避的美學基本概念。在美學史上關于審美經驗的闡述也層出不窮,不斷迭代更新。自美學誕生以來,明確地把審美經驗作為核心概念進行分析的美學家、美學史家有:杜威、塔塔爾凱維奇、杜夫海納等。理解審美經驗成為進入美學大門的一個基本前提。杜威認為,“經驗如果不具有審美的性質,就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整體”[8];塔塔爾凱維奇將美感經驗列為美學史六大基本概念之一,他從鮑姆嘉通對美感的分析出發,區分了美感經驗、美的經驗和藝術經驗,重點討論了美感經驗的幾種歷史形態:美的認知(Cognitio aesthetica)、凝神專注(Concentration)、著迷(Enchantment)、觀念(Idea)、靈魂的內感(Sensus animi)、靈魂的降服(Lantezza)、狂熱(Delirio)、補救無聊(Remedy boredom)。[9]杜夫海納從現象學角度論述了審美經驗的內在知覺機理。[10]
為了更進一步確定審美經驗的本質,我們應當首先在哲學層面上澄清“經驗”的意涵。古希臘哲學時代,哲學家們是從感覺出發討論經驗問題的。柏拉圖懷疑經驗(emperia)在知識中的積極的與肯定的作用。在他那里只有“理念的知識……是清楚明白的。相反經驗的知識是含混不清的,因為它說不出理據或邏各斯。”[11]德謨克利特也同樣貶低感覺的真理性。“伊壁鳩魯則相反,絕對肯定感覺的真理性。”[11]每一位哲學家對于感覺的態度決定了他們對于“經驗”本身在哲學中的定位。不同的定位導致了先天理念論和經驗論的分野,也導致了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分野。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調和了經驗和理性的關系,馬克思在更廣闊的社會生產發展與文化進步中對于感覺的作用進行了辯證地肯定。“人不僅通過思維,而且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任何一個對象對我的意義(它只是對那個與它相適應的感覺來說才有意義)恰好都以我的感覺所及的程度為限。”[12]
經驗之于美學是首要的基礎性概念,離開感覺,離開感性經驗,人類的審美情感(aesthetic emotion)就失去了最鮮活生動的客觀條件,失去了發生的可能。如馬克思所論述,審美經驗不僅體現為現在時的體驗性情感,也包含著經年累月、層層累積的記憶性、模式化的情感。從經驗的哲學本質以及經驗生成的時態來看,審美經驗包含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當前發生的感覺愉悅的審美化體驗,另一個是文化累積的審美記憶。
審美經驗是否是一種特殊的經驗?這已經成為一個美學史上老生常談的問題。但是,針對這個問題,每個時代的每一位探索者的每一次回答,都不是累贅冗余。美學基本問題的開放性與回答方式的多樣性,恰恰是美學不斷向前發展的基本標志。美學研究融入時代新知才能獲得新的答案。
在當代語境下,在審美經驗的科學基礎、社會文化基礎上進一步求索,才有可能對于審美經驗的科學內涵做出新的解答。從認知神經科學層面看,經驗或審美都不是其主題。但是,借助認知神經科學對感知覺、認知與情感、學習與記憶、思維與能力的研究,關于“經驗”的研究可以獲得推進。經驗,在現在進行時,表現為主體感知著某事某物的過程,可以譯為體驗,是認知、情感和能力的現量;在過去時中,它是累積在主體記憶中的認知、情感以及能力的存量;在將來時中,它將表現為認知、情感和能力的可能性的增量。杜威對于審美經驗的概念方法將陷入循環闡釋的怪圈,審美經驗是具有審美屬性的經驗,一切經驗皆可有審美屬性,因而一切經驗皆可為審美經驗。審美屬性又是什么?主體感受到愉快的生理的、物理的物質形式。生理方面可能是神經遞質或者產生神經遞質的神經機制,物理方面是物質存在的可以直接激發審美愉悅的物質存在形式。
現代人類學對于審美經驗的探究更加側重物質形式方面。地方性審美經驗是特定田野上的審美經驗。地方性審美經驗自身具有客觀性與主觀性、物質性與精神二元融合的基本特征。
4.價值追求與實踐方式:傳承與革新
審美人類學在價值取向上倡導古典人類學的人文主義情懷和悲劇情結。以人的尊嚴、自由和解放為使命,這必然要求我們正視資本與意識形態的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又能夠因勢利導,善于把握地方性審美經驗和全球化審美文化傳播之間的微妙關系,在強制影響與保護尊重之間做好平衡。現代化進程中,悲劇性沖突在所難免,無奈又必然的文化現實邏輯促使我們重新鮮明地樹立起悲劇人文主義旗幟,為一切美好生活的愛好者提供理論支持和行動指南。
對于地方性審美經驗的探求,體現了研究者對于淳樸原生態生活、童年故鄉、弱勢空間、傳統農業文明的關懷,也體現了希圖通過邊緣文化映射中心文化,在對照、平衡與協調兩者關系中尋找亟待改良與調整的現實切入點。
在挖掘地方性審美經驗過程中,審美人類學者的烏托邦情懷一方面溯回到過去時的鄉愁舊夢,一方面設想了將來時的烏托邦新世界。如果說鄉愁舊夢蘊含著對農業社會原初經驗的懷戀,烏托邦新世界則是直接體現出對工業資本時代未來形態的現實期許。兩種價值導向引導了兩種審美人類學的實踐行為模式:傳承與革新。
在時代的四重挑戰面前,地方性審美經驗的保護與傳承逐漸變為一個世界性難題,我們若想真正地實現“地方性審美經驗”的與時俱進式發展,僅僅靠保護是不夠的。依靠“他者”的眷顧和幫扶,本土化審美經驗永遠難以形成足夠結實的文化體質。在全球化、網絡化時代,每一種本土文化都面臨著外部多元文化侵入,當其無法拒絕和抵擋外部文化的浸潤時,如何培養傳統封閉式本土審美經驗的“適應性”“外播性”品質,可能是一個有意義的課題。
本土審美經驗的現實品質僅僅依靠他者來培養是無法完成的,這就需要本土審美經驗的自我革新式發展。做好守成與吸納兩個方面的結合,特別要借助于現代文化資本的力量,同時又能夠批判地對待文化資本給“本土文化與藝術形式”帶來的價值與使用價值之間撕裂的嚴重危機。關于傳承與革新,有綿延不盡的話題,需要我們審美人類學學者進一步探索。
三、提煉審美人類學的主要方法
1.審美人類學對一般文化人類學的推進
(1)強化哲學人類學的維度
當局部知識應當由哲學來規范和引導時,總體知識在這里就總是走在局部知識的前面:沒有哲學,一切獲得的知識就只能當作零碎的摸索,而不能認為是科學。[13]
列維-斯特勞斯“使人類學得到一種理性的訓練”,他“一門社會科學第一次贏得了尊敬”,原因就在于他運用結構主義的觀念系統地分析了人類學的零散記錄,從而使人類學成為一門系統的知識。[6]
我們面對人類學記錄進行解讀與分析時,什么樣的哲學立場和流派是基本出發點和依靠呢?結構主義還是精神分析?解釋學的還是存在主義?我們難以給出唯一的答案。對于復雜人類學記錄的分析難免不訴諸多元的哲學立場。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我們訴諸“元哲學”化的思考,實現對審美人類學材料與建構的前提批判;另一方面,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作為基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最終,一切以審美人類學實際材料為依據,以地方性審美經驗為基本對象的有效分析,以形成整體化審美經驗及其闡釋為目的的,都是我們樂于采用的方法。
(2)突破簡單田野工作和深度訪談的有限性
通過審美人類學的哲學化思考,我們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決以往人類學方法之于美學的零散化、淺表化的實際效果。田野工作包括參與觀察、個體訪談、深度訪談、群體調查問卷等多種方法,通過這些方法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地方審美經驗材料。面對這些材料,如何解讀成為一個首要的問題。
通常來看,田野工作之后的簡單分析、總結概括和推論求證總是難以滿足我們對于地方審美經驗的深度思考。總體性地方性知識,也稱為“民族志”[14],則更為全面地描繪出本土居民的整體文化概觀。隨著人類學的發展,站在本土居民的“主位”進行“深描”,正所謂“理解他們的理解”才能深挖一片田野上的審美認知情感結構。
(3)超越實證研究的局限性
人類學以其實證科學的面貌呈現在人文社科領域,主要優勢就是擁有第一手的實證調查材料。實證材料產自于田野調查、深度訪談、深描民族志等人類學工作方法。然而在當代社會的審美問題研究中,人類學的實證研究方法并不足以應對所有難題。一方面,我們要追問,能否搜集整理出絕對客觀的第一手材料,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研究和思考當代中國人的審美情感結構及其復雜的表現形態。
針對第一方面,我們認為“零度寫作”或者“紀錄片式的研究”都無法逃脫主觀立場,而達到絕對的客觀化,人類學的“深描”亦然。能夠明確主觀立場與客觀經驗之間的關系,并在分析中能夠準確把握住主客關系的屬性與結構,就會獲得實證研究的相對客觀性。浙江大學當代美學與藝術批評研究團隊從當代中國審美經驗發生的現場——當代中國電影展開研究,力圖通過對當代文化的審美認知情感的深描,尋求民族審美的當代進路與未來方向,進而為實踐倫理提供認知情感支持。
另一方面,審美研究必將導向倫理入口的預設,不解決倫理實踐方向就無法掌握所有研究的價值立場。闡釋人類學大師格爾茨提出“闡釋人類學的基本使命不是回答我們最深切的問題,而是讓我們了解其他山谷放牧其他羊群的其他人的回答,從而把這些答案放入可供咨詢的有關人類言說的記錄當中”[15],實則是為人類學創建主位、客位平等互動平臺進行了奠基,“深描”本身是這個互動的過程和結果。格爾茨也提倡“投身于這些困境之中去”,然而他與馬克思主義的投身歷史實踐有本質不同。前者止于“深描”,后者則要實實在在地為文化治理、精神革新、社會革新乃至全人類自由平等發展開展社會實踐活動。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在于關注現實、批判現實和改造現實。從馬克思、恩格斯本人,到現當代西方與我國馬克思主義者無不關切現實,投身社會革命與建設運動。[16]我們倡導的人文立場蘊含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更體現于理論研究和社會實踐的緊密結合,體現于理論研究和人民大眾的現實關切的緊密結合,這也正是審美人類學的倫理實踐入口。
2.審美人類學的基本方法
(1)突破簡單的形式研究,在具體的文化語境中研究原初經驗和藝術文本的審美意義。在當代社會和文化中,由于藝術文本和審美經驗都處在多重疊合的文化語境中,從形式分析進入到具體的審美意義的理論把握是一項十分艱難的理論工作。審美人類學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解決這一難題。
(2)特別注意避免任何形式的文化中心主義和文化優越性論, 用靈活多樣性的方式開展田野工作。(參與觀察、訪談對話、撰寫審美民族志等)例如,關于中國當代電影的系列討論是一種當代審美情感結構的民族志研究。通過對當代中國電影的連續討論式闡發,在不同觀點和學術視角的碰撞中,把握住中國當代社會的情感結構。
(3)回歸人類學的初衷:研究和闡釋人性及人文主義問題;在當代中國美學領域,悲劇人文主義的理論闡釋具有重要的意義。這個維度的研究與闡釋,涉及中國文化的倫理重建和審美信仰的回歸。
3.審美人類學的具體應對策略
(1)針對娛樂化、消費化的日常生活審美,倡導悲劇意識的復歸,重塑人文主義立場下的人的全面發展。
日常審美娛樂化和消費化帶來的優勢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過去的廟堂精英藝術普及為普羅的、大眾的波普藝術。精英藝術與大眾審美之間不再涇渭分明。人民大眾有更多機會領略到精英藝術的精妙之處,精英藝術也不再高高在上,以更加喜聞樂見的形式深入到人民生活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日常生活審美化和大眾審美中存在著強烈的娛樂化傾向。因而,審美活動常常追求完滿的結局,編織充滿歡樂的情節;鮮明的色彩、動感的節奏等純形式愉悅因素成為簡化藝術復雜性的主要方法。此時,藝術審美的深沉性與厚重性被嚴重削弱。藝術改造人生,改造社會的功能基本喪失,大多沉淪為制造歡聲笑語的審美資本的工具。當審美活動失去了批判性、改造性力量,其存在的價值就要大打折扣。在審美活動生活化、娛樂化的同時,重提悲劇意識,重提藝術改造人生和社會的功能,仍然具有重大價值。
(2)針對全球化的審美文化共同體的積累力量,倡導地方性審美經驗的自我主體確認,在和而不同的立場上增強本土文化的適應性和外播性。
幾年前,一首《江南style》紅遍了全球,“騎馬舞”成為各類舞臺、各種秀場的必備選項。這體現了全球化文化傳播中審美共同情感的相通性。然而,此曲此舞業已無人問津。全球化的文化共同體在文化經濟時代常常以流行藝術的形式出現,流行藝術的主要特點是如同一陣風,迅速地感物動人,又迅速地離開,難以形成經典化藝術作品。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全球化文化高速發展的當代,各個民族的地方性藝術形式受到了嚴重的破壞,乃至消亡。如何能夠保持地方性審美經驗特征下的藝術形式的傳承性,這是一個永恒的課題。審美人類學認為,任何民族的本土文化既無法完全封閉自足,也不能完全開放放棄傳統。只有保持本土審美經驗的適應性與外播性,才能在各種文化經濟時代的全球化浪潮中留存下來,并獲得新的生機與活力。
(3)針對網絡化的跨界審美現象,倡導多學科交叉的美學研究方法和藝術批評路徑。
網絡時代的一大特征是過去一切封閉自足的學科,都被其他學科所侵蝕介入。作為哲學、藝術批評的美學亦然。美學研究不再僅僅局限于哲學思辨問題和藝術批評領域。它逐漸向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心理學等等各個學科領域擴展。各個學科領域也以其獨特的方法逐漸融入美學研究之中。
針對網絡化時代,學科交叉融合的現象,審美人類學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對待美學和各個交叉領域的融合互滲。在廣闊的田野上和豐富的文化語境中,地方性審美經驗成為各個不同學科介入美學的重要的物質基礎。地方性審美經驗以其豐富的物質形態和精神內涵為各個學科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平臺。總體上看,網絡化時代美學研究的多學科交叉狀態,在審美人類學的大視野下都是可以包容互滲的。
四、運用審美人類學開展藝術批評:以當代電影為例
如同文藝學學科包含美學原理、文學理論和藝術批評三個方向一樣,審美人類學不僅僅追求美學理論體系、文學理論體系的建構,還抱有強烈的現實干預意識,積極開展藝術批評即為其中一條有效的途徑。藝術批評以最敏銳、最直觀的形式,直擊當代藝術的原生態現場,它是審美人類學理論體系的具體運用,也可以作為審美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語境分析、民族志書寫等基本方法的重要補充。[17]
首先,原生態批評。這種批評方式既不同于以往學院派運用經典理論分析經典作品,也不同于民間網絡評論者有感而發的體悟式評論,它呈現為眾說紛紜的多主體、多對象、多價值體系并存的狀態。團隊邀請了導演、編劇、市場總監、大學教授、博士后、博士碩士研究生、普通觀影者參與到討論中來,因而打破了個體評論家、評論者的單一理論架構、單一價值取向的傳統方式,復原了電影在市場、知識域、生活域中的多重變奏的回音。各種不同的回響恰恰蘊涵著各種原生態生活的余韻,賦予這種批評形態以獨特的原生態魅力。
其次,流動生成式批評。批評主體從個體回到了群體,審美標準由獨斷式復歸為協商式。討論過程中,既有參與者對影片的褒揚與批判,也有參與討論者相互之間的認同、辨析和辯論。通過這樣的多維互動模式,批評呈現為一種流動式、生成式的演化過程。主題先行的傳統批評方式,在這里變成主題中行、后行,或者主題懸置化的開放式批評實踐過程。
第三,情感民族志批評。審美人類學指導下的當代電影討論的一個重要目標在于記錄當代都市情感的民族志。當代電影恰恰是當代都市情感最核心的凝結點,導演、編劇、觀眾、批評者的情感都匯聚在這個焦點上。電影討論的過程,一方面是理智的運用過程,另一方面更是所有參與討論者自身情感表達與記錄的過程。這種情感表達與記錄可以折射出電影中主人公的情感、電影創作者的情感乃至當代都市生活的整體情感狀態。對于這樣一種情感記錄過程,我們認為它可以構成有別于傳統電影批評的當代電影情感志批評。
第四,悲劇人文主義批評。在“娛樂至死”的大眾傳媒時代,悲劇對于社會的改造性力量逐漸被人們遺忘,然而它廣泛地存在于現實生活和文藝作品之中。在電影討論過程中,我們注重對于其中的悲劇性力量進行挖掘。鄉愁烏托邦與紅色烏托邦雙螺旋結構為主體的當代情感結構中,悲劇仍然構成推動當代情感嬗變的重要的驅動性力量。
在《戰狼II》和《流浪地球》的討論中,部分地體現出了上述特征中的某些傾向,下面截取部分討論內容和批評內容,來彰顯審美人類學討論式批評的主要特征。
1.《戰狼II》創造了50多億人民幣的票房收入,成為近幾年的現象級電影的代表。中國當代電影高票房現象源于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然而針對目前的本土精神文化供給,若想達到高質量高水準,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間。以期以個案集體訪談的形式分析該類型電影的得與失,特別在批評聲中尋找當代中國文化成長關鍵點。[18]
電影在表達傳統天下國家的武俠模式中,滿足了國內觀眾的心理需求,創造了某種有別于“不抵抗主義”的另一種“把對手打回去”的審美模式。這種審美模式反向折射了當代主流都市生活“陽剛之氣”的缺失,然而滿足這種審美心理需求的過程中,情感戲表達又顯得粗糙,放在國際主義救援這樣的大背景下,很難以一種悲劇人文力量打動人心。今后,如果能夠以平凡生活中樸素的情感和事件為切入點進行深入挖掘,才有可能拍出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大片。
通過這個批評實例,我們嘗試著運用集體訪談的方法,映射出本土文化語境中的審美經驗在當代現實生活中的原貌。借助人類學化的原生態的批評聲音,探尋中國現象級電影的產生規律和未來走向。
2.《流浪地球》的票房達到46億多,緊追《戰狼II》,成為又一部現象級中國電影。具體來看,影片取得了極大的票房成功,然而卻難以成為科幻里程碑式的作品。
從審美人類學的語境理論來看,影片的情感處理方式與預設的語境完全不能自洽,其原因在于技術性情感控制的倫理失調。當前的工業化情感控制術依賴于個別情緒點的爆破,來瞬間感染帶動觀眾情緒,這種情感處理方式是完全脫離語境的。在本片當中,情緒氛圍是脫離了死亡30億人這個大語境的。當然不僅限于《流浪地球》,還包括許多好萊塢大片,工業電影的癥結在于脫離預設語境,更脫離時代語境,傳遞情感,營造情緒。這類似于直接注射情緒激素,刺激觀眾。觀眾想要購買審美精神產品,買來的卻只是缺乏未來倫理道德建構預想的工業文化激素,有時候是興奮劑,有時候是催淚劑。從這個層面看,本片的許多情緒凝結點是脫離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倫理失衡的產品。
工業文化產品已經脫離了情感創作中的原生性、生命性、在場性等人文品性。工業化和技術化的文化生產肢解了原生性情感的動人魅力,只去捕捉那些短暫而直接的情感觸點,制造讓人迅速產生極限式喜、怒、哀、樂的情緒藥品。導演電影是對這種傾向的有效反撥。
影片預設了人類生存環境驟變時期,浩殤帶來了創痛、毀滅與絕望,抗爭與拯救是人類的本能反應,悲劇的本質在于拯救的不可完成性。舊時代終究要過去,新社會終究要來臨。新舊交替之間,拯救行為的結果并不重要,行為的過程因為個體或者集體的認知、情感、意志的充分釋放而具有了人文主義的光輝。在可逆轉與不可逆轉之間,結果難以把握。自然界的小概率或者微概率事件的發生并不會因為人的情感意志發生改變,如果影片充分地表現拯救的動機、拯救的過程以及其中的人類情感,則會有較好的審美效果。
另外,審美人類學的悲劇理論認為,悲劇是新舊審美經驗之間碰撞交流的結果,具有重大的革新力量。在本片中,悲劇性的結局是觀眾不愿見的,成功的拯救又落入了俗套,失去了文本結構需要具有的豐富性、含混性,觀眾期待視野被填滿之后,余韻耗盡,興味索然。因此,在經過激烈的科學辯論,反復的人文理性與情感意志拷問之后,透露出可能的結局,在劉培強決定帶著領航器燃料裝置撞向木星時結束影片。懸置結局將更有助于調動觀眾的情緒,現代悲劇意識也將得到合適的呈現。
如果影片專注于打磨這部作品的情感體驗、科學理性與人文理性,該片是有成為一部劃時代科幻作品的潛質的。它本可以是一部關于未來人類生存的悲劇,可以提示人們的環保意識、自然危機意識,還可以警策人類道德、法律和社會組織方面潛在的制度性內容。伊格爾頓認為,“悲劇實際上是對今天墮落的、庸俗的日常生活所作出的反應”[6],[悲劇的巨石始終懸在人類生存的上空,可以成為信仰缺失的現代社會重新凝聚精神力量的當代情感結構的組織方式。因而,“現代悲劇不但沒有消亡,而且更加多樣且多彩了。”[6]劉慈欣的小說《流浪的地球》本身是一部未來生存倫理小說,他思考了婚姻、生死、政府組織方式等多個方面的未來倫理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劉慈欣的小說原著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科幻小說,而是一部未來主義倫理小說。
當代人文主義悲劇意識的理解不深是影片缺乏深沉悲劇性力量的重要原因。盲目樂觀,心存僥幸,深邃情感讓位于感性沖動,理性缺失依靠情懷勾兌,深沉的悲劇人文主義被工業化情感控制術肢解。我們只好寄希望于未來,并且真誠地期待“科學家到文學中去,作家到科學中去”。[9]
五、關于審美人類學的基本反思
1.在學理上,審美人類學和當代藝術批評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具體表現在:審美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是活動著的審美經驗,不是物化了的藝術作品,因此,審美意義是流動的多重語境中的審美意義,這是審美人類學研究的對象,因此,具有十分突顯的當代性。
審美人類學具有美學理論體系建構的內容,富有形而上的思辨性,追求本體論、方法論和價值論的完備性、系統性和有機統一性,藝術批評則是審美哲學理論的具體運用,強調理論的批判性、實用性和創生未來的引導性。
2.在方法論上,審美人類學把哲學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的實證研究方法結合起來,努力使用多學科綜合性的方法,解決當代美學的一些復雜問題。
中西方人類學都有漫長的發展歷史,每個階段的人類學關注內容和表達方式不盡相同,但是在研究視野、研究方法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上是一以貫之的。處于網絡化時代,審美人類學是向一切關于人的審美問題研究的開放體系,因而有足夠的學術資源解決當代美學中的復雜問題。
3.人們一般認為,審美人類學只能研究少數民族的審美文化,不能研究當代美學的復雜問題,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對審美人類學的誤解。經過對于“田野”的形而上學批判,我們已經開辟了更為廣闊的研究空間:審美人類學既可以融合民族美學研究,也可以融合社會學美學研究。
例如,“field”在人類學和民族學中都翻譯為“田野”,在社會學中翻譯為“場域”,審美人類學除了兼顧傳統人類學、民族學的“田野”之外,也把社會學的“場域”概念納入到了考察范圍內。在某種程度上說,社會學的場域構成了人類學意義上的開放的流動的田野。費孝通先生在人類學、社會學與民族學“三科并舉”的倡導中,已經蘊含了對三種學科的相通性的理解與實踐。當代審美人類學不應該故步自封,而有必要積極融合三個學科的對象和方法,形成包容性研究態勢。
最后,審美人類學經過長期的歷史積淀,已經逐步形成了理論體系雛形。我們經過本體論的構建和方法論的反思,基本具備解決當代的四重難題的能力,期待更多美學研究者與我們一道探討審美人類學,推動當代美學的新發展。

圖1《審美人類學》知識結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