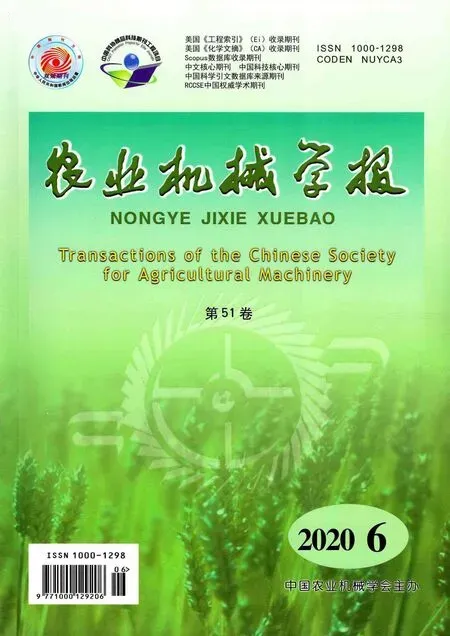大興安嶺蒙古櫟生物量分配格局與可加性模型研究
陽 帆 孟盛旺 王 威 常廣軍 彭道黎 劉秦笑芝
(1.北京林業大學林學院, 北京 100083; 2.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生態系統網絡觀測與模擬重點實驗室, 北京 100101;3.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調查規劃設計院, 北京 100714; 4.內蒙古自治區第二林業監測規劃院, 烏蘭浩特 137400;5.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華北林業實驗中心, 北京 102300)
0 引言
作為陸地生態系統最大的碳庫,森林在維持區域碳平衡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4]。森林碳儲量通常是基于生物量采用含碳系數轉換而來[5],因此,作為重要的生物學特征和生態學指標,森林生物量的準確核算具有重要意義。
生物量最準確的測定方法是在野外將樹木伐倒后直接稱量,也稱為收獲法,但這種方法破壞性大,且耗時、耗力[6],而且僅能在一定范圍或較小的個體上使用,不適合大面積或保護區的森林生物量估算[7]。異速生長模型結構簡單、使用方便,基于易測變量即可快速實現生物量估算,已經成為十分有效的森林生物量測定手段[8-9]。通常情況下,生物量模型是干物質量與胸徑之間的回歸模型,也有許多研究將樹高、冠幅、樹齡等變量添加到模型中,以提高生物量的預測能力[10-12],木材密度也用于混合樹種的生物量模型中[13]。除模型的自變量多樣化外,模型形式也多種多樣,其中,最常用的形式為冪函數及其對數轉換形式[14-15]。
樹木總生物量可分為地上生物量和根系生物量,地上生物量又由樹干、樹枝和樹葉生物量構成,由于林木各組分之間存在內在相關性,因此樹木各組分模型的預測值之和應等于總量模型的預測值[16]。目前,針對全球主要分布樹種構建了許多生物量模型,但大多采用最小二乘法對總量、分量模型單獨擬合,使模型之間不具有可加性[17],導致預測結果不符合生物學邏輯。因此,構建生物量模型時,有必要考慮可加性[18-19]。生物量模型的可加性已有幾十年的研究歷史,研究者提出了多種手段來解決線性或非線性模型的可加性問題[20-22]。近年來,使用最廣泛的是似乎不相關模型(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UR),該模型通過聯立方程系統,綜合考慮了不同組分之間的關聯性,并對方程參數和誤差結構設置約束條件[14],從而保證模型結果之間的可加性。
大興安嶺是我國寒溫帶森林的主要分布區,林區面積廣闊、資源豐富、碳儲量巨大,不僅在全國碳平衡和氣候調控上發揮著重要的生態作用[23-24],而且還是我國重要的木材生產基地,具有很高的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蒙古櫟(QuercusMongolica),又稱柞樹,是國家二級保護珍貴樹種,也是大興安嶺地區的主要建群樹種和優勢樹種[25],具有抗干旱、耐瘠薄、適應性強的特性,在生態環境建設、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森林可持續發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5]。在未來氣候變化下,蒙古櫟的地理分布范圍可能會更廣[26],因此,研究其生物量的變化規律對未來氣候下生態系統碳計量和碳循環具有重要意義。目前,有關蒙古櫟生物量模型的研究相對較少,主要針對黑龍江大興安嶺地區[5,23],而缺少內蒙古大興安嶺地區的數據支撐。本研究通過收獲法采集天然蒙古櫟地上和根系的生物量,旨在探討其生物量的分配格局及變化規律,并基于胸徑、樹高和冠幅變量,采用似乎不相關模型構建可加性生物量模型,為大興安嶺林區蒙古櫟生物量及碳儲量估算提供有效手段。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大興安嶺是我國最大的原始林區,屬于寒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全年氣溫較低,四季溫差大,年平均溫度低于0℃,極端低溫和高溫分別為-52℃和40℃。年降雨量為350~500 mm,且主要集中在5—10月,土壤類型以棕色針葉林土為主。林區內主要樹種有興安落葉松(Larixgmelinii)、樟子松(Pinussylvestrisvar.mongolica)、蒙古櫟(Quercusmongolica)、白樺(Betulaplatyphylla)、山楊(Populusdavidiana)等。灌木層主要有杜鵑(Rhododendronsimsii)、杜香(Ledumpalustre)和越橘(Vacciniumvitis-idaea)等。
1.2 樣木生物量測定
根據蒙古櫟的分布特點和立地條件等,按徑階選取樣木并采用破壞性采樣法測定生物量,胸徑10 cm以下的樹木取樣徑階設置為1 cm,而10 cm以上的樹木設置為2 cm,共選擇78株蒙古櫟,全部測定胸徑和冠幅,伐倒后測定樹干長度(樹高),樹高隨胸徑的變化趨勢及各徑階樣木分布情況見圖1。由于根系生物量取樣、測定費時耗力,尤其對細根的準確計量難度更大,因此,在采集地上生物量數據的78株樣木中,按徑階分布共選擇了31株樣木用于根系生物量的測定。

圖1 樹高-胸徑散點與各徑階樣木分布頻度Fig.1 Distribution frequency of tree height-DBH scatter and sample wood of various sizes
單木生物量測定分為地上和地下兩部分,地上生物量又分為干材、樹皮、樹枝和樹葉4部分。將伐倒木的樹干均勻分為10個區分段,測定各區分段處的帶皮直徑和去皮直徑,然后稱得所有區分段的鮮質量,在全樹高的0.1、0.3、0.7處的上下位置,各取2個3~5 cm厚的圓盤,稱其鮮質量后,將樹皮剝離再次稱量,用于樹皮生物量計算。樹冠生物量分層測定,將樹冠分為3層,每層選擇生長良好、長度和葉量適中的3個標準枝,分別稱枝、葉的鮮質量,然后在各層標準枝分別對枝條和葉片取樣,并稱其鮮質量。根系生物量采用全挖法測定,并對不同位置根系取樣,稱其鮮質量。所有樣品帶回實驗室后,放入105℃的干燥箱中干燥至質量恒定,測量樣品干質量,計算含水率。鮮質量乘以含水率得到各個組分的生物量,各組分生物量相加得到樹木總生物量(表1)。

表1 建模樣木基本統計量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ampled trees for biomass equations development
1.3 數據處理與分析
通過計算干材、樹皮、樹枝和樹葉占地上生物量的比例,分析地上生物量在樹木不同組分的分配模式及隨胸徑的變化趨勢。基于測定根系生物量的樣木,計算根莖比(即根系生物量與地上總生物量之比)并分析其隨胸徑的變化規律。
胸徑和樹高是野外調查中的易測變量,也是樹木生物量模型構建的重要因子。采用胸徑以及胸徑、樹高的組合為自變量,并在此基礎上加入冠幅因子,觀察模型的擬合效果。
lnWi=lnαi+βilnd+εi
(1)
lnWi=lnαi+βiln(d2h)+εi
(2)
lnWi=lnαi+βilnd+γilncw+εi
(3)
lnWi=lnαi+βiln(d2h)+γilncw+εi
(4)
式中Wi——各組分生物量,kg
αi、βi、γi——模型系數
εi——模型誤差d——胸徑,cm
h——樹高,mcw——冠幅,m
由于根系生物量較少,不能與地上部分建立模型系統,故根系生物量模型利用模型(1)~(4)單獨擬合。地上各組分生物量模型則分別以式(1)~(4)為基礎,采用似乎不相關模型構建模型系統對干材、樹皮、樹枝、樹葉、樹冠和地上生物總量同時擬合。似乎不相關模型在參數約束的基礎上,綜合考慮了總量和分量模型之間的誤差結構關聯性,對總量和分量的生物量模型同時構建,使分量模型沒有獨立于總量而構建,確保模型具有可加性[14, 17-18]。模型(1)~(4)的可加性結構形式類似,因此以自變量最多的模型(4)為例,構建可加性模型系統,具體形式為
(5)
式中Wwd——干材生物量,kg
Wbk——樹皮生物量,kg
Wbr——樹枝生物量,kg
Wlf——樹葉生物量,kg
Wcw——樹冠生物量,kg
Wag——地上生物量,kg
α、β、γ——模型系數
ε——模型誤差
所有模型均在R 3.6.1軟件中使用“systemfit”包進行擬合。
1.4 模型評價

生物量模型是否可靠、能否用來合理準確地估算生物量,需要經過檢驗。本文基于全部數據建模,采用留一交叉法(刀切法)對模型進行驗證,即每次留一個樣本進行檢驗,其他樣本用于模型建立。該方法廣泛用于模型檢驗,在相關研究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27-28]。
2 結果與分析
2.1 地上生物量分配模式及根莖比
蒙古櫟各部分生物量占地上生物量的比例差異較大,其中樹干對地上生物量貢獻最高,干材和樹皮占地上生物量的比例分別為51%和14%;與樹干相比,樹冠部分生物量相對較少,約占地上生物量的35%,其中樹枝為28%,樹葉僅為7%(圖2,圖中的點表示平均值)。干材占地上生物量的比例較為穩定,隨胸徑的變化波動性較弱,樹枝生物量比例隨胸徑的增加而逐漸增加,表現為正相關關系,而樹皮和樹葉生物量比例呈相反趨勢(圖3,圖中黑色線條為loess平滑曲線,陰影為95%置信區間,下同)。

圖3 各組分生物量占比隨胸徑的變化趨勢Fig.3 Fraction of aboveground biomass allocated in wood, bark, branch and leaf varied with diameter
根莖比是樹木根系生物量與地上生物量的比值。基于開展根系生物量采樣的31株樣木可知,根莖比的變動范圍為0.11~0.81,主要集中于0.2~0.5之間,均值和標準差分別為0.36和0.17。樹木較小時,根系生物量所占比例較高,根莖較大時,隨著胸徑的增加,根莖比逐漸減小(圖4)。

圖4 根莖比隨胸徑的變化趨勢Fig.4 Root/shoot ratio varied with diameter
2.2 各組分最優模型結構確定

確定地上各組分最優模型(自變量)后,基于似乎不相關模型,構建新的可加性生物量模型系統,并重新進行擬合,得到各組分最優可加性生物量模型(表3)。樹皮、樹枝和樹葉模型擬合優度與原來相比略有提升,干材則略有下降。各組分最優生物量模型的殘差隨預測值的增加基本呈均勻分布,不存在異方差問題(圖5)。

表2 各組分模型系數及擬合優度Tab.2 Coefficients with standard error and goodness-of-fit statistics of four models for wood, bark, branch, leaf and root
注:地上部分生物量采用可加性模型擬合,根系模型單獨擬合,模型系數括號中數據表示標準誤差,***表示顯著性水平(p<0.001),ns表示不顯著。

表3 地上最優可加性生物量模型及根系最優模型Tab.3 Optimum additive biomass models for aboveground parts and selected models for root

圖5 各組分生物量模型殘差Fig.5 Residuals of wood, bark, branch, leaf, aboveground and root biomass models
2.3 留一交叉法模型驗證
采用留一交叉法對根系生物量模型和地上部分最優可加性生物量模型的驗證結果如圖6(圖中灰色虛線為1∶1線,黑色線條為線性回歸結果)所示。

圖6 各組分生物量預測值與實際值散點圖Fig.6 Scatterplots of predicted and observed values for wood, bark, branch, leaf, aboveground and root biomass using leave-one-out cross-validation method
圖中預測值為模型估計值反對數轉換的結果。線性回歸表明,各組分模型的預測值與實際值都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干材、樹皮和地上生物量模型的預測效果相對較好(斜率更接近于1∶1線),而樹枝、樹葉、根系生物量模型的預測誤差相對較大。生物量較小時,各組分模型的預測結果均表現為高估,當生物量較高時,模型的預測值常小于實際值。
3 討論
生物量模型在森林資源清查和碳儲量估計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作為一種高效率、低成本的無損估計方法,使森林碳匯計量變得更加快捷、簡單[29]。本研究基于似乎不相關模型構建了大興安嶺地區蒙古櫟的可加性生物量模型,為該地區森林生物量和碳庫的準確核算提供了有效手段。
3.1 生物量分配格局及根莖比
生物量的增加是樹木對能量的積累過程,其在各組分的分配模式受植物個體和外部環境的共同影響[30],樹齡不同,各組分生物量占總生物量的比例也不相同。而胸徑基本可以反映樹齡的高低[31],本研究中生物量分配模式隨胸徑的變化規律基本反映了樹齡對生物量分配的影響。隨著樹木的逐漸成長,木質生物量的積累常常以消耗樹葉的生物量為代價[32-33],因此,樹干和樹枝生物量占地上總生物量的比例最高,樹葉所占比例較小。樹葉生物量比例隨胸徑的增加而降低,原因可能是樹葉更多的著生在幼年生枝條而不是老年生枝條上,意味著單位干質量枝條上的葉生物量隨著樹木的成長而減少[12]。此外,由于林分中林木對光的競爭,與生長在開闊地帶的樹木相比,地上生物量會更多地分配到樹干部分用于樹高生長[34]。
全球樹木根莖比的平均值為0.26,變化趨勢在0.2~0.3之間,且根莖比的變化趨勢與土壤質地和樹種無關[35]。我國針葉樹和闊葉樹根莖比的平均值分別為0.25和0.29,闊葉樹略高于針葉樹[36]。本研究得到蒙古櫟根莖比為0.36,相比全球和我國平均水平都較高。
3.2 異速生長模型

可加性是樹木生物量估測模型中的一個重要特征,它可以消除分量預測值之和與總量預測值之間的不一致性[16]。但由于目前大多的生物量模型都采用最小二乘回歸估計,使模型之間不具有可加性[43-45]。似乎不相關模型構建的總量和分量模型系統,考慮到各模型誤差的協同相關性,修正了每個模型估計之間的固有誤差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總量方程式是所有分量方程式的累加,即總量方程式的自變量為所有分量方程式的自變量,從而對回歸系數的估計設定了限制條件[15,46],有效降低了回歸系數的方差。模型系統求解的過程中,同時獲得了所有回歸系數,達到減少總量和分量之間不確定性的目的,保證各組分生物量模型估計值之和等于總量模型估計值,提高生物量的預測精度。
基于生物量對數值建立的線性模型,在實際應用時需要將預測值進行反對數轉換,但在轉換的過程中會產生系統偏差[43,47]。為了盡可能地減小偏差,通常使用基于估計值標準誤差計算的校正系數(CF)對模型預測值進行校正。然而,也有研究認為使用校正系數后會使生物量的預測值偏高,而且在反對數轉換過程中產生的偏差與生物量估計過程中產生的總體誤差相比通常較小,實際使用中可忽略不計[48]。本研究中,各組分生物量模型的校正系數均相對較小(CF小于1.1),尤其對于干材、樹皮和地上部分(CF小于1.05),因此,模型估計值在反對數轉換時產生的誤差較小,在實際使用中可忽略不計。此外,若使用轉換系數,會導致各組分之間生物量模型的可加性遭到破壞。
由于生物量與易測變量之間的關系隨樹木大小、年齡和林型等的變化而不同,本研究得到的模型更加適用于大興安嶺林區蒙古櫟生物量的估計,對此區域之外或者其他樹種估計時,會產生較大的誤差[9]。本研究生物量模型建模數據的胸徑范圍為1.5~32.8 cm,超出該胸徑范圍的生物量估計都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應依據特定區域、特定樹種和特定估測范圍選擇模型進行生物量估計。
4 結束語
蒙古櫟地上生物量主要分配在樹干,尤其是干材部分,分配到葉片的生物量最少。根系以胸徑為自變量的根系生物量模型擬合效果最佳,基于胸徑和樹高組合變量的干材和樹皮生物量模型預測能力最強,而在胸徑基礎上添加冠幅變量的樹枝和樹葉生物量模型擬合效果更優。采用似乎不相關模型不僅有助于實現生物量模型的可加性,還可以降低誤差,并提高模型的預測能力。由于對數轉換校正系數通常較小,在實際使用中可以忽略。本研究得到的最優可加性生物量模型可有效估計大興安嶺林區蒙古櫟生物量,但需要特別注意模型的胸徑適用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