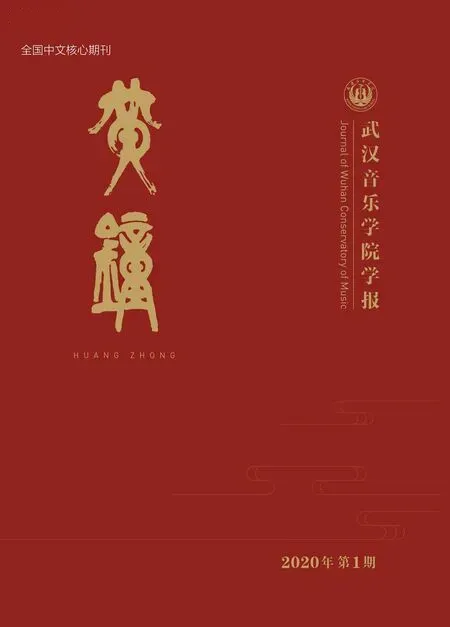莉迪婭·戈爾《人聲之問》中譯本校后瑣記
孫紅杰
1997年,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教授莉迪婭·戈爾①莉迪婭·戈爾(Lydia Goehr,1960-),女,英國哲學家、音樂美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教授,美國美學會理事,紐約人文科學研究院院士。研究領域集中于德國美學理論,尤其關注音樂與哲學、政治和歷史的關系。其專著另有《音樂作品的想象博物館:音樂哲學論稿》、《有擇親和力:美學理論史文集》(Elective Affinities:Musical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 Theory,2008)等。應伯克利加州大學“布洛赫講壇”(Ernest Bloch Lectures)之邀,舉辦了題為“人聲之問”(The Quest for Voice)的系列講座。1998年,這些講稿在經過整理和擴充后形成了一部專著,交由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題為《人聲之問:論音樂、政治兼及哲學的限度》(The Quest for Voice:On Music,Politics,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這是戈爾教授繼《音樂作品的想象博物館》②Lydia Goehr:The Imaginary Museum of Musical Works: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usi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Revised 2007.已有中譯本,題為《音樂作品的想象博物館:音樂哲學論稿》,羅東暉譯,楊燕迪校,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8年版。之后發表的又一部音樂哲學論著,在音樂美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2015年,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購買了此書的簡體中譯版權,歷時5年完成了此書的中譯工作,將于近期出版。中譯本題為《人聲之問:瓦格納引發的音樂文化思想論辯》,由胡子岑、劉丹霓合作翻譯,筆者審校,收入筆者主編的“俄耳甫斯音樂譯叢·名家講壇讀本”系列。全書共五章:第一章“隱秘與緘默:音樂及其隱喻導論”;第二章“《師傅歌手》:瓦格納的典范訓示”;第三章“探問人聲:對音樂自律性的重新定位”;第四章“不完美實踐中關于完美表演的對立理想”;第五章“流亡中的音樂與音樂家:雙重人生的浪漫遺產”。在全書正文之前,另有概述各章主旨的“導言”。

圖 中譯本封面
從確定選題到正式出版,哲學家莉迪婭·戈爾的音樂哲學論著——《人聲之問》的中譯本經歷了非常曲折的過程,五六年間因故更換了兩次譯者,③第一位譯者因中途留學讀博而分身乏術,第二位譯者因身體忽然抱恙而力不從心,最后由胡子岑和劉丹霓兩位青年學者合作完成。胡子岑現于美國奧柏林學院攻讀文學學士、音樂學士雙學位,主修專業為音樂學、哲學和鋼琴演奏,她承擔了此書前三章的翻譯;劉丹霓現為天津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副教授,承擔了后兩章的翻譯任務。筆者幫助子岑同學翻譯了前三章的注釋、篇首語以及書后的索引,并對全書做了逐字逐句的統校。好在結局圓滿。之所以久歷波折,深層緣由或許在于,理解和翻譯此書具有顯著的難度。它的論題晦奧艱澀,論域復雜深廣,幾乎通篇貫穿著“形而上”議題,也夾雜著許多邏輯關系嚴密且復雜的長難句,技術性和思辨性都很強,對初事翻譯者而言尤其是艱巨的考驗。此外,書中的引證材料極其龐雜,許多證詞和引言出自其他哲學和文學著作,當這些話語被抽離了原書的語境后,理解和轉譯的困難也隨之增加。在這方面,兩位譯者鉆研了大量的參考文獻,這項努力部分地體現于她們為方便讀者理解而自主增加的注釋(即譯注)之中。筆者在審校時所做,是進一步提升英文理解的精準度和中文表述的明晰性,以使譯文更多呈現出“從容駕馭”的感覺。此書在旁征博引之際卷入了形形色色的文體和文風,如詩篇、文論、法典、劇本、銘文、格言、筆記、書信、故事等,如何在轉譯時顧及不同文體的文風差異,以使格言簡練、銘文古樸、詩歌合韻、證詞雄辯、私語親切、律條嚴謹,并(通過調節語序、精細斷句、搭配詞組、增刪文字等手段)為讀者預設最佳的“閱讀節奏”,都是審校者認真考慮的問題。
戈爾此書的核心意圖之一,在于對音樂中的形式主義論調做批評式回應。作者想要表明,音樂中內置有“人性”(human voice)因素,因而它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與“音樂外的因素”(extramusical)絕緣。被內置于音樂中的諸多人性因素包括:人類的激情、道德和直覺,人類自身的表現力、創造性和局限性,人類精神的升華性,人體自身的聲音媒介(嗓音)及其隱喻意義,人的(生理性)氣息,人的自由潛能,人的主觀性,人的社群屬性(如民族和宗教屬性),人的各種生活經驗,以及音樂的語言性,器樂的歌唱性,音樂對社會的批判性反映等。戈爾教授力圖探尋音樂中內在的各種人性聲音,這也是原書命題為“The Quest for Voice”的真正原因。現有譯名“人聲之問”是審校者在統校全書前初擬的方案,在統校全書后審校者隱約感到譯為“音樂中的人性之聲”更為妥帖,但也有資深譯者認為,“人聲之問”有朗朗上口、易于言傳的優點,加之修改書名的程序比較復雜,故而保留了這個譯名。
從“人性之聲”的角度審視音樂的形態和意義,可以在絕對音樂(absolute music)和標題音樂(programme music)這兩種對立主張之間搭起“橋梁”,后者視之為立論之基,而前者也無法將之輕易剝離。戈爾所質疑的“形式主義”立場及其背后錯綜復雜的思想體系和思維方式,因而被置于了“人性”——這是音樂作為人類創造物所被內置的因子——這一“砧板”之上加以錘煉:聚縮其內核,翻轉其側面,拉伸其潛能。此間,戈爾并非是要將“形式主義”完全否定,而是以“調合”姿態,兼而從其自身立場出發,尋找其漏洞和薄弱之處,為之注入新的視角和理念,以促使其“升級”和轉型,這在第三章的標題上就有反映——“探問人聲:對音樂自律性的重新定位”。這種既“攻”又“救”的辯證姿態,使戈爾的論述增加了論辯的魅力。這種辯證調合的姿態契合了戈爾在本書中貫穿強調的“雙重性”(doubleness,強調矛盾雙方的并置共存)哲學立場。實際上,她從“人性因子”中獲得的這一啟迪,也被用于闡釋其他問題,尤其是第五章“流亡中的音樂與音樂家:雙重人生的浪漫遺產”。
全書圍繞瓦格納的音樂思想展開,幾乎每個章節里都有對瓦格納音樂思想的回應。戈爾教授在導言中寫道,“審校者的考察……聚焦在理查德·瓦格納身上:他在自己的理論和實踐中,展示了從音樂的角度思考哲學和政治以及從哲學和政治的角度思考音樂的深遠意義,其影響之大無可匹敵”④[英]莉迪婭·戈爾:《人聲之問:瓦格納引發的音樂文化思想論辯》,胡子岑、劉丹霓譯,孫紅杰校,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導言,第2頁。。戈爾在書中涉及深入剖析并回應了瓦格納的言論、作品、思想及其蘊藏的深層政治意涵。瓦格納的許多言論在深層維度上支持了戈爾此書的中心議題——音樂中的人性之聲。瓦格納本人曾就音樂中的“內在人性”發表宣言:
“音樂”一詞最初被發明時,所涵蓋的并不僅僅是詩歌和音調的藝術。它也涵蓋了內在人(inner man)的若干藝術表現,諸如以聲音語言為媒介,采用最有說服力的實施手段,富有表現力地傳達自己的情感和直覺。⑤[英]莉迪婭·戈爾:《人聲之問:瓦格納引發的音樂文化思想論辯》,胡子岑、劉丹霓譯,孫紅杰校,第154-155頁。
瓦格納的音樂著述和音樂作品強有力地彰顯了這種音樂思想,以至于哲學家尼采曾對瓦格納音樂中的“人性之聲”奉獻如下一段頌詞:
對于瓦格納這位音樂家,我們可以整體評價如下:他賦予了自然中那些無望言說之物以言語;他不相信世上有必然無聲之物。他甚至縱身于黎明、日出、森林、迷霧、溝壑、山峰、寂夜和月光之中,發現了它們那秘而不宣的共同渴望——想要發聲。⑥[英]莉迪婭·戈爾:《人聲之問:瓦格納引發的音樂文化思想論辯》,胡子岑、劉丹霓譯,孫紅杰校,篇首語第四則。
這也是為何我們要在中譯本副標題上點出“瓦格納”這一關鍵詞的緣由。我們希望讀者注意到,這本論著有助于讀者更好地認識瓦格納的偉大性,尤其是這位音樂巨人在文化和哲學領域中產生的深遠影響。除瓦格納和尼采之外,戈爾此書還對歷史上其他許多學者(從蘇格拉底到阿多諾)相關于音樂人性的言論進行了剖析和回應,包括蘇格拉底所謂“繆斯藝術旨在培育靈魂”的信念,盧梭關于語言起源的深刻洞見,尼采針對“為藝術而藝術”的評論,漢斯立克的純音樂觀,以及古爾德將“看不見表演者”的錄音奉為“完美演繹”的理想主張等。
此書是1997年戈爾教授在加州大學“布洛赫講壇”上的系列講座文稿,在出版時經過了大幅度的書面化修訂,以至于它們不再像是“講稿”,而更像是“論文”。事實上,作為講座的發言,本書的內容似乎偏多,議題也偏重了一些,尤其是第一章和第三章的內容,需要聆聽者有較多關于音樂哲學的知識儲備。考慮到此類講壇的聽眾群體多為綜合性高校各專業的在校生,于是不免令人好奇——戈爾教授這些講稿的原貌如何?當時的講座現場是怎樣的氛圍?它們曾引起過怎樣的反響?這一反常現象也從側面反映出了“布洛赫講壇”作為加州大學一個重要學術品牌所具有的高端品質。
本書較為典型地體現了戈爾教授的著述風格:她慣于機敏而巧妙地提出問題,迂回而鋪陳地加以論證,最后以開放且略帶延伸的方式進行總結。這種寫作風格具有引人入勝的奇妙效應,或可援引“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這句詩文來形容。置身于戈爾教授的宏篇大論之中,讀者有時會抓不住作者的主要思路或核心觀點,但在豐富的“岔道”上依然有絕妙幽深的“風景”。審校者在校譯全書的過程中無數次感到,戈爾所引證的材料是那樣有趣,以至于屢屢使人想要立刻找來那些文獻去一探究竟。而當審校者聚精會神校畢全書之后,所獲得的并不是對某些問題有了確定答案這樣的滿足感,而是對更多問題產生了強烈好奇的興奮感。換言之,戈爾的論證過程極具吸引力,顯示了一位資深哲學家的開闊視野和精細思維,就像布道的老法師有抖不完的“包袱”那樣,信息量龐大,以至于讀著讀著會讓你忘記最初的問題是什么,于是也就不在乎到底有沒有明確的結論了,而且此時你頭腦中很可能已被植入了更多懸而未決的新問題。無怪乎國外的學術期刊紛紛評價此書為:一本“引人深思的書”(thought-provoking book),一本“具有歷險效應的書”(an adventurous book),一本包含“高度可讀性”(highly readable)的書,一本體現了“非凡智力成就”(extraordinary intellectual feat)的書。⑦這些評價均引自原書封底,所涉及的國外學術期刊依次為《Music&Letters》《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The Wagner Society of New York》《Notes》。
正因此書有上述特點,它可以讓具有不同知識背景、懷著不同閱讀旨趣的讀者從中受益——哪怕你沒有時間通讀全書,而僅僅是瀏覽其中的某些章節或段落,也能有明確的收獲。瓦格納的樂迷們可以深入了解這位作曲家的戲劇理論、政治立場、音樂思想,其歌劇《紐倫堡的師傅歌手》的戲劇立意,他和叔本華、尼采、漢斯立克等人的關系,他的歷史、文化影響以及偉大性問題。音樂表演者和音樂表演學者可以讀到帕格尼尼、李斯特、古爾德等人的表演風格或表演觀,以及作曲家瓦格納、德彪西、欣德米特,哲學家尼采,文藝批評家薩義德等人對于表演實踐的精辟論述,并獲得有關表演的原則、境界、哲學等的理論知識。音樂社會學家可以讀到音樂的社會功能和政治意義,政治審查制度對音樂的影響,二戰期間流亡美國的音樂家境遇等方面的內容。而對音樂美學感興趣的讀者,則可以讀到蘇格拉底、盧梭、康德、叔本華、瓦格納、漢斯立克、尼采、阿多諾藝術(音樂)觀的某些方面,并獲得有關形式主義、自律論、“純音樂”或“音樂外”的意義、音樂的人性、哲性、政治性、語言性(或稱人文關懷)等眾多議題的認識。
審校譯稿既是改善譯文、培養譯者的過程,更是審校者自我學習和提升的寶貴經歷,它迫使審校者努力站在較高的立場上,對作者的思路、文風、觀點、立場以及字面背后的言外之意進行考量,以此來引導譯文的品格和風貌。這是一個持續鉆研和推敲的過程,其間不僅要為應接不暇的新術語和陌生表達謀定合適的譯名,也要對一些不夠準確的通用譯名進行修訂,在此試舉三例。
案例一是個音樂術語。瓦格納的歌劇“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有多種譯名,有作《紐倫堡的名歌手》,有作《紐倫堡的工匠歌手》,有作《紐倫堡的工匠師傅歌手》。審校者經過充分考慮,決定采用“紐倫堡的師傅歌手”這個譯名,理由是:相比于“名歌手”和“工匠歌手”而言,“師傅歌手”這個譯名最能傳達“Meistersinger”一詞的本義。在歐洲15-16世紀的行會傳統中,工匠的職業生涯被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作為“學徒”(apprentice),拜于某位師傅門下,在他的作坊內經歷5-7年的學藝期,此間他能獲得基本生活保障,但不領薪水;第二階段是成為“熟工”(journeyman),學藝期滿后留在師傅的作坊里操練技藝,此間他獲得薪水,并開始積累資本,生活待遇受行會保護;第三階段是自己升格為“師傅”(master),此時他已積累了足夠的資本,可以在行會的支持下“自立門戶”開作坊授徒。所謂“師傅歌手”,即指“師傅級別的歌手”。戈爾此書的第二章集中考察了這部歌劇的戲劇立意及其影射的政治立場,并以它作為瓦格納音樂思想的范例。
案例二是個人類學術語。“invented tradi-tions”一詞在人類學界常被譯為“被發明的傳統”或“傳統的發明”。不過審校者認為,“發明”一詞并不十分貼切。且不說該譯名在漢語中主要指的是科技領域中的革新創造,移諸人文語境會顯得突兀;而且,在我們的常識中,事物一旦被“發明”便會成為確鑿的“事實”,而被發明的“傳統”卻始終具有某種“非真實性”。有鑒于此,審校者在校譯中將這一術語改稱為“被虛構的傳統”。戈爾在論述瓦格納歌劇《紐倫堡的師傅歌手》時援引了這個術語,她指出瓦格納在劇中針對中世紀紐倫堡行會音樂家歌詠比賽規則的描述,滲入了浪漫主義時期的音樂美學思想,是一種刻意而為的“時代誤置”,旨在為自己的音樂觀“嫁接”一種古老的文化“根基”,以使它聽起來“自然”“純正”,仿佛已然是綿延存在了許多世紀的“真理”,這也就是戈爾所說“被虛構的傳統”。
案例三是個哲學術語。戈爾在舉證歷代先哲關于“音樂中的人性之聲”的論述時提到了蘇格拉底所謂的“mousikē”。教育界通常把這一術語譯為“教育”或“美育”。然而通觀戈爾此書會發覺,譯為“教育”或“美育”都不合適。這一古希臘語詞的意義較為豐富,它在詞形上相當于如今的“music”,但并不單指音樂,而是指繆斯(Muse)女神們的藝術,故而是涉及多種科學和藝術門類的綜合概念,審校者建議將其直譯為“繆斯藝術”,保持其字面意思。此舉的便利在于,它能照顧使用該詞的多種語境,保留這個術語在名稱上的統一性,而若通譯為“教育”或“美育”,則會在許多語境中顯得不夠通順或準確,而如果每次都依照實際語境對中文譯名進行調整,又會抹煞該詞作為一個術語所具有的確定性。為了說明這一點,在此將列舉戈爾應用該詞的四處語境供讀者品酌、對比。戈爾第一次提到該詞時說,“‘音樂’這一現代隱喻,對應于蘇格拉底所說的‘mousikē’[繆斯藝術],蘇格拉底曾用這個詞來形容作為人文科學[liberal art]的哲學實踐。”⑧[英]莉迪婭·戈爾:《人聲之問:瓦格納引發的音樂文化思想論辯》,胡子岑、劉丹霓譯,孫紅杰校,第41頁。第二次說“[瓦格納]整體藝術品中對表達的強調,將瓦格納的企圖與古代蘇格拉底對mousikē[繆斯藝術]的追求聯系起來”。第三次說:
蘇格拉底曾說過,哲學是為死亡而受訓。它是為根植在欲望中的靈魂所做的一種準備,為的是了解美德[the Good],并遵照美德生活。它是一種道德追求,旨在保護靈魂不受肉體、世俗欲望和短暫滿足的誘惑,不受權利、意見和外表的腐蝕。實踐[practise]哲學,對蘇格拉底來說,就是去實踐最高的mousikē[繆斯藝術]……⑨[英]莉迪婭·戈爾:《人聲之問:瓦格納引發的音樂文化思想論辯》,胡子岑、劉丹霓譯,孫紅杰校,第65-66頁。
第四次說:“當音樂所伴隨的情節或氛圍與音樂本身相關時,它的秘密或無法表達的意義,就會與mousikē[繆斯藝術]的啟示密切融合——這是任何只憑言語作為表達媒介的事物都無法做到的。”⑩[英]莉迪婭·戈爾:《人聲之問:瓦格納引發的音樂文化思想論辯》,胡子岑、劉丹霓譯,孫紅杰校,第123頁。如果將上述四處mousikē通譯為“教育”而不是“繆斯藝術”,則在本書語境中會令人費解,因為盡管“教育”一詞的本義相當寬泛,但學科語境中的“教育”卻同時也是相對具體的“單門”學科,這會使讀者在理解mousikē一詞與“人文學科的哲學實踐”“整體藝術品的表達意味”“培育靈魂的道德訴求”“音樂外的意義”等概念之間的深層聯系時,變得晦奧難懂甚至邏輯不通,而譯為“繆斯藝術”則反而能使句意更明確。
此外,某些漢譯名著的現成譯文在被選入這個譯本時,審校者也會根據戈爾著作的實際語境做出必要的調整。例如,在中譯本頁邊碼第48頁的注釋中,審校者對柏拉圖《斐多篇》的現成中譯文進行了改動。實際上戈爾教授在援引某些非英語著作的英譯本時也會如此,例如,在中譯本頁邊碼第41頁,她對阿多諾觀點的現成英譯文進行了調整。總之,審校者所做的一切,都只為使譯文更顯準確、流暢和通達。
如果說對于學術著作而言,翻譯是最好的精讀方式,那么校譯(由于有更多的考量因素)則不僅能最好地精讀著作本身,還能更好地促進知識的“內化”,使之融入既有的素養。審校者從中獲得的回報,是愈發擴展的知識結構,愈發敏銳的學術眼光,愈發考究的書面語言,以及——最為重要的——愈發精細的思維方式。也正因如此,筆者會心甘情愿地在不收取任何費用的前提下,對涉及多種學科背景的一部又一部譯著進行字斟句酌的通篇審校,期待能在這條孤寂清冷卻也不無風景的狹路之上偶遇同行。毋庸諱言,在筆者審校的譯著中也會存在因自身功力不及而造成的疏忽錯訛,懇望讀者及時指出。
《人聲之問》中譯本的推出,應能對中國音樂學多個學科領域的研究起到推動作用:為音樂美學中對于音樂意義的持續探問提供參考,為西方音樂史學中對于瓦格納戲劇觀念和思想成就的認識提供資料,為音樂人類學中對于音樂、社會、文化、政治關系的闡釋提供觀察視角,以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為當下在中國學界已呼之欲出的“音樂表演學”提供文獻和理論的雙重支持。本書第四章“不完美實踐中關于完美表演的對立理想”以三萬五千字的篇幅,對音樂表演中“強調音樂作品的形式構思”(指向作曲家)與“強調音樂表演的詮釋過程”(指向表演家)這兩種理想的錯綜關系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對比和剖析,向讀者展示了表演實踐實際存在的復雜性以及表演理論所可能企及的深度,其中對表演家、批評家的許多精彩言論和表演理論中的許多經典文獻進行了評注,耐人尋味。此外,戈爾基于音樂中的“人性之聲”而總結的一番妙語——“作為一種普適性的語言,音樂獲得了深刻的意義:它囊獲了人類所致力的全部成就,‘人類意愿和情感的最深層秘密’”?[英]莉迪婭·戈爾:《人聲之問:瓦格納引發的音樂文化思想論辯》,胡子岑、劉丹霓譯,孫紅杰校,第24頁。——也定能引發深信音樂學作為“人文學科”的廣大知識分子的心靈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