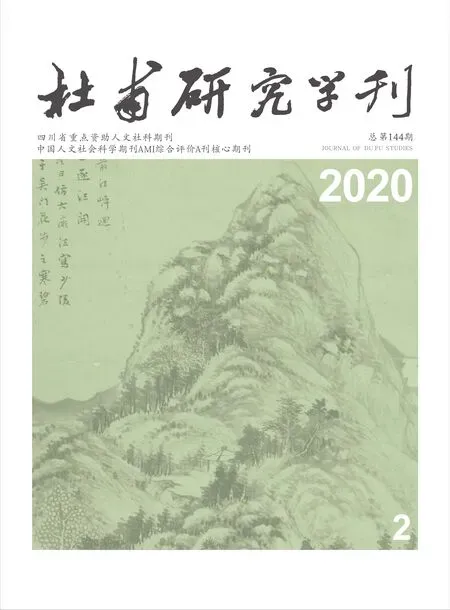成州杜甫遺跡考論
王 超
乾元二年(759)十月,杜甫攜家自秦州出發,前往成州同谷縣(今甘肅成縣)。《元和郡縣圖志》載:“同谷縣,本漢下辨道地,屬武都郡。故氐白馬王國。后魏宣武帝于此置廣業郡并白石縣,恭帝改白石為同谷縣。隋開皇三年罷郡,以縣屬康州,大業初屬鳳州,貞觀元年屬成州。”此時,成州下轄上祿、同谷、長道三縣,州治在上祿縣。同谷縣位于上祿縣東南,較為偏僻。杜甫在《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中講述了“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的凄慘遭遇,這也是詩人一生中最為困頓的時期。杜甫雖然只在同谷停留了不到一個月,卻留下了不少杰作,后人在登臨杜甫同谷詩中所描繪的地點時,無不肅然感懷。宋人在尋訪杜甫同谷草堂原址的基礎上建祠祭祀,留下了不朽的詩圣遺跡。
一、成州杜甫故居方位考辨
杜甫在同谷寓居時間雖短,但其故宅的方位卻一直為后人所關注。自晚唐至今,學者皆有考證研究。
(一)唐人趙鴻所指杜甫茅茨
杜甫在同谷的寓居之所,唐人趙鴻已有紀念題刻。錢謙益《錢注杜詩》載:“唐咸通十四載,西康州刺史趙鴻刻《萬丈潭》詩,又題《杜甫同谷茅茨》曰:‘工部棲遲后,鄰家大半無。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大雅》何人繼,全生此地孤。孤云飛鳥什,空勒舊山隅。’鴻曰:‘萬丈潭在公宅西,洪濤蒼石,山徑岸壁,如目見之。’”唐懿宗咸通十四年為公元873年,此時距杜甫離開同谷已有114年,故趙鴻《栗亭》詩又云:“杜甫栗亭詩,詩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題記今何有?”
趙鴻時任西康州刺史,此西康州即在同谷縣。《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四·山南道》載:“同谷,中下。武德元年以縣置西康州,貞觀元年州廢,來屬,咸通十三年復置。”由此可知,就在同谷再置西康州的次年,刺史趙鴻為杜甫樹立了紀念題刻,并作詩立石緬懷杜甫。依趙鴻所言,萬丈潭在杜甫茅茨以西。南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七〇《同慶府》則載:“萬丈潭,在同谷縣東南七里。《舊經》:‘昔有黑龍自潭飛出。’”。這就是唐宋文獻對杜甫故宅方位的記載。
清乾隆《成縣新志》則在唐宋文獻的基礎上,進一步引入了其他地標:“萬丈潭,在鳳凰山下、飛龍峽中,距縣東南七里。相傳有龍自潭飛出,洪濤蒼石,其深莫測。杜甫祠在其口。有詩云‘龍依積水蟠,窟厭萬丈內’,即此。”那么,鳳凰山、飛龍峽又在何處?《方輿勝覽》載:“鳳凰山,在州東南十里。下為鳳村溪,中有二石如闕。……相傳漢世有鳳凰棲其上,號鳳凰臺。”下引杜甫《鳳凰臺》詩。據此,鳳凰山在萬丈潭東南方,與萬丈潭鄰近。但同書又載:“飛龍峽,在仇池山下。氐楊飛龍者據仇池,因得名。”而仇池山則在“郡西百里”,與鳳凰山、萬丈潭相去甚遠。這顯然與乾隆《成縣新志》中鳳凰山和飛龍峽同在一處的記載存在矛盾。不過《成縣新志》對此另有解釋:“飛龍峽有二,一在仇池山下,晉氐楊飛龍據仇池,因名。一在縣之東南七里,河水經流,相傳有龍飛出,故名。峽口有杜甫草堂。杜詩:‘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即此。”可知,成縣有兩處飛龍峽,與杜甫故宅相關的是后者。這便可以解釋萬丈潭、鳳凰山、飛龍峽的位置關系了。即自同谷縣城東南行七里,入飛龍峽,峽口為萬丈潭,再行三里,有鳳凰山,山上有鳳凰臺。趙鴻所說的萬丈潭在杜甫茅茨以西,則杜甫茅茨位于萬丈潭與鳳凰山之間。
(二)宋人晁說之因宅興祠
北宋宣和五年(1123),成州知州晁說之作《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云:“祠望鳳凰臺,而臨百丈潭,皆公昔日所為詩賦之所也。公去此而汗漫之游遠矣哉。而此邦之人思公,因石林之虛徐,溪月之澄霽,則尚曰:‘公之故廬,今公在是也。’予嘗北至鄜畤,觀公三川之居,愛之矣,而此又其勝也。不知成都浣花之居,復又何如哉?信乎!居室可以觀士也已。同谷秀才趙惟恭捐地五畝,縣涑水郭慥始立祠,而屬余為之記。”由此記述,成州杜工部祠介于鳳凰臺與百丈潭之間,是在“故廬”的原址上興建的祠堂。宣和六年(1124)晁氏又作《發興閣記》,再次說明:“予始因子美之故居而祠之,距祠堂而南還十步有萬丈潭。”顯然,“百丈潭”就是“萬丈潭”,宋人因故居所在而選址,已是非常了然。
成州杜公祠建成后,再未出現遷移改建的情況。今杜公祠內有南宋成州知州宇文子震詩碑,詩云:“燕寢香殘日欲西,來尋陳跡路逶迤。江濤動蕩一何壯,石壁崔嵬也自奇。雞犬便殊塵世事,蛟龍長護老翁詩。草堂歘見垂扁榜,卻憶身游濯錦時。”碑末跋:“右賦龍峽草堂。紹熙癸丑(1193)□□十七日,郡守□都宇文子震題。”,由宇文子震詩及題跋可知,此地就是自唐以來人們認定的杜甫茅茨所在。其所謂“龍峽”,《元一統志》亦載:“杜少陵故居。在同谷縣龍峽之東。天寶末避亂居此,所為‘面勢龍泓頭’是也。”明代陜西提刑按察司副使李昆《訪杜少陵詞》亦云:“侵晨入龍峽,杳靄足云霧。”可知“龍峽”即后代文獻所說的“飛龍峽”,這也說明了明清時人亦認定杜公祠所在地就是杜甫同谷茅茨所在。
(三)杜甫故宅方位異議考辨
對杜甫同谷故宅所在地,后人也存在不同意見。《方輿勝覽》卷七〇《同慶府》載:“飛龍峽,在仇池山下。氐楊飛龍者據仇池,因得名。其東乃杜甫天寶避亂居此,有龍灣、虎穴。杜甫詩:‘停驂龍潭云,回首虎崖石。’又《寄贊上人》詩‘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認為杜甫曾避居仇池山飛龍峽。但杜甫避居仇池山的說法并不可信。
首先,“停驂龍潭云,回首虎崖石”二句見杜甫《發同谷縣》,題下原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可知此詩是一首紀行詩。此二句之前二句云:“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之后二句云:“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由詩意分析,“停驂龍潭云,回首虎崖石”二句,寫的或是同谷寓所之地標,或是旅途中所見景物。從地理方位與交通路線看,杜甫自同谷赴劍南,詩中景物應與遠在同谷縣西百里的仇池山無關。其次,此飛龍峽在仇池山下,仇池山則在上祿縣境內。《元和郡縣圖志》載:“仇池山,在(上祿)縣南八十里。”按前引《方輿勝覽》,仇池山在同谷以西百里。因此,杜甫無論是自秦州至同谷,還是自同谷赴劍南,沿途絕不會經過仇池山,更不可能避居于此了。再次,《寄贊上人》詩云:“一昨陪錫杖,卜鄰南山幽。……茅屋買兼土,斯焉心所求。近聞西枝西,有谷杉黍稠。……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荊具茶茗,徑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可知杜甫此詩是為感謝贊上人陪同尋找棲身之所。“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二句應是對贊上人所居環境,或是對備選居處“西枝西”周邊景物的描繪;杜甫又說愿與贊公為鄰,可見贊公的居所與“西枝西”相鄰。但依據宋代以來的舊說,除《大云寺贊公房四首》作于長安之外,普遍認為《宿贊公房》《寄贊上人》《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均是杜甫移居秦州時與贊公交往所作,屬“秦州詩”之列。這自然就否定了杜甫避居仇池山的可能。明人王嗣奭則指“成縣有杜甫故居,注引‘虎穴’、‘龍泓’之詩為證,則居在西枝村之西;然公似未曾居西枝,恐當以同谷為是”。按此說,杜甫與贊公應相遇于同谷。近年亦有學者據宋人《輿地碑記目》卷四“成州碑記”所載:“大云寺石碑,在鳳凰山上。去州七里。創始莫考。殿后崖上有刻字云‘漢永平十二年’,又經閣崖上刻云‘梁大同九年’”,指同谷鳳凰山亦有大云寺,且杜甫與贊公交往詩歌皆與同谷環境相合。此不可定論,但可備一說。若贊公確居同谷鳳凰山大云寺,亦可證杜甫意欲卜居鳳凰山麓,與贊公毗鄰居于飛龍峽中,仇池山便更不可能有杜甫寓所了。
杜甫隱居仇池山飛龍峽之說,應當是根據其《秦州雜詩二十首》之十四“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云邊”演繹推想而來。因《秦州雜詩二十首》最末首有“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朱鶴齡據此注曰:“前詩聞東柯谷之勝而欲卜居,此述仇池穴之勝而欲卜居也。觀卒章‘讀記憶仇池’,則前六句皆是引記中語。”此說甚是。杜甫因讀仇池文獻,想仇池山之勝景,故而發出“何時一茅屋,送老白云邊”的感慨。秦州地近仇池山,但杜甫未至仇池山,更未隱居仇池山下之飛龍峽當為定論。
另一位對杜甫同谷舊居所在地提出間接質疑的是嚴耕望先生。嚴耕望根據《杜詩詳注》卷八自秦州赴蜀詩,對杜甫自秦州入蜀行程作了詳盡考證。他認為“《杜集》編次,此詩(指《鳳凰臺》)次《積草嶺》《泥功山》之后,《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之前,似當在成州東南至同谷道上作。然地在同谷東南十里,杜翁自成州南來之旅似不應先繞經同谷東南。今檢各本標題下皆有原注:‘山峻,人不至高頂’一句。按通道所行,例不經高頂。杜翁此段行程諸詩皆無此原注,惟此題有之,似為杜翁寓居同谷時游覽之作,作于七歌之前,故次于成州東南來最后一詩《泥功山》之后,而實非旅程中所作也”。針對《萬丈潭》一詩,嚴耕望又云:“《同谷七歌》之后,《發同谷》之前又有《萬丈潭》一詩。……是萬丈潭與鳳凰臺為同一地區,惟臺又在潭東南三里耳。此詩亦游覽時作,非行旅中作也。”
嚴耕望認為《鳳凰臺》《萬丈潭》二詩并非作于自秦州至同谷途中是極為準確的,但認為二詩僅是游覽所作,理由卻并不充分。嚴耕望只考慮了杜甫行程所經,而未考慮到杜甫寓居于此的問題。杜甫《木皮嶺》詩云:“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前引《方輿勝覽》載:“鳳凰山,在州東南十里。下為鳳村溪。”清楊倫《杜詩鏡銓》卷七引“朱注”亦認為“鳳凰村當與鳳凰臺相近,在同谷。”則杜甫想念之鳳凰村,確實可能是寓居之地。嚴耕望認為:“詩云:‘尚想鳳凰村’,似此行未經過臺村,只是回想前次登臨賦詩耳。”如果將杜甫回想賦詩之地改為杜甫回想同谷茅茨,同樣是可以說得通的。
總而言之,唐咸通年間,趙鴻即認為杜甫同谷茅茨在萬丈潭以東。后代文獻引入了鳳凰山、飛龍峽等地標更加明確地標明了杜甫故宅的確切位置。宋人晁說之在故宅原址創建了祠堂,此后歷代皆在此地祭祀杜甫。仇池山飛龍峽有杜甫故居之說并不可信,嚴耕望僅將鳳凰臺、萬丈潭當作杜甫游覽賦詩之地,也并不確實。在沒有更多文獻證據的情況下,杜甫同谷故居“望鳳凰臺,而臨百丈潭”是切實可信的。
二、成州杜公祠建祠緣由
北宋宣和五年(1123),成州知州晁說之在杜甫同谷故宅處興建了杜工部祠,并作《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今人多以此文作為晁說之建祠的歷史依據引用。然而,晁氏文中敘述杜公祠創建經過的文字極少,只在文末提及了因宅興祠,同谷秀才趙惟恭捐地五畝,同谷縣知縣涑水郭慥主持興建等情況。該文的大部分筆墨則花在了論述建祠因由以及杜甫的地位評價之上。深入分析此文則可發現,前文所述的“因宅興祠”,僅僅是晁氏建祠時的選址理由罷了,并非其建祠的真正原因。晁氏到底因何建祠?建祠一事又與杜甫的地位評價有何聯系?這是前人未曾在文章之中深入發掘的。
(一)晁說之“欲揚先抑”帶來的懸念
晁說之認為歷史上被后代祭祀的人物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古往今來的帝王將相,他們為后人祭祀是由于“乘時奮厲,冒敗虎狼,死守以身,為天下臨沖;或巖廊嚬笑,以治易亂,即危而安”,此類人是亂世豪杰或治世能臣之屬,因此“其在鼎彝之外,而人有奉焉”;第二類則是有功德于一方的地方大員,他們“為民之父母,斯民謠頌之不足,取其姓以名其子孫,久益不能忘”,此類人是古時被稱為父母官的地方主政官員,因造福一方,“則一郡之邑祠之”;最后一類則是“躬德高隱,崇仁篤行,若節婦、孝女,有功于風俗者”,此類人是百姓身邊德行高潔之人,理應“一鄉一社祠之”。上述三項標準,杜甫顯然都不符合。這就為晁說之講述真正的建祠緣由設下了巨大懸念。晁氏行文至此,欲揚先抑,就此評價道:“顧惟老儒士,身屯喪亂,羈旅流寓。呻吟饑寒之余,數百年之后,即其故廬而祠焉,如吾同谷之于杜工部者,殆未之或有也。”總而言之,為杜甫建祠祭祀是一種極其特殊的情況。
晁氏隨即進一步指出,杜甫得到祠祀并非“名高而得之”,“當時王維之名出杜之上。蓋有天子宰相之目,且眾方才李白而多之也”,更何況唐天寶年間“人物特盛”,高適、岑參、孟浩然、崔顥諸多詩人“粲然振耀于世,未肯少自屈,而人亦莫敢致之也”。既然在詩人輩出的天寶年間,時人認為杜甫之名高不如王維,詩才亦不及李白,那么如今為其建祠的原因就需要大書特書了。
至此,晁氏才引出杜甫區別于盛唐其他詩人之處:“然有良玉必有善賈,厚矣!韓文公之德吾工部也。自是而工部嶷嶷絕去,一代頡頏,不可揉屈之士而岳立矣。”顯然,晁氏將韓愈對于杜甫的充分肯定,視為杜甫可以獲得崇祀的重要條件。這在今天看來,理由并不充分,然而放在晁氏當時的語境中,卻隱含著諸多深意。
(二)儒家道統觀引發的建祠動機
眾所周知,與韓愈同時期的白居易雖然對杜甫的評價高于李白,但總體上持“李、杜交譏”的態度,元稹則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中對杜甫評價極高,但對李白則極力貶斥。韓愈對元白二人的觀點頗為不齒,并在《調張籍》中指出“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很明顯,韓愈的觀點是李杜并尊,皆不可謗傷。
晁說之作為杜甫的仰慕者,雖然認同韓愈尊杜的觀點,但對韓愈李杜并重之說頗有微詞,遺憾道:“然猶惜也,何庸李白之抗邪!昔夫子錄秦詩而不錄楚詩。蓋秦有周之遺俗,如玉之人在板屋,則傷之也。楚則僭周而王矣,滄浪之水既以濯吾纓,雖濁,忍以濯吾足哉!李則楚也,亦不得與杜并矣,況余子哉?”晁氏認為孔子整理《詩經》,有《秦風》而無《楚風》,是因為秦繼承了西周“遺俗”;而楚國國君自稱楚王,是周禮的破壞者與僭越者。《秦風·小戎》有:“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之句,讀之感傷,而《楚辭》則不然。屈原流放于江潭,有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此歌孔子也曾聽過,《孟子·離婁上》云:“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晁氏據此認為孔子明明聽過此歌,卻不收入《詩》中,足見孔子對楚歌,乃至對楚國的態度了。
晁氏以此論為基礎,進而引出了杜甫類秦、李白類楚的觀點。李白曾因加入了永王集團而遭到貶謫流放。晁氏將李白比為“楚風”,是類比“楚則僭周而王”,將李白視為唐王朝統治秩序的破壞者與僭越者。反觀安史之亂中只身奔赴行在的杜甫,則是忠君愛國的典范,自然是“秦風”了。正因如此,晁氏才認為韓愈李杜并重的觀點存在問題,需要予以糾正。
耐人尋味的是,元、白、韓等人對于李杜高下的品評無論公正與否,大抵還是從文學標準出發的,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晁說之看似持論與元稹相似,同樣尊杜貶李,但二者的出發點卻截然不同。晁說之完全是出于政治標準,即韓愈創立的儒家“道統”說,其《原道》云:“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韓愈的學說后為宋儒繼承發展,最終成為“道”或“理”,為萬事萬物的本源。晁氏論李杜優劣,考量標準就是杜甫符合道統要求,李白則不符合。
這就解釋了為何晁氏明明在觀點上與元稹相似,但卻一定要越過元稹,引出韓愈對杜甫的看法來說明杜甫有無資格被后人建祠祭祀,而后又費盡心思試圖糾正韓愈李杜并重的看法。果不其然,晁氏在后文中立刻與元稹劃清界限,并解釋了自己無視元稹的理由:“彼元微之,讒謟小人也,身不知裴度、李宗閔之邪正,尚何有于李杜之優劣也邪?”這便是告訴旁人,他本人雖然與元稹都尊杜貶李,但卻有本質區別:自己尊杜貶李,是占據了道統大義的行為;而元稹身為“讒謟小人”,連品評李杜高下的基本資格都不具備,當然也就更不配與自己持相似觀點了。
晁說之的一系列論斷,看似強詞奪理,卻又能環環相扣,在其話語體系之中形成邏輯自洽。晁氏從道統觀出發,認為杜甫符合道統,而李白不符合,所以要尊杜貶李。但創立道統的韓愈雖然尊杜,卻同樣尊李,所以需要糾正。糾正的最佳方式便是在貶李的同時全力突出杜甫,顯然,建祠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與此同時,晁氏還需要與同樣尊杜貶李,卻“人品卑劣”的元稹劃清界限,體現二者在“尊杜”這件事上的本質區別。如此一來,為杜甫創建祠堂便有了足夠的動機。
(三)杜甫“一發忠義之誠”提供的建祠理據
除了道統觀引發的建祠動機外,晁說之對杜甫的敬仰也的確發自內心。他認為唐代中后期有很多學杜的詩人。“然前乎韓而詩名之重者錢起,后有李商隱、杜牧、張祜,晚惟司空圖,是五子之詩,其源皆出諸杜者也。”入宋之后,“本朝王元之(王禹偁)學白公,楊大年(楊億)矯之,專尚李義山(李商隱),歐陽公(歐陽修)又矯楊而歸韓門,而梅圣俞(梅堯臣)則法韋蘇州(韋應物)者也。”但這些都不是正途,學杜才是正宗,“實自王原叔(王洙)始勤于工部之數集,定著一書,懸諸日月矣。
晁氏進而推崇道:“唯知其為人,世濟忠義,遭時艱難,所感者益深,則真識其詩之所以尊,而宜夫數百年之后,即其流寓之地而祠之不忘也。工部之詩,一發諸忠義之誠,雖取以配《國風》之怨、《大雅》之群,可也。或玩其英華而不薦其實,或力索故事之微而自謂有得者,不亦負乎!”杜甫生平艱難,仍不忘忠義。蘊含“忠義之誠”的杜詩,在晁氏看來,已非僅止于繼承《風》《雅》,而是直接可與《風》《雅》相比,評價可謂至高。與此同時,晁氏亦不忘提醒后學,應當透過杜詩得其本質,而不是“玩其英華”“力索故事之微”,關注那些無關宏旨的細節,因為杜詩的本質特征就在“一發忠義之誠”。
顯然,在晁氏看來,杜甫既是儒家道統的代表人物,其詩文又具備“忠義之誠”,如此人物,當然應該景仰至極。在自己治下為杜甫建祠祭祀,既能夠弘揚杜甫的“忠義”,教化一方;又可以讓文人認識到學杜才是詩學正途。這不僅增加了晁氏建祠的主觀意愿,也為建祠一事提供了充足的理據。
綜合以上三點可見,晁說之在成州為杜甫建祠祭祀的原因是比較復雜的。首先,他就任成州知州,其轄下有杜甫故宅,這是建祠的前提條件;其次,晁氏認為杜甫雖然不符合一般祠祀的三個原則,但完全符合儒家道統。想要糾正韓愈李杜并重的觀點,便需要全力突出杜甫的地位;同時也想將自己與同樣尊杜貶李卻有人品問題的元稹區別開來,這兩個目的皆可通過建祠來實現,這便具備了直接的建祠動機。最后,建祠既能表達晁氏本人對杜甫的尊崇,又能以杜甫的“忠義之誠”教化一方,還能宣揚詩學正途,這些益處都為建祠提供了充足的理據。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晁氏為杜甫建祠之事也就理所當然了。
三、明清時期成縣杜公祠“以詩代文”傳統
成州杜公祠在文化傳統上也很有獨到之處。成州杜公祠歷史上僅有晁說之一篇篇幅較長的碑記,這與別處杜公祠創建、重修碑記眾多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尤其在明清兩代五百余年中,成縣(明洪武十年改州為縣)杜公祠數次重修,多以詩紀事,僅存有萬歷四十六年(戊午,1618)管應律《重建杜少陵祠記》一篇簡短記文。有趣的是,管氏碑記上半部分鐫刻著當時倡建之人知縣趙相宇的題詩一首。由此可見,碑記鮮少并非失傳所致,而是古人有意以紀事詩代替碑記。在這樣的風尚下,杜公祠內題詩數量很多。據統計,成縣杜公祠現存前代詩碑十三通,“其中南宋1品、明8品、清3品、民國1品”。如果再將乾隆《成縣新志》中收錄的杜公祠題詩計算在內,數量更為豐富。就目前所見,自南宋成州知州宇文子震在此題詩刻碑以來,后人修葺杜公祠或到此瞻拜杜甫時,形成了皆以詩歌紀事繪景、表情達意的文學傳統。這種文學傳統或許可以稱之為“以詩代文”,它不僅造成了成縣杜公祠碑記少而題詩多的情況,由此也形成了成縣杜公祠的獨特文化現象。
明清兩代的成縣杜公祠題詩數量既多,內容也十分豐富。其主要價值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介紹明清成縣杜公祠的重修情況
由現存文獻可知明代成縣杜公祠曾有兩次重修。明正德五年(1510)八月,陜西按察司僉事李昆升任陜西按察司副使,分管提調陜西學校。作為陜西教育的最高負責人,李昆的職責是巡察轄區內的科舉考試及學校教育工作。正德八年(1513)六月,李昆與陜西按察司僉事分巡隴右道李璋同游杜公祠。此時的杜公祠“蕭條翳榛莽,搖落傷指顧。兩楹蓋數瓦,垣毀門不具。四壁繪浮屠,訛舛更堪怒。拂蘚讀殘碑,字漫不可句”,建筑殘破不堪,李昆等人見此情景感慨道:“東渠臺中彥,感此激情愫。創始伊何人?興仆吾可作。抗手進縣令,茲亦豈末務?我當力規畫,爾宜亟舉措。會使道路人,從知古賢慕。予聞重嘆息,因之資覺悟。”李昆、李璋二人特命成縣知縣重修杜公祠。這是目前所知明代首次重修杜公祠的基本情況。
明代第二次重修杜公祠是在萬歷四十六年(1618)二月(仲春),由成縣知縣趙相宇主持。成縣儒學教諭管應律《重建杜少陵祠記》載:“嗣是棟宇傾圮,風景依然,謁祠者每愀然發孤嘯焉。我趙侯奉命尹是邑。春日修常祀,登堂拜像,賞鑒殊絕。乃捐俸命工經營之。不日落成,祠煥然一新。……侯,三晉世科也,諱相宇,字冠卿,號玉鉉。太原之狼孟人。”清乾隆《成縣新志》卷二《官師·明成縣知縣》載:“趙相宇,山西太原人,舉人。”
清代重建、重修杜公祠的情況不甚明晰,可以確知的有兩次,分別為清初順治年間宋琬重建杜公祠,以及清末光緒年間葉公重修杜公祠。清初著名詩人宋琬于順治十年(1653)至十四年(1657)間任陜西按察司僉事分巡隴右道。隴右道道署在秦州(今甘肅天水),地近成縣,宋琬仰慕杜甫已久,曾三度來到成縣,專程拜謁杜甫草堂。其《題杜子美秦州流寓詩石刻跋》云:“余小子備官天水,拜先生之祠宇(此處指秦州天靖山李杜祠)而新之。嘗兩登成州之鳳凰臺,其下有飛龍峽,先生之草堂在焉。群峰刺天,怒濤飛雪,酹酒臨流,未嘗不慨然想見其為人。”宋琬首次來到成縣杜甫草堂應是冬季,飛龍峽內風雪彌漫,宋琬內心凄愴,祭拜杜公祠,作《祭杜少陵草堂文》,文中說:“某海陬之豎子,奉哲匠以為師。偶省風于下邑,敬酹酒于荒祠。撫寒流以淅淅,悵衰草之離離。溯音徽于遺址,宛風流其在茲。爰周咨于茂宰,將再筑夫堂基。庶以永庚桑之社稷,而慰邦人伏臘之哀思。”該祭文已經明確指出杜甫草堂經歷明末清初戰火洗禮,鞠于荒煙蔓草之中的破敗情景。
在宋琬的授意與支持下,成縣杜公祠得以重建。完工后,宋琬再度來訪,作《同歐陽介庵拜杜子美草堂》:“少陵棲隱處,古屋鎖莓苔。峭壁星辰上,驚濤風雨來。人從三峽去,地入七歌哀。欲作招魂賦,臨留首從回。”又有《同歐陽令飲鳳凰山下》二首等詩作,吟詠鳳凰山,追懷杜甫。順治十四年(1657)二月,宋琬奉調直隸永平道,臨行前,又前往杜公祠祭拜辭行,作《丁酉仲春夜拜別杜少陵草堂因讌于有客亭》:“最愛溪山好,因成五夜游。碧潭春響亂,紅樹晚香浮。橡栗遺歌在,蘋蘩過客修。先生如何起,為我聽吳謳。”宋琬在任四年,三度來訪,可見對成縣杜公祠感情之深。
清代另一次重修杜公祠則在光緒年間。光緒九年(1883),湖南益陽人李焌出任成縣知縣。光緒十一年(1885),其子李炳麟至成縣省親。適逢杜公祠重修竣工,征集詩篇,李炳麟作七言詩四首,刊刻詩碑一方。詩序云:“家君治成邑三年矣,麟亦需次西安,久疏定省。光緒乙酉(十一年)冬,奉差赴漢中,繞道省親。適葉公補修同谷草堂征詩。落成,麟依韻和酬,囑同補壁,聊成一時鴻印云耳。”此葉公不詳何人,或為知縣李焌的同僚。此次杜公祠僅為“補修”,規模并不大。

(二)描摹成縣杜公祠的風物景觀



(三)展現多元化的杜甫形象
明清成縣杜公祠題詩中體現出的對杜甫形象的認知并非是單一的,主要有以下幾類:




總之,在明清詩人筆下,杜甫有時是忠義的化身,有時是詩才絕倫的先賢,這兩種形象雖然相互交織,但在不同人筆下,仍然要分個先后。而那些將杜甫作為有求輒應的神祇或引杜甫為人生知己、欲與之神交的詩人,立意就頗為有趣了。這些不同的側面,不僅豐富了成縣杜公祠的祭祀內涵,也使杜甫形象在后人心中更加鮮活。
四、結語
杜甫同谷故宅所在地,歷史上確有異說。但自唐以來的主流觀點及文獻支撐皆將杜甫同谷故宅定于飛龍峽鳳凰山麓,他處皆不可信。故厘清源流,辨明真偽,對研究成州杜甫遺跡乃至研究杜甫本人行蹤都具有一定意義。成州(縣)杜公祠是傳承時間最悠久的杜甫祭祀場所之一,依托于杜甫同谷故宅而選址,又經歷代不斷修葺,最終保存至今。這座祠堂的創建原因復雜,展現了創建人晁說之多方面的意圖和豐富的內心活動。或許正是由于晁說之等人對杜甫及杜詩非同一般的推崇,激發了后人的詩歌創作熱情,在此地留下了大量題詩。這些詩歌從不同側面展現了杜甫的形象,歌頌了杜甫的精神品格。悠久的歷史,傳承有序且豐富的文化內涵,使這里成為現存最重要的杜甫遺跡之一。
(本文是在筆者博士學位論文《杜甫遺跡研究》的基礎上修改而成)
注釋:
①?(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二
《山南道三》,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72-573、第572頁。
②??(唐)杜甫著,謝思煒校注:《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14、第418-419、第1653頁。
③④(清)錢謙益箋注:《錢注杜詩》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98、第99頁。按,趙鴻題刻已無存,初見錢謙益《錢注杜詩》著錄。《錢注杜詩》收錄趙鴻詩《杜甫同谷茅茨》《栗亭》二首,分別見杜詩《萬丈潭》《發秦州》注釋。(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七〇《利州西路·同慶府山川》“泥功山”又錄趙鴻詩一首。以上趙鴻三詩《全唐詩》卷六〇七均收錄。
⑤(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四·山南道》,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036頁。
⑥⑧?(宋)祝穆撰,祝洙增訂,施和金點校:《方輿勝覽》卷七〇《利州西路·同慶府·山川》,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1224、第1222-1223、第1223頁。按,同慶府即成州。《方輿勝覽》同卷載:成州“皇(宋)朝屬陜西,尋以秦、隴、鳳、階、成州、鳳翔府自為一路;中興隸利州路,升同慶府。”

⑩按,蔡副全《成縣杜甫草堂歷代詩碑考述》一文認為趙鴻所說萬丈潭在杜甫宅西與后世所說杜甫故宅在飛龍峽之東存在矛盾,進而認為二者并非同地(《杜甫研究學刊》2009年第1期,第82頁)。這是未弄清歷史文獻所載萬丈潭、飛龍峽、鳳凰山三者關系造成的誤解。
??????(宋)晁說之撰:《嵩山文集》卷十六《記》,第36b、第28b、第34a-35a、第35a-35b、第35b、第35b-36a頁,《四部叢刊續編》影印南宋抄本。
?見(民國)張維《隴右金石錄》卷四《宋下》,影印民國三十二年甘肅省文獻征集委員會校印本,《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西北考古文獻》第3冊,第568頁。按,此詩有碑刻在杜公祠內,但已殘損。原碑跋文共四行,分別存留“右賦龍峽草堂”“紹熙癸”“十七日郡守”“都宇文子震題”。
?(元)孛蘭肹等撰,趙萬里校輯:《元一統志》卷四《陜西等處行中書省·成州·古跡》,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479頁。

?參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407、第714、第716、第720頁。
?(明)王嗣奭撰:《杜臆》卷三《鳳凰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112頁。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卷四,影印清《粵雅堂叢書》本,《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第24冊,第18578頁。
?參見蔡副全:《杜甫與贊上人交游在同谷考》,《前沿》2009年第7期,第181-184頁。
??嚴耕望撰:《唐代交通圖考》卷三《秦嶺仇池區》篇二二《仇池山區交通諸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36頁。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02頁。
?(清)方世舉著,郝潤華、丁俊麗整理:《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九,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517-518頁。
?程俊英、蔣見元著:《詩經注析》,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340頁。
?蔣天樞校釋:《楚辭校釋》卷八《漁父傳第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01頁。
?(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十四《離婁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98頁。
?(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頁。
?蔡副全:《成縣杜甫草堂歷代詩碑考述》,《杜甫研究學刊》2009年第1期,第82頁。
?《明武宗實錄》卷六六“正德五年八月己酉”載:“命河南按察司張琎、陜西按察司僉事李昆俱提調本處學校。”(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校勘本,1962年,第1460頁)嘉靖《陜西通志》卷十九《名宦·按察司副使》有題名。正德十年七月,李昆由陜西左布政使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地方”(《明武宗實錄》卷一二七“正德十年七月己丑”,第2535頁),故嘉靖《陜西通志》卷十九《名宦·巡撫甘肅都御史》載:“李昆,山東高密人。弘治庚戌進士。官至侍郎。”影印嘉靖二十一年(1593)年刻本,《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3冊,第33頁。
?李昆有詩碑現存成縣杜公祠內。詩前有小序云:“正德癸酉六月暇日,與東渠訪杜少陵祠址有述。東渠吾臺長,燕山李公德方也,時分巡至成縣。”燕山李公德方即李璋,李璋于正德六年十二月,由刑部署員外郎為陜西按察司僉事(《明武宗實錄》卷八二“正德六年十二月己卯”,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校勘本,1962年,第1767頁),次年到任。此時起于正德三年的巴蜀寇亂持續蔓延,李璋安撫徽州百姓,多所興復。正德九年遷陜西按察司副使整飭洮岷兵備道。李璋事跡見明人張潛《分巡李君祠記》(見(清)費廷珍修,胡釴纂:乾隆《直隸秦州新志》卷十一《藝文中》,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清)馬呈圖纂修:宣統《高要縣志》卷二三《金石篇二》收錄明人王洙《一壺亭記》,文載:“主人謂誰?曰‘東渠李公’。……東渠名璋,字德方。古燕籍,浙之景寧人,前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影印民國二十七年鉛印本,上海書店2003年版,第47冊,第351頁)亦可證與李昆同游成縣杜公祠者為李璋。
?按,汪超宏考證:宋琬順治十一年“與人游杜甫草堂。重修草堂,作祭文。”此處將秦州天靖山李杜祠與成縣杜公祠兩地混為一談。參見汪超宏著:《宋琬年譜》,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頁。
??(清)宋琬著:《安雅堂文集》卷二,《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5冊,第76、第71頁。
??(清)宋琬著:《安雅堂詩》不分卷《五言律》,《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4冊,第568、第571頁。按,宋琬修祠后來訪時間不詳,據“古屋鎖莓苔”,當在順治十三年及此前某年的春季。
?(清)葉恩沛修,呂震南纂:光緒《階州直隸州續志》卷二一《職官表·成縣國朝知縣》,清光緒十二年(1886)刻本,《中國地方志集成·甘肅府縣志輯》第10冊,第364頁。
?按,《清高宗實錄》卷八一八“乾隆三十三年九月癸巳”載:“陜西學政。著劉墫去。”(《清實錄》,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8冊,第1096頁。)同書卷八四六“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庚辰”載:“諭:據明山參奏,成縣知縣湯尚箴徇縱蠹役、索詐滋事。階州知州汪沁毫無覺察,請旨分別革審。再鐔壯聚眾案內,有生員鐔克仁等附和隨行。訓導白士鈞平日不能訓飭士子,請革職。學政劉墫,失于覺察,請交部察議,并自請議處等語。湯尚箴著革職,交與該督嚴審,定擬具奏。汪沁、白士鈞俱著革職。劉墫、明山著一并交部分別議處。”(《清實錄》,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9冊,第327頁。)
?按,(清)宮懋讓修,李文藻纂:乾隆《諸城縣志》卷二二《選舉下》載:劉塒,為雍正十三年舉人,“字敬庵,綋熙子。第六十九名。現任福建鹽課大使。”(影印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8冊,第168頁。)其任成縣知縣事未見光緒《階州直隸州續志》等志書記載。(清)毛永柏修,李圖纂:咸豐《青州府志》卷四七《人物傳十》載:劉棨孫“塒成縣知縣”(清咸豐九年刻本,第16a頁)。(清)劉嘉樹修,苑棻池纂:光緒《增修諸城縣續志》卷十三《列傳一》載:“(劉)塒,字靜庵,舉人,為成縣知縣,有清名。歲饑,大府屬發倉庾貸民,民不能償,塒代償之。以勞致疾,卒于館舍,貧不能歸櫬。布政使貲助以歸。”(《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清光緒十八年刻本,第38冊,第394頁。)但任職時間不詳,與《清高宗實錄》所載成縣知縣為湯尚箴有矛盾。尚待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