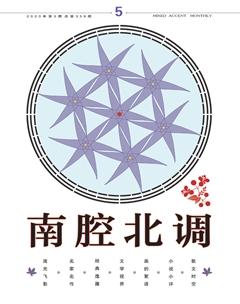發散與反思
趙振杰

在攻讀文學碩士學位期間,我的導師郭寶亮教授曾多次提醒我:“做文學研究,不僅要知道前人都說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力接著說,甚至反著說。”同樣的意思,已經過世的陳超老師也曾在他的課堂上多次提及。他經常告誡我們:“聽我的課,不需要記筆記,大家最好能夠少動筆多動腦。與其說我是傳授知識,毋寧說是在訓練一種思維方式。我的課并不提供現成的答案或權威性的學術論斷,希望同學們在聽講時能夠與我建立一種潛在的交流,這種潛交流既可以是延展性的,也可以是對話性的。”兩位恩師的諄諄教誨,令我記憶猶新,終生難忘,以至于我在閱讀文本或聆聽講座時,逐漸形成了自覺的發散性思維和反思性意識。這一話題延伸開來,格非先生在清華人文講堂上作的題為“重返時間的河流”的文學報告,也讓我獲益良多。作為一節非同步性的線上課堂,想要與格非先生互動問答顯然無法實現,于是,陳超老師所強調的“潛對話”或“暗交流”就顯得尤為重要。下面,我就試著從發散性與反思性兩個維度,淺談一些個人的觀后感想與思考。
格非是我非常崇拜的當代小說家,而且我的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就是他的“江南三部曲”,所以對于格非先生其人其作,還是算得上了解的。格非以“先鋒文學”著稱于文壇,他的作品因帶有深邃的形而上思辨色彩而被學界冠以“智性寫作”的標簽。早在先鋒時期,他就在小說創作之余,寫就了《塞壬的歌聲》《小說敘事面面觀》《小說講稿》等諸多文學隨筆,從華東師范大學調入清華大學后,格非不僅完成了“江南三部曲”、《隱身衣》《望春風》《月落荒寺》等多部力作,同時還先后出版了《文學的邀約》《雪隱鷺鷥》等學術專著。可以說,格非是當代文壇為數不多的兼具作家、教師、學者多重身份的人文知識分子。常年的小說創作、教學實踐與學術研究,形成了格非先生頗具個人化的文學理念與觀點。“重返時間的河流”這場講座便極為充分地呈現出他對文學史、文學現狀、文學未來的獨到見解與反思。
正如格非開場所提到的,講座其實還有一個副標題——文學的時空觀及其意義,“時間”與“空間”這兩個文學文本的基本構成要素,在格非看來,這并非僅僅是小說敘事學或小說修辭學意義上的概念,也是構成了文學史范式轉換、作家創作方法論革命,以及讀者審美接受變遷上的關鍵線索,同時還是銜接文學內部與外部,文學自律性與他律性,文學與歷史、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其他時代屬性的重要樞紐。為了方便聽眾的理解,同時增強講演的趣味性,格非先生首先以包法利夫人的“帽子”和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為切入點,生動且直觀地呈現出當代文學藝術中一個重要的范式轉型,即“場景獨立”,進而深入到創作實踐與文藝理論內部,揭示出文學從“空間時間化”,到“時間空間化”再到“空間碎片化”的審美變遷歷程,同時以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卡夫卡、普魯斯特、喬伊斯等作家作品之間差異性,柄谷行人、雷蒙·威廉斯等專家學者的理論觀點,以及《春江花月夜》《金瓶梅》《紅樓夢》等中國古典文學的內在敘事邏輯與倫理為佐證,最終得出一個發人深省的結論——“空間”自身并不產生意義,它只有附著于“時間”之中才具有意義,古典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夠提供“完美的結尾”,源自于作者自身對于“時間”永恒性的篤定與確信,而深處在一個“空間”驅逐“時間”的文化現場之中的當代作家們,已然無力提供任何確鑿性的、本質意義上的答案,相反他們只能將自身深切感受到的矛盾、糾結、惶惑、恐懼、無奈一股腦地拋給讀者。這不禁讓我聯想到本雅明著名的現代性“寓言”理論:“寓言”對立于古典主義的“象征”。“象征”是一種世界繁榮期的藝術形式,它對應的是一部理想的歷史,表現的是一個“生機勃勃”的“明白曉暢”的世界,以和諧、對稱、明晰、完整為標志;而“寓言”則是一種世界衰落期的藝術形式,它對應著一部理想崩潰、社會傾頹的歷史,表現的是一個混亂不堪、殘缺不全的社會,以憂郁、破碎、含混、多義為特征。“寓言”是藝術在衰微的、充滿災難與痛苦的現代社會“唯一的形式”。
即便是回顧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學史,我們亦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時間空間化”的審美癥候與病灶。一言蔽之,就是“人”與“文”在敘事倫理上的同步貶值——一方面是“人”的光環不斷脫魅,乃至頹敗入俗的過程;另一方面是“文”的逐漸自覺進而提純最終又被邊緣化、商品化的過程。這種現象在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個人化(私人化)寫作”浪潮中表現尤為突出。伴隨著改革開放與市場化進程的加速,當時被冠以“新新人類”之名的一大批作家開始普遍對宏大敘事產生厭倦情緒,于是轉而耽溺于個人經驗和體驗的私密性空間,以性為主要描寫對象,專注于表現自虐、自戀、自慰等變態性心理活動。當宏大敘事中的“時間”屬性被擱置乃至拋棄后,他們筆下必然充斥著形形色色的狹小、封閉、昏暗、頹廢、人工氣十足的“官能空間”(或稱“欲望空間”)。浴室、酒吧、迪廳以及遍布其中的鏡子、花瓶、窗簾、爵士樂、大麻、烈酒、香煙……成為作家筆下反復書寫的對象。所有的跡象都表明,格非先生提出的“時間空間化”“空間碎片化”觀點,正在被當下的生活實際和文本實際所充分地證實。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重返時間的河流”才顯得如此迫切與必要。
需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格非先生呼吁“重返時間的河流”并非是要提供一個解決問題的終極答案,其側重點恰恰在于提出新的問題。他在與聽眾的互動交流中也反復強調,“重返”是一種隱喻,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核心在于我們要善于發現問題,并且帶著問題進行反思,提問和思考本身才具有意義。抱著這樣的理性思辨態度,我們完全有理由在承認“時間空間化”邏輯自洽性與現實合理性的基礎上,提出與之相反的理論構想,即“空間的時間化”審美意識形態癥候。如果我們稍加留意便會發現,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以及勞動分工的日益精細化,一方面,時間逐漸被空間擠占,人逐漸異化為物,進而淪為機器的附庸;而另一方面,空間也在被時間驅遣,人自覺不自覺地被時間綁架,最終成為“鐘表”的奴隸。由世界級喜劇大師卓別林主演的電影《摩登時代》中所呈現的工作場景便是最好的證明。當然,這并非我個人的獨到發現,我國著名的人類學、社會學家項飚先生在他學術專著《跨越邊界的社區》中很早就提出了“附近的消失”這一理論概念。近期,他在許知遠主持的“十三邀”訪談節目中也曾就這一概念進行過較為通俗化地闡述:所謂“附近的消失”,從人類學的角度上講,可以簡單概括為時間征服空間的過程,我們以前感知世界的方式是由具象的空間來指認的,所有的時間概念都是由空間物象來表達,比方說,“一盞茶的空檔”“一炷香的時間”“一袋煙的功夫”等等。抽象的“時間”其實是相對晚近的產物,它是工業時代鐘表被發明以后所衍生出的意識形態。到了現在的網絡社交時代,時間又由連貫的線性變得日益碎片化,并隨著“時間就是生命”“時間就是效率”“時間就是財富”等話語霸權的極度擴張,分秒必爭的時間邏輯日漸表現為“即刻顯現”“時不我待”“刻不容緩”……于是,時間感愈發強烈的現代人,變得異常的焦慮、暴躁、易怒、抑郁、憤懣。不得不說,“我太難了!”之所以能夠成為2019年度核心關鍵詞,與國民生存空間的極度時間化現狀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格非先生在講演中,為了闡釋現實生活中“時間被空間化”這一現象時,提到“現代交通的發達讓人感受不到時間的流逝,一個人上午在香港吃飯,下午有可能就已經在北京喝茶了,只不過是空間的位移罷了。”如果我們換個角度,反過來看,這又何嘗不是“空間”的消失。高速的城市化進程,致使現在的城市建筑大同小異,千篇一律,從香港飛到北京,目力所及不過是玻璃混凝土,空間的差異性遠不及同質性。一個人所能切身感受到的,反而是手機里設置的鬧鐘提醒,機場航班的時刻表,以及出租車上的計時器。時間在鐘表上的物理性空轉構成了我們感知空間變換的唯一方式。
此外,格非先生在講演中所列舉的武漢東湖與杭州西湖的例子,亦可作如是觀。從“時間空間化”的邏輯出發,誠如格非先生所言,西湖之所以比東湖更著名,原因不在于風景,而在于其中蘊藏的人文底蘊,而這些人文底蘊恰恰是歷代的文人墨客通過時間賦予的。然而,換一個邏輯出發點,我們同時不能忽略這樣一個不爭的現實:對于大多數游客而言,東湖與西湖在空間意義上并沒有什么本質性的分別。時間的緊迫感導致他們不是在景點上匆忙地拍照留念,就是在匆忙地趕往下一個拍照留念的景點的路上。空間的獨特性被時間的緊張感剝奪,游人連駐足欣賞風景的時間都變得奢侈,更遑論穿越時間與歷代古人對話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時間焦慮感不僅源自外在不可抗力的制約,更大程度上是自我規訓機制在起著支配性作用——與導游催促游客上車相比,游客不耐煩導游的冗長講解,更是司空見慣的事實,手機、手表上的時間仿佛在時刻提醒著我們,此地的過分逗留,便意味著對遠方風景的割舍。
格非先生說:空間不具有獨立意義,是時間為空間賦予意義。而我們同樣可以說,時間本身并不自動攜帶意義,是空間的承載力以及作為空間結構主體的人的審美感受力,為時間賦予意義。關鍵在于,我們不僅要自覺抵御“時間的空間化”,同時也要時刻警惕“空間的時間化”。某種程度上講,日本學者柄谷行人先生所提出的“風景獨立”觀點既是對時間的肯定,也是對空間的強調。我們只有在看“風景”的時候暫時忘卻時間的存在,走出經濟學意義上的“損失厭惡”思維誤區,給“空間”留出必要的時間,歷史、文化、心理層面上的“時間性”才能在“空間”中得以充分顯現。因此,竊以為,我們當下其實面臨著雙重任務,一方面要“重返時間的河流”,另一方面也要“找尋空間的堤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