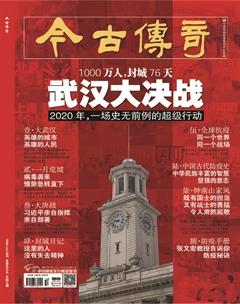鐘南山家風(fēng)

2020年春天,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在奔波于抗疫前線的醫(yī)護人員中,鐘南山是一位備受矚目的代表。他青年棄體從醫(yī),43歲出國留學(xué),60歲做院士,67歲抗擊非典,84歲再戰(zhàn)新冠肺炎。人們說他妙手仁心,國士無雙,他說“我不過是救人的醫(yī)生”。鐘家三代人懸壺濟世,“最大的不變有兩個:第一個是對病人的責(zé)任感;第二個是不滿足于現(xiàn)狀,就是對研究孜孜不倦的追求”。
三代九人從醫(yī),兄弟同為院士
1936年10月20日,南京中央醫(yī)院內(nèi),該院兒科主任醫(yī)師鐘世藩的長子呱呱墜地。由于醫(yī)院地處鐘山之南,鐘氏夫婦遂為其取名為“南山”。“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期待他能不負(fù)父母所愿,成長為一個如大山般仁厚正直、崇高穩(wěn)重的人。
“硬核”家族
鐘世藩1901年出生于福建廈門,8歲時父母雙亡,9歲被人帶到上海,在一個大戶人家做小工,寄人籬下。
在艱苦的環(huán)境下,鐘世藩仍然堅持學(xué)習(xí)。23歲時,他考入北京協(xié)和醫(yī)學(xué)院,當(dāng)時醫(yī)學(xué)院在全國只招收40名新生。畢業(yè)時,醫(yī)學(xué)院采取淘汰制,最終40名學(xué)生中畢業(yè)的僅8名,鐘世藩是其中之一,與他一同畢業(yè)的還有后來成為皮膚病專家的胡傳揆、生化學(xué)家劉士豪。1932年,年僅31歲的鐘世藩取得了美國紐約州立大學(xué)的醫(yī)學(xué)博士學(xué)位,成為當(dāng)時中國醫(yī)學(xué)界赫赫有名的“八大金剛”之一。
1934年,鐘世藩與同鄉(xiāng)的名門淑女廖月琴結(jié)婚。廖月琴出生于鼓浪嶼名門廖家,父親廖照熙和著名作家林語堂的妻子廖翠鳳是一個屋檐下長大的堂兄妹。廖月琴畢業(yè)于北平協(xié)和醫(yī)學(xué)院的高級護士學(xué)校,新中國成立后擔(dān)任過會南腫瘤醫(yī)院(今中山醫(yī)科大學(xué)腫瘤醫(yī)院)的副院長,也是該醫(yī)院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
鐘南山的舅舅廖永廉,曾任廈門第二醫(yī)院內(nèi)科主任,1957年發(fā)現(xiàn)福建省第一例鉤端螺旋體病。舅媽陳錦彩,畢業(yè)于上海醫(yī)學(xué)院附屬高級護士學(xué)校,參加過淞滬會戰(zhàn)戰(zhàn)地救護,在鼓浪嶼是家喻戶曉的人物。
詩人舒婷曾在散文中寫道:“廖娘一輩子熱心參與本島大大小小事件……有天早晨,隔墻那邊人聲鼎沸,原來鄰家的女主人跳井自殺了。公安人員放下鐵鉤去撈尸,廖娘一旁心有不忍,上前阻止道:‘你們這樣亂耙,不但衣褲破爛不堪,恐怕還會皮開肉綻,那死者就更可憐了。可是井深口小,警察腰粗下不去……廖娘自告奮勇,在自己腰間挽了根麻繩,腳踩井沿慢慢下到井底……對于這件往事,當(dāng)人們問她下井怕不怕時,陳錦彩總是說:‘救人不怕的。”
鐘南山的大姨媽廖素琴,曾任上海第一醫(yī)院營養(yǎng)室主任。大姨夫戴天佑是著名的肺科專家。他們的兒子,也就是鐘南山的表哥戴尅戎,是骨科生物力學(xué)專家,也是中國工程院院士。
加上鐘南山與兒子鐘惟德,這個“硬核”家族三代一共有九人從事醫(yī)學(xué)行業(yè),見證了20世紀(jì)以來的中國現(xiàn)代醫(yī)學(xué)史。
尚在襁褓中的鐘南山遭遇日機轟炸,被壓在廢墟之下
1937年8月15日,淞滬會戰(zhàn)激戰(zhàn)正酣,日軍戰(zhàn)機對南京城實施瘋狂的轟炸。鐘宅被炸塌,尚在襁褓之中的鐘南山被壓在了廢墟下。萬幸的是,外婆、母親二人找到了他所在的位置,徒手將他從廢墟瓦礫間救了出來。鐘南山日后回憶:“據(jù)姨媽告訴我,當(dāng)時我的臉已經(jīng)發(fā)紫,再晚一步可能就救不活了,是外婆和母親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淞滬會戰(zhàn)結(jié)束后,鐘氏夫婦帶著兒子逃離南京,從湖南長沙一路輾轉(zhuǎn),最終來到貴州貴陽。此后的八九年間,鐘家人一直定居貴陽。1946年,鐘世藩任廣州中央醫(yī)院院長兼兒科主任、嶺南大學(xué)醫(yī)學(xué)院兒科教授。鐘南山隨父母遷居廣州,就讀于嶺南大學(xué)附小(今中山大學(xué)附小)。
鐘南山小時候很貪玩,有一次因為向往武俠世界中飛檐走壁的輕功,他從家中的三樓撐著一把大傘一躍而下,結(jié)果摔傷了腰。他還常常逃學(xué),成績很差,留過兩次級。鐘南山回憶:“五年級時有一次考試我偶然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媽媽知道了很高興,她對我說,南山,你還是行的啊!那時我覺得媽媽一下子把我的一個亮點找了出來,我有了自尊心,覺得有人贊美我。從那時起,我就開始認(rèn)真讀書了。”
鐘南山一直珍藏著一張1950年他騎自行車的黑白照片。他回憶:
當(dāng)時我看到別的孩子有自行車,非常羨慕。小學(xué)六年級時,媽媽對我說:“你要是小學(xué)畢業(yè)能考到前5名,我就獎你一輛自行車!”我說:“真的呀?”媽媽說:“真的。”后來媽媽也沒再提過這件事,但11歲的我記住了媽媽的話。1949年,我在嶺南大學(xué)附小讀書,學(xué)校因故不舉行畢業(yè)考試,但后來,學(xué)校根據(jù)平時的成績發(fā)了一份成績單,我排在第二名。我很高興,但也不敢說什么,因為媽媽是說考試才有自行車的。而且,那一年解放軍南下,國民黨發(fā)行金圓券,通貨膨脹非常厲害,家里生活很困難。但是沒想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媽媽還是給我買了一輛自行車。當(dāng)時我在日記里這樣寫道:“媽媽實現(xiàn)了她的諾言,給我買了一輛自行車,我是多么高興啊!”從那時起,我就記住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只要你答應(yīng)的事,就一定要做到,這就是媽媽教給我的。我現(xiàn)在對我的孩子、對我的研究生也是這樣,要么不答應(yīng),答應(yīng)了我就一定要做到。
“我感覺當(dāng)醫(yī)生還是挺受人尊重的,而且真的幫人解決問題”
鐘南山曾說:“在我的生活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我的父親鐘世藩。”他始終記得一件小事:那時候他還小,有一次因為嘴饞想吃零食,欺騙父母,把本應(yīng)該交給學(xué)校的午餐費扣下。“當(dāng)時母親回家跟父親講起這個事,我以為大難臨頭了,就說一定會把我痛打一頓。沒想到,我父親沒說太多,他說:‘南山你好好想一想,你這樣做來騙我們,你做得對不對?這個感覺比他打我一頓對我的刺激都大。”鐘南山懂得了要講老實話、做老實人,這種信念貫穿了他的一生。
1949年,鐘世藩被世界衛(wèi)生組織聘為醫(yī)學(xué)顧問。廣州解放前夕,有兩個不速之客常常光臨鐘家。他們總是夾著鼓鼓的黑色公文皮包,鬼鬼祟祟地來找鐘世藩。鐘南山后來才知道,這兩個人是南京國民黨政府衛(wèi)生署的,其中一個還是衛(wèi)生署署長,他們是來勸鐘世藩帶上醫(yī)院的巨款去臺灣的。
就在國民黨炸毀海珠橋的那天,在距海珠橋不遠(yuǎn)的鐘家小樓里,鐘世藩再次憤怒地拒絕了國民黨的脅迫。廣州解放后,他將一筆款項如數(shù)上交給軍管會,一共是13萬美元。這一年,鐘南山13歲。這一幕幕,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腦海里。
20世紀(jì)50年代,鐘世藩創(chuàng)辦了中山醫(yī)學(xué)院兒科病毒實驗室,這是中國最早的臨床病毒實驗室之一。那時,新中國剛成立不久,百廢待興,科研經(jīng)費很困難。為了研究病毒,鐘世藩只好在自家天臺上搭了一個棚子,又自掏腰包買了三四百只小白鼠喂在里面。鐘南山回憶說:“那時家里總有一股特殊的氣味,來我們家的人,還在馬路邊就可以循著這股氣味找過來了。”
當(dāng)時,鐘南山已經(jīng)升入初中。每每父親忙碌時,他就自覺當(dāng)起了飼養(yǎng)員,樂此不疲地為小白鼠們喂谷子、喂水。父親見他對小白鼠這么熱心,就有意地讓他多接觸。父親做解剖實驗時,盡管看不太懂,鐘南山仍會立在他身側(cè)饒有興趣地觀察,“一直堅持了三四年,是很長一段時間”。
最讓鐘南山難忘的是,每當(dāng)?shù)搅艘雇恚依锟倳裢鉄狒[。親戚朋友、街坊鄰居們經(jīng)常會趁此時來找父親看病。對于上門的病患,鐘世藩從不推辭拒絕。
“我感覺當(dāng)醫(yī)生還是挺受人尊重的,而且真的幫人解決問題。那個感受讓我覺得爸爸很開心,家庭也很開心,這是一個原始的感受。”鐘南山心中已然深深埋下了學(xué)醫(yī)的種子。
(責(zé)編/陳小婷 責(zé)校/蘭嘉娜 來源/《勇敢戰(zhàn)士:鐘南山傳奇》,魏東海著,經(jīng)濟日報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鐘南山:就這么成為了“中年醫(yī)生”》,吳志菲/文,《科學(xué)24小時》 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