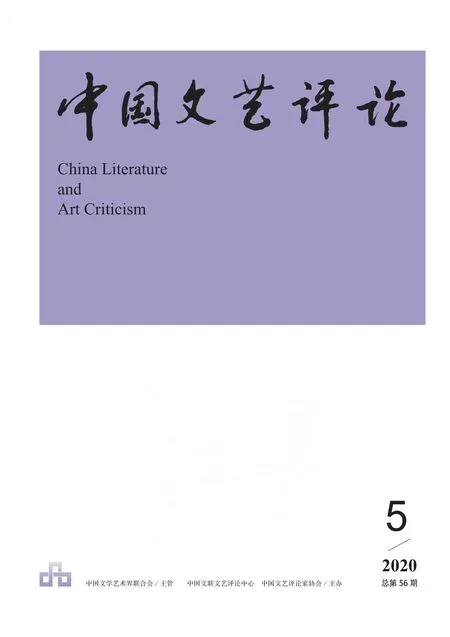只有山歌敬親人
——訪表演藝術家黃婉秋
采訪人:李彬彬
一、與藝術結緣:那份執著和靈動
李彬彬(以下簡稱“李”):黃老師您好,很開心您接受我們的采訪。您14歲登臺,17歲就出演了電影《劉三姐》,并且轟動全國乃至海外,可以簡單談一談您是怎樣走上藝術之路的嗎?您又是怎樣與電影《劉三姐》結緣的呢?
黃婉秋(以下簡稱“黃”):我13歲學藝,14歲登臺。那時我剛讀五年級,正值寒假,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一個招生廣告,桂劇團在招學員。也許是喝著漓江水長大的原因,受了大自然的熏陶,我從小就喜歡唱啊、跳啊的,特別喜歡美。我很小的時候看過一些桂劇的演出,很羨慕人家能在臺上演出,那樣有功夫,所以看到那個廣告后我想都沒想就去報名了。在當時報名還需要戶口本,結果家里不同意。
那時去學戲的很多都是因為家里窮,上不起學,負擔不起,逼不得已讓小孩子去找一個生計。我們家還不到這個地步,家里人還是想讓我好好念書。可他們怎么說我都說不通,我就是喜歡,就是想去,后來家里人也沒有辦法,讓我寫信問我哥。我哥那時候在長春上大學,可能父母覺得他起碼有文化,看問題也能看得透徹一點,就讓我征求他的意見。沒想到我哥哥挺開明的,他很支持我,給我父母回了一封信,說她喜歡就讓她去,讓她走自己的路吧,現在時代不同了,都解放了,不像以前說學戲的是“戲子”,演員也有一定的地位了,就讓她去吧。其實我早早就去報名了,得到這封信我興奮極了,馬上就去報到了,那時候我才13歲,要說懂事也不算太懂。
進團之后就開始嚴格的基本功訓練,1956年那時候的劇團還不是國營的,是民營的,條件很艱苦,都是駐在租的老百姓的小院子里,我們住宿、練功都在里面。沒有正規的練功房,更沒有把桿,我們就在窗戶口欄桿上面壓腿,就這樣練出來的基本功。老師們也很辛苦,他們不管演出情況好不好,每個月都會給我們七塊錢,那是絕對保障的。所以我們也覺得很舒服,也不懂得什么艱苦。因為喜歡,練起功來就不覺得疼,怎么練功都不覺得疼,甚至練得兩個腳都腫了,蹲都蹲不下,但自己還是挺高興的。那時候還不真正懂得什么“為人民服務”,也不懂什么是藝術,純粹就是出于喜歡,就想學一身本領。
就這樣,我們學了快三年。由于團里是自負盈虧的,不可能養很多人,我們這幫學生得有50個,后來慢慢淘汰完還有30個。不可能給你單獨訓練,也沒有條件進行那種封閉式的訓練,我們就上臺跑龍套,演小丫鬟,一邊上臺看老師演出,一邊學習,一邊平時練功。我們那時候中午要演出,晚上也要演出,那時候沒有電視,沒有什么娛樂,電影都很少。我們就是一個勁地在練功,跟著老師學習。我們看會了就可以跟老師講,老師我看會這個戲了,老師就教你。老師也沒有劇本,他講一句你抄一句臺詞,劇本都在老師心里,都是口傳身授的。那時候我記性特別好,老師講一句我抄一句,一個折子戲講半個鐘頭,抄完了我基本上就會背了。可能是因為自己太喜歡了,太專心了,有記憶的天分。雖然那時候學習很苦,但是也很快樂,覺得生活就是這樣,學習就是這樣,本就該是苦的吧,所以自己也心甘情愿。
17歲的時候,我們畢業了,三年就出科班了。那時候正好廣西排《劉三姐》,全區都要排,不管什么劇種都要演《劉三姐》,就像現在抓精品藝術那樣,要求創作改編成非常完美的能夠代表廣西的最好的作品。當時桂林市代表團組織了一個創作班子在排練《劉三姐》,還有彩調和民歌,不是以桂劇的形式,也不是彩調,是把彩調和歌劇結合起來的一個作品,叫做歌舞劇《劉三姐》。演員一共分A、B、C三組,很幸運的是我被選進了C組。那時候我畢竟年紀小,初出茅廬,沒有別的演員有舞臺經驗,能夠跟著他們學,進入C組已經使我覺得很榮幸了。
經過一段時間的排練,我很幸運地被升到了A組,代表桂林市到南寧市參加比賽。能夠得到這個機會也源于一個因素,就是我的表演相對專門演舞臺劇的演員來說更靈活一些。我曾經演過舞臺劇,但時間并不久,我也學習過彩調戲,彩調在表演形式上要比古裝戲的京劇、桂劇等開朗一些,表演空間更自由一些,所以我在演出方面許多天性的東西還沒有被規訓,保留了靈動的成分,那種表演程式還沒有完全固定在我身上。所以相對于純粹的舞臺劇,我的表演不是單純的舞臺劇那種程式化和夸張化的表演,盡量地源于生活、尊重生活,顯得比較生活化,也可以說是一種非常單純的情感的自然流露。電影《劉三姐》的導演來到廣西選演員時看中的也正是我的這一點。后來我就接到了一封信,讓我到長春電影制片廠參加試鏡,最終我得到了劉三姐這個角色。所以我想,這既是一種命運,也是一種努力的結果,只要認認真真地去學習,什么都不用想,一切自有安排,我覺得是這樣的,自己付出了努力就一定會得到收獲。我覺得老天可能很眷顧我,認可我對藝術的追求和執著,所以就給了我這么好的一個機遇。

圖1 17歲的黃婉秋
李:您作為“劉三姐”的扮演者,這部電影對您的影響應該說是很大的,它伴隨了您一生的榮辱興衰,在一段特殊歲月里,您的演藝事業從高峰到低谷,后來又重新回歸舞臺,這一人生跌宕對您始終堅持藝術事業有什么特別的影響嗎?
黃:拍了電影之后,我的人生確實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還沒有真正享受到鮮花和掌聲,“文革”就到來了,突然間好像天都黑了,一下就受沖擊了。最難以承受的是一種人格和精神上的壓力。那時候我21歲,很懵懂,但也突然間充滿正氣。我看過江姐的戲,也演過江姐,就像是她那種視死如歸的感覺,一點都不害怕了。從學藝開始,許多戲里的諸如“寧愿站著死、不愿跪著生”“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類的理念和戲詞真正地融入了我的血液,這是一種人格,一種做人的姿態,是這些豪言壯語增強了我內心的承受力。而且劉三姐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給予我這樣一股子硬氣,她的精神已經滲透到了我的骨子里。
經歷了這些,我變得很勇敢,而且很快地成熟起來。俗話說磨煉使人趨于完善,這是有道理的。前后一共15年,在這15年里我真的成熟了很多,長大了很多,我明白了這是大的時代環境,是一場全國性的運動,所以不去埋怨它,而是調整自己的心態,懂得怎樣才能在這樣的環境里生存下來,并且不放棄自己的追求。如果沒有這個磨煉,也一定不會有后來的我,更不會是像現在這樣的“劉三姐”,不會像現在這樣有底氣。從那以后,我變得從容了,沒有什么能輕易地打倒我。我想這不論是對我的生活還是藝術創作,都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
二、“劉三姐”:經典符號的恒久魅力
李:代表作電影《劉三姐》創作陣容非常豪華,從導演到作詞、作曲,可謂“神仙級別”的主創團隊,團隊創作的初衷和預期是怎樣的呢?有想到過它所產生的轟動效應和持續不斷的熱度嗎?一部反對土豪劣紳的電影,卻歷經五十余年而不過時,您是怎樣看待這部作品和這種現象的呢?
黃:是的,這個劇的導演是蘇里,作詞是喬羽,作曲是雷振邦,三個“巨頭”,在當時是實力派的團隊,可以說是大手筆。其實《劉三姐》這個戲早已有之,是廣西柳州創作的。開始是一場戲,就是對歌那場,后來覺得不錯就把它擴充成一個小時的戲,有七場。導演看了劇本之后和喬羽先生商量,想把這個戲做大做好,做出個性化,區別于其他形式的《劉三姐》。要做到個性化,主要從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著手。在形式上,主要以對歌的形式來展現和推動劇情,用山歌來表現人物個性。而且這部戲很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即使是反面人物,也沒有刻意過分地丑化,這樣立意就高了,所以說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正劇。雖然這是一部反對土豪劣紳的電影,但它不同于當時其他的許多戲,不是那種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模式,里面既沒有表現很激烈的階級斗爭,也看不到一味的謾罵和橫眉冷對千夫指,全劇沒有提到“階級”兩個字,對白中也沒有很生硬的階級斗爭的語言,它是在一種歡快的、很有人情味的氛圍中展開斗爭的。影片中的人物都是飽滿鮮活、有情緒、有情感的,體現了一種人性的純凈和浪漫,非常淳樸自然,同時又充滿詩意和智慧。作品突出了笑的力量和諷刺的力量,在輕松愉快的氛圍里給觀眾上了一堂階級斗爭的課,讓觀眾知道,除了拿起槍桿子去斗爭,還有其他的群眾斗爭方式。所以拍攝的初衷也是希望這是一部好看的戲,能夠讓觀眾在一種輕松的氛圍里受到教育和鼓舞,懂得應該像劉三姐那樣,用正氣和智慧爭取美好的未來。再加上雷振邦先生的作曲,又把原來廣西的民歌彩調融入其中,全劇圍繞“歌”字做文章。劇中基本沒有對白,全部是通過歌唱形式,把它提升了一個檔次,也可以講提升了格局。這是電影音樂劇的一個突破、一個高峰。它創造了多個“第一”的記錄,比如,它是中國第一部音樂電影,也是第一部彩色影片,第一部賺取外匯的影片。
所以后來我們講,為什么這么多年以后,老百姓還是那么喜愛《劉三姐》,就是因為這個戲讓更多的人記住了劉三姐、了解了山歌、以及山歌的魅力和靈魂。山歌是我國勞動人民尤其是少數民族勞動人民的智慧,劉三姐就是民間智慧的一個典型代表。通過《劉三姐》的演繹,使觀眾更加明白應該怎樣去生活,怎樣去創造,怎樣做好自己的工作,在潛移默化中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我想這也是這部電影能夠超越題材本身而經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吧。這個電影唱出了真善美,唱出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展現了廣西的民族文化。現在,劉三姐的山歌不僅在國內,甚至在全世界都很有名,它已經成為廣西一張獨特的文化名片。

圖2 電影《劉三姐》劇照
李:《劉三姐》作為幾代人的文化記憶,已然是一種文化符號,它曾創下過多個票房紀錄,走出中國、走向世界,在國外多次掀起“桂林熱”和“三姐熱”,是國際文化交流中不可忽視的角色。那么,這樣一部有著廣西濃郁的地域文化和中國深厚的歷史背景的一部典型創作,為什么會在全世界取得如此熱烈的反響呢?

圖3 黃婉秋和愛人何有才在蘇州首屆藝術節開幕式上
黃:這部劇里有人性當中共通的東西,這些特質不分時間和地域,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都有一種感召力。尤其對海外一些華人眾多的國家和地區,《劉三姐》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就非常大,比如它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和當時還沒有回歸祖國的香港等地都產生了轟動的影響。我曾多次到過這些地方,也現場演出過,可以說每次都是一票難求,盛況空前,極大地激發了當地華人的愛國熱情,喚醒了深埋已久的民族認同感和歸屬感。這樣,很容易就把我們海外華人的心凝聚了起來,同時也對當地的華人教育、文化乃至經濟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就像以前華人做生意,都是各做各的,各自為陣,互相的往來極少,看過我們的電影和演出之后,他們空前地團結了起來,互相幫助協作,也不由地產生了一種民族自豪感。在中國和馬來西亞建交30周年紀念時,馬來西亞以電影《劉三姐》為藍本,改編成歌舞劇,并邀請我們夫婦指導和參與演出;劉三姐藝術團在美國舊金山及西雅圖文化交流中也獲得了很多贊譽。所以,當時很多人給這個電影一個評價,說它是文化外交很重要的一項,這是很高的贊譽。這也使我想到當下的一些文化政策,比如“文化自信”,這個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個自信之一,還有中國文藝“走出去”這樣的時代號召。現在回頭看來,我想《劉三姐》就是一個很好的實踐,實際上《劉三姐》在全國和海外的影響就和當下我們的文藝政策和號召是一致的。原來我們沒有這么高的立意,也不懂得這樣去總結,但是幾十年過后,它沒有一點遜色,還這樣廣泛地流傳著,并且經久不衰。所以我覺得這個題材,圍繞用山歌來唱好中國故事,現在把它立起來也為時不晚,這對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和塑造國家形象都有著積極意義。
三、終生的事業:弘揚與傳承
李:從歷史傳說“劉三姐”故事,到彩調劇《劉三姐》,到音樂故事電影《劉三姐》,到歌舞劇《劉三姐》,到為了紀念劉三姐而形成的民間紀念性節日“三月三”,再到大型山水實景演出《印象·劉三姐》,“劉三姐”這一文化符號內容不斷豐富,形式不斷多樣,可謂同一題材的多種體裁和表現形式的呈現,對于這種特別的文化現象,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黃:劉三姐的故事最早只是一個歷史傳說,后來有了各種各樣的形式去演繹它,而且出現了像“三月三”這樣的民間紀念性節日,這的確是很少見的一種文化現象。我想是因為大家都想去嘗試,想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表現它,這就是一種創新。這其中不乏很多優秀的作品,但是,也有一些做得不太好,比如,有些作品加入了比較荒誕的元素,歪曲了劉三姐這個題材。我認為不應該把它做成一種搞笑的效果去丑化它,比如在秀才、媒婆等地方大做文章,這是我不太贊賞的一種改編方式。改編是沒有問題的,但我想說的是一定要嚴肅,要認真對待,尊重劇本、尊重藝術,我們不是為了迎合市場,這種戲謔化的表演丟掉了該劇最精華、最獨特的藝術特質,反而失去了許多觀眾。
當然,大部分的演繹是很優秀、完美的。比如我們電影版的《劉三姐》,集中了最優秀的創作班底,經過反復的討論、琢磨,下了很多功夫,最終呈現出來,體現出了很高的藝術水準,難以超越。所以說在一種表演方式已經接近頂峰的時候,相同的或類似的表演就難以再有突破,難以贏得觀眾,而我們又不想浪費這么好的劇本和題材,大家就想辦法進行再度創新創作,用其他的藝術形式去表現它。另外一個成功的例子就是你提到的張藝謀導演的大型山水實景演出《印象·劉三姐》。當年張導對《劉三姐》這個電影也很欣賞,想進行再度創作,于是就有了后來的山水實景演出。我覺得這個演出豐富了劉三姐這一題材,充分展示了廣西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風情,生動地體現了廣西勞動人民的面貌,而且表演也很生活化,很接地氣。無論從視覺效果,還是從觀賞體驗上來說,都非常震撼,場面非常壯觀。它把廣西的許多特色都濃縮到了這個演出當中,可以說很完美,大大地提升了劉三姐這一文化元素的影響力,同時再度使之經典化。無論是哪種表現方式,只要認真做、好好做,都是一種傳承、一種宣傳,是弘揚我們的優秀文化,也是一種兼容并包的表現。

圖4 三代“劉三姐”,黃婉秋與女兒和兩個外孫女
李:我們知道,您在“劉三姐”藝術的培養與傳承上做出了許多努力,其中包括您和您女兒以及兩個外孫女的三代傳承,這是一種血脈的文化延續,有著不可復制的獨特價值。這種親情和畢生事業的緊密結合對您本人和家人來說有著怎樣的意義呢,您是怎樣想到這樣一種傳承方式的呢?
黃:我對女兒和外孫女們的培養,對我和我的家庭,以及劉三姐文化都有著特殊的意義。正如我最開始所說的,我們一直在做傳承劉三姐的工作,幾十年如一日。拍電影、做宣傳、做舞臺劇、駐場演出、培養新人。就拿駐場演出來說,好多劇場我都演過,一演就是十幾年。那么后來我為什么要傳承呢?因為我培養了很多的劉三姐,但是這些演員演一場是一場,演三年是三年,總要離開這個地方,去組建自己的家庭,去發展自己的事業,不可能永遠跟著我做劉三姐的傳承,十幾年、幾十年如一日地做一件事情。當然,這不是人家的問題,而是傳承這件事情本身就有相當大的難度。所以往往是費了很多心思,付出了很多心血,而沒有得到理想的結果。所以我想要把它一代代傳承下去,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培養自己的女兒、女兒的女兒,一輩輩可以這樣傳承下去。我的兩個外孫女現在已經是第三代劉三姐了,她們很有天賦,我并沒有強迫她們,最主要的是她們都對這個事業非常熱愛。這里有個小故事,我最小的外孫女羽秋,在她五歲的時候參加了慶祝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央視“心連心”藝術團慰問演出,但是演出那天她生病了,要先去打針后回來參加演出。我們就說要不要找個姐姐替你,她很堅決地說不要。第一次錄音就表現得很從容,也不怯場,從走臺到演唱,整個表演都完成得很好。而且那場演出改了節奏,原來的節奏是四拍,那天的演出是三拍,她也記得住,唱得出來。記得有一次一位上海的記者在采訪我時說,“劉三姐”這一家人就是為劉三姐而生、為劉三姐而來的。真的是這樣,現在我們一家人都是為了把劉三姐文化永遠地傳承下去。對于我和我的家庭來說,這是一個天時、地利、人和的事情,她們自身有條件,也都很熱愛這個事業,那我何樂而不為呢。這就是我們共同的事業,我不行了有我女兒,我女兒不行了有我女兒的女兒,我們就世世代代去傳承它。我想這也算是我對家鄉、對三姐文化的貢獻吧。
李:那么,您對當下年輕的文藝工作者又有怎樣的建議和期待呢?
黃:首先我想談談對年輕文藝工作者的一些看法。從整個社會現象來看,我最初對現在的許多年輕藝人不甚了解,甚至有種誤解和偏見,總覺得他們比較浮躁,好像沒有更大的理想,就是想唱一首好歌,參加一個比賽,拿個名次,賺些錢,沒有太大的上進心。我總是覺得現在這樣想的年輕人太多了。但是,最近我看到許多年輕藝人的努力,我的看法也在發生轉變,我也在反思自己固有的一些思維。比如,我最近一直在看央視的《經典詠流傳》這個節目,許多年輕的歌手,許多所謂的“小鮮肉”都參加了這個節目。通過他們的演唱和在節目中的表現,改變了我對他們的固有看法。實際上,這些年輕的歌手都是非常努力的,也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很想成為一名優秀的歌唱演員。也許是社會上某些不良的風氣誤導了他們,也誤導了許多不了解他們的觀眾。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當下年輕人為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所做的努力。從演唱來講,他們能夠唱出對這些古典詩詞的理解,充分表現其中的內涵和精髓,我覺得這一點很了不起。所以,以后“小鮮肉”這種包含貶義的稱謂要在我的心中去掉,不能把他們看作只有顏值而沒有內涵和實力的歌手,而要把他們當作是傳承我們優秀傳統文化的先行者、代言人和接班人。實際上,優秀的年輕演員自身的影響力也能夠對青少年起到積極的示范引導作用,應該認可他們所做的努力和貢獻。
如果從更廣泛和更深的層次來講,我也想提出自己的一點看法和期待。其實創作本身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既要創作出新的東西,能跟上這個時代;又要創作出優秀的東西,能夠傳承和發揚傳統文化中精華的部分,確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成的,需要具備很多因素和條件。其中,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責任心。文藝工作者,尤其是年輕的文藝工作者,首先就應該做到熱愛你所選擇、所從事的行業,熱愛這份事業,真心實意地、認真地去體會它、鉆研它,要肯吃苦、肯下功夫。當年為了創作《劉三姐》, 我們下到農村深入生活,放到現在來講也是需要的。如果當年雷振邦不下基層去采風,喬羽老先生不來我們這邊看《劉三姐》,蘇里導演不來體驗我們的生活、采集這里的生活素材,就憑我們自己的能力,怎么可能創作出這樣優秀的電影呢。這需要付出真摯的愛,不僅要愛藝術,還要愛這個民族。不負韶華,不是一句空話,靈感和聰明才智當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相當一部分靈感是源于生活的,是生活的積累。只有經歷了、走過了,才能用這些靈感去豐富自己的創作,才會有想象力,才會有才情。還有一點就是我們文藝工作者的態度問題,也就是對自己的認知和定位。要有一顆平常心,在心里把自己放在普通人的位置上。要明白演員、歌手都沒有什么了不起的,沒有觀眾來捧你、來欣賞你,我們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就。這些都是觀眾對我們文藝工作者的厚愛,我們要永遠懷有一顆尊重和感恩的心。
李:除了電影《劉三姐》,您還參演了眾多影視劇和舞臺戲劇,也常常走到民眾當中現場演出,因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那么這些作品和演出經歷在您的藝術生涯中有著怎樣的意義,您怎么看待它們呢?
黃:如果這些都算上,我確實演了很多,自己也數不清了。最開始的時候我學桂劇,演了很多桂劇的折子戲、傳統戲和整本的大型戲,像《紅樓夢》《西廂記》《白蛇傳》等,我都演過。出演了電影《劉三姐》之后,我就從桂劇團調到了歌舞團,彩調劇團我也待過,演了許多彩調折子戲。而且這些劇團都是下到農村,真正地“為工農兵服務”的,和現在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是一樣的。那時候沒有發達的交通工具,沒有音響設備,演出條件非常艱苦,但這就是我們的工作,這就是“為人民服務”。我們從心底里認同,默默付出,想法非常單純。至于說意義,那就是覺得所有的這些辛苦都是分內之事,“為人民服務”就是我們這些演員需要做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人民服務”,這是我們從小就接受的教育和熏陶。底層勞動人民的日子很艱苦、很單調,看到了我們的演出也就豐富了他們的生活,讓他們明白了什么是美好,什么是文藝,使他們的生活和工作充滿信心。同時我們也明白了什么是深入生活,什么是“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服務”。我們做了,我們付出了,同時自己也成長了,并且收獲了很多東西。我們了解了農民,了解了工人,了解了最基層的百姓,也豐富了我們的人生閱歷和經歷。而且這真的是件偉大的事情,沒有這些工農兵,沒有這些偉大的勞動人民,就沒有《劉三姐》的誕生,也就沒有我們這些源于生活的藝術。可以說,文藝工作者服務于廣大的勞動人民,勞動人民也成就了我們文藝工作者,這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
李:最后想請您談一談您的家鄉廣西,這個以壯族為主的多民族省份,她在您的藝術和人生中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呢?您如何看待這片美麗神奇的土地和她所孕育的多彩文化?
黃: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廣西的整體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尤其是近幾年,感覺講話都更有底氣了。作為廣西人,我們應該好好認識廣西這個地域,找準廣西的定位和特色,去發展自己家鄉的特色文化,將這些文化特色發揮成優勢。實際上《劉三姐》正是在踐行這一努力,讓更多人知道廣西、了解廣西,在地域優秀傳統文化傳播方面做出自己的貢獻。比如現在提出的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東盟博覽會等,這些對廣西來說都是很好的歷史機遇,我們要從歷史和地域上尋找突破口,努力讓文藝精品走出國門,面向世界,得到更廣泛的交流和發展。
我對廣西的情感,那自然是無比熱愛,這里是我的家鄉,是生我養我、讓我一生眷戀的地方。我有許多次機會去到一些更為發達的地區,但是我都沒有離開。是廣西培育了我,劉三姐成就了我,我要對得起這個山歌眷戀的地方。尤其是現在,廣西在不斷地飛躍、不斷地發展,使我們更加有自信。我希望廣西越來越好,能夠在新的歷史定位中經濟更加繁榮,文化也更加繁榮、更加自信。
訪后跋語:
接到《中國文藝評論》雜志的委托采訪黃老師的任務時,很開心,也很激動。隨后我翻閱了許多黃老師的資料,也重溫了黃老師的代表作電影《劉三姐》,那個正義、美麗、聰慧的“歌仙”劉三姐深深地打動了我,毫不因歲月的流逝和時代審美的變遷而失色。因此,也期待著與黃老師的見面。可到約定好的采訪日期時,正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肆虐,因此原定的當面采訪不得不改成電話采訪,心里不免有些失落,又有些擔心電話訪談的不便,從而影響到采訪效果。開始電話訪談之后,我的緊張和擔心隨著黃老師洋溢的熱情和誠摯的話語慢慢緩和下來,一起與黃老師進入她五十余年的藝術生涯,緩緩展開,順利完成。
喬羽老先生曾有評價:劉三姐是廣西沃土上開出的一朵光彩奪目的佳花,黃婉秋則是這種佳花結成的果實。是的,黃老師的成功,她自謙為偶然,實際上是種必然。這種必然首先源自于她生長在廣西桂林,這里的山山水水、風土人情,這個山歌眷戀的地方孕育出了質樸又靈動的黃婉秋,加之她少年刻苦的訓練和扎實的童子功,為后來與劉三姐的結緣埋下伏筆。而更為重要的一點,則是她的氣質與人品。在訪談中,黃老師提到,當年導演看中的正是她身上的淳樸自然,那種沒有被規訓的靈動,和對人物多面向的理解,能夠超越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并歷久彌新。除此,那些不為人知的辛苦與堅守更是在歲月滌蕩諸多風云變幻后所保留下的最珍貴、最堅實的財富,使她能夠在古稀之年從容平和、談笑風生,并懷著一份永遠為人民歌唱的赤誠活躍在舞臺和培養新人、傳承劉三姐藝術的事業中。
“連就連,我倆結交訂百年,哪個九十七歲死,奈何橋上等三年。”我想這或許是世間最動人的情話,通過黃老師的演繹,飛滿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