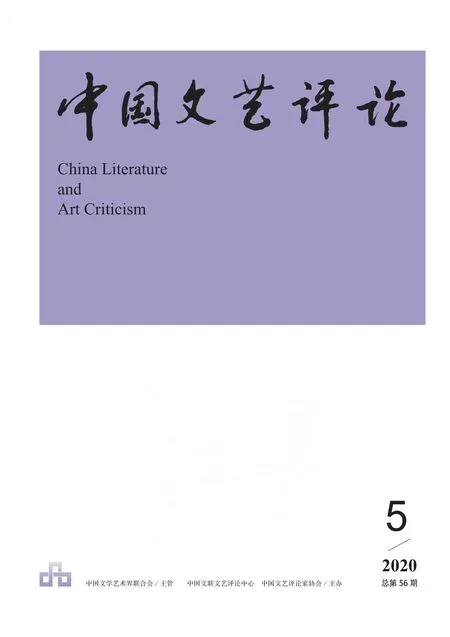中國鄉村的文學在地書寫
——評“鄉村志”系列作品
張麗軍 范伊寧
20世紀90年代以后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中國城市化、現代化進程急劇“加速”。面對當下急速發展變化的新現實,作家們不得不思考如何呈現新的社會風貌和人的心理變動。從《蒼涼后土》《土地神》《村官牛二》到近期出版的“鄉村志”系列小說,四川作家賀享雍的創作始終立足鄉村、面向當下,書寫鄉村發展的新現實,思考鄉村發展遇到的新問題。新世紀以來“不少鄉土小說,寫的不再是一個或幾個人物,而是寫了一個村莊、一個文化群落、一種生存狀態”。[1]雷達:《新世紀以來長篇小說概觀》,《文藝報》2006年10月26日,第3版。賀享雍的“鄉村志”系列小說集中描寫了賀家灣在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村變遷,著重表現了賀家灣三代人在改革開放以后物質生活的提高、內心情感和價值取向的轉變以及現代文明和傳統文化、倫理的沖突與融合。通過描寫賀家灣在土地、醫療、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發展變化,可以尋找到整個中國鄉村當下發展的機遇與困境以及人的內心波動與焦慮。縱觀“鄉村志”系列的十部長篇小說乃至其早期的鄉土小說創作,賀享雍直面鄉村現實、反映鄉村現狀的問題意識,堅持民間立場,吸取傳統和民間的敘事資源以及面對鄉土文化建設的危機感始終貫穿于他的創作之中,展現其對鄉村、對農民乃至對當下社會整體的關懷與反思,體現出作家的博大胸懷和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感,體現出新世紀以來中國鄉村書寫的新主題、新風格和新審美思考。
一、當代鄉村發展新現實的審美書寫
“任何一個時代一個偉大的作家跟這個社會的關系永遠帶有一種批判和審視”[1]劉衛東:《圪蹴在“形而中”的秦嶺》,《文學界》2010年第2期,第16頁。,在賀享雍的創作中,作家本人直面現實的創作姿態和問題意識貫穿始終,作家從鄉村的各個角落、發展的多個方面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入手,重點呈現了當下現實社會背景下農村發展面臨的困境和新時代背景下農民在情感上的變化。有學者說:“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像一個偉大的發現病情并治療病情的醫師一樣,診斷現實生活中的殘缺和病象。”[2]《現實主義的此岸與彼岸——專家、作家在第八屆中國文學論壇上的發言》,《名作欣賞》2012年第3期,第7頁。在賀享雍筆下“診斷”的不僅僅是中國鄉村和農民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危機與困境,更是社會、國民在當下真實存在和不得不面對、解決的現實問題。
1. 當下鄉村發展現狀的外部描寫
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給鄉村帶來重大利好。首先體現在農村的生產力,以及農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賀享雍在進行小說創作時將這一現實情況通過對農民生活細節的描寫自然呈現出來,如《土地之癢》中賀世龍回憶饑荒歲月中家人被餓死的慘狀、帶弟弟討要紅薯干的情景。在進入新世紀以后,隨著農民收入的增加,小說中多次出現“現在誰還缺這口吃喝”“大魚大肉吃得多了,反而更喜歡吃點清淡的”之類的文字。在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滿足之后,村民們有了更高的追求,如休閑娛樂、提升自己賺錢的能力等。但是在農民的休閑娛樂中,一些不良的休閑方式日益流行,在“鄉村志”系列中幾乎每一部小說都描寫了賀家灣人對打麻將、賭錢的癡迷。這既是對鄉村現狀的真實描繪,也是反思鄉村文化建設的一大體現。農民在富起來之后如何進一步提升自己的能力與審美等,都是在人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亟需解決的問題。
其次是隨著科學技術和工業的發展,農耕器具也發生了重要變化,農業機械化的生產方式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生產效率,使得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而城市化建設過程中對勞動力的需求和更高的經濟收益,吸引了大量的農民進城。賀世海進城從事建筑行業后,因工地缺乏人手想要從賀家灣帶領一批人進城務工,農閑時的村民們十分樂意再多掙一份錢。而這些人在嘗到進城打工收入高的甜頭后,越來越愿意進城,甚至開始以打工為主,對種地的熱情卻日益減退,減免農業稅后也沒有明顯改善這一情況,土地拋荒成為當下農村的普遍現象。在《土地之癢》中,這一問題集中體現在對土地大量拋荒的描寫以及老一輩農民賀世龍面對無人耕種的土地時的痛心和不舍。
“在城市文明和鄉村文明的極大落差中,作為一個擺脫物質和精神貧困的人的生存本能來說,農民的逃離鄉村意識成為一種幸福和榮譽的象征。”[1]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論》,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30頁。賀家灣走出去的知識分子,如老一輩的賀世普、第二代進城的賀健,以及第三代研究生畢業的賀華斌,無一不留在了城市中工作、生活,而他們對賀家灣的發展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在《大城小城》中,作家更是集中描寫了賀家灣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在城市的生活與工作,他們在城市生活雖不易,但回到鄉村卻更不可能。一批一批的人走向城市,鄉村成為他們回不去或者不愿回去的遠方。在這一角度上,作家給我們打開了這樣一個思考的空間。“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農村逐步失卻了一個中堅力量——鄉村精英”[2]林文勛:《歷史與現實:中國傳統社會變遷啟示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82頁。,而留守鄉村的主要是“386199”[3]即以“三八婦女節”“六一兒童節““九九重陽節”等節日的日期來指稱婦女、兒童和老人等留守鄉村的群體。群體。農村不斷向城市輸送人才和勞動力,老一輩的農民很明顯不足以將農村發展向前再推進一步,沒有新生力量的注入,鄉村的發展勢必要呈現萎縮的狀態,如何為農村發展提供新鮮有力的力量?這無疑是當下鄉村所面臨的最為嚴峻的問題。盡管推行大學生村官等政策,但也遠遠不夠解決鄉村發展的積弊。小說中專科學校畢業的賀端陽想要競選鄉村基層干部幾度受挫,正說明了鄉村問題的難點。這個“難”和根植于農民血液中的傳統倫理觀念以及價值觀有大關系,更與那種膜拜權力的劣根性有不可推脫的關系。對權力的爭奪和耍弄、拉幫結派、幫親不幫理等思想的根深蒂固才是阻止鄉村進一步邁向現代化發展的障礙。盡管農民經濟收入增加了,鄉村新的樓房也接二連三地建起,但村里稀稀落落的人口讓村莊顯得空蕩蕩,這種“人去樓空”的景象不僅僅是由于鄉村人口流失帶來的鄉村萎縮,還有村民們在情感上的空虛感。
2. 展現當代農民的心靈情感之變
在生產生活方式得到改變的情況下,人與土地、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也都悄然發生了變化。在上述鄉村發展問題之外,更深層次的是農民的精神危機以及鄉村文化建設過程中的焦慮。“靠土地謀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貴”[4]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鄉土重建》,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頁。,人與土地的關系的親密程度決定了情感程度的不同。改革開放以前,農民的主要經濟收入靠的是種植農作物,改革開放以后農民獲取經濟收入的途徑越來越多,相比之下土地帶來的收益卻顯得微薄,大部分農民尤其是年輕人選擇進入城市謀生。其他留在村子里生活的人,也不再是完全依靠種地,如身體不好的賀世鳳和妻子開飯店、賀端陽決心種植果樹。老一輩農民與第二代、第三代的賀家灣農民對待土地的情感是不一樣的,進城離鄉的人更希望能夠在城市中扎根生活,土地對于他們來說不是很重要,而對于堅守在土地上的老一輩農民,比較典型的如賀世龍,深深眷戀著土地,即使不掙錢也堅持種下去。但是在歷經多次土地制度改革后的賀世龍最后也對自己是否真正擁有土地產生了疑惑,土地制度改革帶來的“癢”也只對真正對土地擁有深厚情感的農民產生影響,而那些早已背井離鄉的人已不再將工作、生活乃至情感的重心放在土地上。
“人在改造其與物的關系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改造著與世界的審美聯系”[1]趙園:《地之子:鄉村小說與農民文化》,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87頁。。在傳統鄉村倫理中,血緣親族關系是維系人們之間情感的紐帶,但生活方式以及生產方式的改變和現代文明的進入,不僅使農民對土地的情感發生了變化,在血緣親族關系上也發生了變化。盡管人們之間依舊重視血緣關系,但在更多時候血緣關系已經開始讓位于經濟利益關系。如競選村主任拉票時,誰能夠給選民更高的利益誰就能夠獲得他們手里的選票;想要跟著賀世海繼續在工地務工的村民也在努力拉攏、修復和賀世海家的關系。一方面現代文明的進入給村民們帶來了思想上的革新,使他們能夠更加適應現代化建設的節奏,另一方面這種變化也造成了人與人之間情感的隔膜。如小說中對“人情淡薄”的描寫:村民們對“瘋子”賀貴的疏遠以及對他死亡的冷漠;賀家灣村民在得知村委會沒有將制藥公司額外補貼村民的錢發放,不顧往日看重的親情要求查賬。在個人利益面前往日的親情倫理也要做出讓步,這也是現代化進程中人們思想經歷的一個階段,如何平衡傳統倫理與現代文明之間的關系仍是當下整個社會需要關注和探索的問題。
“我國要實現現代化,最大的一個瓶頸就是城鄉二元結構和城市化水平問題。”[2]李培林:《小城鎮依然是大問題》,《甘肅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第3頁。城鄉發展不平衡是當下社會備受關注的現實問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到城市謀生,更多是因為城市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條件和公共服務、更高的經濟收入,但進入城市后能夠真正融入的人卻少之又少,這就給他們帶來了極為矛盾復雜的精神困擾:不愿意回到故鄉但是又無法融入城市,于是他們成為城市的“漂泊者”。近年來作家們也越來越多地關注進城后的農民的生活、情感困境,如石一楓筆下的陳金芳、賈平凹筆下的劉高興等不同類型、以不同身份進入城市的人物形象,展現了進城農民生活上的困頓以及精神情感上的焦慮。賀享雍在《大城小城》中描寫了以不同身份進入城市的賀家灣農民的心理狀態,一類是生活在城市最底層的農民,如賀興瓊靠在勞動市場打零工、服侍癱瘓病人獲得收入,生活較為拮據,還有一類是在城市中站穩腳跟的農民。這里面有的是靠自身的專業知識,如做校長的賀世普;有的是靠最初的資本積累逐漸在城市扎根生活,如依靠承包建筑工程獲得資金的賀世海、賀興仁;還有的則是通過出賣自己的情感和身體留在城市,如出賣情感的賀健、出賣身體的賀冬梅。盡管他們以各自的方式留在了城市,但是距離被城市接納還有很大一段距離,他們雖然人在城市但心靈卻無法真正安放。即使是村民們眼中的“驕傲”的賀華斌,在研究生畢業后留在了城市工作,“可他在這個城市里像個流浪兒一樣,別看地方這樣大,他卻沒處可去”[1]賀享雍:《大城小城》,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9頁。,狹小擁擠的出租屋、忙碌的工作、靠外賣度日的他在城市中感受著前所未有的孤獨,而這一切卻無人可訴說。
“文學要面對人生,講人文精神,講人道主義,就要關注生活在重重困境中的社會底層的基本群眾,滿足他們的審美意愿,其手段只能是現實主義。”[2]楊立元:《新現實主義小說出現的歷史情境》,《新現實主義小說論》,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第32頁。賀享雍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表明了他的民間立場,不管是對鄉村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的揭露與反思,還是對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心理變遷、精神困境的描寫,賀享雍的創作具有很強的“問題小說”傾向[3]此處關于“問題小說”的定義是寬泛的,“任何具有社會價值和社會反響的文學作品,都或深或淺地提出一些社會問題。……廣義地說,思想性和社會針對性強的小說,都可以歸入‘問題小說’,在作家以文學參與歷史發展的自覺性”。參見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第229頁。。這些問題的發掘與呈現的背后不僅僅是作家對當下鄉村發展新現實的擔憂,更揭示了整個社會面臨的現代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二、植根于民間與傳統的審美形式創新
“民間是自由自在無法無天的所在,民間是生機昂然熱情奔放的狀態,民間是輝煌壯闊溫柔淳厚的精神,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4]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頁。縱觀賀享雍迄今為止的創作,堅持以民間立場書寫鄉村現狀是其創作的重要特色。除了大量使用四川方言、俚語營造獨特的地域文化氛圍,在他的創作中,對民俗、民間故事和傳說等民間藝術資源的汲取,豐富了小說的表現力,讓小說的情境更加具有真實感和生活氣息,也為讀者了解當地人文風情提供了更好的窗口。除了對民俗的書寫和民間神鬼傳說的引用外,賀享雍還借鑒了“說書人”和章回體結構等傳統小說敘事手法,增強了故事情節的曲折性和可讀性。在上述現實主義手法和對民間藝術、傳統小說敘事手法繼承與發展的基礎上,賀享雍為中國當代文學新鄉土小說添寫了濃厚的一筆。
1. 地方民俗和民間故事的引用
民俗指“一個國家或者民族中廣大民眾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文化生活。民俗起源于人類社會群體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時代和地域中不斷形成、擴布和演變,為民眾的日常生活服務”。[5]鐘敬文:《民俗學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頁。民俗涉及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鄉土小說創作中對民俗的書寫似乎成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無論是五四時期的鄉土小說,還是十七年間農業合作化題材小說、新時期的尋根小說,對民間風俗的書寫都有跡可尋,民俗也是小說中表現獨特地方色彩的重要部分。賀享雍鄉土小說的創作為我們呈現了生動的川東風土人情畫卷,但更為重要的是在賀享雍所描寫的民俗活動中,蘊涵著作家對“人”的關注,將貫穿于民俗活動中的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情感,以及人的心理變遷很好地呈現出來,令風俗更加具有人情溫度而不僅僅是鄉土小說中的裝飾品。
小說中既有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民俗描寫,還有很多體現地方特色風俗的書寫,如川東地區正月里大型游藝——“抬亭子”,小說給予了大量筆墨,從彩亭制作藝術的講究、人物造型的雅致、表演技術的高難度等多方面向讀者展現了這項精彩絕倫的民間藝術。還有婆婆娶兒媳婦時眾人對公婆“鲊寒(咸) 老婆婆”和“抬椅轎”、春節期間的“壩壩戲”等都展現了獨特的川東風情。除了具體的民俗活動描寫,作家在小說中還提及了許多民間的鬼神和傳奇故事,增強了小說的神秘色彩。同時,對鬼神故事的描寫也從側面反映了民間的信仰。如賈佳桂因多年與丈夫不睦懷疑是灶神不安造成的,因此特地請村里的風水先生賀鳳山來幫助安灶。面對這樣的封建迷信活動,賀世普并沒有像以往那樣批評妻妹的愚昧與迷信,而是報以理解和同情:“人活著都要有個精神寄托,我去打破佳桂的夢做啥?”同樣,對“灶神”的崇拜體現了人們內心對家庭和睦的一種渴望與追求。此外,還有對“樹神”的崇拜。賀家灣村口據說有一棵有著六百多年歷史的老黃葛樹,成為了許多村民們的“干保保”,備受村民的崇敬,老樹福蔭著村民,同時也是整個賀家灣歷史的見證,在賀家灣發展的不同時期這棵老黃葛樹都以自己獨特的姿態參與其中。小說中最富有傳奇色彩的是對村里修公路要砍伐黃葛樹時的一段描寫,老樹仿佛有所感應一般搖晃著樹枝,流出“血液”一般的液體。除了對神明的崇拜,作家還寫到許多與鬼魂有關的故事,其中多與親情倫理相關,如賀端陽和賀貴看到鳥兒認為是自己父親的靈魂、賀端陽母親夢到丈夫對兒子前途的擔憂與忠告、賀世龍欲持刀與人爭執時鐮刀突然掉落等,這些描述除了增加故事的神秘色彩之外,更多傳達的是民間重視親情倫理的文化氛圍,也正是基于以上種種文化和信仰的基礎,賀鳳山以及他的兒子賀福來能夠依靠看風水、占卜等獲取生活來源并受到村民們的敬重,這些與長期積淀在人們心中的傳統思維方式有著很大關系。
“中式的民俗文化因子深深扎根于廣大鄉村并占據主導地位,西式的一些文化風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廣大鄉村。”[1]陶維兵:《新時代鄉村民俗文化的變遷、傳承與創新路徑》,《學習與實踐》2018年第1期,第134頁。農民的文化心理和價值觀念在具體的民俗活動中悄然展露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鄉土小說中民俗的描寫并不僅僅是為了裝點作品的“鄉土”性,而是有著更大的文化內涵和價值意義。民俗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隨著時代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一些新的民俗得以出現或者舊有民俗逐漸演變來適應現代人的生活需求。如喪葬活動中出現燒紙汽車、冰箱等現代交通工具和家電等祭奠先人,婚嫁也省略了一些低俗的“婚鬧”行為。賀享雍筆下充滿人情味的民俗書寫很好地再現了農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倫理觀念及其變遷的過程。在城市化進程加速的時代,村莊的萎縮乃至消失愈發常見,與此同時依附在鄉村生活中的鄉土民俗也在大量消失,作家通過對鄉村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民俗活動的描寫,為時代留下了重要的鄉村生活風貌的歷史畫卷。
2. 傳統小說敘事藝術的轉化
除了對獨特民俗的細節呈現,作家在敘事手法上也借鑒了民間說話藝術和傳統長篇章回體小說的敘事結構。小說中“說書人”角色的設定拉近了作家與讀者的距離,同時能夠很靈活地變換敘述對象,以便于展開不同人物的故事情節。對古代長篇章回體小說情節結構方式的借鑒也使得小說對每個人物性格、故事情節的展開更加清晰。
在賀享雍早期作品《后土》中就鮮明體現了“說書人”敘述視角的特征,小說開頭“楔子”中以第二人稱“你”為說話對象,通過潛在的說書人視角逐一向讀者介紹佘家灣的自然環境和地理特征。在《村醫之家》中,這一敘事手法表現得更為典型,作家將敘事視角鎖定在村醫賀萬山身上,并讓其以第一人稱“我”來完成整個故事的講述,但是在小說中這個“我”卻是以第一人稱的全知視角的方式展開敘述的,如賀萬山回憶自己小時候的故事,雖然開頭就交代了是自己母親告訴他的,但是在具體展開的過程中對很多細節的描述是超越了第一人稱視角限制的,如對爺爺、母親的動作、心理等細節的描寫。最為主要的是作為賀萬山交流對象的“我”的聲音卻不曾出現過,二人的對話幾乎是賀萬山一人自問自答或者自己轉移話題完成的,“我把這次進城端‘鐵飯碗’的機會給放棄了……我后來后悔過沒有?實話對大侄兒說吧,直到今日,我也沒有后悔過。為啥?”“既然剛才我說到兩小子的事,從現在開始,我就來說說他們的事。”[1]賀享雍:《村醫之家》,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127頁、165頁。在賀萬山這些“自言自語”中,小說的故事情節轉換自然順暢,說書人的口吻也給讀者做了很好的提示,既交代了故事的前因,又自然過渡到后續來展開,便于讀者在眾多人物的繁雜故事情節中理清思路。此外,利用說書人的特征還能夠對情節的詳略做出合理的安排。民間的說話藝術講究情節緊湊、曲折動人,對人物心理活動的展開相對于西方小說來說則較為簡略,如《土地之癢》中賀世龍看見兒子賀興成長大懂事時的心理描寫沒有展開,而是被一句“心里自然高興不提”帶過,還有李春英和畢玉玲兩妯娌鬧矛盾后,二人由停止爭吵到后面幾年又和好,這一過程作者也只用“這已是后話,不提”省略過去。小說中還經常出現一些自問自答的句子,如“鄭支書為什么要在他這個大隊按老祖業分田呢?難道他不曉得用這種方法分田毛病很多?個中原委其實十分簡單……”[1]賀享雍:《土地之癢》,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17頁。通過這種方式來引出下文。無論是設置懸念、轉折過渡,還是進行情節的詳略安排,“說書人”的敘述技巧極大地方便了故事情節的展開、提高了文本的趣味性,拉近了與讀者之間的距離。
除了利用說書人敘述視角的設置串聯轉換故事情節以外,賀享雍作品中的情節結構設置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我國古代長篇章回體小說的結構方式。在小說的回目形式上保留了古代章回小說的神韻。如《村醫之家》由“楔子”和13章組成,每一個章節名稱概括了主要故事內容,如第一章“我爺爺和我爹都是鄉村郎中”;第二章“我治好了自己的病”;第三章“我暗戀上了鄭彩虹”,每個章節下面又由不同的小節組成。小說由多個主要情節構成的發展脈絡層層遞進,每個主要故事情節中通過回憶或者插敘等方式交代人物背景,既豐富了人物形象又能夠讓讀者更全面地了解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在線型敘事結構下,賀享雍將幾十年來中國鄉村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風俗文化等方面的變遷歷史清晰地再現出來,為我們提供了一幅具有獨特地域風貌和生活溫度的風景畫、心靈史。
三、傳統鄉村倫理體系的解體與新建
“在特殊的風土人情而外,應當還有普遍性的與我們共同的對于命運的掙扎。”[2]茅盾:《關于鄉土文學》,《茅盾論中國現代作家作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年,第241頁。如果說對當下農村、農民命運的關注與關懷,以及對民俗的書寫和傳統小說敘事經驗的借鑒是賀享雍鄉土小說創作的藝術特色,那么在這背后更大的關懷和視野,則是作家對整個社會和人類命運的思考。從表面上看作品中對不同農民形象的塑造是在寫當下農民的心理和精神狀態,實則是對整個國民性的反思。按照“鄉村志”系列小說的出版時間來看,較早出版的《土地之癢》《民意是天》《人心不古》《村醫之家》故事的發生地主要在賀家灣,《是是非非》《青天在上》則是以官場政治為書寫重點,講述重心在鄉村和城鎮之間,而到了后期出版的《大城小城》則將故事發生的地點徹底轉移至城市。這種“由鄉入城”的變化體現了作家創作視野的逐漸擴大,對農民的現實境遇描寫不拘泥于鄉村,而是擴大到進城的農民。賀家灣人生命軌跡的演變歷程展現了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和人民心靈的變遷史。
鄉土倫理產生于傳統的熟人社會和單一的小農經濟之中,“是在鄉土社會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和相對封閉的生活方式基礎上,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關系時應該遵循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3]李良、韋瀟竹:《傳統“鄉土倫理”的現代轉型與農村基層行政倫理建設》,《廣東開放大學學報》2016年第3期,第107頁。傳統農耕社會的封閉性和保守性使得人們生產生活主要依靠家庭和家族來完成,對土地的依戀是人們安土重遷心理的重要原因,封閉性和交通的不便使得人口流動性較弱,人們就更加重視家族倫理和熟人社會關系。這種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以家庭為本位、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倫理價值觀念影響了幾千年來中國人的性格和處事方式。但是改革開放以后,市場經濟的進入打破了傳統鄉村的經濟模式,因此傳統鄉土倫理體系的破裂也在意料之中。“我國社會轉型期的二元化城鄉經濟結構類型勢必孕育著二元化的城鄉倫理結構類型,即城市倫理與鄉土倫理之分辨。”[1]王露璐:《社會轉型期的中國鄉土倫理研究及其方法》,《哲學研究》2007年第12期,第80頁。在傳統與現代碰撞之中如何建構我們的鄉土文化乃至民族文化,是作家和研究者們都不得不面對的重要現實問題。
1. 現代制度對傳統鄉土倫理價值的沖擊
“現代生活已在世界范圍內打碎種種古老傳統,中國農村也在開始變革,但觀念形態這方面的變化卻并不能算迅速”[2]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284頁。,現代文明的進入對于傳統保守的鄉村來說首先沖擊了人們心中固有的思想觀念和行為習慣,打破了人們以往對于經濟、基層管理的認知,同時鄉村百姓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也影響了鄉村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現代文明與傳統鄉土文化的沖突首先體現在經濟方面,市場經濟的建立與推廣打破了鄉村小農經濟的保守封建。原有的鄉村主要是自然經濟,人們依靠土地獲得生活來源,村鄰之間經常互幫互助完成耕種和收獲。土地制度由合作社改革為生產責任制分田到戶的時候,人與人之間緊密互助的關系已經有所瓦解,家家戶戶忙著開墾屬于自己的土地,在《土地之癢》中,村民們開荒熱情的高度膨脹以至于破壞了當地的環境,村鄰之間也經常因爭地邊發生矛盾,即使賀世龍、賀世鳳兩兄弟之間也因一垅地而鬧得不愉快。伴隨市場經濟而來的效率和報酬意識受到了農民內心的不滿和抗拒,也打破了傳統鄉土文化中親緣關系和地緣關系中互幫互助的傳統。
其次是現代法律制度對傳統鄉土文化的沖擊。過去鄉村的“法”主要是指宗族家法和人們習慣性的行為規則,靠的是宗族長老或地方鄉紳。在熟人社會中“情”是人們衡量事情對錯的一個重要考量標準。而現代法律制度是依照法律條文辦事,法理之外再考慮情的部分。“即使經歷了五十多年的時間以及當代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制定法的規則還是沒有根本改變這種已深深扎入我們靈魂和軀體中的習慣”。[3]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82-184 頁。小說中,賀世普和賀家灣村民之間的沖突具體、形象地體現了現代法律意識在基層推行之艱難。中學校長賀世普退休后回到家鄉出任村矛盾糾紛調解小組的組長,依靠自身在村民心中的權威性和可信度,賀世普確實為賀家灣村民們解決了不少問題,但是在很多時候村民們覺得賀世普和他們不是一路人,比如賀世普在處理賀建華撫恤金時堅持其配偶和女兒的繼承權,堅持將妹夫告上法院判刑等,在村民們“就活人不就死人”的親情倫理觀念、鄉情大于國法的觀念中,賀世普這樣的做法是不近人情的。“習慣要服從法律”是賀世普在家鄉的處事原則,但在傳統倫理價值面前,賀世普一次次碰壁,最終因不得人心不得不回城里去。現代法律制度推廣之難還體現在基層政治方面。關于基層組織的民主選舉,賀享雍早期在《土地神》中條分縷析地剖析了基層如何應對“民主”。在《民意是天》中則更加深入展開農村基層政治生態的現狀,一方面寫出了村民對《選舉法》相關法律知識的匱乏,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村民們對選舉漠不關心的態度。村民們面對選舉有著各種人情和利益關系的考慮,賀端陽經歷三次選舉,每一次選舉作家都讓讀者看到了當下鄉村基層政治的缺陷,以及法律規則被無視、玩弄。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賀享雍對農村基層干部形象的描寫與刻畫是極為突出、傳神的,既寫出了官場弄虛作假、權力勾結、玩弄權柄等不良風氣,又寫出了基層干部的不容易,作者在審視和反思他們性格上的缺陷之外又抱有一種同情,如早期作品中牛二、“鄉村志”中的鄭鋒、賀世忠、賀春乾等人工作中的無奈之處。
2. 現代思想意識的悄然融入
有學者提出:“我國的現代化進程歸根結底是個農民社會改造過程,這一過程不僅是變農業人口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農民文化、農民心態與農民人格。”[1]秦暉:《耕耘者言——一個農民學研究者的心路》,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3頁。當下的鄉村倫理和文化具有轉型時代的鮮明特征,既保留了傳統的一面又有現代性的一面。伴隨著現代生活方式的適應,農民的思想也在逐漸向現代靠攏,在“鄉村志”系列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已經普遍接受市場經濟帶來的公平、效率、交易的意識,賀家灣的村民在請人幫忙時已經習慣了支付一定報酬。同樣村民們的法律意識和民主意識也在悄悄發芽。在描寫村民現代法律意識淡薄的同時,作家不僅僅指出了農民的思想現狀和后果,而是進一步探尋問題的成因。小說寫到的問題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基層干部沒有宣傳普及到位,甚至根本沒有向群眾宣傳基本的知識。長期以來選舉組織者選舉投票的不正規操作給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中國農民確實缺乏民主的實踐,對民主選舉制度沒有太深的認識,這不能怪他們,只能怪我們這些選舉的組織者嘛!”[2]賀享雍:《民意是天》,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316頁。盡管在具體過程中仍存在著很多問題,但是現代經濟、法律意識已經影響了人們的行為規則和當代鄉村倫理體系的新建,在今后的中國鄉村發展中如何普及、規范制度操作是當下需要解決的問題。
總之,鄉土文學是百年來中國文學書寫中最重要、影響最大的審美主題,由此產生了魯迅、茅盾、廢名、沈從文、趙樹理、孫犁、柳青、梁斌、莫言、賈平凹、趙德發等眾多名家。魯迅、趙樹理等吸取民間藝術資源和傳統小說敘事經驗,描繪出一幅幅獨具地方特色的鄉村風情畫。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何申、關仁山、劉醒龍等作家為代表創作了一批關注社會現實的作品,因此形成“現實主義沖擊波”的文學創作潮流,反映了20世紀末面對社會轉型期的重要社會問題和人們所經歷的轉型期的陣痛。作家們的這種創作姿態體現了他們身上的“一種人之所以為人的精神,一種對于人類發展前景的真誠和關懷,一種作為知識分子對自身所能承擔的社會責任與專業崗位如何結合的總體思考”。[1]陳思和:《就 95“人文精神”論爭致日本學者》,《天涯》1996年第1期,第19-25頁。鄉村生活經驗是作家們進行鄉土小說創作時不可或缺的生活體驗,但是由于現代化進程的加速以及作家們在創作時多數已經久居城市等現實原因,讓作家們在捕捉當下鄉村發展的問題和農民的精神情感狀態時往往有“隔膜”之感。當下能夠像趙樹理、柳青等作家深入鄉村生活進行創作的作家實在少之又少,賀享雍則是其中不可多得的一位。他對農村和農民始終抱著理解和共情,在作品中一直試圖為農民解決眼下的困境。
賀享雍“鄉村志”系列小說的推出,不僅直指當下鄉村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直面農村背后更大的中國社會現實。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賀家灣幾十年來的發展正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縮影,許多問題不是農村獨有的,而是整個社會不可忽視的更為普遍的問題,涉及到整個社會的精神危機和文化重建的困境。作家通過小說世界對當下社會構成一種對話關系,這種對話不僅僅是針對過去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和我們當下剛發生和正在發生的社會現實進行對話。這種直面當下的勇氣,以及洞悉一切生活細節和人的心理變化的筆力,為我們呈現了當下鄉土小說寫作所需要的一種重要的品格,體現出一種“當下現實主義”的可貴審美姿態和建構精神。更為寶貴的是,在當下諸多由作家在城中創作的“緬懷”式的鄉土文學作品中,賀享雍通過扎實的在鄉寫作所捕捉到的同時代人的心路變化歷程,為研究者以及后人們提供了一份更具有生活細節和生命溫度的文本。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盡管“鄉村志”系列小說在敘事技巧上仍有一些不足,但是小說所建構的完整的鄉村發展史、農民心靈變遷史,為我們回顧歷史、反省當下提供了一面很好的審美之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