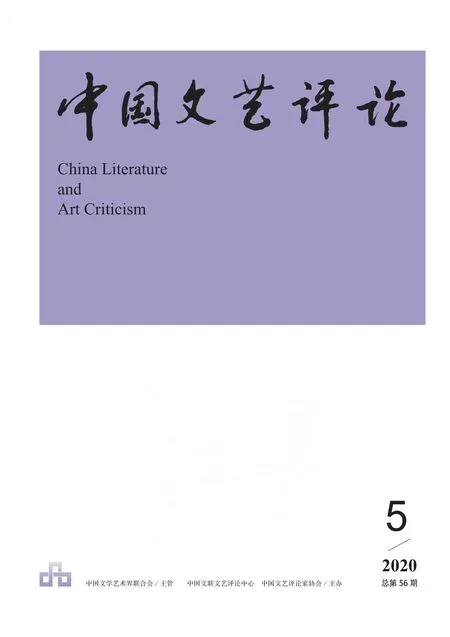新時代需要怎樣的現實主義戲劇
王長安
當前,隨著“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這一創作導向的持續發力,以及“抓住重大節點”這一創作要求的有力推動,現實題材戲劇創作呈現井噴之勢,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再度回歸主流。盡管參與廣泛,場面壯觀,其情也高漲,其勢也洶涌,但結果依然沒有跳出——作品多,佳作少;來得快,去得疾;冀望高,收效低;“有高原”“沒高峰”——這一故轍。個中原由或許有潮流之下倉促投身,只能借助既有儲備和習慣認知勉力而為的匆忙;亦或有未及審慎考量當今現實主義的特殊內涵和嶄新使命而隨流跟風的盲目,故而在總體上未能收獲預期成果。
在我看來,現實主義盡管是一個并不算新鮮的話題,但要真正實現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發掘現實主義的廣闊內涵,弘揚現實主義的深厚能量,并非輕而易舉之事。現實主義是一個常做常新并需要不斷生發、賦予新解的時代命題。
一、現實主義旨在表現題材精神本質的現實性
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創作方法是相對晚出的。它是西方繼古典主義、浪漫主義之后出現的一個較富時代意義的新的創作思潮,其主要成就在小說領域。由于其正式產生的時代距我們較近,名稱中有“現實”二字,早期作品內容又以反映現實居多,故而人們就悄然地把這種創作方法與題材選擇畫了等號,理所當然地認為:現實主義創作就是寫現實題材。
其實,現實主義盡管較為看重表現真實,但這個“真實”并非只是“現實”,也不是現象和存在的簡單真實,而是本質和精神的真實。作家何其芳先生就曾指出:
現實主義是按照生活實際存在的樣子反映生活,這樣一個解釋好像許多人都不否認。生活的實際存在的樣子,并不只是生活的外貌,同時還包含它的內在意義。這樣,現實主義就不僅要求細節真實,而且還要求本質的真實。文學藝術的典型性就是從后一要求來的。[1]何其芳:《文學史討論中的幾個問題》,《文學藝術的春天》,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年,第131頁。
可見,現實主義從來就不止于所謂的客觀真實,也不止于對現實存在的如實反映,而是要體現作家、藝術家的主觀能動性,按照歷史和人民的意愿揭示生活的本質,反映出現實生活所體現或代表的現實社會的理想。換言之,一切能抒發現實社會情感、理想,并代表其精神本質的題材,都為現實主義所冀望、所歡迎。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實主義不僅不必拘泥于現實題材,有能力面對廣闊社會和深遠歷史,而且還可以進入非現實的神話世界和未來世界。中國古代的神話故事,如“后羿射日”“女媧補天”“愚公移山”“精衛填海”之類,都可看作是有浪漫主義成分的現實主義創作,至今仍散發著鼓舞人心的現實主義光芒。茅盾先生在談及現實主義創作時曾說過:
先秦時代記錄下來的神話片段,如射日、補天、移山、填海,都表示了人類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堅決意志和偉大氣魄。……我們的神話反映了我們的先民不肯受命運(自然力是其象征)的支配,是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這都是不承認宇宙間有全能的主宰(天帝,至高無上的尊神),而確認人是宇宙間的主宰。[2]茅盾:《夜讀偶記》,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58年,第29-41頁,轉引自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編:《茅盾論現實主義產生的時代》,《文學理論學習參考資料》(下),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2年,第516頁。
茅盾先生的這段話,正是說明了現實主義的要義不僅僅指題材要有當下屬性,更指其所表現出的精神本質的現實性。不觸及精神實質,不反映人的本質,不揭示人類的總體意志,即使是最現實、最當下、最熱點的題材也難當現實主義之名。如若很好地反映了人們的當下訴求,即使是現實以外的事情也是現實主義的。因此,茅盾先生才把“表示了人類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堅決意志和偉大氣魄”的古代神話堅定而又深刻地稱為“神話的現實主義”[3]同上,第517頁。。可見,現實主義并不只由題材本身的現實性所決定,而要看它給人們創造和提供了怎樣的精神世界。在我看來,這些古代神話作品不僅“表示了人類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堅決意志和偉大氣魄”,而且表現了其所產生的那個時代的社會訴求,創造了人的精神世界的本質真實。故而,它是“神話的”,更是“現實主義的”。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現實主義就題材而言其領域是廣闊的,話題是廣泛的,真實亦是廣義的,遠大于現實題材本身。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有了從上古神話到《詩經》《楚辭》,從《十五從軍征》到“三吏”“三別”,從《竇娥冤》到《秦香蓮》,從《白毛女》到《朝陽溝》等一條縱貫幾千年,影響數百世的偉大的現實主義文藝傳統。
如今,由于我們對現實主義的理解或狹隘、或膚淺,使得我們在題材選擇上拘謹、僵化,甚至盲目。一說到關注現實,便不管自己是否熟悉、是否擅長,不管題材本身是否能體現現實本質和時代訴求,或是否可以代表當下社會的整體意志和受眾的價值取向,便一擁而上地去寫現實事件、熱點題材,把決定作品成敗的籌碼押在題材上,重蹈了“題材決定論”的覆轍。一時間“扶貧戲”“革命斗爭戲”鋪天蓋地而來,但其中多數作品淺薄空洞,無任何精神引領和本質真實可言。就連“一個都不能少”“母親”這樣的熟語、名詞,都被多部“扶貧戲”和“革命斗爭戲”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為劇名。所不同的只是“一個‘都’(不能少)”和“一個‘也’(不能少)”,“‘母’親”“‘娘’親”或“……母親”等一些字詞游戲罷了,內容的蒼白由此可見一斑。沒有真情實感,沒有精神追求,現實題材也會淪為老生常談,其出之也迅,朽之也疾。現實主義和其他一切創作方法一樣,靠的是作品的精神內涵和本質力量,而非題材的熱、冷、新、舊。若不能在本質層面接通人們的情感,反映藝術的“大真實”,完成精神構建,再現實、再搶手、再“熱辣”的題材都將與現實主義的本真相距甚遠,終究成不了現實主義的力作,而淪為“現‘世’主義”。
二、現實主義中的典型人物是有人氣的英雄
恩格斯曾指出:“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1]《恩格斯致瑪格麗特·哈克奈斯(4月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0頁。這里,恩格斯指出了現實主義的兩個層級。一是真實,現實主義必須以真實為基礎,離開真實,現實主義將不復存在。甚至,這個真實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簡單真實,而是連細節都必須經得起推敲的全面真實。二是典型,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創作方法,真實并不是也不應是其全部。它要在真實的基礎上創造典型人物,并且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典型人物,而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里,完成典型人物的塑造才是它的最高追求和最終目的,是其使命所在。
近年來的某些戲劇創作,出于對某種現實精神弘揚的需要,在人物塑造上有意放大其人格光環,背離了典型性原則,一味拔高人物,使其英雄化,把現實主義對典型人物的追求誤讀為對人物的“高大上”追求。凡人不再平凡,小人物變成大英雄,大有重蹈概念化覆轍之虞。例如黃梅戲《遍地月光》[1]黃梅戲《遍地月光》由安徽省黃梅戲劇院于2016年9月在合肥首演,編劇陳明,導演孫虹江,主演吳亞玲。,其原本是要塑造一位善良的農村女性(林月芳),為了鄉鄰的托付,她毅然肩負起了為突然處孤的孩子當臨時媽媽的重擔。劇中有這樣一個情節,當其生活入不敷出時,她瞞著孩子悄悄接受了一個給當地學校送桶裝水的工作。這本足以讓人們看到小人物的善良和努力,看到平凡者的擔當和高尚情懷。但編導對此似乎仍不滿足,認為沒有凸顯英雄感,于是專門為之設計了一個艱難拉車送水的場面,試圖以此表現她的艱辛、堅毅和自強不息。然而,編導在做這種“拔高”時,卻忘記了故事所發生的環境是江南水鄉。劇中人的日常往來、出出進進都以船代步,基本上沒有用車的習慣。就其環境而言,也沒有使用車輛的必要和可能。編導自認為“行船送水”會使人物表現得很輕松,沒有直覺上的那種艱難之感,而“拉車送水”“引頸前行”,就使主人公在造型上有某種堅韌和崇高之感。因此為了讓人物更高大,創作者就脫離生活實際,丟開典型環境,令其舍舟船而駕轅軒。演出中,看著人物彎腰引頸,吃力而又夸張地一步一滑,舞蹈化地艱難前行,觀眾非但沒有被感染,反而疑竇叢生。大家不明白天天出出進進、買米買煤都可舟來舟往,為什么偏偏到了給學校送桶裝水的時候就非得拉車不可?竊以為,正是一味英雄化,脫離典型環境的刻意拔高,只追求感官效果,最終造成了對人物和演出的傷害,事與愿違。如同古羅馬文藝家朗格諾斯在他的《論崇高》中曾經批評過的某些一廂情愿的表達那樣:“說者固然心蕩神馳,聽者卻無動于中(衷)。”[2]參見繆朗山:《西方文藝理論史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58頁。
由此,我想起了另一部新古典廬劇《孔雀東南飛之焦仲卿妻》[3]新古典廬劇《孔雀東南飛之焦仲卿妻》由合肥演藝股份有限公司廬劇院于2015年11月參加“2015·中國長江流域非遺傳統劇目展演”時在武漢劇院演出,編劇余青峰,導演韓劍英,主演段婷婷、孫繩驥。,此劇的故事毋庸多說,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焦仲卿與劉蘭芝的愛情悲劇。演出中有這樣一處情節,劉蘭芝突然生病發高燒,為了給心愛之人降溫,焦仲卿竟脫去衣物,跑到屋外站在嚴寒中把自己“凍涼”,然后奔回屋內伏于劉蘭芝身上……同時音樂驟起,一片禮贊。我們知道編導這樣做是要表現焦仲卿對于劉蘭芝的感情,為后面的“不忍分別”“相約再會”作鋪墊,編導的用心可以理解。但由于我們長期以來對于塑造主要人物的突出和拔高習慣,使我們在設計情節時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要給人物來那么一點造型感、英雄氣,仿佛不如此就不高大、不完美,不能盡興,結果導致人物和演出效果走到了初衷的反面。劇場中,伴隨音樂而起的不是編導預期的掌聲和叫好,而是一片唏噓和訕笑。誰都知道,只要一條涼毛巾就能辦到的事,在劇中似乎成了驚天動地的大陣仗。這種夸張和造作,直接把人物帶入了滑稽。若要給發熱者降溫,以身體“冷敷”遠比用毛巾冷敷要耗時長(先要凍涼自己)、效果差(進屋后體溫很快會恢復)、風險高(自己可能因此發病),這是觀眾所不能理解的。這種英雄化人物的做法,實質上是一種不接地氣的拔高和造圣,不免讓人產生對堂吉訶德的聯想。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筆下的人物如果不高大、不英雄就不可愛了?表現常人常情就一定不受歡迎了?現實主義可以表現英雄,但要以人物真實和受眾認同為前提。現實主義中典型人物的存在空間應當廣于英雄世界。法國古典主義文藝批評家布瓦洛在他用詩體寫作的《詩的藝術》中曾旗幟鮮明地指出:
切莫演出一件事使觀眾難以置信;
有時候真實的事演出來可能并不逼真。
我絕對不能欣賞一個背理的神奇,
感動人的絕不是人所不信的東西。[1]轉引自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第298頁。
在這出《孔雀東南飛之焦仲卿妻》中,我們不否認有人可能會做出這樣的舉動,但這正屬于“演出來可能并不逼真”的“使觀眾難以置信”的事,這種“背理的神奇”當然也就不能收獲“感動人”的效果。其癥結在于它違反了普通人的認知和情感,為求高大而失卻“逼真”,淪為“人所不信的東西”。如此,對人物“高大全”和“英雄化”的追求也就只會弄巧成拙。德國文學革命的開拓者萊辛曾告誡:“習慣于這種矯揉造作的死亡場面,最有悲劇天才的詩人也會墮落到浮夸。”[2][德]萊辛:《拉奧孔》,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30頁。
其實,任何平凡人只要盡其所能,做了自己該做和能做之事,就是一種高尚、一種感動,“形成一個有人氣的英雄”[3]同上。。大可不必強作不凡,逞英顯豪擺pose,故作英雄狀。刻意制造的不凡,其實是一種游離常人、脫離實際、缺乏“溫度”,亦令人不能欣賞的虛假與浮夸。這與現實主義所追求的現實感召力是背道而馳的。現實主義的力量在于依托共情的真實,表現典型環境下的真實行為,塑造“有人氣的英雄”或典型人物來感動人、引領人,使情節成為生活應有的樣子,而非“背理的神奇”和“人所不信的東西”。英雄可以典型,但典型絕不止于英雄,更不能簡單“造圣”。
三、現實主義的真實是合邏輯與合目的的有機統一
真實是現實主義的“生命”,也是現實主義的一個顯著標志。但在實際創作中,遵循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不是簡單地照搬生活真實。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曾提出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的分野,指出文藝作品不僅應當源于生活而且應當高于生活:
人類的社會生活雖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雖是較之后者有不可比擬的生動豐富的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這是為什么呢?因為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1]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1頁。
源于生活,是要保障作品的現實質感,依托堅實的生活基礎;高于生活,則要求作家、藝術家對生活進行理性選取和本質洞察,從而在更高層次上反映生活,贏得藝術真實。
近年來多數“扶貧戲”“革命斗爭戲”不能令人滿意,其原因往往不是在生活層面失卻真實,而是在藝術層面丟失了“真實‘感’”,無法在精神認知上為廣大受眾所接受。例如,所謂的扶貧戲通常都是一個扶貧干部和三個貧困戶的故事。扶貧干部要么是駐村書記,要么是大學生村官。三個貧困戶則分別是一個懶漢因懶惰而致貧,一個“五保戶”因沒有勞動能力而致貧,一個病人因患病而致貧。然后就是這個書記或村官如何“對癥下藥”,扶志并扶智,開展相應的互助和救助工作來解決問題。最后找到一個發展鄉村經濟的捷徑,如光伏發電、鄉村旅游或網上銷售等,最終任務完成,全劇結束。要說真實,這確實就是當下農村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一些作者甚至說自己的人物、事件全都有生活原型,是活生生的現實,甚至是他們的親身經歷。但這些真實,觀眾并不認可。原因不是它是否真實存在,而是這種種“存在”被普遍而又簡單地照搬、重復,喪失了“真實‘感’”,逐漸步入了概念化、公式化的軌道,成了“非真實”。戲不同了,人不同了,場合不同了,但遇到的問題卻完全相同。其真實性必然因重復、因千篇一律而遭顛覆和質疑。農村的貧困,究其本質也絕不是簡單的個人品質和偶然的身體、生理問題。若果真如此,那就只是解決人口素質和社會保障的問題了。每一個看似相同情況的背后都有著千差萬別的社會和個體原因,實質上是一個鄉村發達度不夠的問題。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說,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把這些東西搬上臺,與其說是戲劇創作,不如說是“調查報告”更準確。這使我想起了曾經的現代戲創作模式——“隊長犯錯誤,書記來幫助。抓住狗地主,全劇就結束”。由此導致了舞臺的多年沉寂。
對生活真實的簡單照搬,導致了戲劇思維的僵化,藝術創作的膚淺,舞臺形象的蒼白和概念化,也弱化了現實主義反映生活、干預生活,從而改造和提升生活的能力。高爾基曾經說過:
我們不僅要知道兩種現實——過去的現實和現在的現實,也就是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參加創造的某種現實。我們還必須知道第三種現實——未來的現實。[2][蘇聯]高爾基:《在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演說(1935年)》,《蘇聯作家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第19頁。
這就是說,現實本身有“已發生的”“正在發生的”和“將要發生的”三種。“已發生的”是歷史,“正在發生的”是現實,而“將要發生的”則是未來、理想和希望。我們所說的“中國夢”就屬于“將要發生的”現實。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生活本質的真實,人類理想的真實、希望的真實和社會發展的必然方向的真實。亞理斯多德在《詩學》中說:“正像索福克勒斯所說,他按照人應有的樣子來描寫,歐里庇得斯按照人本來的樣子來描寫。”[1][古希臘]亞理斯多德:《詩學》,羅念生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94頁。這里,“按照人應有的樣子來描寫”——我們曾更多地把它看作是浪漫主義的,“按照人本來的樣子來描寫”——我們通常認為這才是現實主義的。其實,“按照人應有的樣子來描寫”正是高爾基所說的“第三種現實”,它是現實發展和人類意志的必然產物,是一種雖然當前不存在但最終一定會出現的“未來的現實”。而“按照人本來的樣子來描寫”與其說是現實主義,毋寧說是自然主義更準確,它的實質是忽視了人對事實的主宰。一切真實,其實都是人根據自己的意志結合特定情境創造的,是人類實踐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真實如果偏離了“應有的樣子”,有悖于“未來的現實”,那就是“非真實”或者說是不具備藝術表現價值的。現實主義的真實,必須是合邏輯與合目的的有機統一。
不久前一位朋友轉來一個新創劇本[2]該劇本為同行交流,閱讀時尚未發表和演出,這里只是借以說明創作中存在的問題,恕不公開劇名和作者信息。,要求我閱讀并給出修改意見。劇本是以內蒙古草原上一位模范人物為原型而創作的,結構、人物和語言都比較出色。尤其是對這位模范人物的塑造,可謂用力非凡。我絲毫不懷疑劇本中圍繞這位模范人物展開的主要情節的真實性,正因如此,他才成了模范人物,才有了這個劇本的誕生。但通讀下來,我無論如何也產生不了對劇本所著力塑造的主人公的敬慕之情,反而生出了絲絲哀婉。劇本中有這么一處情節,饑荒年,剛分娩不久的兒媳因營養不足而缺少奶水,面對嗷嗷待哺的嬰兒,婆婆建議兒媳去找正在為集體養羊的公公討一點羊奶喂孩子。兒媳本不情愿,但實在別無他法,只好硬著頭皮去找公公。孰料,竟被公公嚴詞拒絕,理由是小羊羔更需要羊奶。看到這里,我的心里五味雜陳。我絕不懷疑這個情節的生活真實性,也愿意相信這或許就是該模范人物事跡中的閃光之處。但這樣的生活真實進入劇作,呈現在觀眾面前,就很難在受眾心里獲得共情。
藝術審美是訴諸情感的,而這個情感又是建立在受眾普遍的人生經驗和審美認知水平上的。如同懲罰罪惡的手段不能過于血腥,塑造高尚的舉動也不能過于悖情。這位公公拒絕兒媳的要求是其大公無私情懷的展現,也是其集體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光彩。但這應當屬于“過去的現實”,是那個物質相對匱乏,社會也還沒有升華到把情感和精神視作更高價值的程度的時候,人物本身甚至是社會可能還基本認可集體的羊比自家的孩子更值得護衛。這件事之所以產生,有它所處的時代的理由,屬“過去的現實”。但這劇本是今天創作的,是要給今天的觀眾看的,它就必須同時是“現在的現實”,甚至從社會發展方向上來說,還應該是“未來的現實”。人們人本意識的不斷覺醒,對人自身價值的尊重,對生命的敬畏,都會將天平傾向人類這一方。如此,這個哪怕是確有其事的“真實”,也很難成為作品中的“當下”真實,更難以成為受眾所期望的“未來”真實。今天或者未來的觀眾一定會認為,需要奶水的羊和需要奶水的人不能相提并論,一個新生嬰兒的生命應當高于一切,集體的羊只有真正為個體的生命服務才有它的價值。當然,就這一頓奶水而言,嬰兒和羊羔都不會立刻喪失生命,但這里人與羊以及該模范人物的道德判斷孰輕孰重,觀眾是必然要作出裁量的。觀眾所喜愛和推崇的高尚人物,一定是在更高層面上富有親情、珍重生命、愛戴人類自己的、接通“現在”和“未來”精神的尊者和模范。這既是人“應有的樣子”,也是人“本來的樣子”,是現實主義真實觀的核心所在。
四、現實主義中的理性邏輯應先于感性邏輯
20世紀50年代,在結合社會主義時代文藝創作實際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即“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俗稱“兩結合”。這無疑發展和延伸了現實主義的內涵。“革命的”這一前綴表明立場,是創作的出發點、根本點,故而作品中必須是我方勝利,敵方失敗,叛徒沒有好下場,英雄升華為“青松”或“紅梅”。今天,我們好像不再過分強調這個前綴了。但在我們頭腦里根深蒂固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兩結合,無形中使我們對作為現實主義核心的“真實性”要求降低了。創作中每每把主觀愿望和情感傾向當作真實,以主觀邏輯代替客觀邏輯,以感性邏輯代替理性邏輯,最終使現實主義擁有的反映生活、揭示真理的這一功能退化,甚至喪失。
例如,就我們已知的歷史上的中共女黨員、地下工作者,也包括女軍人,雖然革命意志堅定如鋼,機智勇敢,但似乎沒有一個是善于拳腳、武藝超人的。劉胡蘭不是,江姐不是,趙一曼、“八女投江”中的任何一個都不是,但她們的氣概和精神足以壓倒一切敵人,閃耀著革命英雄主義的光輝,令人難忘。而在近期的一些作品中,我們卻看到一個個文弱娟秀的女地下黨員、女戰士孔武生猛,無所不能。數個身強力壯的敵方警察、日偽軍或土匪、黑幫都近不得她的身,而她也是三拳兩腳就把敵人打倒,使對方絕無還手之力。2020年年初熱播的電視劇《新世界》[1]電視劇《新世界》由北京衛視、東方衛視在2020年春節檔黃金時間播出,全片70集,編劇、導演徐兵,主演孫紅雷等,演員萬茜在劇中飾演共產黨員田丹。里的女共產黨員田丹就身懷如此絕技,雖體格單薄,但武藝高強,甚至還會洋式搏擊,在逮捕她入獄時數個獄警竟然奈何不了她。這在娛樂片中或許不成大問題,權當圖個熱鬧,不必當真。可在一部認真的現實主義作品中,這樣的呈現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誠然,現實主義創作不僅要講求真實,也要講究傾向性。編導對“自己人”傾注情感,著意謳歌,放大其神通是可以理解甚至認同的。但前提是不能離開生活依據,應源于生活,同時還要把握分寸,即高于生活應“高”到什么程度。如果脫離生活基礎,“高”到失真,傾向性壓倒真實性,就會成為一種噱頭和搞笑,從而丟失了現實主義所賴以建立的全方位可信的理性邏輯。理性邏輯是一種客觀邏輯,應先于感性邏輯,即情感邏輯。情感的任何恣意,都應得到理性的清醒把控,從而明晰疆界。盡管我們渴望自己認可和喜愛的人物能夠更加英武、非凡,更富所向披靡的能力和氣度,但這種愿望最終還是得回到人物的現實可能性上來。感性邏輯過于活躍,天馬行空,不受理性邏輯和客觀規律的約束,好的愿望也難免事與愿違,弄出了損害人物、殃及作品的不良后果。觀眾面對這樣的人物既不會產生敬慕,也不會產生因目睹人物的豪壯而得之的快感和安慰,更談不上領略英雄氣魄和受其鼓舞了。
傾向代替真實,情感超越邏輯,最終使人物異化,失去歸屬,精神力量必然隨之消散。這類人物的神勇或犧牲,絲毫不比江姐在敵特分子一句“江雪琴,走吧!”的催促中的“平靜”——捋一捋頭發,抻一抻衣襟,大步前行——更令人崇敬和心動;也絲毫不比李玉和在面對日寇逮捕時的一句“臨行喝媽一碗酒”和李奶奶的一句“鐵梅,開開門,讓你爹‘赴宴’去!”[1]中國京劇團集體改編:《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1970年5月演出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頁。的“家常”更顯威武雄壯、豪氣干云。氣焰洶洶的敵人其實已在她們的鎮定英勇、大義凜然面前退卻,在她們坦然而堅定的邁步之中潰敗。偉大人格從人物平靜而真實的行為中升騰出來,觀眾亦能從中體會到英雄的力量和非凡,由此洞見了革命英雄人物那無與倫比的精神世界。這里,作者盡管也有傾向性,但遵循了理性邏輯,依據客觀實際反映客觀真實,賦予人物以典型環境下可能也只能如此的行為,是“這一個”令人信服的真實和光芒四射的典型,因此這樣的人物塑造無疑是成功的。而前述那些作品,雖然讓人物過了一把癮,讓觀眾解了一回氣,也顯示了英雄的無敵,但究其實質卻并不成功,因為它超出了我們對人物所可能的共情范圍。編導希望看到我方強大、敵人無能,以及享受到打倒敵人的快感,于是錯用感性邏輯代替理性邏輯,致使人物由失真而失信,步入滑稽,淪為虛幻,當引以為訓。
2018年有一部較受矚目的現代京劇《紅軍故事》[2]現代京劇《紅軍故事》由國家京劇院于2018年7月在北京梅蘭芳大劇院首演,作品由《半截皮帶》《半條棉被》《豐碑》三個小戲組成,導演張曼君,其中《豐碑》的編劇為王宏,《半條棉被》的編劇為徐新華,《半截皮帶》的編劇為胡應明,文字劇本參見《劇本》2018年第11期,第55-70頁。,全劇由《半截皮帶》《半條棉被》和《豐碑》三個小戲組成。此劇以小見大,以小人物、小事件展現大主題、大境界,藝術成就可圈可點。通過流傳甚廣的紅軍時期的三個小故事,發掘了我黨的光榮傳統,謳歌了紅軍的鋼鐵意志和共產黨人的堅定信仰、美好情操。作品意在弘揚初心,喚醒使命,為實現新時代的新作為凝聚意志、激發斗志,可以說是一部昂揚向上的作品。但或許是因為主創人員過于強烈的傾向性,太過注重情感的飽和度,也出現了以感性邏輯替代理性邏輯,以浪漫淹沒生活依據,從而使人物虛化的情況。
《豐碑》中,為了詩化軍需處長火雁的精神世界,編劇設計了這樣一處情節:他把自己的棉衣讓給戰友,在他因寒冷而即將死去的最后時刻,先后劃亮了三根火柴,他分別看到了家鄉的和諧生活,看到了情人的燦爛笑臉,看到了戰友們奪取勝利的場面。這里,作者是要贊美這位軍需處長的大愛情操——管軍需的人居然自己凍餒而死,呼應“如果勝利不屬于這支隊伍,那還會屬于誰!”(“軍長”臺詞)[1]王宏編劇:《豐碑》,《劇本》2018年第11期,第59頁。這一深刻主題。我們且不說這種設計有模仿《賣火柴的小女孩》之嫌,更重要的是這種對人物的傾向性,這種感性邏輯的恣肆,造成了對所要塑造的英雄人物的傷害。一個軍需處長應當比誰都明白在當時的環境下一根火柴的稀缺性絕不比一件棉衣差多少。這里的“三根”雖是一種表演需要、一種寫意表達,未必是確數。但讓人難以置信的是,有如此境界的軍需處長怎么竟獨獨沒有想到要為部隊留下這最后的也是最為寶貴的火柴呢?他有這樣在最后時刻任意消耗寶貴物資的權力和心思嗎?這里,作者原是要深化人物,但卻讓感性邏輯掩埋了理性邏輯,使人物走向了意圖的反面。
《半條棉被》則為了表現紅軍女戰士對鄉親的愛,當場把一條棉被一分為二,給老百姓留下半條,從而引出一句頗為動情的臺詞:“紅軍和共產黨就是有一條棉被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好人哪!”(村民“徐解秀”臺詞)[2]徐新華編劇:《半條棉被》,《劇本》2018年第11期,第65頁。。若從感性上來說,這個行動確實有助于紅軍女戰士的形象塑造。她把珍愛的哪怕別人碰一下都不行的棉被剪開來送給鄉親,其心、其情呼之欲出。但是,這種情感的傾向還是應該讓理性來參與把控,感性邏輯其實是離不開理性邏輯的驗證的。我們且不說韌性很強的棉被,尤其是一床曾被打濕過的棉被是否可以輕而易舉地被剪開,只是如此珍貴難得的一條棉被被剪開后還能有多少作用呢?棉被不是毛毯,無論是橫向還是縱向剪開,其使用功能都會遭到破壞,甚至報廢,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結果。人物只是要表達自己的心情,作者只是要追求那句動人的臺詞,就讓一條棉被變成了兩個基本喪失功能的“半條棉被”,這并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主觀欲望過強,感性邏輯替代了理性邏輯,傾向性替代了客觀性,人物的典型性和作品的感染力必然大受傷害。原本或許真實的內容也失去了真實“感”。文藝理論家繆朗山先生在論述萊莘主張的戲劇教育功能時就曾指出:“戲劇的教育不是抽象的說教,不是徒然借用人物的口吻說出一番大道理,也不是利用戲劇終場的一兩句格言來教育觀眾。”[1]繆朗山:《西方文藝理論史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627頁。由此我們說,感性邏輯的浪濤應當奔涌在理性邏輯的河床上,這也是現實主義創作的基本要義之一。
現實主義是一個老傳統,但又是一個新課題。尤其是面對當前新時代戲劇創作的新使命,我們只有更加深刻地理解它,更加多元地豐富它,更加積極地發展它,才有可能更加廣泛地收獲現實主義創作的新成果,向時代和人民交出滿意答卷,迎來現實主義創作的又一個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