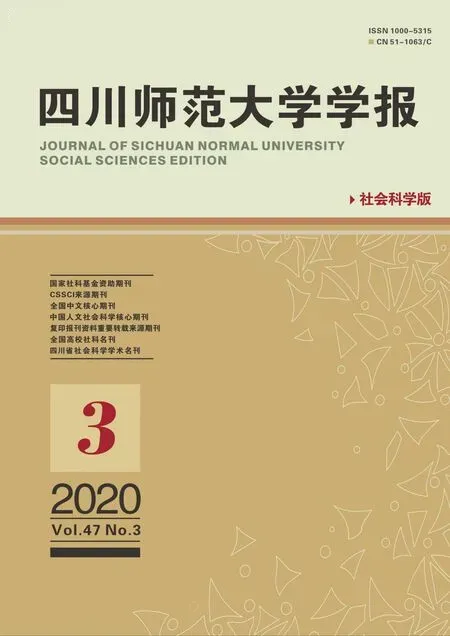從杜威“經驗”理論看深度學習的發生
夏 淑 玉
(北京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北京 100875)
近年來,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對深度學習的理解已經跨越了認知科學的單一視角。有學者指出,我們應該以“全視角”的視域來認識深度學習;(1)吳永軍《關于深度學習的再認識》,《課程·教材·教法》2019年第2期,第51-58、36頁。更高水平和更深層次的認知發展不應該是深度學習的唯一追求,深度學習應該是個體感知覺、思維、情感、意志、價值觀全方位投入的過程;(2)郭華《深度學習及其意義》,《課程·教材·教法》2016年第11期,第26頁。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不僅要注重學生的個體經驗發展,還要注重社會價值與意義的建構。(3)張詩雅《深度學習中的價值觀培養:理念、模式與實踐》,《課程·教材·教法》2017年第2期,第67-73頁。全視角下的深度學習,不僅強調學生對知識的記憶與理解,還關注學生對知識的遷移與運用;不僅強調學習過程中學生與文本的互動,還關注學生與學習內容、學習環境和他人的互動;不僅強調學生認知水平的發展,還注重學生在思維、情感、意志等多方面個體經驗與社會意義的多重建構;不僅強調學生知識掌握的最終結果,還關注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思維的鍛煉和能力的提升。因此,深度學習是一個知識與能力協調發展的過程,也是個體經驗和社會意義共同建構的過程。學生是這一活動的主體,學生所學的知識是有情境、有意義并且與他們的生活經驗相聯系的,學習的過程是學生個體經驗升級的過程,也是學生在參與社會歷史實踐中社會意義建構的過程。
但是,任何學習都不是憑空產生的,都需要具體的內容與載體、特定的過程與方法。無論是強調運用“明了-聯想-系統-方法”幫助學生建立新舊知識聯系的傳統教育,還是強調通過“做中學”幫助學生實現經驗的改組與改造的“進步主義”教育,他們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共同的,即如何將外部知識轉化為學生個體的內在力量和精神財富的問題(4)郭華《帶領學生進入歷史:“兩次倒轉”教學機制的理論意義》,《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6年第2期,第8頁。。因此,當我們明確了深度學習的內涵與特征,我們仍然需要面對所有教學的根本問題:教師如何通過有效地組織教學內容與活動,幫助學生迅捷、愉快而徹底地將廣闊而復雜的理論知識轉化為可以被理解、掌握和運用的個體經驗;學生又是如何在活動中將自己零散的、樸素的生活經驗提升為系統的、科學的反省經驗(知識)。
簡言之,我們需要明晰深度學習的發生機制,明確學生是如何在深度學習中掌握知識,又是如何在教師指導下通過深度學習實現自身的全面發展的。探究深度學習的發生機制,無論從教師“教”的角度還是從學生“學”的角度,都必須解決知識與經驗相互轉化的問題。打破知識與經驗割裂的局面,使二者在教學過程中統一起來并最終幫助學生實現深度學習,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
一 統一而非割裂:對杜威“經驗”理論的澄清
在教學論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人們都試圖闡明經驗與知識這一對矛盾關系,并努力將二者統一起來:在赫爾巴特的論著中,這對矛盾被定義為新的觀念與學生已有觀念的矛盾(5)赫爾巴特強調以“統覺”來協調新舊觀念,并在觀念間建立“聯結”,將新的知識與早期習得的知識結合起來。參見:赫爾巴特《教育學講授綱要》,李其龍譯,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41-43頁。;在杜威的論述中,這個矛盾被描述為兒童與課程(知識)的差距(6)約翰·杜威《學校與社會·明日之學校》,趙相麟等譯,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113頁。,原始經驗與反省經驗的差距(7)約翰·杜威《經驗與自然》,傅統先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5-19頁。;楊建華在分析教學認識的客體時也對經驗知識(生活經驗)與理論知識做了區分(8)楊建華提出:人們對于教學實踐的重要批判就是“學生的整個精神生活被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來自學校的,一部分是來自生活的”,“學校所學的知識與學生經驗、學生生活的現實相分離”,因此,必須通過教學認識將經驗知識(生活經驗)與理論知識統一起來。參見:王策三主編《教學認識論(修訂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頁。。經驗與知識之間的矛盾與差異在赫爾巴特那里雖然被注意到了,但如何通過教學彌補兩者之間的巨大差距并沒有得到系統的闡釋。杜威認識到了兩者之間的差異,明確提出兒童的生活世界與學校所提供的課程之間是存在距離的,教育者要通過指導的方式幫助學生進行經驗的改組與改造,并由此提出教學要以學生經驗為主導,以學生的經驗作為教學的起點和出發點。(9)約翰·杜威《學校與社會·明日之學校》,第115-116頁。針對杜威的這一觀點,楊建華曾進行評述,認為經驗雖然在教學中有重要意義,但是從兒童經驗出發的教學不利于經驗的提升與整合,教學的實際情況應該與此“恰好相反”,“應當充分發揮教學認識的優勢,以較高起點的系統理論知識為主導,對學生的經驗加以提升,使兩者結合起來”。(10)參見:王策三主編《教學認識論(修訂本)》,第89頁。后續學者在對教學認識的機制進行探索時,又再次強調教學應該是一個“高起點的認識過程”(11)郭華《帶領學生進入歷史:“兩次倒轉”教學機制的理論意義》,《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6年第2期,第12-13頁。。那么,從理論知識出發的“高起點”教學與從兒童經驗出發的“低起點”教學一定是相異、相斥的嗎?杜威基于經驗的教學是否就一定忽視了理論知識在教學中的重要價值呢?
作為進步主義教育的代表人物,杜威在一段時期內被認為是反對傳統教育而被推崇,不少學者曾在論著中援引杜威的相關論述,并將其概括為以“活動中心”取代“書本中心”,以“兒童中心”取代“教師中心”,以“問題-解決”教學模式取代“知識授受”教學模式。也因此有了新“三中心”與舊“三中心”對立的說法,認為杜威的兒童中心課程或基于經驗的教學忽視系統知識學習,忽視教師的指導。這實際上是對杜威思想的誤讀或片面的夸大。這一錯誤的傾向后來被很多學者意識到并予以了及時的糾正:王道俊就曾撰文澄清對杜威教育思想的某些認識,并在文中肯定了杜威強調學生的主體地位,重視活動的價值,提倡知識學習要向自我意識轉向等方面對于教學具有重要意義;(12)王道俊《知識的教育價值及其實現方式問題初探——兼談對杜威教育思想的某些認識》,《課程·教材·教法》2011年第1期,第21-25頁。涂詩萬、扈中平在研究中對于“知識與活動相對立”的說法進行了駁斥,認為杜威實用主義知識觀下,知識與活動不是二元對立的,而是連續的、統一的;(13)涂詩萬、扈中平《超越知識與活動的二元對立——杜威教學思想再認識》,《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7期,第24-31頁。丁道勇也在文章中反對將杜威教學思想概括為“兒童中心”的做法,認為杜威在兒童與課程相關論述中表達的觀點是要在起點(兒童)與終點(課程)之間搭建有效而人道的聯系,而非單純地關注和保護兒童。(14)丁道勇《兒童不是中心——對杜威教學思想的再認識》,《全球教育展望》2016第11期,第110-128頁。越來越多的反思、審視、獻疑吸引我們重新閱讀和思考杜威,糾正原有的各種片面論斷,擺脫二元對立思維,以更加客觀、理性的態度對杜威思想、理論進行準確和全面的認識。
事實上,杜威的確反對傳統教育中的諸多做法,但同時他也清醒地認識到“假如以為拋棄舊教育的觀念和實踐就足夠了,并且走到對立的極端上去,那么,這些問題不僅談不上解決,甚至還沒有被認識到”,“一種新的運動往往有一種危險,即當它拋棄它將取而代之的一些目標和方法時,它可能只是消極地而不是積極地、建設性地提出它的原則”(15)約翰·杜威《我們怎樣思維·經驗與教育》,姜文閔譯,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246、245頁。。他反對教師作為教學中的絕對權威,但他仍舊堅持教育者不應放棄對兒童應有的指導,相反,在教育性的環境當中,教師的知識、判斷或者經驗,將成為一個更大而不是更小的因素。只不過,教師不再是那種高高在上的、擁有獨斷權威的“官老爺”,而是作為友善的合作者,在與學生的共同活動當中給予指導。從他的諸多論述中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杜威對“傳統教育”的反對從不止步于反對本身,也從未站在對立面上要求對傳統教育全盤否定,他明確批判用“非此即彼”(either-or)的公式來解決教育中的一切問題,反對認為兩個極端之間沒有種種調和的可能性的做法。因此,與我國許多研究者一樣,杜威所做的一切努力正是希望在兒童與教師、書本與活動、知識授受與發現探究之間尋找一種平衡,而“經驗”理論就是杜威尋找的一劑良藥。杜威旗幟鮮明地指出,“在全部不確定的情況當中,有一種永久不變的東西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鑒,即教育和個人經驗之間的有機聯系”(16)約翰·杜威《我們怎樣思維·經驗與教育》,第248頁。,我們“需要一種經驗的理論”(17)在《經驗與教育》的第二章,杜威直接以“需要一種經驗的理論”為標題,詳細闡述了經驗的概念以及經驗在教育中的重要意義。參見:約翰·杜威《我們怎樣思維·經驗與教育》,第248-253頁。。
因此,杜威“經驗”理論的初衷和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在新舊教育中尋求一種中庸之道,將教育中種種對立的觀點調和起來。他倡導教學要基于學生的經驗,以兒童作為教學的起點,但“經驗”絕不是通常意義上樸素的、自發的生活經驗,它有著豐富的內涵和層級。同時,杜威重視兒童的個體經驗,卻堅持反對“滿足于一時的和現有的水平”的放任行為,他所強調的是關注兒童現有經驗中存在的“為達到較高級的水平提供一種推動力”的能力(18)約翰·杜威《學校與社會·明日之學校》,第118頁。。因此,這種所謂的“低起點”教學與我國教學認識論中倡導的“高起點”教學在本質上都是希望通過教學中的種種手段(教學內容的組織與呈現方式、教學活動的展開等)幫助學生將豐富的人類歷史經驗轉化為能夠被理解、掌握和運用的個體經驗,從而促進學生的發展。而在教學的整個過程中,教師與學生、知識與經驗的統一與協調是幫助學生實現深度學習必不可少的關鍵。無論是“低起點”把學生經驗“升上去”的過程,還是“高起點”把理論知識“拉下來”(教學認識論中活動展開或打開)的過程,都需要統一到教學活動中來,是同一活動的兩個方面。經驗與知識在教學活動中更是協調統一、不可分割的:只有理解了兒童豐富的個人世界,才能更好地創造情境、組織恰當的內容與活動,將豐富的人類歷史經驗(知識)還原、打開并轉化為兒童能夠理解、接受和掌握的內容;也只有充分重視和尊重理論知識在教育中的價值,對知識產生和發展的整個過程與脈絡有清晰的了解,才能在教學活動中幫助兒童重新經歷人類歷史經驗的發生過程,使兒童實現個體經驗的升級轉化和社會意義的建構,才能真正地實現深度學習。
二 變革傳統的知識觀與學生觀:“經驗”理論下深度學習發生的前提
為了改變傳統教育的種種弊端,同時也為了調和傳統教育與新教育的極端對立,杜威所倡導的教育哲學是“屬于經驗、由于經驗和為著經驗的”(19)約翰·杜威《我們怎樣思維·經驗與教育》,第251頁。。“經驗”的理論貫穿了杜威教育哲學的始終,從杜威關于“經驗”的諸多論述中,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到他對傳統知識觀、兒童觀的變革,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對教學的有益指導。
(一)對知識的重新解讀:從“已完成的產品”到發展中的經驗
杜威“經驗”理論視角下的知識觀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知識本身就是一種高水平、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經驗,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積累而來的、經過驗證和系統組織的經驗;第二,知識不是自然事物本身,也不僅僅是各種原理、概念、事實這些結果和形式,而是過程和結果、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知識有其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和特定情境。
傳統教育將知識看作是過去的、靜止的,知識被當作“已經完成的產品”由教師以成年人的標準和方法傳授給學生,絲毫不顧及這些已經形成的知識體系最初是怎樣被建立起來的,學生則成為了這種教育情境下的知識的被動接受者。這種知識觀下的教學,其本質上“是來自上面的和來自外部的灌輸”(20)約翰·杜威《我們怎樣思維·經驗與教育》,第244頁。。杜威的“經驗”理論則給了我們認識和理解知識的新視角,知識可以看作是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不斷積累起來的經驗,“它們體現了人類一代一代的努力、斗爭和成就而積累起來的結果”(21)約翰·杜威《學校與社會·明日之學校》,第116頁。。與個體經驗不同,知識是人類“種族的經驗”(22)約翰·杜威《學校與社會·明日之學校》,第116頁。,是經過時間積累、實踐檢驗后邏輯化、系統化的經驗,是經驗發展到一定水平的一種組織形式。從“經驗”的視角出發,我們得以將知識置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在每一個歷史發展時期,先前的、已有的經驗在實踐中不斷被挑戰、被檢驗和驗證;而在新的情境中產生的新的經驗又不斷匯入、整合和被吸收。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每種經驗既從過去經驗中采納了某些東西,同時又以某種方式改變著未來經驗的性質”(23)約翰·杜威《我們怎樣思維·經驗與教育》,第256頁。。當我們將經驗置于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軸上去重新認識,經驗就具有了流動性和生命力,從而解決了傳統教育中知識的“已完成性”帶來的灌輸和被動接受等問題。當我們以發展的眼光看待當下現成的知識時,知識不再是“死”的、“已完成的”產品,而是記錄著人類社會歷史實踐不斷滾滾向前的、鮮活的、發展中的經驗。這些“經驗”記錄著人類一代一代努力和斗爭的成就,并且以最有效、最簡約、系統化、邏輯化的形式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此外,我們還需要將經驗和經驗的對象區分開來,從而理解經驗的完整意義,并為教學提供相應的指導。杜威認為自然中的各種事物本身不是經驗,而只是經驗的對象,只有當人與各種事物發生相互作用時,經驗才產生了。這個相互作用的過程就是經驗的方式,通過這一過程獲得的結果我們才能稱之為經驗。因此,每一種經驗都包含著兩個層次,即經驗的結果和形式以及隱含在背后的經驗的過程和內涵。正如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太陽、樹木、河流,它們本身并不能成為經驗,更不能稱為知識,它們只是自然存在的事物。只有當個體將這些事物作為認識活動的對象,并在個體與對象的交互作用中不斷賦予其“意義”的時候,經驗才產生了。譬如,我們通過感知覺感受到太陽的光和熱,通過觀察與觸摸感受到樹木的顏色和紋理,或者是因為蘋果的掉落開始思考地球的引力。我們在與這些事物的相互作用中賦予其意義,獲得相應的經驗。這些經驗又在后續的實踐中不斷被檢驗、被抽象化、系統化、邏輯化,這時經驗才具有了一套完整的意義,從而以“知識”的形式呈現出來。在這一活動中,最后形成的具有完整意義的“知識”只是經驗的最終形式和結果,而不是經驗的全部內涵。經驗的內容與過程也是經驗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切的經驗都是過程和結果的統一,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知識是發展到一定水平的經驗,而經驗是有情境和過程的,那么知識就如同經驗一樣都不是憑空產生,也不是自然存在的;任何一種知識都是在人與對象相互作用的活動中發展起來的,從其產生之初到它發展的整個過程,都有著其賴以存在的情境和發生、發展的過程。那么,當我們教授知識時,就不能僅僅教授知識最后的“形式”或結果,而應該同樣教授知識產生和發展的過程。這樣,知識學習才不是灌輸,學生才能在知識學習的過程中既掌握知識的最終形式和結果,也理解知識的產生情境和過程,才能獲得關于知識的全部意義。
(二)學生主體的確立:從知識的“旁觀者”到知識的“參與者”
落實學生的主體地位,是實現深度學習的關鍵。(24)郭華《深度學習的關鍵是真正落實學生的主體地位》,《人民教育》2019年第13/14期,第55-58頁。杜威從兒童的世界出發,幫助我們理解了教學要基于學生經驗、以學生為主體的重要意義,更提醒教育者要充分抓住機遇,幫助學生實現經驗的轉化,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
對兒童個人世界的承認與尊重是杜威在教學中確立學生主體地位的第一步。杜威將兒童的生活看作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是兒童感情和活動的連結,是他們各種親身經驗的綜合。(25)約翰·杜威《學校與社會·明日之學校》,第112頁。從“經驗”的視角看待兒童,他們就不再是一張張等待著被隨意填涂的“白紙”,而是有著豐富個人經驗的載體,這些樸素的、已有的經驗使每個兒童都有著自己的特點和興趣。與系統的理論知識相比,兒童的經驗雖然是簡陋的、零散的、未成熟的,卻也是各種更高級的、系統的經驗發展和生長的基礎。因此,要想使來自成人世界的、以標準化形式呈現的知識更易于被兒童接受,我們在教學中就不能罔顧和忽視兒童個人的特點、聯想和經驗,要充分尊重兒童的經驗并在教學中努力尋找知識(人類歷史經驗)與兒童生活世界的聯結。
同時,杜威還提醒我們要正視和珍視兒童“未成熟狀態”(26)約翰·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王承緒譯,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49頁。。這種“未成熟狀態”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兒童所保有的經驗是初級的、匱乏的和不完善的。兒童的個人世界雖然賦予了他們豐富的個人經驗,但這些經驗通常都是粗淺的、簡陋的,是在個體生活中偶得的和未經驗證的,這些初級的經驗往往包含著錯誤的傾向。另一方面,杜威非常樂觀地發現了這些“未成熟”的經驗所展現出的另一面,即經驗的“依賴性”和“可塑性”(27)約翰·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第50頁。。雖然相較于成人而言,兒童是未成熟而有待成熟的個體,但我們不能以成人的標準要求兒童,不能只是把這種未成熟狀態當作是一種匱乏。我們要能夠看到與這種未成熟的狀態相應而生的是兒童的依賴性和可塑性。他們依賴著成人和社會的指導,需要在指導下將未成熟狀態中蘊含的各種潛在的可能變為現實,將他們已有的、初級的、原始的經驗變成真正需要的、系統成熟的、經過反省的經驗。因此,兒童的生長不是自發的,是需要教師指導的。教師在看到兒童經驗“未成熟狀態”的同時,也要看到其中蘊含著的某些向前生長的信號或標志,要認識到“兒童現在的經驗決不是自明的。它不是終極的,而是轉化的”(28)約翰·杜威《學校與社會·明日之學校》,第117頁。。正是由于兒童經驗的未終結性,才給了教育者空間和機遇,讓教師可以利用這些經驗進行指導,從而實現經驗的“轉化”并促進兒童的“生長”。
經驗的交互作用則是幫助我們實現這種生長與轉化的關鍵。這一原則“賦予經驗的客觀條件和內部條件這兩種因素以同樣的權利”(29)約翰·杜威《我們怎樣思維·經驗與教育》,第261頁。,使兒童這個主體從知識的旁觀者變為了知識的參與者,也為教師的指導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依照杜威的觀點,任何一種經驗都包含著一個主動的因素和一個被動的因素。單純的自然存在物不是經驗,單純的活動也不能構成經驗。經驗是主體與外部環境交互作用的產物,知識想要轉化為學生的個體經驗得以保存下來,就必須進入到學生的主體活動中,經過主客體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才能最終轉化為學生的個體經驗并在生活中得以運用。經驗的交互作用原則改變了傳統教育中學生被動接受知識的局面,強調學生需要通過“行動”來獲取知識,而教育者的關鍵作用就在于通過控制和調整“行動”的情境、材料和方式來幫助學生在活動中獲得可以促進其生長的經驗。
三 深度學習的發生機制:基于經驗的指導和個體經驗的升級與轉化
當我們探討深度學習的發生機制時,首先必須明確一點:對學生而言,深度學習一定不是其在現有發展水平下可以獨立完成的學習,而應該是學生在教師引導和幫助下才能夠完成的具有挑戰性的、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學習。按照維果茨基的觀點,學生在現有發展水平下可以獨立完成的學習是教學的最低界限,而在最低教學界限外,還存在著最高教學界限,這兩個界限之間即是“教學最佳期”,與“教學最佳期”相對應的是學生的“最近發展區”。(30)維果茨基《維果茨基教育論著選》,余震球選譯,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384-390頁。深度學習的發生需要教師能夠把握好“教學最佳期”,從而最大程度地實現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同時,深度學習要實現的發展不是單純的智力或者認知的發展,而是個體的全面發展,是個體經驗的全面升級與轉化。
因此,深度學習不是學生的自學活動,而是“教”與“學”相統一的活動,是教師有計劃、有組織地“教”和學生高水平、深層次地“學”相互促進的活動。從教師“教”的方面來看,深度學習的過程是教師基于學生現有的經驗有計劃、有組織地給予指導的過程,是有目的地將人類歷史經驗轉化為學生個體經驗的過程;從學生“學”的方面來看,深度學習的過程是學生現有經驗不斷向更高水平和更深層次的經驗升級與轉化的過程,是學生個體以一種典型的、簡約的方式參與和重演人類社會歷史經驗發生、發展的過程。基于經驗的指導和個體經驗的升級與轉化是深度學習中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必須結合起來才能獲得對深度學習更加全面的認識。
(一)教師基于經驗的指導過程
在《民主主義與教育》一書中,杜威明確地提出“教育即指導”,認為“使動作集中和有順序是指導的兩個方面”。(31)約翰·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第30、32頁。在促進深度學習的教學中,動作的集中意味著教師指導下的活動不是散漫的,而是有明確的、特定的目標和任務;動作的有序意味著教師指導下的活動不是片段的,而是前后連續并向前發展的。因此,能夠引發學生深度學習的教學活動在開始之初,就應該確定好教學的起點和終點,明確教學活動的順序和方向,在此基礎上,通過各種方式在起點與終點間建立連接。
1.確立起點與終點,明確指導的順序和方向
通過教學促進深度學習的過程要求教師首先要認識到兒童與知識之間的差距。杜威從經驗的范圍、組織形式和內容三個方面對二者之間的差距進行了闡釋(如表1所示)。(32)約翰·杜威《學校與社會·明日之學校》,第113頁。兒童與知識之間有限與無限、統一與專門、具體與抽象的差別是巨大的,但是,認識到它們之間的差距并不是要將兒童與知識對立起來,而是要看到其中的聯系并從中發現教學活動的指引。我們不能“把教材當做某些固定的和現成的東西,當做在兒童的經驗之外的東西”,也不能夠把“兒童的經驗當做一成不變的東西”,“兒童和課程僅僅是構成一個單一的過程的兩極。正如兩點構成一條直線一樣,兒童現在的觀點以及構成各種科目的事實和真理,構成了教學”。(33)約翰·杜威《學校與社會·明日之學校》,第116頁。兒童現在的經驗雖然還是初級的,但這些初級的經驗中可能包含著各種事實和真理的萌芽,例如兒童可能無法直接理解“增大接觸面的粗糙程度可以增大摩擦力”的原理,但是兒童卻可能有“冰面比柏油馬路更便于滑行”的經驗;兒童可能無法直接領會“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詩情,卻可能有在中秋月圓之夜思念親朋的體驗。因而,教育者要做的不是把外在的、抽象的知識直接“拉”到學生面前,試圖用知識直接遮蔽和替換學生原有經驗的方式來消除學生經驗和知識之間的差距,而應該承認并面對學生經驗與知識的差距,并將學生現有的經驗和邏輯化、抽象化的知識分別作為自己教學的起點和通過教學需要達到的終點。

表1. 兒童與知識之間的差距
說明:表格內容源自杜威在《兒童與課程》一文中對兒童與課程(知識)之間分歧的論述,筆者抽取了文中的關鍵詞對表格進行了整理。
當我們以經驗的視角出發,將兒童的經驗和知識作為教學的起點和終點時,就意味著我們在教學開始之初就能夠明確地知道教學應該從哪里出發,要到哪里去。就如同一場長跑,在長跑開始之時知道終點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明確跑步的方向,還可以幫助我們做好規劃:我們應該將整個跑程分為幾個階段,在每一個階段以怎樣的速度前進,跑完全程需要多少時間。對于教師而言,教學就應該在兒童與知識之間建起一條跑道,教師要能夠發現通過這一條跑道所需要的各個步驟,并指導兒童一步步地走向終點。
2.理解抽象與還原,明確指導的方式
確立了教學的起點與終點,明確了教學發展的方向,剩下的全部精力就是尋找一種恰當的方式在起點與終點之間建立起連接,指導兒童從現有經驗的起點出發,沿著正確的方向有步驟地經歷人類歷史經驗發展的過程,走向教學的終點。這種恰當的方式就是杜威所說的“使教材心理化”,將抽象的、邏輯的經驗還原到心理的層面,使之重新情境化、具體化,使“各門學科的教材或知識各部分恢復到原來的經驗”(34)約翰·杜威《學校與社會·明日之學校》,第122頁。。
在這里,我們以杜威常用的“探險家的筆記”與“地圖”的比喻(35)在《兒童與課程》《我們怎樣思維》等文中杜威都引用了這一比喻。參見:約翰·杜威《學校與社會·明日之學校》,第121頁;《我們怎樣思維·經驗與教育》,第67頁。來說明經驗的心理方面和經驗的邏輯方面的差別與關聯。一代又一代的探險家游歷世界,將他們在途中的所見所聞、經歷、發現等等以十分詳盡的方式記錄成探險筆記。這些筆記保留了世界被發現的完整過程,是他們個人經驗的完整記錄,可以看作是經驗的心理方面。而探險家們努力探索之后形成的地圖,將他們對世界的發現以最簡明、抽象、符號化的形式呈現出來,是對他們探險經歷的高度概括與總結,只保留了探險的結果而沒有呈現過程,是經驗的邏輯方面。將探險家的筆記重新組織排列、抽象整合為地圖的過程是經驗的抽象過程;反過來,通過地圖來認識世界、理解世界被“發現”的過程則是經驗的還原過程。教師在教學中要想使學生更深刻地理解地圖、學會利用地圖來認識世界,就必須將地圖重新還原為“探險家的筆記”,需要將地圖中抽象的符號、版圖以簡明、典型的方式還原成探險家探險歷程中曾經經歷的種種情境、見聞,讓學生在經驗的還原中重新經歷世界被發現的過程。
在一般的教學過程中,教材中的知識(概念、原理、定理等)就如“地圖”一樣是經驗的邏輯方面,是脫離原始情境、以抽象的形式呈現的。教師在開展教學活動時,必須要能夠理解知識的邏輯方面背后隱藏著的知識的心理方面,要能夠發現“地圖”背后的“探險家的筆記”,即知識發生和發展的歷程。在此基礎上,教師要努力將這些抽象的形式還原到經驗的心理方面,選擇合適的內容并組織恰當的活動,讓學生如同重讀“探險家的筆記”一般重新以簡約的、典型的方式經歷知識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使知識與學生的經驗關聯起來。
(二)學生個體經驗升級與轉化的過程
教育即生長,教育即是經驗的改組與改造,那么從“經驗”改造的視角來看,深度學習就是學生在教師指導下個體經驗不斷升級并向更高水平經驗轉化的過程。這種經驗的改造活動絕不是單純的個體內部的活動,而是需要依靠內部條件與外部條件相互作用來實現的,需要學生在教師帶領下,在回溯人類社會歷史經驗的活動中實現。這一經驗改造的過程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對學生個體而言,經驗的改造是將個體的原始經驗向反省的經驗升級的過程;對社會而言,經驗的改造是社會歷史經驗融入個體經驗而得以傳承的過程,也是個體經驗升級甚至創造新的社會歷史經驗的過程。
1.從原始經驗升級為反省的經驗
我們已經知道,兒童有著豐富的個體經驗,但兒童經驗最顯著的特征在于它處于“未成熟狀態”,這種未成熟的、依靠個體的感知覺得到的零散的、初級的、未經驗證的經驗被杜威稱作“原始經驗”。與原始經驗相對應的,是個體通過反省思維獲得的、經過推演和提煉的反省的經驗。原始經驗并不能成為具有完整意義的經驗,它對事物不具有解釋力,它只能告訴我們“發生了什么”,但并不能告訴我們“發生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36)約翰·杜威《經驗與自然》,第15頁。,或者向我們解釋這件事情為什么發生、是怎么發生的。但是,原始的經驗卻可以為反省的經驗提供第一手的材料,并成為反省經驗的對象。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學生已經具備的原始經驗是深度學習的起點,也是教師必須加以利用并幫助學生進行經驗改造的關鍵。
比如,當我們在進行“(滑動)摩擦力的大小與哪些因素有關”的教學時,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已有的經驗是“在冰面上滑行比在柏油馬路上更容易”、“在客廳里拖動桌子比拖動椅子更困難”,這些經驗是學生的原始經驗。根據先前所學的“阻礙物體相對運動的力叫做摩擦力”,在教師啟發下學生能夠將原始經驗與已有的科學概念聯系起來,將原始經驗理智化并形成推理:在路面滑行和拖動桌椅受到的阻力就是摩擦力,之所以我們感受到運動的難易度不同,是物體間的摩擦力不同。在此基礎上,學生可以展開豐富的聯想并提出多種假設:摩擦力的大小和物體質量有關、摩擦力的大小和接觸面所受壓力有關、摩擦力的大小和物體接觸面的粗糙程度有關、摩擦力的大小和物體運動的速度有關,等等。最后,學生在教師帶領下,通過多種不同情境下的典型實驗(改變物體質量、改變物體接觸面所受壓力、改變物體表面的粗糙程度、改變物體運動速度等),從而驗證自己的假設并得出結論:(滑動)摩擦力的大小與物體接觸面的粗糙程度和表面壓力有關。這時學生得出的結論就是經過驗證和提煉的反省的經驗,也是我們希望通過教學讓學生掌握的知識。這一過程可以被抽象為如圖1所示的流程:學生在日常生活中通過感知覺獲得關于事物的原始經驗,教師要通過創設情境的方式將這些原始的經驗喚醒;原始經驗與先前已有的科學概念建立聯系從而得到理智化,形成關于事物的推理;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展開聯想,提出關于事物的多種假設;學生在教師帶領下,通過多種變式下的典型實驗驗證提出的假設;將實驗所得的結論系統化、邏輯化、抽象化,最終形成關于某一事物的反省的經驗。

圖1. 杜威“經驗”視角下學生原始經驗升級為反省經驗的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學生所習得的知識和所得出的結論都是從自己的原始經驗中一步步推演出來的,但又是遠高于自己的原始經驗的。這些經驗雖然對學生個人而言是新的發現、新的創生,但對人類總體而言則是已有的、經過驗證的。通過個體經驗的升級與轉化,學生既實現了對知識全面而系統的掌握,也在知識的還原與打開過程中重溫著人類社會歷史經驗發生和發展的過程。
2.社會歷史經驗向個體經驗轉化
在深度學習中,學生個體意義的建構和社會意義的建構是同時發生、不可分割的。以“經驗”的視角來看,這種雙重意義的建構也長期、連續不斷地存在于教學的全部進程中。
我們可以將基于經驗的教學過程中社會歷史經驗向個體經驗的轉化過程抽象為如圖2所示的簡圖。
在每一個教學進程中,學生個體現有的經驗都是教學活動開始的起點,人類的社會歷史經驗則是教學活動的終點。教師通過為學生提供有刺激性的情境或者內容,喚醒學生的原始經驗,帶領學生經過推理、假設和驗證等一系列的活動,以典型的、簡化了的方式重新經歷人類社會歷史經驗進化與發展的整個過程,并最終將這些就人類總體而言已經存在的社會歷史經驗轉化為學生個體的新的、反省的經驗。而這些新的、反省的經驗又將作為學生的已有經驗被保存下來,成為開啟下一個教學進程的起點。如此循環下去,學生在經歷人類社會歷史經驗發展的過程中,社會歷史經驗不斷轉化為學生的個體經驗,個體經驗也不斷被社會歷史經驗所充實,從而實現其個體經驗中社會意義的建構。

圖2. 杜威“經驗”視角下個體經驗與社會歷史經驗轉化的過程
在這樣一個社會歷史經驗向個體經驗的轉化過程中,學生不斷“重溫”著人類社會歷史經驗的發展歷程,知道自己所處的社會中已有的經驗從何而來;也在這一轉化中學會新的概念、原理,掌握新的方法、技能,萌發新的思考也體驗著新的情感,不斷開啟著對他們自己而言的“新世界”的大門。
可以發現,無論是知識觀還是學生觀,無論是從教師的“教”還是學生的“學”,杜威都在著力強調內部條件與外部條件的互動,強調學生個體與社會歷史的關聯,強調知識與經驗的統一與協調。學生所學的知識是包含著社會歷史文化因素的發展著的經驗;教師要通過“還原”的方式在學生與知識、個體經驗和社會歷史經驗間建立連接;學生更是要通過重溫人類社會歷史經驗發展的方式來實現個體經驗的升級與轉化。這一系列的“包含”“連接”“重溫”都說明,只有在知識與經驗的統一中,在個人與社會的統一中,學生才能真正參與到人類的社會歷史實踐中,才能將人類社會的歷史經驗轉化為個體的精神財富,才能夠真正實現深度學習;而深度學習的結果,正是使學生獲得發展并最終成為人類社會歷史的真正參與者。正如杜威所說:“社會在指導青少年活動的過程中決定青少年的未來,也因而決定社會自己的未來。”(37)約翰·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第49頁。我們通過深度學習,希望塑造的正是這樣一批能夠讀懂自己民族的歷史、參與自己民族的現在、塑造自己民族的未來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