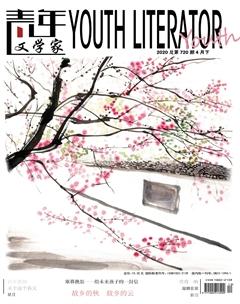論魯迅《弟兄》的復(fù)調(diào)性
云霄
摘 ?要:復(fù)調(diào)性是魯迅小說(shuō)的一大特點(diǎn),也是“魯迅氣氛”的主要構(gòu)成元素。研究者歷來(lái)將研究魯迅小說(shuō)中的復(fù)調(diào)性的重點(diǎn)放在《孤獨(dú)者》、《在酒樓上》、《傷逝》等作品中。本文試分析《弟兄》中的復(fù)調(diào)性,復(fù)調(diào)性對(duì)于作品中兄弟關(guān)系和人物性格刻畫(huà)得作用,并結(jié)合周氏兄弟失和這一現(xiàn)實(shí)背景討論《弟兄》這篇短篇小說(shuō)的思想內(nèi)涵。
關(guān)鍵詞:魯迅;《弟兄》;復(fù)調(diào)性
[中圖分類(lèi)號(hào)]:I2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20)-12-0-02
復(fù)調(diào)原是音樂(lè)術(shù)語(yǔ),指兩段及兩段以上相互對(duì)等的聲部同時(shí)進(jìn)行,它們彼此對(duì)立統(tǒng)一,形成和聲關(guān)系。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shī)學(xué)問(wèn)題》中將這一音樂(lè)術(shù)語(yǔ)引申到文學(xué)批評(píng)領(lǐng)域,用以區(qū)別“獨(dú)白型”的小說(shuō)模式。大體而言,即小說(shuō)作品并非按照一條平滑的敘述思路順延下去,而是小說(shuō)內(nèi)部充斥著多種交織在一起的聲音和意識(shí)。小說(shuō)主人公的思想并非在作者的操控下走向一個(gè)明確的節(jié)點(diǎn),而是多種復(fù)雜的思想意識(shí)平等地各抒己見(jiàn),表達(dá)自我。魯迅的多部短篇小說(shuō)中都多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復(fù)調(diào)性的影子,可以說(shuō),小說(shuō)的復(fù)調(diào)性成為了“魯迅氣氛”的構(gòu)成元素之一。尤其是《彷徨》這部短篇小說(shuō)集中,《孤獨(dú)者》、《在酒樓上》、《傷逝》多有名家研究,這三部作品以第一人稱(chēng)出發(fā),多種聲音、意識(shí)交替辯駁,集中體現(xiàn)了復(fù)調(diào)性。
收錄在《彷徨》中的《弟兄》以第三人稱(chēng)視角進(jìn)行敘述,也同樣也體現(xiàn)了復(fù)調(diào)性小說(shuō)的特點(diǎn)。在早期的與《弟兄》文本相關(guān)的研究中,不少學(xué)者認(rèn)為魯迅是通過(guò)寫(xiě)沛君、靖甫這對(duì)兄弟身上的故事來(lái)揭露兄長(zhǎng)沛君的偽善和自私,其主要依據(jù)是對(duì)文本中沛君的夢(mèng)境的解讀,認(rèn)為沛君夢(mèng)到自己打弟弟靖甫的孩子荷生正體現(xiàn)了其心懷惡念的一面;近年來(lái),更多的研究?jī)A向于認(rèn)為《弟兄》中的兄弟二人即是魯迅與周作人的寫(xiě)照。《弟兄》寫(xiě)于1926年,那時(shí)自周氏兄弟決裂已逾三年,小說(shuō)中靖甫生病的情節(jié)幾乎還原了周作人初到北京時(shí)起疹子的經(jīng)歷。因此一部分學(xué)者們對(duì)于先前的“偽善和自私說(shuō)”予以否定,認(rèn)為《弟兄》體現(xiàn)了魯迅身為一個(gè)長(zhǎng)子對(duì)兄弟的真切的關(guān)懷,“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難,他還愿像當(dāng)年周作人患病時(shí)那樣救助。”[1]筆者認(rèn)為,《弟兄》并不是魯迅用以揭示人性中的偽善和自私,也不完全是周氏兄弟的寫(xiě)照。《弟兄》同樣有著非常明顯的復(fù)調(diào)特征,這主要體現(xiàn)在文本中兩種兄弟關(guān)系的對(duì)照和沛君內(nèi)心世界的掙扎兩個(gè)方面,這兩個(gè)方面作用于環(huán)境內(nèi)外,更彰顯了人的復(fù)雜和矛盾,這也正是魯迅創(chuàng)作的一貫主題。
一.為錢(qián)而傷與兄弟怡怡:文本中的兩種兄弟關(guān)系
在《弟兄》的文本敘述中有兩對(duì)兄弟,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兄弟關(guān)系。文本開(kāi)頭旋即提到的是沛君的同事秦益堂家的兩兄弟:“到昨天,他們又打起架來(lái)了,從堂屋一直打到門(mén)口……老三說(shuō),老五折在公債票上的錢(qián)是不能開(kāi)公賬的,應(yīng)該自己賠出來(lái)……”可以說(shuō),這對(duì)只存在于他人議論中的兄弟的出場(chǎng)即表現(xiàn)了兄弟間不和睦的一面,他們?yōu)樨?cái)而傷,因?yàn)殄X(qián)的事“從堂屋一直打到門(mén)口”。沛君評(píng)論性質(zhì)的話語(yǔ)緊隨著這對(duì)不和睦的兄弟二人出現(xiàn)在文本中,他對(duì)于兄弟因錢(qián)反目的行為表示不理解,因?yàn)樵谒募彝ブ校?他和弟弟靖甫兩人兄弟怡怡,關(guān)系融洽。這樣,在小說(shuō)的一開(kāi)始,魯迅就為我們展現(xiàn)了兩對(duì)對(duì)立的兄弟關(guān)系:一對(duì)兄弟因錢(qián)反目,另一對(duì)兄弟則和睦融洽。
如果這兩對(duì)兄弟的對(duì)立關(guān)系只在小說(shuō)開(kāi)端出現(xiàn)了一次,那這種對(duì)立則更像是一種對(duì)比——以秦益堂家交惡的兄弟關(guān)系反襯突出沛君靖甫二人的兄弟情深。但這一對(duì)立關(guān)系也出現(xiàn)在了小說(shuō)結(jié)尾,即沛君在靖甫病情好轉(zhuǎn)后回到工作崗位上時(shí),秦益堂再次提及了他家中的兩兄弟因?yàn)殄X(qián)的問(wèn)題陷入爭(zhēng)執(zhí),而這次沛君并未主動(dòng)參與討論,在秦益堂夸贊沛君與靖甫“兄弟怡怡”時(shí),沛君也沒(méi)有做出回應(yīng)。開(kāi)頭與結(jié)尾的相似的情節(jié)的照應(yīng),使得這兩對(duì)兄弟在文本中的地位處于平等的位置上,而不是一方的存在是為了突出彰顯另一方。
兄弟之間的關(guān)系究竟應(yīng)該是什么樣的?《弟兄》并未給出明確的答案:如果說(shuō)魯迅旨在肯定兄弟和睦,排斥兄弟反目,那么就不應(yīng)將這兩者在文本中置于平等的位置上,文本中沛君也不會(huì)從起初堅(jiān)持兄弟間應(yīng)當(dāng)不計(jì)較,不該因財(cái)而傷到最后面對(duì)別家兄弟的反目變得沉默無(wú)語(yǔ)。交惡與和睦,兄弟關(guān)系的兩級(jí),成為了文本中鮮明的兩種聲音,它們?cè)谖谋镜牟煌恢媒惶嬲紦?jù)上風(fēng),也反映了魯迅對(duì)于兄弟關(guān)系的思考,這種思考是存在矛盾和掙扎的。兄弟情誼固重,但經(jīng)濟(jì)問(wèn)題也確實(shí)是橫亙?cè)诟星橹g的現(xiàn)實(shí)。魯迅也曾一度因?yàn)槠溟L(zhǎng)子身份,放棄留學(xué)轉(zhuǎn)而回國(guó)承擔(dān)起家庭的開(kāi)支。文本中兩對(duì)兄弟間對(duì)立的關(guān)系,實(shí)則也體現(xiàn)了情感和現(xiàn)實(shí)沖突。從兄弟怡怡到兄弟反目,魯迅和周作人的關(guān)系正經(jīng)歷了這樣一個(gè)過(guò)程,單從《弟兄》文本這樣一個(gè)框架來(lái)看,魯迅并沒(méi)有明確自己的態(tài)度,至少?zèng)]有完全將自我的情感傾向植入文本,而依然是采取了復(fù)調(diào)的方式,將兄弟關(guān)系放在兩種極端的矛盾的關(guān)系中進(jìn)行隱性的辯駁。
二.利他與利己:沛君心理的兩重屬性
《弟兄》中存在的矛盾和對(duì)立不僅體現(xiàn)在文本的兩對(duì)兄弟關(guān)系中,也體現(xiàn)在沛君一個(gè)人身上,這種矛盾的雙重屬性在一個(gè)人的心理活動(dòng)中更加得到彰顯。
沛君在中醫(yī)誤診靖甫得的是紅斑痧(西醫(yī)叫猩紅熱)后一度陷入絕望,在沛君堅(jiān)持等待另一位西醫(yī)再次來(lái)確診的時(shí)候,有一段對(duì)病房外汽車(chē)的汽笛的細(xì)致描寫(xiě)(在夜的漸就寂靜中,在他的翹盼中,每一輛汽車(chē)的汽笛的呼嘯聲更使他聽(tīng)得分明……他知道了汽笛聲的各樣:有如吹哨子的,有如擊鼓的,有如放屁的,有如狗叫的,有如鴨叫的……),這部分看似是對(duì)外界靜寂幽深的夜的描寫(xiě),實(shí)則是在寫(xiě)沛君的心理。被寂然的夜所籠罩的世界里傳來(lái)紛雜的汽笛聲,而汽笛只能聽(tīng)到,無(wú)法看到,這樣模糊了視覺(jué)的描寫(xiě)給人夢(mèng)境般的不真實(shí),也使文本由實(shí)入虛——沛君從靖甫的病房轉(zhuǎn)入了自己的心理世界,漆黑的環(huán)境,被無(wú)限放大的汽笛聲,都體現(xiàn)了沛君心中的絕望,壓抑以及等待西醫(yī)到來(lái)的急切焦慮。汽車(chē)的汽笛真的有這么多種千奇百怪的聲音嗎?在寂靜的深夜里真的會(huì)有這么多車(chē)輛往來(lái)嗎?這些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大可以認(rèn)為這是沛君在焦慮中等待時(shí)產(chǎn)生的幻覺(jué)。魯迅寫(xiě)沛君對(duì)靖甫的關(guān)切,并沒(méi)有過(guò)多從其行動(dòng)上著手,而是以近乎虛寫(xiě)得方式潛入到沛君的心理世界,用似真似假的夜、呼吸聲、烏鴉叫、此起彼伏的汽笛聲來(lái)營(yíng)造出心理由于焦慮和絕望的擠壓而產(chǎn)生幻覺(jué)的氣氛,給人以強(qiáng)烈的窒息感,而這也正是沛君心理正經(jīng)歷的。
同樣地,這種對(duì)靖甫關(guān)切的心情也沒(méi)有貫穿文本,而是很快又被接下來(lái)的沛君的夢(mèng)境打斷。在誤以為靖甫得的是猩紅熱時(shí),沛君在悲傷壓抑的同時(shí)也想到了靖甫死后的后續(xù)問(wèn)題,即不得不承擔(dān)起撫養(yǎng)靖甫的孩子荷生的重任這其實(shí)是完全出于現(xiàn)實(shí)的考慮。但在靖甫被西醫(yī)確診只不過(guò)是普通地起疹子后,撫養(yǎng)荷生的這一想法依然在沛君腦海中揮之不去,對(duì)此,他甚至做了一個(gè)夢(mèng),夢(mèng)到靖甫已經(jīng)死了,他忙著收殮;夢(mèng)到荷生站在自己面前,滿臉是血;夢(mèng)到自己以在家里最高權(quán)威的力量狠狠地打了荷生一巴掌;又夢(mèng)到自己站在家人面前,在一片指責(zé)中辯解自己并未打荷生……這些可怖的夢(mèng)境反復(fù)交織出現(xiàn),直至天明。有研究認(rèn)為這一段夢(mèng)境敘述體現(xiàn)了沛君的偽善和自私:他既不愿在靖甫死后承擔(dān)撫養(yǎng)兄弟的孩子的重任,又不想因?yàn)樘澊诵值艿暮⒆颖患胰素?zé)備,害自己丟了面子,這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在小說(shuō)的結(jié)尾部分,當(dāng)秦益堂再次提及他家中兩個(gè)兄弟因錢(qián)反目的事情時(shí),沛君沒(méi)有再想開(kāi)頭那樣接話,自信地否認(rèn)這樣一種兄弟關(guān)系,而是多少變得沉默不語(yǔ)。促使沛君做出這樣的改變的正是靖甫生病這件事,在經(jīng)歷了那樣的夢(mèng)境后,沛君也對(duì)自己的感情產(chǎn)生了質(zhì)疑,無(wú)法再給出自己曾經(jīng)堅(jiān)定的答復(fù)。但所謂偽善和自私說(shuō)到底也只是沛君人格中的一部分,對(duì)家庭負(fù)擔(dān)家中的擔(dān)憂,難以把愛(ài)平均分給自己的孩子和弟弟的孩子,這難道不也是人之常情嗎?不正符合一個(gè)小公務(wù)員對(duì)現(xiàn)實(shí)處境做出的合理反映嗎?更重要的是,在夢(mèng)境之前,還有那一部分對(duì)汽笛的描寫(xiě),也即對(duì)沛君心理的描寫(xiě)。對(duì)沛君的心理描寫(xiě)的部分,并沒(méi)有像之后的夢(mèng)境描寫(xiě)一樣直接揭示這是沛君的幻覺(jué)或者是沛君的夢(mèng),這種心理狀態(tài)更像是處于夢(mèng)和現(xiàn)實(shí)的邊緣地帶,更像是沛君的一種潛意識(shí)。這種潛意識(shí)里自發(fā)的緊張、壓抑、焦慮與絕望,正是沛君對(duì)靖甫的關(guān)切和真情流露,魯迅寫(xiě)得很隱蔽,仿佛沛君自己都未覺(jué)察到這一點(diǎn)。而未察覺(jué)便已經(jīng)存在于心底的情感,不正是兄弟怡怡的一種更深層次的體現(xiàn)嗎?沛君無(wú)疑是真切地關(guān)心著弟弟的,他為靖甫的病而奔走求醫(yī),在絕望和焦慮中忘卻自我;但沛君同樣也陷入對(duì)自己的生活的悲觀想象中無(wú)法自拔,他想到靖甫死后,荷生將成為自己的負(fù)擔(dān),想到自己責(zé)打荷生又必會(huì)在家人面前丟了面子。一面是對(duì)兄弟感情的真實(shí)流露,一面又是全然顧己的自私,利他和利己寓于沛君這一個(gè)的人格之中,既矛盾,又達(dá)到了某種平衡,再次體現(xiàn)了魯迅筆下的人物的復(fù)雜性。
三.總結(jié)
《弟兄》這篇短篇小說(shuō)最后的落腳點(diǎn),究竟是用以揭露沛君人性中的虛偽和自私,還是實(shí)則是對(duì)魯迅和周作人的兄弟關(guān)系的一種寫(xiě)照?筆者認(rèn)為兩者都不完全是。
《弟兄》有強(qiáng)烈的復(fù)調(diào)小說(shuō)的色彩,短短的篇幅中故事并未順延著一條通向唯一終點(diǎn)的敘述線進(jìn)行,而是交織在不同的兄弟關(guān)系和主人公不同的心理狀態(tài)中,我們也在這多種可能的辯駁中看到沛君并不是一個(gè)全然虛偽自私的單薄的人物,他以自我為中心,但也深?lèi)?ài)著自己的弟弟靖甫。另外,《弟兄》中的故事,確實(shí)有現(xiàn)實(shí)中的來(lái)源,即開(kāi)頭提到的周作人初到北京時(shí)生病一事。根據(jù)《魯迅日記》和《周作人日記》的記錄,1917年5月,周作人剛到北京沒(méi)多久就發(fā)了高燒,病狀很?chē)?yán)重,魯迅先后請(qǐng)俄國(guó)醫(yī)生蘇達(dá)科甫、德國(guó)醫(yī)生格林和狄博爾前來(lái)治療,后來(lái)確診只是普通地起疹子,魯迅這才感到懸著的心放下了。《弟兄》寫(xiě)到靖甫痊愈的那天,掛著的日歷上寫(xiě)著漆黑的“廿七”,這和現(xiàn)實(shí)中周作人病愈的時(shí)間是一樣的,這一天對(duì)于魯迅來(lái)說(shuō)印象深刻。對(duì)此,我們可以說(shuō)《弟兄》正如傷逝般,有著鮮明的現(xiàn)實(shí)的色彩,有著魯迅本人的清晰的影子,但并不完全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寫(xiě)照。我們能從現(xiàn)實(shí)事件中和多方回憶中看到魯迅對(duì)周作人的兄弟情深,也能從《弟兄》中看到對(duì)這一事件的反映,但魯迅始終與自己的作品保持著一定距離,能夠在虛構(gòu)抵達(dá)真實(shí)的邊緣時(shí)從作品中將自己抽離。《弟兄》中也有更多現(xiàn)實(shí)中沒(méi)有的元素,例如多重存在的矛盾關(guān)系和矛盾心理。魯迅以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做《弟兄》的原材料,在他與周作人決裂后不動(dòng)聲色地表露了重歸于好的心跡,但《弟兄》的故事畢竟是圍繞沛君而非魯迅本人展開(kāi),從文本中我們能看到的更多的是魯迅氣氛中鮮明的復(fù)調(diào)性,以及魯迅對(duì)人性的矛盾復(fù)雜的展現(xiàn)和思考。
注釋?zhuān)?/p>
[1]出自《魯迅和周作人》,《新文學(xué)史料》1983年第4期.
參考文獻(xiàn):
[1]顧農(nóng).魯迅的長(zhǎng)子情結(jié)與《弟兄》[J].博覽群書(shū),2013(02):81-85.
[2]張艷麗. 白晝之光,豈知夜色之深——重讀魯迅《弟兄》[J].民間故事, 2018, (2)
[3]陳佳任.論魯迅《幸福的家庭》的復(fù)調(diào)性[J].名作欣賞,2018(29):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