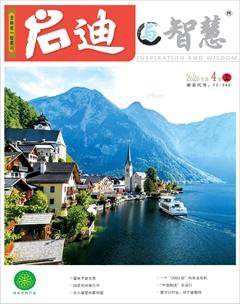不將精力做人情
樂朋
學(xué)界泰斗顧頡剛和錢鍾書,1978年在北京三里河公寓成了鄰里。7月18日,兩家人在小區(qū)散步邂逅,當(dāng)天顧的日記記載:“鍾書以洪邁‘不將精力做人情語(yǔ)相勸,當(dāng)勉勵(lì)行之。”
一向惜字如金、沉默寡言的錢鍾書,緣何贈(zèng)顧“不將精力做人情”之語(yǔ),豈非有些唐突?
當(dāng)時(shí)剛度過十年浩劫的中國(guó)學(xué)界,亟須撥亂反正,百?gòu)U待興;顧、錢兩位,本是相交幾十年的老友。可當(dāng)時(shí)顧頡剛年過古稀,又處于半退休狀態(tài),但他忙得不可開交,被大量瑣碎雜務(wù)、人情纏住了身。除了出席重要會(huì)議和必要的社會(huì)活動(dòng),他另有一堆雜事:
院、所來了賓客,他出面作陪;學(xué)界同行的研討會(huì)、成果發(fā)布,他要去捧場(chǎng);門下弟子的學(xué)業(yè)、工作、生活,他又得關(guān)照、出面疏通;各路媒體的采訪,他要接待、交談;還有各種飯局,為人作序,推薦書稿,等等。
總而言之,他這個(gè)史學(xué)大家從早忙到晚,幾乎做了社會(huì)活動(dòng)家、公關(guān)先生。他的時(shí)間、精力大半都用在了非學(xué)術(shù)的人情、應(yīng)酬上。
冷眼旁觀的錢鍾書忍不住開“金口”,規(guī)勸“不將精力做人情”,切中其軟肋,顧頡剛深受感動(dòng),以至震撼!他稱錢鍾書贈(zèng)語(yǔ)為“箴言”,“鍾書勸予勿于(與)社會(huì)上無(wú)聊人往來,浪費(fèi)垂盡的精力……良友之言敢不遵從。”
“不將精力做人情”,其實(shí)這是錢鍾書治學(xué)的經(jīng)驗(yàn)之談。他埋頭書齋,傾心治學(xué),對(duì)社會(huì)上的應(yīng)酬、人情之類,能推則推,能拒則拒,不隨波逐流。他幾乎不出席與自己學(xué)術(shù)無(wú)關(guān)的任何會(huì)議,更不交無(wú)聊之人,也從不接受報(bào)紙采訪,不上電視節(jié)目,不隨意題字、薦人,應(yīng)酬飯局都不參加。“謝絕一切人事”的錢鍾書,年方花甲就出版了百萬(wàn)字的皇皇巨著《管錐編》,引起學(xué)界轟動(dòng)。他排除一切干擾,專心致志著書立說,讓顧頡剛羨嘆不已。
人的時(shí)間、精力是有限的。尤其對(duì)顧頡剛這樣的老學(xué)者而言,來日無(wú)多,因而其精力、生命就殊為寶貴。此時(shí)仍將精力做人情,不專注于學(xué)術(shù),那就簡(jiǎn)直是浪費(fèi)生命、耽誤正業(yè);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gè)中國(guó)的文化名流,身負(fù)著振興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文化的歷史責(zé)任。如果不能專精于學(xué)術(shù)創(chuàng)造,把時(shí)間和精力耗費(fèi)在雜事、人情上,那么就辜負(fù)了社會(huì)的期望,同時(shí)也失去了學(xué)者的價(jià)值。學(xué)者不治學(xué),總?cè)プ鋈饲椋€能稱學(xué)者嗎?
錢鍾書的金玉良言,如醍醐灌頂。此后的顧頡剛,把“要無(wú)恨于此生”作為座右銘,決意擺脫雜務(wù),集中精力于學(xué)術(shù)。他訂下未來五年計(jì)劃,編好自己的筆記和論文集,出了十種書。1980年,病床上的顧頡剛?cè)栽谛i喤f作《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的重排版樣;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還在病床邊的沙發(fā)上研讀《十三經(jīng)注疏》。爭(zhēng)分奪秒地與時(shí)間賽跑,他要為后人留下自己的學(xué)術(shù)成果。
我佩服錢鍾書的睿智淡泊、孤傲高雅,我也贊賞顧頡剛善納良友箴言。“不將精力做人情”,不只當(dāng)是學(xué)者的品格,你我這些普通人,又何嘗不需要擺脫人情糾纏,用心干好本行?
茹茹薦自《雜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