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之際宗教觀念轉變芻議
□王婉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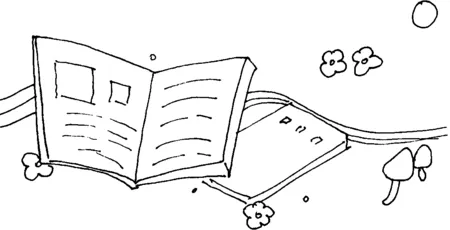
追溯中國古代宗教思想的源頭,早在商周時期就有關于宗教信仰、祖先崇拜的濫觴。處于蒙昧階段的原始族群對于宇宙自然的生成變化抱有巨大的疑問,由于個體生存的無法保障,使得他們對自然界有著強烈的崇拜。直至殷商之時,人們仍然保留著原始社會的多神信仰體系,他們的宗教中還保有相當濃厚的神秘色彩。這種原始性和神秘性表現在:至上神的地位不明確,以及由神界秩序的不確定所反映出的人類社會的不穩定,此時的人們還多半受巫術等思想觀念的深刻影響。
西周興起“以德配天”的思想觀念,使宗教意識開始逐漸擺脫了原始自然宗教中神秘化、巫術化的色彩,減輕了盲目迷信所帶來的猜忌和恐懼心理。同時,周人明確了至上神的身份,即“天”。周人將天與時王之間建立道德聯系,并對祖先神的崇拜加之以德性的依附,這樣人間的德行就有了神權保障。從西周始,“神”的人格化內涵就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人文化成的觀念萌芽,人們關注的重點從神轉移到了人。
一、殷商時期的宗教
(一)混亂的多神崇拜
殷人的宗教信仰具有多神崇拜的特點,自然神、祖先神、上帝都是他們崇拜的對象。殷人的崇拜對象基本可分為天神(包括上帝和自然神,如日、東母、西母、云、風、雨等)、地示(包括土地等自然神,如社、四方、四戈、四巫等)和人鬼(包括先王、先公、先妣、諸子、諸母、舊臣)三種(陳夢家 :《殷墟卜辭綜述》,中華書局,1988年,第562頁),這在殷墟的甲骨卜辭中就能體現出來。而在他們心中至高無上的神則是“上帝”,它掌控著一切,是全知全能的神。但由于殷商的神系分工不明確,殷人心中的至上神究竟是一神還是多神仍存在疑問。
并且,殷始祖與“上帝”的關系也是至今沒有定論的。郭沫若認為“殷人的帝就是帝嚳,是以至上神而兼祖宗神。”(郭沫若 :《青銅時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8頁)陳夢家認為帝并非祖先神只是自然神(陳夢家 :《殷墟卜辭綜述》,中華書局,1988年,第580頁),王國維認為帝嚳為殷祖先神(《古史新證·殷之先公先王》)。目前,經由考古出土的材料,比較可靠的說法是認為殷人是多神崇拜,至上神并非一個(晁福林 :《論殷代神權》,《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同時,由于殷商時期的宗法制度沒有建立起來,許多時候并非是“父死子繼”,而是“兄終弟及”,如從成湯到帝辛的三十帝中,“以弟繼兄者凡十四帝”(王國維 :《殷周制度論》)。這種社會政治秩序的不穩定反映在信仰生活中就出現了龐雜的祖先神沒有統屬的秩序,這必然造成神意的難以預測。
殷人對至上神的崇拜達到極致,他們非常崇信神,并熱衷占卜。至上神統領和掌管著世間萬物,并且是具有人格的神,它能通過天神行風降雨,也能降下人間禍福。正是這種觀念的支配和影響,殷人每逢重大事件都會向上天占卜祈禱,也會舉行祭祀以祈福禳災。從安陽殷墟出土的王室卜辭來看,從天時、年成、祭祀、征伐到商王田獵、疾病、生育等,都要通過占卜求問上帝。
(二)殷商“殘民事神”的祭祀
殷商時期最重要的社會活動就是祭祀典禮,祭祀鬼神已成為當時的一種制度并指導著國家的日常活動,并且這時的祭祀極為隆重,每次祭祀動輒就要殺牲數百頭。《禮記·表記》云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在如此尚鬼的國度,占卜與祭祀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祭祀就會有祭品——犧牲,其目的是為了取悅祖先和神靈。考古發現殷墟王陵區有祭祀坑約2200余座,這些祭祀坑連成一片可以形成一個總面積在10萬平方米以上的巨大祭祀場(楊寶成 :《殷墟文化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97頁)。祭祀所用的祭品也分為牛、馬、羊等動物和奴隸。殷人崇信神權而輕視人的生命,他們在祭祀和殉葬中大量使用人牲,且在當時極為普遍。
據胡厚宣統計,甲骨卜辭中有人祭內容的甲骨有1350片,卜辭1992條,用人量一次最高可達300-500人;從盤庚遷殷到帝辛亡國共用人牲13052人,另外還有1145條卜辭未記人數,若每條按一人計算,至少用人牲14197人;武丁時期的規模最為龐大,有甲骨673片,卜辭1006條,記載祭祀用9021人,最多的一次用500人,另有相關531條卜辭未記人數(胡厚宣 :《中國奴隸社會的人殉和人祭(下)》,《文物》1974年第8期)。如此大量的殺生祀神足以表現出殷人對于他們所崇拜的“命運之神”“主宰之神”的陌生與恐懼。在當時社會生產力低下的條件下,人們認識事物的能力也是有限的,這使得他們未能正確地看待神與人之間的關系,所以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意識。同時,由于這時的“神”多是不可捉摸、變幻無常的自然神,還沒有倫理的性質,是自然性的,有時也會“暴虐無比”。這種神意的難以預測性又反過來加深了殷人對于神的恐懼,那么為了取悅神而不惜以人為牲也就不難理解了。
此外,關于殷人“殘民事神”的做法,有學者認為是源于原始社會時把人作為“食物”奉獻給祖先食用的習俗(于省吾、姚孝遂 :《甲骨文字詁林》,中華書局,1999年,第115頁)。在政治層面上,殷商統治者從戰爭中獲得大量戰俘,并將這些異族戰俘以殘酷的方式作為祭品,將殺人祭祀宗教化,呈現出政治的宗教化與宗教的政治化的雙重關系。從這一角度講,殷商的統治者在祭祀中大量使用人牲有武力震懾其他方國的可能,與其實行的恐怖政策有關;從生產力發展水平看,較低的生產力以及有限的生存資源也有可能難以保證對民眾、戰俘的供給,由此間接導致了“人牲”的出現。
二、“神性”的淡化與“德性”的覺醒
殷人的宗教觀念,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早期的殷人向祖先提供祭品時,都誠心實意地使用品質優良的禮器或者生活中的實用器。但到了晚期,后人向死者提供的隨葬品越來越簡單,逐漸發展成“冥器”(也稱明器)。所謂冥器實際上是一種專門為“鬼”制作的僅具象征意義的隨葬品。從葬禮的角度看,明器開始普遍用于隨葬,意味著殷人越來越少地在落葬時舉行奉獻食物的祭祀活動。因為明器細小、粗糙,不可能真正放置食物,反映了其時人們對鬼神已不像先前那樣敬畏了。
殷人宗教觀念中對鬼神的畏懼之感到了商中后期就逐漸淡化,這種觀念到了周人那里又有了變化。周人承襲了殷人對天命鬼神的基本觀念,但殷商的覆滅也使周人對天命人事進行深刻反思,從而全面變革了信仰方式和理念。周人在尊天命的基礎上提高了“德”的重要性,這其中難免有借助“神”之力來論證周奪取政權合理性的意圖,但更重要的則是建立起了德、神、人之間的關系。如《尚書·召誥》中,周公對殷遺民所說: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周公認為,夏殷兩國之所以不能長久延續,是因為不敬德而失去了天命。德的功能不僅在于處理人事,它同時還是連接神與人的中介。周人的天神有德的屬性,所以只有有德的君王才能獲得天命,進而得到天神的庇佑。人在神面前不再只是匍匐在地的畏懼狀態,而是開始用德來配天,人身上有天的某種屬性,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人地位的提升。
與此同時,雖然殷商時期宗教色彩濃重,但我們應當認識到,在殷商時期確立的人神關系中,神雖然具有最終的決定性作用,但同時也透露出了一絲人們力求以卜筮為媒介,通過祭祀去影響至上神的訊息。什么是“人”?《尚書·泰誓上》稱 :“惟人萬物之靈。”“靈”在哪里?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群體生活的動物,并且有各種社會關系還能妥善處理各種社會關系的行為規范(張豈之 :《中華人文精神》,陜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3頁)。隨著社會歷史的進步,人類理性思維日益發達,鬼神等宗教觀念的淡化,歸根結底意味著人對自身的理解進一步合理化,意味著人越來越擺脫鬼神這一曲折的形象來理解自身。確切地說,這是“人本”思想的萌芽,中國社會思想已經逐漸地從“尚鬼”“崇天”轉向“重人事”。隨著祭祀越來越淡化巫術占卜的色彩,逐步使祭祀禮儀規范化與系統化,并最終演化為周禮,即變成“禮樂文化”。
三、西周時期的宗教
(一)對殷商宗教的繼承與發展
首先,周人繼承了殷人遵循天命的思想,制定出上承天命以統萬民的君權神授論,如《尚書·召誥》中就有“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之說。在《尚書·召誥》中,周公從夏受天命開始一直論述到周人受天命統治天下。在他看來,上帝之所以不斷委派不同的部落或民族統治天下,完全是因為民心的向背是天命所在,民心才是使上帝決定選擇哪個部落或民族統治天下的最后決定力量。這表明,周公對殷商以來的君權神授論思想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調整。因此,《尚書·泰誓》指出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一個人能否受天命,成為天子進而統治整個國家,歸根結底在于是否有德,是否得民心。可以說,自周公開始,“社會人生的重心,已從天帝鬼神一邊,轉到了人類內在德行一邊。”(王處輝 :《中國社會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66頁)
其次,西周時期的宗教思想是對殷商宗教觀念的損益,其中有變革,也有整合。如西周時把上帝和祖先神分離對待就是一個例子。一方面,周人繼承了殷人崇拜祖先神的觀念,認為祭奉祖先是子孫的神圣義務。但另一方面,周人降低了“上帝”的人格神色彩,增加了至上神的抽象性和理性成分。他們將殷人的“上帝”觀念改造成為以“天”為中心的至上神信仰 :“天”是主宰人類禍福的全能神,天下大事均取決于“天”的意志。于是,有了區別于祖先神的至上神“天”,就有了各族必須共同尊奉的權威。從人的角度看,現實的人們擺脫了祖先的制約,取消了神人聯系的中間環節,提高了現實的人在神圣“天”界的地位,是后來儒家肯定人在“天”面前擁有較高地位的最早淵源(張茂澤 :《中國思想文化十八講》,陜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頁)。
另外,在祭祀祖先方面,周人更加重視等級和儀式。根據宗法制和分封制的規定,周人將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的祭祀范圍作了不同的劃定。《禮記·王制》也講到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為了強調宗族內的血緣親疏,維護嫡長子在族內的權威,禮制規定只有嫡長子才有祭祖的特權。《禮記·喪服小記》也記載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這表明祭祖制度在宗族內部劃分出嫡與庶、貴與賤、親與疏,是宗法制度的一部分。
(二)“天命有德”與“以德配天”
在西周的話語體系里,“德”與“天命”有著緊密聯系。《尚書》中多有論及“德與天命”關系的句子,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蔡仲之命》)“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尚書·康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書·召誥》)等等。如果說殷商社會的制度基礎是天命的話,那么西周社會的各項制度基礎則要在天命的基礎上加上“德”。這里的“德”不是自然的性質或關系,而是一種有人類社會性質的規范。在周人心中,“天”的作用與體現,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德”作為中介。周人提出的“德”,包括敬天、孝祖、保民三項內容,要求統治者在執政時要做到明察、寬厚。周公反復強調,周人取代殷人受命,是修德所致。“德”的倫理思想因宗法制度產生,又為宗法制度服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被奉為天神規定的人間規范,神圣不可侵犯。
《尚書·皋陶謨》言 :“天命有德。”這表明西周的統治者們開始意識到,天命的轉移是以自身的行為是否合德、是否有利于民為依據的。他們對天命有了更加理性的認識,形成了新的天命觀:天命不再是神秘不可知的異己權威,它可以從統治者的德行和民心向背中得知;天命也并非絕對保佑統治者的權威。德行成為了唯一可靠的標準。
同時,由于西周統治者推崇“以德配天”的思想觀念,民眾與天神之間的關系出現了變化 :“重神輕民”的思想逐漸淡化,人或民的地位得到了凸顯。在周代的喪葬禮中,用活人殉葬逐漸減少,改為用俑代替,隨葬品也大為減少。在神人關系中,突出人在“神”面前的地位和作用。天神要聆聽民眾的心愿和想法,神民之間可以互相溝通,即“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暉 :《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2頁)因此,周王在治國方面也只有“王其德之用”,做到“以德配天”,才能真正“祈天承命”。這使民眾的意志與神的權威之間產生了微妙的內在聯系。將人的問題作為解決神人關系或天人關系問題的重點,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特色。
四、殷周之際宗教觀念轉變的原因
首先,一種觀念的形成和變化必定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著緊密關聯,宗教思想觀念也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理應遵循這一準則。商周革命的完成并不簡單意味著殷商政權的覆滅、周政權的確立,其深刻意義更應該從社會經濟文化等多個角度來看待與分析。對于這種不同于殷人匍匐在神腳下的無奈祈禱,周人則試圖認識并利用“天”來為人服務。周人在“天命”面前的自信,可能與周人改朝換代革命成功所產生的自信有關,與西周初年王朝新立,國家疆域空前龐大也當不無關系(張茂澤 :《中國思想文化十八講》,陜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頁)。疆域的擴大有力地消化了殷商時期剩余奴隸的勞動力,將他們用于農業生產中的水利灌溉等具體事項,也使得殺祭現象逐漸減少。武王伐紂的勝利,在社會政治層面上由神權政治向倫理政治轉變。隨著周王王權的日漸強大,弱化了神權政治的統治基礎,從神權政治到倫理政治的轉變不僅是文化上的一個大命題,同時也是社會上層群體選擇的結果。
其次,殷商篤信上帝卻最終被周所取代,這是建立新朝要解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問題。周人將“德”這一概念融入宗教思想觀念之中,恰好對這樣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給予了積極的解釋。《尚書·周書》的十九篇中始終是以“德”作為配天和受民受土的依據。這種“敬德”思想的出現,比較順利地解決了商周何以易代的現實問題。《尚書》云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周書·多方》)這一材料恰好印證了:在西周初期,天命與德行已經有了某種聯系,而這種聯系恰恰體現了西周統治承于天命的正統性。這也是“敬德”觀念之所以滲入到宗教儀式中來的原因。為了確立周的正統地位,解釋其代商的正義性,西周的統治者必須強調其德行的重要性與天之屬性的相似性。由于這時天的神性和意志雖然相比殷商時期有所淡化,但仍沒有完全擺脫神權色彩,西周的統治者遂以德來配天,某種意義上達到其政治的功利性目的。
隨著統治地位的確立,周人為有效管理日常生活,使其制度化、規范化,又對禮儀制度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包括確立一整套典章、制度、規矩、禮節,成為“周禮”。禮的核心是規定社會關系,包括祭祀天地祖先和調節社會各階層的相互關系。周禮在祭祀中的貫徹實行,實際上有效遏止了殷商時人們的宗教狂熱,使祭祀活動變得有序、有度,且逐漸理智起來,而這對于西周時期倫理化宗教的形成也頗具意義。
五、結語
縱觀殷周社會變革,我們可以發現盡管還無法完全擺脫神秘色彩,但這一時期宗教觀念的確是展現了從重視神到逐漸重視人的過程。夏商時期,統治者為了使自己的統治合法化,極力宣傳天命鬼神觀念,甚至通過祭祀時“殘民事神”來宣稱自己是“天”的代理人。由于殷人對神的認識不夠清晰,其所做的也只是去揣摩神意,以上天的庇佑來作為政權延續的解釋,所以在遇到異常事件時往往通過占卜來尊崇神的意愿。商周革命后,周人不僅在政治上確立了政權的正統地位,同時也在文化層面作出了調整和改變。西周的統治者將“天命—德—君”三者聯系在一起,使原來具有神性的宗教思想也開始偏向倫理的一邊。內在的德行外化成為禮儀規范,統治者又以這套標準來規范和統治民眾,由此實現了宗教的倫理化與倫理的宗教化的雙向互動。但此時宗教的去神化傾向發展還很緩慢,雖然有“惟天時求民主”的“敬德保民”思想,但也只意味著神權的動搖,事實上并沒有完全擺脫神權的色彩。
自商周革命之后的幾百年里,以德為核心的思想文化得到了充足發展,它不僅成為支撐儒家思想的主干,也對后來產生的本土道教與西傳佛教的本土化有深刻的影響。對于道家道教思想而言,“德”與“道”一起,作為道教的最高教理教義,其“德”的觀念可以追溯到老子《道德經》中“上德”“玄德”的概念;同時,印度佛教為了適應當時中原的思想文化而吸收和轉化了儒家、道家道教部分思想,并借由魏晉玄學的發展一步步實現其本土化,在這之中就包含了德性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