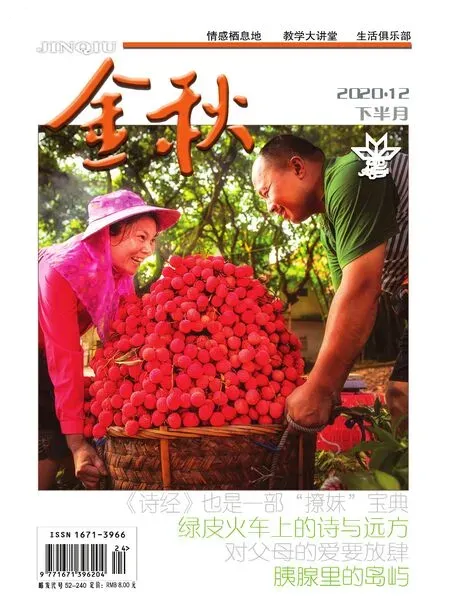揚州八怪中的鬼才
文/兵團戰士
世人說,“揚州八怪”中的羅聘心里有鬼,所以他畫鬼。他是金農的弟子,很有才華,有人稱其“五分人才、五分鬼才”。
羅聘畫鬼,很多人不理解,而袁枚卻是羅聘的知己,對其《鬼趣圖》大加贊賞,在畫上題:“見君畫鬼圖,方知鬼如許。得此趣者誰?其惟吾與汝。”鬼之趣,袁枚默契地意會了。兩人相視而笑。
畫人反類鬼
說起袁枚還有個插曲。隨園老人袁枚交友十分廣泛,羅聘便是其好友之一。某日,羅聘興起,給袁枚畫了一幅像。這幅像,據袁枚的家人說,根本不像是袁枚。而袁枚自己望著這幅畫像,也是眉頭緊鎖。羅聘在一旁仰著臉問,您還滿意嗎?袁枚不好意思說不滿意,畢竟是好友的心血之作,又不好違心地說滿意。良久,他動用了一番心思,寫了頗為拗口的大段題跋:“兩峰居士為我畫像,兩峰以為是我也,家人以為非我也,兩爭不決……我亦有二我,家人目中之我,一我也,兩峰畫中之我,一我也……兩峰居士既以為似我矣,若藏之兩峰處,勢必推愛友之心,自愛其畫,將與鬼趣圖、冬心、龍泓兩先生像共熏奉珍護于無窮,是又二我中一我之幸也。”
袁枚的意思是,家人眼中的我,羅聘眼中的我,究竟哪一個是真實的“我”,世間哪能有定論呢?再說又該怎么處理這幅畫呢?袁枚有主意,說且將此畫由羅聘先生您保管吧,跟《鬼趣圖》一樣,使朋友們都能欣賞到。眾人猜測,這是袁枚不滿意畫像,所以不肯親自收藏。
袁枚的這幅畫像,流傳得相當廣。且看畫中袁枚,光頭,長臉長髯,像羅漢,右手持兩枝菊花。嚴肅中有點戲謔,端莊中夾雜風流。寫意的風格,筆墨相當自在松弛,正是羅聘眼中的隨園老人形象。后來人想象袁枚樣貌,大多以此像為藍本,只是很多人不曉得作者是誰。

羅聘筆下的袁枚
名隨鬼影傳
扯遠了,回到羅聘。紀曉嵐說,羅聘長了一雙綠眼珠,大白天能見鬼。《閱微草堂筆記》這樣描述羅聘所見:凡有人處,皆有鬼。那些橫死的鬼,通常害人,萬萬不可接近。一般的鬼,上午陽氣旺盛,他們在墻根底下庇蔭。午后,陰氣盛行,他們則四散游走,穿墻而過,遇路人則避著走……紀曉嵐娓娓道來,如數家珍。
羅聘本人,貌似也喜歡談論鬼。他在《香葉草堂詩存》里有《秋葉集黃瘦石齋中說鬼》一詩,我試著將其翻譯成白話文,像是恐怖小說:
秋天的黃昏,我在一盞孤燈下靜讀,只見三五個狂鬼,前來揶揄。偏偏我異于常人,將他們看得個個仔細分明。他們脖子很長,身材矮小岣嶁,齜牙咧嘴。陰風陣陣,忽遠忽近,所過之處,落葉聲如雨……
寫詩,畢竟不是羅聘的主業。所以,他將目之所見畫下來。羅聘作鬼圖有多幅,流傳最廣的是八幅一組的《鬼趣圖》。羅聘本人對這幅畫相當喜歡,多年隨身攜帶。他在京城鬻畫期間,參加官員文人士大夫的雅集,展開《鬼趣圖》,人人稱奇。羅聘的名氣,因此隨著鬼影子傳得越來越遠。

青林黃草中黑石一堆,有兩具骷髏站立,是一男一女兩鬼在說話
《鬼趣圖》題材新奇,觀者的心里預期,似乎要驚悚得汗毛直豎了,然而展開后卻有些失望。大鬼小鬼,形象不見得有多奇特,略顯得平淡。當年魯迅先生在琉璃廠第一次見該圖,評價也是如此,認為“哪里有鬼影子,只不過是一些怪人而已嘛”。
有一鬼頭顱巨大,有一鬼四肢超長,有一鬼骨瘦如柴,有眾鬼骷髏林立……充其量稱得上丑,并不會令人受到驚嚇。以我看來,最妙的是,羅聘用墨法,淡淡的氤氳開來,像是黃昏的霧氣,神秘曖昧,制造出陰陰鬼氣。跟米芾的米家山水類似,將一種蒙蒙的氣息,浮于紙面。人物半遮半掩,似遠似近。
羅聘畫鬼,之所以名耀京城,畫功只占一半,另一半,是心思的奇巧。
師徒“代筆情”
揚州八怪,怪在擅長于世俗之外尋求奇趣。他們并非刻意尋求,而是看世界的眼光確實不同常人。羅聘畫鬼,也是受了其師傅金農的影響。在羅聘心中,金農是一盞燈。他的藝術之旅,完全是被金農照亮的。作為晚輩,他對金農的崇拜無以復加。1756年,24歲的羅聘以詩為禮,拜在金農門下。當時金農71歲,漫游天下后棲居揚州。他很喜歡羅聘這個學生,對羅聘的詩文、畫作都予以高度肯定,并將自己畫畫的本領傾囊相授。
金農詩才高,學養深。他的詩句古奧新鮮,一出口,人便稱奇又稱妙。金農本人,是完全不入世俗的。其《題自寫小像》曰:“對鏡濡毫,自寫側身小像,掉頭獨往,免得折腰向人俯仰。”傲岸狂狷,一覽無余。金農好種梅,好養鶴。可以想象一個畫面:揚州城,古樸荒率的西方寺,僧人模樣的金農,著長衫,慢捋著胡須,左側是瘦癯的鶴,坦坦而行,右側則是弟子羅聘,談文論藝,此情此景,不似人間。羅聘跟在金農身邊,日熏夜染,才情日盛。
還有個尷尬的問題不得不談。羅聘為金農代筆,是眾所周知的事。似乎,金農是羅聘的眼——眼光、眼界,而羅聘則是金農的筆。金農心里,多有奇崛的構思和別致的畫面,但礙于筆力不精,常常遺憾。幸好有了羅聘。
據說,金農著名的《設色佛像》,便是羅聘代筆,金農題跋。而署名,當然是金農。另有多幅梅花圖、竹圖,都由羅聘代筆,師生之間,對此毫無芥蒂。羅聘對老師的才情太過景仰,情到了深處,便是無我。此舉還反映出一個問題,文人畫的心思,也就是立意,究竟是排在技巧之上的。乾隆二十四年,金農曾畫了一組《雜畫冊》,其中一幅是《山魅林憩圖》,金農題跋“戲筆為之”,純粹游戲罷了,可卻為羅聘創作《鬼趣圖》埋下了種子。
鬼趣的時代
當時的社會環境,該是《鬼趣圖》誕生的土壤。幾乎在《鬼趣圖》創作同一時期,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刻畢付印。前文提到的才子袁枚劍走偏鋒,著《子不語》大講“怪、力、亂、神”,偏要將這些拿不到臺面上的東西說明白,說透徹。此外,《閱微草堂筆記》《北東園筆錄》《繭窗異草》等大量文人筆記、野史,讓文壇一時間鬼影幢幢。仿佛地獄大門忽然敞開,各方鬼怪齊登場。這種現象似一面鏡子,反射某種社會弊病。人的世界,或病,或陰郁,惶惑,怪異,扭曲,遂有了鬼。
比如1724年,大才子汪景祺終于對科考心灰意冷,想要另辟蹊徑。不幸的是,他投奔了大將軍年羹堯。汪景祺作了六首吹捧年羹堯的詩,極盡阿諛奉承,讓年羹堯心花怒放,收為幕僚。不料,世事輪轉,年羹堯被抄家,那些吹捧的詩文及不當的言論便落到了雍正皇帝手中,結果是,汪景祺被“梟首示眾”,家人被流放或為奴。
1727年,禮部侍郎查嗣庭在獄中自殺,但仍免不了將其頭顱掛起來示眾的下場。其子十六歲以上者判斬刑,十五歲以下者流放,罪名是“語多悖逆,諷刺時事,心懷怨望”。
這些自以為是、亂發言論的酸文人,實在讓雍正皇帝怒不可遏。雍正四年起,各省設立“觀風整俗使”,專門對付知識分子,受懲戒者無數。
嚴密的文網之下,文人噤若寒蟬。那些掛在鬧市區的頭顱,讓很多人嚇破了膽。眾所周知,不論多么嚴苛的制度,都是管得了身,卻管不住心。文人們滿心幽怨情緒無處訴說,壓抑久了,變型發泄。于是鬼神登場,人間的事說不得,說說鬼怪還不行嗎?
中年羅聘,正是飽嘗曲折坎坷的年紀。他從揚州北上京城賣畫,狀況是很頹唐的。行萬里路,他見識了官場的虛偽,體會了人情冷暖,山水花鳥是考慮到市場需求,生計所迫,卻不足以表達胸中意氣。于是,他畫鬼。
鬼趣引共鳴
《鬼趣圖》引來眾多好友的共鳴、附和。1766年,自文人沈大成為《鬼趣圖》寫下第一則題跋起,先后在《鬼趣圖》上留下題跋的竟有70余人,有論鬼神者,有感慨命運者,有諷喻世事者,各種“私人話語”借由鬼的天地發揮出來,成為現象級藝壇盛事。其中奧妙理趣,可寫成長篇論文。現截取幾則如下:
周有聲直言,羅聘不便于描摹人間百態,轉畫鬼趣:“人間變態畫不得,只有鬼趣堪描摹。”楊元錫借此表達了文人的落魄:“我將人鬼相繩準,鬼反嬉游人反窘。痛哭英雄落魄時,可憐被鬼揶揄畫。”
張世進認為,畫鬼即是畫人:“言己托諸鬼,人鬼了不異。”覺羅桂芳借《鬼趣圖》嘲諷人世:“一朝薤露歌聲起,紛紛富貴貧賤皆吾徒。”“田竇升沉朝暮變,翻手覆手常須臾。”諷人終將變成鬼的同類,世事翻云覆雨,富貴貧賤無常。
蔣士銓針對畫中兩鬼場景,一個瘦弱得只剩一副骨架,亦步亦趨地跟在另一個滿身橫肉的鬼后面,他將兩鬼的關系理解成主仆,并將諷刺矛頭直指后面的小鬼,說他“但能依勢得紙錢,鼻涕何妨一尺長。”張問陶題詩也與之類似:“冠狗隨人空跳舞,沐猴無發尚威儀。”
當然,也有人讀不懂《鬼趣圖》,認為羅聘入了邪道。青天白日的畫鬼,不如學學李公麟,畫馬。這當然是對羅聘的誤讀。綜觀羅聘的藝術世界,實在是精彩紛呈。他筆下梅花極盡繁茂,洋洋灑灑。深谷幽蘭筆筆精到,與之對視,像山谷里傳來沁涼的風,直接沐浴了靈魂。十余米長的《三友圖》長卷,構圖極盡活潑,文人意氣滲透在骨子里。
然而,提到羅聘,人們還是會忍不住想起他的《鬼趣圖》。誠然,畫鬼非藝術之大道,只是一個頗有意思的話題。但其衍生出的現實主義價值,卻是其他題材畫作不能比的。

美人著紅衣,向右依靠一男子,男子執蘭媚之,兩情慘戀,行走在冷霧中。有高帽白衣鬼持傘搖扇送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