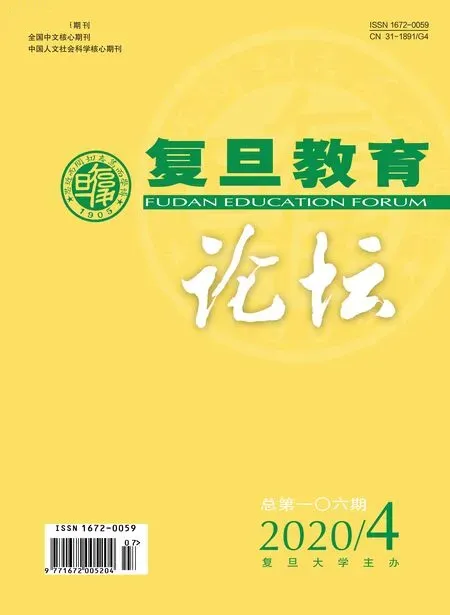秘魯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經(jīng)驗與啟示
岡薩羅·巴切科·雷伊,王語琪
(1.國立圣馬爾科斯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利馬15081;2.浙江大學外國語言文化與國際交流學院,浙江杭州310058)
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相比,秘魯?shù)慕逃J脚c本國的經(jīng)濟和社會特性聯(lián)系更加緊密。大學教育和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息息相關,在考察秘魯教育的同時,需要重點考慮幾個世紀以來,其自然資源出口在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秘魯高等教育的發(fā)展階段
馬丁·特羅(Martin Trow)[1]在一份關于精英教育轉向大眾教育的報告中指出,如何協(xié)調(diào)增長與教育的關系是發(fā)達國家高等教育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zhàn)。這里的增長表現(xiàn)為:(1)學費的增長,(2)學校教師人數(shù)的增長,(3)學生人數(shù)的增長。拉瑪[2]提出了三種面對快速增長的方案:(1)大學自治和共同治理,(2)市場化,(3)國際化。特羅主要針對的是精英教育,而拉瑪主要討論的是大眾教育。后者認為大眾教育分為二元體制(公立/私立)和三元體制(公立/私立/國際),這種劃分方式打破了公立教育的一元壟斷地位。基于上述觀點,本文將秘魯高等教育的發(fā)展進程劃分為精英化、大眾化、國際化三個階段。
16 世紀以來,秘魯在世界上一直扮演著一個重商主義國家的角色[3]。然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秘魯所面對的國際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不盡相同[4],按照“霸權周期”可分為:(1)1495—1650 年,哈布斯堡王朝統(tǒng)治的西班牙;(2)1650—1814 年,法國和英國;(3)1814—1917 年,英國;(4)1917 年至今,美國。之所以提到這一點是因為秘魯?shù)慕逃吲c國際局勢和處于經(jīng)濟中心的國家密切相關。
(一)高等教育精英化階段
通過查閱秘魯總督府的歷史資料,不難發(fā)現(xiàn)當時的社會中存在兩類群體:第一類是以西班牙王室為中心的社會階層,他們?nèi)藬?shù)少,但擁有政治經(jīng)濟實力;第二類是印第安人、黑人和亞洲人,人口眾多,生活貧困。兩者遵循宗主國—殖民地的頂層設計關系。精英階層本身具有的排斥性和階級性,導致殖民時期所推行的大學教育體系符合其自身利益。不過,從1821年秘魯共和國成立到20 世紀60 年代,精英階層的地位不斷被削弱。為了更好地說明精英教育的特點、頂層設計和利益關系,本文將高等教育精英化階段劃分為1555—1820年和1821—1960年兩個階段。
15 世紀西班牙人抵達拉美,對前哥倫布文化產(chǎn)生影響,殖民者開始在新大陸推行符合自身期望的教育體制。通過利用土地和當?shù)厝丝冢麄兿蛭靼嘌劳跏逸斔忘S金和白銀,農(nóng)業(yè)種植及其相伴而生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隸制也成為拉美經(jīng)濟的一部分,天主教信仰成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
秘魯?shù)母叩冉逃趁袷肪o密相連。1551 年,國立圣馬爾科斯大學[5]在“卡洛斯五世和其母胡安娜的諭旨”下建立。這所大學被賦予知識教育和意識形態(tài)建立的雙重功能,幫助西班牙維持了在拉丁美洲的統(tǒng)治秩序。可以說,秘魯?shù)母叩冉逃菑睦R公學(Estudio General de Lima)建立開始的。利馬公學是國立圣馬爾科斯大學初始的名字,其治理模式仿照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貝爾納萊斯指出:“大學的設立與管理殖民地密切相關,王室希望控制殖民地的社會結構,建立大學恰好符合這一要求。殖民戰(zhàn)爭后,王室仿照西班牙的行政組織,把國家、教會、軍隊的官僚體系帶到拉美,奠定了這里的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權力基礎。”[6]
利馬城建立20 年后已成為秘魯總督轄區(qū)的政治和社會中心,這一時期學校的分布充分反映了西班牙王室推行的教育政策。無疑,王室從未將印第安人的教育納入計劃。此時的學校分為三類:(1)初級學校和基礎教育學校(由多明我教會負責,數(shù)量少);(2)預科學校和地方貴族學校;(3)高等教育學校[7]。到西班牙接受教育距離遠、花費高,秘魯當?shù)氐拇髮W可以有效解決殖民初期總督領地官員子女的教育問題。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多明我教會和耶穌教會致力于未來總督領地官員的宗教教育。到1637年,有超過一百名學者投身于“神學、藝術和法律”的教育事業(yè),不少醫(yī)生也參與其中。教會法在法律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教會更是在維持統(tǒng)治秩序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6]。因為貴族不僅代表物質(zhì)上的權力,更要求靈魂上的純粹[8]。
殖民時期尚不存在如今所定義的教育體系。圣馬爾科斯大學初期只設神學系、藝術系、醫(yī)學系和法律系。圣馬爾科斯大學建立后一百多年,在安第斯地區(qū)的瓦曼加和庫斯科才相繼設立了國立圣克里斯多巴大學(1677年)和圣安托尼奧阿巴德大學(1692年)。
殖民者抵達美洲的同時,歐洲經(jīng)歷了政治、經(jīng)濟、社會領域的巨大變革。英法兩國取代哈布斯堡王朝,成為新的霸權中心。印刷機、新教改革和第一批科學聯(lián)合會的成立推動了現(xiàn)代化進程。在意識到科學發(fā)明對經(jīng)濟的重要性后,歐洲新崛起的領導力量,特別是英國,開啟了第一次工業(yè)革命。雖然歐洲發(fā)生了巨變,可是啟蒙思想并未被納入秘魯?shù)拇髮W教育。直到18 世紀末,“開明專制主義的改革措施才在圣卡洛斯寄宿學院和圣費爾南多醫(yī)學院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9]。
經(jīng)歷了三個世紀的殖民統(tǒng)治,秘魯?shù)脑牧铣隹谡嫉搅藝鴥?nèi)生產(chǎn)總值的41.3%[4]。從1821 年獨立到20世紀中葉,秘魯政府不斷地頒布新法案,國家政治形勢動蕩,政權不斷更替,軍閥多次掌權。
1823 年,秘魯頒布了歷史上的第一部政治憲法,精英、軍隊和教會共同開啟了新的篇章。新憲法符合公民的“普遍需要”,對他們“平等對待”(第181 條)。憲法規(guī)定科研機構的研究員能夠“享受終身的資金支持”(第182 條),同時“在各省省會設立大學”(第184條)。這部具有宗教色彩的憲法涉及教育改革,引進了17 和18 世紀的現(xiàn)代化教育成果。作為對形勢的研判,在這部憲法中,政治和知識精英揭露了總督轄區(qū)近三百年來印第安族群缺乏基礎教育的情況。在絕大多數(shù)為文盲的民眾中,推行共和派的自由思想舉步維艱,帶有開明君主色彩的解放思想必須利用學校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傳播機構。盡管教育領域推行了新的法規(guī),共和國成立的前幾十年,不同社會階層的公民能夠享受的教育資源仍然差距很大。
19世紀50年代,政府頒布了一系列關于教育系統(tǒng)化的法令。加爾菲阿斯認為,在1850年教育法和1855年教育法頒布前,秘魯并不存在“高等教育”和“教育體系”的概念[9]。
受到復雜的政治和社會原因影響,如1918年科爾多瓦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墨西哥革命和1917 年的俄國十月革命等,學生逐漸成為大學治理中的主要角色。中產(chǎn)階級學生入學率的提升促使秘魯大學進行改革。改革帶來了雙重影響:一方面,長久以來的治理和科研模式得到了有效的改變,學校開始采納學生的意見,比如推行新的教學法、注重教學實踐、允許學生代表參與大學管理、大學擴招和引進新教師、注重教學自由、教職分級(分主講教師、助教和特級教授三級)等,上述條例均被納入1920 年的教育法;另一方面,改革對秘魯20 世紀的政治動態(tài)也產(chǎn)生了影響,路易斯·阿爾貝托·桑切斯(Luis Alberto Sánchez),勞爾·珀拉斯·巴勒內(nèi)切阿(Raúl Porras Barrenechea),維克多·勞爾·阿亞·德·拉·托雷(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等年輕的知識分子借此契機登上了秘魯?shù)恼挝枧_。
20 世紀初,大學生仍屬于精英階層,入學人數(shù)占總人口的比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大學生占人口總數(shù)的0.05%都不到……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shù)只占初級教育的0.6%。”[9]因為寡頭集團控制教育通道,知識壟斷的問題依舊存在。
1920 年和1933 年的憲法彰顯了統(tǒng)治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思想。雖然天主教仍然占據(jù)主要地位,但1933 年憲法已經(jīng)放寬了對宗教信仰的限制(第5 條),奴隸制也被正式廢除。憲法對教育的治理和財政管理都做出了新的規(guī)定,如初級教育為免費義務教育(第72 條),至少在每省建立一所工業(yè)學院(第76 條),教師被納入公務員編制(第83條),國家有責任對教育進行監(jiān)管(第71條),等等。
1821 年至1960 年,隨著世界經(jīng)濟中心改變,秘魯經(jīng)歷了兩次工業(yè)革命,分別在1794—1876年和1877—1964 年間。薩米納里奧[4]指出,這段時間秘魯?shù)某跫壣a(chǎn)仍然占到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的54.7%,和殖民時期并無顯著差別。
(二)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
漫長的高等教育精英化階段之后,秘魯在1961年邁入了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根據(jù)國家高等教育監(jiān)管局(SUNEDU)2019 年的報告,1821 年秘魯共和國成立時全國有3 所公立大學,1960 年這一數(shù)量達到8 所。新成立的5 所大學分別是國立特魯希略大學、國立阿雷基帕圣奧古斯都大學、國立工程大學、國立拉莫利納農(nóng)業(yè)大學、國立圣路易斯貢薩加大學。私立教育方面,秘魯天主教大學于1917 年在利馬成立,1921 年開始投入科研教學。
影響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因素既包括政府教育國際化的政治決策,也包括一國經(jīng)濟、社會、人口等方面的狀況,特別是其自身的教育發(fā)展階段。
1948 年聯(lián)合國頒布《世界人權宣言》,規(guī)定教育權為人的基本權利之一,該宣言被視為教育擴張需求的起點。溫斯洛普和麥吉夫尼[10]指出,不同于某些歐洲國家(如普魯士從1768年起就推行義務教育),拉美的義務教育屬于新現(xiàn)象。
卡爾多、迪亞斯、巴爾加斯和瑪爾畢加[11]對于20世紀40 年代秘魯?shù)拇蟊娀逃偨Y如下:(1)根據(jù)1940 年人口普查的結果,全國平均受教育率為1.9%;(2)文盲率為48%;(3)農(nóng)村地區(qū)的學校條件艱苦,省會城市的學校條件相對優(yōu)越;(4)教師數(shù)量無法滿足需求,許多教師沒有接受過教學培訓;(5)培養(yǎng)方案沒有一致性,教育政策缺乏連貫性。
在基礎教育擴張的影響下,大學招生率不斷提高。首先,1950—2000 年間整體入學率不斷增長,2001 到2018 年逐步趨于穩(wěn)定;第二,公立學校的增長態(tài)勢與之類似;第三,2000 年起公立學校的入學率緩慢下降,而私立學校入學率增長;第四,1996 年秘魯政府通過鼓勵私人投資教育的法令,推動了私立學校的入學率增長(2000 年起私立學校入學人數(shù)和整體入學人數(shù)間的比率不斷攀升)。
中等教育的擴張潛在地推動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進程。1961 年起,大學開始進行擴招。1960—1965年間,大學入學率增長了113.8%。1970年的在籍學生數(shù)量比1965年增長了68.9%,從30247增長至109230。1961—1970 年間,在秘魯共開設了13 所公立大學和9所私立大學。大學的增多使得學生數(shù)量也相應增長。
1961 年,國立圣馬爾科斯大學校長委派當?shù)氐慕淌诮⒘送ㄗR教育學院,招生委員會要求“學生必須成為大學有機的組成部分”[12],并符合以下條件:掌握高等教育所需要的基本知識和技術知識;具備科研方面的知識儲備和人文底蘊;積極參與學校生活;對專業(yè)有使命感;能認識到國家存在的問題[12]。委員會認為,學生在高中的教育空白(如“心理不成熟”和“知識儲備不足”)是大學教育問題的主要原因。
20世紀60年代末,胡安·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軍政府執(zhí)政時期(1969—1975 年)的教育改革主要在就業(yè)和發(fā)展、社會結構轉型、國家政權穩(wěn)固和獨立自主幾個方面展開[13]。1969 年,秘魯政府頒布了17437 號法案,即秘魯大學組織法,規(guī)定“將大學納入教育體系以保證其協(xié)調(diào)發(fā)展”。
20 世紀90 年代初,秘魯?shù)脑诩髮W生為359461名,比1960 年增長了約12 倍,其中主要是公立大學的人數(shù)上升。2015 年,大學生入學人數(shù)創(chuàng)下新高:1317024 人。其中私立大學的人數(shù)為979896 人,公立大學的人數(shù)為337128人。2010—2015年,私立大學的注冊人數(shù)增長了106.9%。2001—2016年,私立大學入學率上升,公立大學入學率下降,不過后者的在籍學生還是占多數(shù)。[5]此外,政府對于教育的財政投入不斷增加,占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的比例從1990 年的2.2%提高到2017 年的3.8%。2016 年對公立大學的投入占到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的0.5%。在研究員數(shù)量方面,2001 年,每一百萬人中有226 名研究員,但仍低于拉丁美洲國家的平均水平。
職業(yè)生涯競爭力是反映公民融入現(xiàn)代社會程度的重要指數(shù),因此包括秘魯在內(nèi)的許多國家都采用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對學生進行評定。PISA是國際公認的標準化測評,專門測試15 歲中學生的閱讀、數(shù)學和科學能力。
秘魯?shù)哪贻p人在這三方面的得分普遍較低,在世界排名中處于落后水平。閱讀、科學、數(shù)學的不合格率分別為:64.8%,58.5%,63.1%。男生在數(shù)學和科學兩科中分數(shù)較高,女生的閱讀分數(shù)較高。以西班牙語為母語的學生分數(shù)高于以方言為母語的學生分數(shù),私立學校學生的分數(shù)高于公立學校的學生分數(shù),城市學生的分數(shù)高于農(nóng)村地區(qū)的學生分數(shù)。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20 世紀下半葉,城市人口開始增長。人口辦公室的數(shù)據(jù)顯示[14]:1940 年全國總人口為6207967 人,其中城市人口占26.9%;1972 年,總人口為13572072 人,城市人口上升至53.0%。在政治中心利馬,隨著居民對教育和醫(yī)療的需求增加,學校的數(shù)量也不斷增多。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和就業(yè)息息相關。國家數(shù)據(jù)信息研究院(INEI)2007 年和2017 年的數(shù)據(jù)顯示[15],受人口因素影響,2017 年就業(yè)人口約為1650 萬,其中男性中工作的人數(shù)占男性總體的56.3%,女性中工作的人數(shù)占女性總體的55.8%。雖然就業(yè)人口比2007 年增長了16.3%,但男女的就業(yè)比例基本沒有變化。男性適齡勞動力人口中有工作的比例,2007 年為83.0%,2017 年為81.0%,比女性高出約19 個百分點。從就業(yè)方向來看,農(nóng)業(yè)占27.0%,商業(yè)占18.5%,手工機器制造業(yè)占10.2%,其他領域占18.5%。在就業(yè)人口中,占比最高的是雇員(46.4%),其次是個體戶(36.9%)和無薪家庭工人(10.1%)。14 到29 歲之間的就業(yè)人口從2007年的25.4%增長至2017年的38.5%。此外,從2007 年到2017 年以現(xiàn)匯價格計算,平均月薪有明顯增長。
非正規(guī)性是秘魯就業(yè)市場的整體特征。根據(jù)國際勞工組織2014年的報告,非正規(guī)就業(yè)占秘魯整體就業(yè)的69.2%,女性占其中的73.5%。非正規(guī)就業(yè)在農(nóng)業(yè)領域占94.9%,在工業(yè)中占59.9%,在服務業(yè)中占58.9%。在農(nóng)業(yè)以外的其他領域中,非正規(guī)就業(yè)占59.1%,女性占其中的64.6%。在農(nóng)村地區(qū),非正規(guī)就業(yè)占整體就業(yè)的95.7%。在城市地區(qū),非正規(guī)就業(yè)占整體就業(yè)的61.1%。按職業(yè)類型劃分,在個體戶中,非正規(guī)就業(yè)占整體的47.8%;在雇員中,非正規(guī)就業(yè)占到整體的33.4%。
1990 至2014 年,受《華盛頓公約》經(jīng)濟政策的影響,秘魯在政治、經(jīng)濟和教育方面逐步邁入了新階段,大學教育也步入國際化的新階段。
(三)高等教育國際化階段
秘魯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的起點是第30220號大學法(2014),該法案屬于教育科研領域的經(jīng)典法案。費爾利認為,國際化是指“教師、學生與科研機構的跨國流動,通過遠程網(wǎng)絡教學手段實現(xiàn)跨境教育,以及科研的國際化。”[16]
秘魯推行教育國際化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背景主要包括:(1)城市化和宗教改革的深入;(2)國家積極爭取加入經(jīng)濟發(fā)展合作組織(OECD);(3)重視大學管理績效的國際大趨勢;(4)以市場為主導的經(jīng)濟發(fā)展。
2017 年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秘魯?shù)娜珖丝谠诓粩嘞虺鞘芯奂H缃瘢?9.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5],使得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成為可能。近70 年來的人口學跟蹤研究發(fā)現(xiàn),宗教信仰是影響殖民時期以來秘魯人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2017年,12歲以上的秘魯人有76%信仰天主教[15]。大多數(shù)秘魯人有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他們生活的必需[17]。
秘魯政府從21 世紀初一直尋求加入OECD。OECD 成員國的國民生產(chǎn)總值占到了全球的66%,秘魯戰(zhàn)略規(guī)劃中心(CEPLAN)對此有著充分的認識。然而,根據(jù)OECD 的規(guī)定[18],如果秘魯想成為其成員,必須在以下三方面做出改變:(1)提升教育質(zhì)量(秘魯在PISA 測評中通常處于倒數(shù)第一或第二的位置);(2)解決非正規(guī)就業(yè)的問題;(3)對居民的社會需求給予必要的財政保障(在秘魯有近1000萬人無法使用自來水和排水系統(tǒng))[19]。
通過比較OECD 成員國的最新數(shù)據(jù)不難發(fā)現(xiàn),加入該組織意味著傳統(tǒng)經(jīng)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未來,秘魯將會建立一種新的依賴于自然資源(銀、鳥糞、磷礦、硝石、糖、銅、金、石油等)的發(fā)展模式,根據(jù)各個國家不同的經(jīng)濟需求確定出口政策。若能通過不斷的出口來推動改革,秘魯對世界商品與服務生產(chǎn)的貢獻度便可以逐步增加。2015 年,秘魯對世界商品與服務生產(chǎn)的貢獻度只有0.26%,低于拉美的平均水平。另外,還可以改善收入貧富分配不均的問題,2000—2015年秘魯?shù)幕嵯禂?shù)為0.48[20]。
新的大學法對高等教育學術和行政的影響效果立竿見影。2016 年起,各類國際組織的測評結果開始在秘魯傳播,這使比較各個大學并對其排名成為可能。《美洲經(jīng)濟研究》(2019)的數(shù)據(jù)顯示,2016 至2018年參與測評的秘魯大學具有以下特征:(1)數(shù)量增加,從2016 年的20 所增長至2017 年的25 所和2018 年的26 所;(2)參評大學包含公立大學、公私合營大學和私立大學三類;(3)秘魯天主教大學、卡耶塔諾埃-雷迪亞大學、太平洋大學、國立圣馬爾科斯大學、國立工程大學連續(xù)三年排名前五,這五所學校均為公立和合辦類型的院校;(4)參評高校各具特色,如秘魯天主教大學以就業(yè)情況取勝,卡耶塔諾埃-雷迪亞大學科研創(chuàng)新突出,太平洋大學教學質(zhì)量高,秘魯應用科技大學國際化水平高,拉莫里納農(nóng)業(yè)大學基礎設施齊全。[21]
在國家數(shù)據(jù)信息院2014 年的大學質(zhì)量報告中,60.5%的公立學校學生和62.3%的私立學校學生認為“掌握了該學科的相關知識”;在“外語的讀寫說”一項中,24.3%的公立學校學生和40.5%的私立學校學生評價為“良好”。在基礎設施方面,51.6%的公立學校學生對“教室”一項給出了“良好”的評價;56.0%的私立大學學生對“醫(yī)療設施”評價“良好”;滿意率較低的有“科學實驗室”,只有22.5%的公立大學學生和39%的私立大學學生評價為“良好”。54.9%的公立大學學生和59.3%的私立學校學生對教師評價為“良好”。在“知識內(nèi)容是否與時俱進”這項中,44.8%的公立大學學生和59.3%的私立大學學生給出了“良好”的評價。[22]
2016 年,秘魯國家高等教育監(jiān)管局(SUNEDU)發(fā)布了關于本科教學現(xiàn)狀的檢視報告。報告以“高等教育-經(jīng)濟增長”為理論框架,從三條指標進行測評:(1)人力資本,(2)創(chuàng)新性,(3)民主價值的踐行和學校建設。在大學服務質(zhì)量方面,報告分為獨創(chuàng)性、持續(xù)性、適宜性、轉型、資源的有效利用五個方面。在32 所學校中,排名前五名的分別是:秘魯天主教大學(100.0分)、卡耶塔諾埃-雷迪亞大學(69.1 分)、國立圣馬爾科斯大學(54.5分)、拉莫利納農(nóng)業(yè)大學(38.4分)和國立工程大學(26.0分)。[23]
市場主導的經(jīng)濟活動也是高等教育國際化催化因素之一。有競爭力的經(jīng)濟體往往能調(diào)動經(jīng)濟資源,將培養(yǎng)科學技術的人力資本放在首要位置[24]。PISA等國際測試體現(xiàn)了15歲青少年數(shù)學、科學和通信的能力。這三種技能是1965年以來信息革命的根本,即曼里克[25]所說的信息資本主義,或“電腦和網(wǎng)絡”的資本主義。
二、秘魯高等教育發(fā)展的制約因素
雖然近幾十年政治格局風云變幻,科技日新月異,新的政策與時俱進,但秘魯仍舊延續(xù)了過往的一些政策。在回顧了近500 年的高等教育變遷后,我們可以總結出制約秘魯高等教育發(fā)展的三個因素:
(一)市場經(jīng)濟特性
秘魯?shù)靥幚来箨懳髂希瑩碛袃?yōu)越的地理環(huán)境。安第斯山脈和洪堡洋流使得這里氣候多樣,物種豐富。秘魯是世界上礦產(chǎn)最豐富的七個區(qū)域之一,三大自然區(qū)之一的安第斯山脈埋藏著大量礦石,使得秘魯?shù)慕?jīng)濟發(fā)展主要依賴豐富多樣的自然資源。
如今發(fā)達國家普遍推行在自然資源創(chuàng)造價值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更多的附加值,但秘魯尚難以做到這一點。只有在市場的驅(qū)動或是國家政策的推動下,生產(chǎn)要素(包括人力資本)的水平才能提高。由于秘魯經(jīng)濟主要依賴自然資源的出口,國際市場的價格水平構成了重要因素,決定了企業(yè)家對經(jīng)濟的投入以及原材料生產(chǎn)的情況。
(二)宗教信仰影響
殖民初期時西班牙人推行天主教,對印第安人進行思想教化和社會隔離。正如上文所述,雖然自發(fā)現(xiàn)新大陸500 年來不斷有非洲裔和亞洲裔的新移民到來,但是天主教如今在秘魯仍然處于主導地位。
隨著社會科學的發(fā)展,宗教信仰被視作阻礙社會活動的誘因。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地圖作為有效的思維工具,能夠確定秘魯在宗教信仰坐標系中的位置,讓國民更加適應激烈的競爭。文化地圖[26]考察公民融入高競爭性環(huán)境的情況,以“宗教-理性”和“群體-個人”兩個維度將公民的信仰狀況劃分為四種類型:(1)宗教-群體,(2)宗教-個人,(3)理性-群體,(4)理性-個人。生活質(zhì)量高的居民一般屬于(3)和(4)。對于理性的信仰獨立于群體-個人存在。換句話講,如果國家推行的教育政策是理性-科學的,國民的生活質(zhì)量相應也會比較高。但大多數(shù)秘魯居民屬于類型(1),因此他們的生活質(zhì)量并不高。
(三)非正規(guī)就業(yè)市場
在20 世紀70 年代學者們研究非洲國家時,非正規(guī)就業(yè)這一命題就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它是很多國家共有的問題。根據(jù)秘魯國家統(tǒng)計局的資料[27],殖民時期人民飽受歧視和排擠,長期徘徊在溫飽線上,非正規(guī)就業(yè)與這段歷史不無聯(lián)系。
生產(chǎn)結構導致了非正規(guī)經(jīng)濟的出現(xiàn)。秘魯在國際市場長期扮演著自然資源提供者的角色。從殖民時期至今,礦產(chǎn)、鳥糞、硝石、魚骨粉一直是出口的主要收入來源。大部分勞動力人口集中在農(nóng)業(yè)領域,城市的勞動力人口集中在商業(yè)領域,上述兩個領域的非正規(guī)就業(yè)比例近些年都有所上升。
非正規(guī)就業(yè)的問題和高等教育聯(lián)系密切,職業(yè)規(guī)劃和職業(yè)回報率都與其息息相關,這在公立大學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大學和勞動市場之間的關系不健全導致秘魯?shù)姆钦?guī)就業(yè)率居高不下。
三、秘魯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啟示
也許我們無法用成功一詞定義秘魯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但就像政治學界將拉美當作政治理論的實驗場一樣,秘魯教育的發(fā)展歷程或許能為中國的高等教育發(fā)展提供經(jīng)驗和借鑒,為未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提供正反兩方面的啟示。
(一)科學教育和科技人才的重要性
在出口原材料上增加附加值,不僅意味著經(jīng)濟增長模式的改變,更意味著大學必須培養(yǎng)出合格的專業(yè)人才和新知識的生產(chǎn)者。盡管近些年秘魯全職研究員的數(shù)量在不斷上升,但人力資本在世界上仍然處于落后的水平。圣馬爾科斯大學的報告明確指出,這種情況是不利于生產(chǎn)發(fā)展的。科學家和研究員的培養(yǎng)必須從早期抓起,盡管大學內(nèi)部積極尋求解決辦法,但初級教育始終存在投入低的問題。
20 世紀50 年代,教育擴張和城市化進程相伴而生。幾十年來,秘魯提高入學率的目標已經(jīng)實現(xiàn),學生的復讀率也降低了。如果以PISA測試為衡量標準,秘魯學生的科學知識水平還有待提高。當下的關鍵是如何在教學內(nèi)容中增加科學知識,為培養(yǎng)科研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礎。
(二)健全教育體系的缺失
1950 年的中小學教育擴招拉開了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序幕。幾個世紀以來,能夠接受中小學和大學教育的人在秘魯一直是少數(shù),殖民地的屬性導致占人口多數(shù)的印第安人無法享受系統(tǒng)化的教育。秘魯國內(nèi)已經(jīng)達成共識,各個教育階段(學前、初級、中等和高等)的學業(yè)規(guī)劃和學習內(nèi)容缺乏連貫性,這對于老師們來說構成了巨大的挑戰(zhàn)。
秘魯?shù)奈幕哂卸鄻有缘奶卣鳌5靥幧絽^(qū)和熱帶雨林的不同文化群體建立聯(lián)系的機制缺乏是導致教育體系不健全的另一原因,即便是西班牙語也可以因為所處的地域不同而相互之間有很大的區(qū)別。另外,專門講授當?shù)匚幕慕處熞泊嬖跀?shù)量不足的問題。
教育體系的不健全還體現(xiàn)在某些專業(yè)的就業(yè)率過低,有些職業(yè)甚至沒有設立相關的專業(yè)進行人才培養(yǎng)。
(三)高等教育私有化的風險
近20 年秘魯私立大學爆炸式的增長體現(xiàn)了私人資本對于長期投資的偏愛。對于私立高等教育的需求體現(xiàn)了居民對于教育服務的需要。各地區(qū)人均生活水平的差異清楚地說明了為何私人資本愿意在能收到穩(wěn)定經(jīng)濟回報的地區(qū)進行投資。
為了保證教育領域私人投資的安全,需要政府進行引導。20世紀90年代起,政府頒布了符合本國經(jīng)濟框架的投資法令,在教育領域進行高風險投資的投資者可以獲得長期貸款和減稅等經(jīng)濟補償。
為了讓教育覆蓋盡可能多的家庭,大學的收費高低不等。年輕人可以選擇公立院校或私立院校。數(shù)據(jù)顯示,選擇私立學校的學生近些年不斷增多。
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教育發(fā)展不平衡,地方缺乏提供良好教育的高等學府是導致內(nèi)陸地區(qū)人口分布不均的原因之一,在秘魯有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口聚集在首都利馬。雖然私人的投資增長了,但投資分布不均的問題依然存在。各地不同的投資條件(如回報率)也導致教育領域的私人資本主要集中在能夠保證投資回報率的地區(qū)。
無論是在科學教育和教育體系的健全程度方面,還是在教育私有化方面,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的秘魯表現(xiàn)都不盡如人意。鑒往知來,這或許能為中國的高等教育發(fā)展提供一些啟示。
致謝
特別感謝熊慶年教授在作者岡薩羅·巴切科·雷伊于復旦大學訪學期間所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