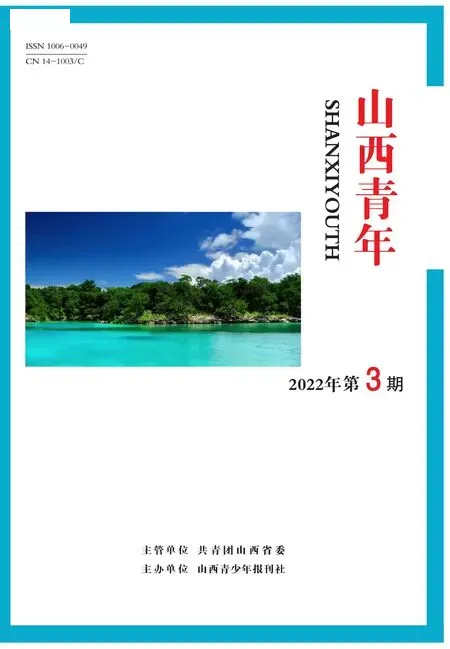歷史學在旅游管理教學中的價值及應用
高小紅
松原職業技術學院,吉林 松原 138000
隨著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及社會和諧穩定發展,人民經濟收入水平躍上了新臺階,人們已經不再滿足于簡單、表象的游山玩水、觀花賞景,而是迫切希望通過旅游實現感知、了解、體察人類文化。歷史文化、現代文化、民俗文化、道德倫理文化已成為旅游文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漠視文化的旅游只是身體在行走,為此,旅游管理從業者應提升歷史文化素養,并給游客提供良好的歷史文化傳導。旅游行業的蓬勃發展對于從業者的要求無形中在提升,而歷史學是旅游管理專業必不可少的一門課程,在旅游管理專業教學中有著重要價值。
一、旅游管理專業的相關介紹
旅游管理專業是隨著我國旅游經濟的發展、旅游產業的發育而建立的一個新型學科。在我國,這門學科的產生只有二十年的時間,但已成為管理學科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學科部門。旅游管理已與工商管理并列,是管理學下的一級學科。旅游管理專業主要是培養適應新形勢旅游企事業單位需要的一線服務與管理類專門人才,具有旅游管理專業知識,較好的思想道德品質和綜合素質,具備較強的綜合職業能力和發展基礎,能在各級旅游行政管理部門、旅游企事業單位從事旅游管理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1]。旅游管理專業的學習內容是極其龐雜的,它既需要學生對于旅游文化具有學習和理解能力,又需要學生學習旅游法規,了解旅游經濟,并能對旅游景區規劃提出一定的指導意義。總體而言,旅游管理專業對學生各方面能力的要求都相對嚴格,學生學習到的知識也較為全面。
二、歷史學與旅游管理專業的聯系
歷史既是溝通古與今的橋梁,又是連接中國與西方的媒介。在旅游管理的教學過程中,歷史學是必不可少的一門學科。就中國史而言,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它的歷史是從遠古時期就開始的,它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為子孫后代留下了一系列優秀文化、精美建筑和山河遺跡,而這些優秀的旅游文化資源之所以受人喜歡,不僅僅是靠后天的加工和宣傳,更是靠自身所具有的歷史文化底蘊,在經過歷史長河的洗滌后,它們自身所具有的獨特魅力,既能吸引人也能使人受到啟發,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們的情感共鳴。而這些歷史發展軌跡是需要人們去學習,去了解的,人們只有在了解歷史的過程中,才能感受到歷史文化、歷史遺跡所具有的特殊魅力和教育意義。歷史的學習對于中西方旅游管理專業的重要意義都是相通的,歷史是根基,只有根基牢固了,旅游業的發展才能越來越好,人們在旅游過程中才能收獲滿滿[2]。游客在旅游中不再是消費旅游產品時“上車就睡覺,下車就拍照”,而有更高的期待,希望通過旅游體驗找尋到詩和遠方,尋味到歷史的氣息,了解到景點的“前世今生”。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旅游管理者的職業素養,“要想給別人一滴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為此,旅游管理者歷史文化知識底蘊夯實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未來從業者的職業素養水平。
三、歷史學在旅游管理專業教學中的重要意義
(一)歷史學對旅游管理專業學生的學習具有促進作用
歷史是在社會的一步步發展中形成的,它具有社會發展過程中包含的一切特點。歷史中既有歷史事件,又有歷史人物,同時歷史人物在活動中所能體現出來的感情又容易引起人的情感共鳴。我國具有五千年的歷史文化,而歷史課程已經成為基礎教育中的通識性課程,具有極其廣泛的影響力和生命力,歷史更具有十分鞏固的群眾基礎,學生們在旅游管理專業學習之前,都已經或多或少地接受過歷史教育與歷史文化熏陶,具有一定的歷史常識和基礎歷史文化,這樣一來可以幫助學生們在旅游管理專業學習中繼續接受歷史教育而言具有一定的理論奠定作用。學生們可以進一步學習各類旅游文化、中國歷史常識、旅游史等課程,不僅可以有效豐富學生們的歷史人文素養以及旅游管理專業知識,同時還可以幫助學生們在今后的職業生涯中不斷促進導游服務技能水平的專業性得到提升,所以在旅游管理專業教學中融入歷史學,對于學生而言博古通今可極大促進其專業課的學習。
(二)歷史文化有利于培養學生的認知
“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雖然已成歷史,但歷史反映著過去的事物,學史用史可以讓學生從歷史中汲取養分,反觀歷史,或有成功典范,或有失敗教訓,這些可以幫助學生成長。典范人物或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勵后人,學習其智慧,發揚其精神,失敗教訓也可以警示后人,避免重蹈覆轍。每一段歷史都是一筆珍貴的財富,我們都要傳承下去,而旅游管理就是傳播歷史的一種渠道,可以通過這種方式提高學生的認知水平,客觀的評判歷史,在現實生活中真正以史為鑒。
(三)崗位(群)所需必備知識
在旅游管理專業中很多學生都不重視歷史這門課程,然而在今后的工作中才會倍感書到用時方恨少。從市場需求來看,旅游專業管理學生未來如果對口就業就面向旅游公司或旅游局或景區,負責旅游管理或旅游產品的開發與推廣或導游,但無論何種工作性質歷史學都是其必備的知識與素養。因為,無論是旅游管理或旅游產品的開發與推廣,還是導游都需要一定的歷史學知識,在開發國際國內旅游線路時要研究歷史,在向旅客推介旅游路線時要闡述其人文地理歷史風土人情以吸引旅客,在導游解說中將景點的古今解說清楚,這不是單單背誦千篇一律的解說詞就可以的,要做到游刃有余就要博古通今。總之,一個出色的旅游管理者除了有夯實的專業知識外,同樣需要一定的歷史學知識儲備,這是崗位(群)所需必備知識,是立足就業市場,滿足崗位(群)的必然要求。
四、歷史學在旅游管理專業教學中的實際運用
(一)旅游文化教學中運用歷史學的教學策略
在有關旅游文化的教學過程中,對與之相關的歷史文化的學習是必不可少的。旅游與文化是相輔相成的,如果將其關系比作一棵大樹,則旅游是樹干,文化是其根,只有把根扎緊,樹干才能粗壯。歷史文化作為旅游的精髓和靈魂,通過旅游管理者、導游向游客傳輸,游客的功能則是解讀與發展,通過旅游管理者、導游聲情并茂地講解,游客會有靈魂上的呼應。把歷史文化運用于旅游管理教學中可加速文化的傳播與發展,更有利于文化的保護和傳承。例如在介紹木蘭圍場時,教師可以穿插歷史文化知識對木蘭圍場的初建、發展以及現今情況進行介紹。木蘭圍場始建于公元1681年,位于現今河北省東北部,圍場草原廣袤、山丘連綿、冰水交融、野生動物繁多,除了得天獨厚的生態資源外,更因該地是歷史上的戰略要地,這里才成為皇家獵苑,這也凸顯了康熙帝的戰略眼光。教師可結合地圖分析為何該地是戰略要地,并結合網絡教學播放木蘭圍場的宣傳片,讓學生領略塞罕壩國家森林公園、御道口草原森林風景區和紅松洼國家自然保護區的風采。又如西安是著名的四大古都之一,歷史文化底蘊深厚,游西安,必要知曉西安的歷史沿革,才能更好地了解西安、認知西安、走進西安。西安有著幾千年的悠久歷史,1981年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確定為“世界歷史名城”,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大雁塔、小雁塔、唐長安城大明宮遺址、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興教寺塔馳名中外。教師可布置學生自行搜集與西安有關的資料,寫一寫西安的歷史沿革并擬一份西安旅游攻略,提升歷史旅游文化知識。
(二)旅游管理教學中運用歷史學的教學策略
在學習有關旅游管理的知識時,教師可以通過相應歷史的講授使學生認識到歷史學對旅游管理的重要作用。例如教師在講授知識的過程中可以適時穿插“曲突徒薪”“子賤放權”的小故事,使學生認識到歷史故事中所蘊含的管理知識,并將其靈活運用到旅游管理中。又比如以紅色旅游為代表的歷史文化旅游是傳統教育與現代旅游有機結合的典型產品,是凸顯中國特色旅游經濟文化的主要方式。傳統革命時代賦予了我國豐富的紅色旅游資源,開發紅色旅游資源,實現旅游經濟持續發展勢在必行。在資源開發中可以結合當地豐富的紅色史實案例,并不斷整合與修復,以歌舞等多種形式為載體,升級旅游產品類型,向游客再現歷史革命時期的紅色風情,使得游客能夠在感官上更加深入紅色精神并參與其中。東北抗聯英勇事跡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吉林省在旅游管理中就可以著力挖掘、整合紅色資源,打造紅色之旅的旅游文化品牌。東北抗聯蒿子湖密營又稱“楊靖宇密營”是很好的紅色旅游資源,但如果不懂歷史,不懂得這些資源的歷史意義,那就沒有開發這些資源的眼界,因此,歷史學無論是在旅游資源的開發,還是在旅游管理中都有助于從業者樹立大格局。
(三)景區規劃學習中運用歷史學的教學策略
歷史學對于旅游景區規劃也是具有實用意義的。旅游景區的規劃不僅要便于景區規劃發展和游人賞鑒,更要符合其表達的歷史主體和存在的歷史氛圍。例如在對承德避暑山莊進行介紹時,運用歷史學知識學生不僅能學習到其發展過程,又能對其場景布局和園林規劃有大致了解。根據教師所講授的歷史學知識,學生還可以了解到自承德避暑山莊初建到擴建成現今規模的過程中,隨著朝代的不斷更替,它都有何種變化,而這種變化與當時所處的歷史文化背景又有何種聯系。這不僅使學生學習了有關承德避暑山莊的相關知識,還使學生了解到景區規劃與歷史文化之間的重要聯系。總之,景區的規劃不是隨心所欲的“臨時發揮”,而要結合景區的歷史、人文、自然景觀等綜合布局,既要充分挖掘其歷史價值,又要突出特色。
(四)旅游管理專業教學中融入歷史學的教學建議
在知識背景與學科體系角度上我們可以顯然看到,旅游管理學與歷史學均屬于人文社會科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實際研究對象都是在整個社會體系中所涵蓋的人物、活動、事件等要素,甚至從遠古時代到現代中都有所涉及,學生們在學習這兩大學科過程中,都需要合理協調配合、對多學科知識點進行綜合性運用,在深入學習與研究中解決學科實際問題。而在實際教學運用歷史學的過程中,需要注意如下幾點問題:
1.加強歷史通識教育
在學習與研究中國歷史學過程中,要讓學生們加強對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脈絡之間聯系的認識與理解,對今后職業發展具有很大的幫助。比如在今后導游工作中帶領游客們參觀長平古戰場紀念館過程中,可以在其中結合相關歷史進行講解,如長平之戰的導火線、爆發點、事后結局以及對秦國統一六國的影響等,在此之間不斷豐富游客們對長平之戰的了解與認識,加深游客們的旅游印象、開闊旅游視野,提高游客們對先秦歷史的認識。事實上,只有旅游管理專業的學生們能夠在歷史通識教育中掌握這些歷史的相關知識、背景,才能夠熟練、有條不紊地在今后帶團過程中回答游客們的提問,真正促進自身導游服務水平得到提升,使游客們在旅游過程中感受到歷史濃郁的人文性特征。
2.開設歷史第二課堂
事實上在旅游管理專業中融入歷史學課程,也并非純粹的歷史理論教學,更多需要的是實踐應用歷史。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有必要讓學生們從旅游經典的實踐環境中進行學習,最好能夠在歷史教師與專業教師的帶領下組織學生們模擬導游帶團活動,在這其中讓學生們分為游客與導游等兩個身份,學生們可以輪流來當導游,另外一部分學生當游客,游客負責對導游的導游服務水平進行打分,在實踐模擬中統計學生們的得分狀況,可以將這些評分一并納入學科成績中。這就是歷史第二課堂的開設,在這樣的實踐環境構建中不僅可以有效提高學生們的導游專業水平,還可以在此之間檢驗學生們的歷史文化知識學習狀況。另外還要能夠定期邀請校外旅游專業專家、從業者入校進行指導學習,能夠針對旅游管理專業的學生在行業發展與職業生涯規劃中進行必要的指導性教育,這樣一來還可以進一步提升學生們對歷史學課程的重視程度,提高學生們學習歷史文化的信心與決心。
3.合理編寫校本教材
在旅游管理專業學習中開展歷史學課程,還要能夠重視校本教材的積極作用。由于該專業在不同地區中存在著不同的教學對象與教材內容,因此在專業教材編寫中最好能夠結合本地歷史文化、民俗風情進行編寫,可以組織學生們利用假期時間參觀本地歷史景觀以及相關紀念館等,由教師的組織與安排下,通過制定提綱、搜集材料、組織編寫內容等過程,完善校本教材,為旅游管理專業的學生提供更符合學情狀況的教材內容,也可以在這其中鍛煉學生們的歷史學習水平以及綜合能力,真正促進歷史學在旅游管理專業中的滲透程度得到提升。
綜上所述,歷史學在旅游管理專業的教學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本文從對旅游管理專業的相關介紹開始,分析了歷史學與旅游管理專業的重要聯系,并通過對歷史學在旅游管理專業教學中的實際運用進行舉例,展現了歷史學在旅游文化、旅游管理、旅游景區規劃中的部分作用,后續通過進一步總結明確了歷史學在旅游管理專業教學中對學生學習的促進作用和對教師教學工作的推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