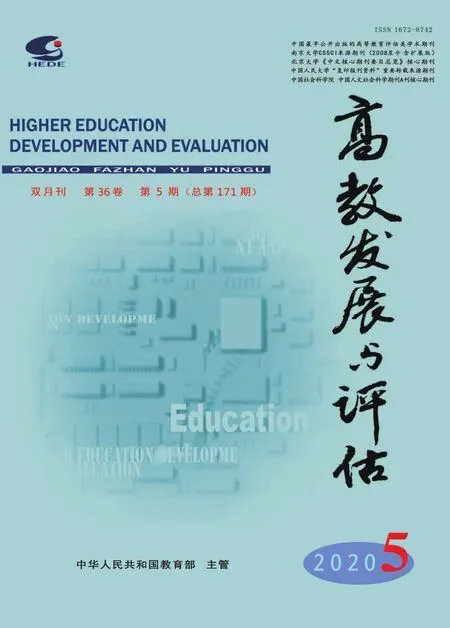美國高校選修制度的緣起、價值與啟示
單媛媛,鄭長龍
(1.東北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吉林 長春 130024;2.東北師范大學 化學教育研究所,吉林 長春 130024)
美國大學的現代化轉折,起始于查爾斯·艾略特(Charles WEliot)就任校長后在哈佛大學推行的自由選修制,這段時期的發展歷程蘊涵著當時許多教育革新的內容,大至現代教育理念的傳播、現代課程論和學生觀的轉型,小到教學活動的組織、學習方式的變化等。從歷史的角度考察這一發展過程并發掘其背后隱含的教育和社會意義,可以使我們更好地洞察美國大學迅速發展的真諦,對選修制進行更全面的認識,也有助于我們反思當代高校實行的選修制,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發展提供經驗啟示。
一、選修制度的緣起
美國歷史學家亨利·康馬杰(Henry Commager)曾寫道:“19世紀90年代的十年是美國歷史的分水嶺,處于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美國’和一個‘以城市工業為主的美國’之間的分水嶺。”[1]19世紀中期,美國面對著招生人數急劇下降和學生學業成績下降的危機,哈佛大學的查爾斯·艾略特堅持選修制度的引入和發展,提供了一個及時的解決方案。許多相關研究都表明,在高等教育中引入選修制是美國高等教育最重大的轉變之一[2-5]。
當艾略特于1869年就職時,選修制度對大學來說并不是一個新概念,艾略特的叔叔喬治·蒂克諾(George Ticknor)在1825年引入了選修課的想法[6-8]。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也是選修制度的主要支持者,批評課程的僵化[9]。艾略特受蒂克諾和愛默生的啟發,決定對早期的選修制度進行更徹底的改革,給予學生選擇課程的自由,給予學生實現學術抱負的機會[10]。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校長丹尼爾·吉爾曼(Daniel C. Gilman)的支持下,他提出了選修系統的觀點,1869年,艾略特在其就職演說中提出以下思想[11]。
人們的文明可以從其各種工具中推斷出來。石斧和機械車間之間有數千年的歷史。隨著工具的增加,每個工具都更加巧妙地適應了自身專屬的價值。那些建立了國家的人也是一樣,對于個人,專注于自己特有能力的充分發展,是唯一的最重要的事。但是對于國家來說,知識產品需要多樣性而不是統一性。這些原則是過去二十年來在學院逐步發展的選修課程體系的理由。
選修制度能夠促進獎學金制度發展,因為它能自由發揮自然的偏好和先天的才能,能使學生對選修的工作產生熱情,使教授免于面對一群被迫接受任務的學生。運用小型而生動的課堂擴大教學范圍,從而代替給許多班級多次重復的上課。因此,建議學院堅持不懈地努力建立、改進和擴展選修制度。
二、選修制度的價值
盡管選修制度對美國高等教育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并存在于今天的學院和大學里,但在艾略特最初提出時卻遭到了教派、校長和教職員工的反對,其發展緩慢。1869年至1909年,作為哈佛大學校長,他和同事提倡通過州立法提供選修課程的制度,那時并沒有意識到這些對于今后高等教育制度產生了重大而廣泛的影響。
(一)順應不同學生群體和社會需求
19世紀前半期,美國大學的發展落后于時代,哈佛大學依然是一個地方性學校,課程設置傳統,學習方式機械重復,1807年和1819年,哈佛大學先后發生多次學生騷亂,最嚴重的是1823年,學生騷亂導致臨近畢業的學生超過一半被開除。在北卡羅來納州大學,總共230名學生,1851年就發生了282次違規行為。19世紀中期,人們對這種僵化的形式主義教育以及融入其中的宗派主義和社會排外性的批評與日俱增。1850年,馬薩諸塞州議會指責哈佛大學沒有“提供實用教學和給予學生專業化學習自由”[12]。盡管教派資金短缺,但許多較小的中西部和東北部的大學仍然堅持傳統課程的教派中心,因為他們在重建時期面臨著全國范圍的巨大變化[13]。
艾略特和幾位富有洞察力的教授預測,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趨勢,并開始進行自身的變革。如何留住教師和學生,緩解內戰后的學生保留率和入學率大幅下降的問題,這些是為防止大學關閉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隨著國家經濟的復蘇,白手起家的人越來越多,人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下降。那些仍然重視并且能夠負擔得起高等教育的富裕家庭把他們的子女送往歐洲學習,因為美國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因此,在1862年《莫里爾法案》通過后,明確了高等教育需要競爭性和實用性的課程。到了1885年,哈佛大學的入學人數增加了66.4%,只排在康奈爾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之后,到90年代增加了88.8%,僅位居布朗大學之后[14]32。
雖然選修制度最初是針對精英學生開發的,但隨著學生群體變得更加多樣化,選修制度產生了更多其他有益的影響。19世紀,女性和非裔美國學生進入大學,促使大學課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總體而言,當時的大學都多次嘗試避免男女同校問題,直至不斷增加的壓力迫使他們作出妥協。為了應對波士頓婦女教育協會等女性團體不斷給出的壓力,哈佛大學在1874年開始接受女生,由哈佛專門為女性提供考試,并且由哈佛大學的教授進行評分。正如1985年所羅門(Solomon)所說的,“1870年至1915年之間,在各個學校,大學課程都發生了巨大而漸進的改變。選修制度成為了大學滿足學生不同學術需求的手段[15]。
根據所羅門的研究,“大學總人口中女性比例從1870年的21.0%上升到1910年的39.6%再到1920年的47.3%”。隨著學生人口統計的快速變化,選修制度為大學提供了一種手段,以適應了新的多樣化學生群體的課程。
(二)有效推進美國大學課程的改革
選修課程的發展,不僅有效緩解了內戰后幾十年內保留率和入學率大幅下降的問題,而且改善了學院和大學運作等許多其他方面的問題[16]。首先,選修制使所有科目均具有同等重要價值這一課程觀念贏得了普遍認同,從根本上動搖了以往古典人文學科獨霸高校課程的思想基礎,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現代語言等知識領域在高校課程中取得合法地位提供了理論支持。其次,選修制度促進了學科專門化的快速發展,強調由專門化的院系來設置課程。傳統學院的教授往往要教多門課程,他們不需要也不向往專門化。在艾略特任哈佛大學校長的那個時代,越來越多的學院教授傾向于成為學科專家,其課程歸屬于專門化的學系[17]。那時,自由與民主已成為美國大學的核心特色。選修制度推倒了規定課程封閉下的思想圍墻,使教師和學生的思想得到了徹底解放,它一方面符合美國社會自由、民主的價值取向,一方面順應了工業化的時代需要,從而開啟了美國高等教育的新時代。
雖然選修制度的引入并不是大學重新取得成功的唯一原因,但它促進了大學改革,創建了作為大學附屬單位的學院,增加了課程數量和類型,促進了學科、師資和獎學金的多樣化,推動了研究生學習的發展,為不同學生群體提供了實用和職業學習的機會[18]。從整體上看,選修制重塑了高等教育機構,打破了私立大學對經典課程的嚴格規定,轉變為允許課程多樣性、增強了學生權力,使得高等教育蓬勃發展[19]。
(三)兼顧個人與國家發展的價值追求
艾略特在1869年的就職演說凸顯了選修制度對于個人和國家兩個層面的意義,既關注個人特有能力發展,也著眼國家需求的多樣性。霍金斯(Hawkins)指出,艾略特的首要關注點是學生發展對未來社會的貢獻,但是選修制度對學校也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當美國在尋求“美國大學”的定義時,艾略特把目光投向了“美國環境作為大學成長的塑造力量”上。耶魯大學,康奈爾大學和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等大學在效仿德國模式之后努力構建自己的模式,同時保持其文化,使得其在使命和身份上發生了重大沖突[20]。
隨著選修制度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學生在選擇新課程時有機會作出更多的決策。艾略特指出,他們的偏好從希臘語或拉丁語轉向更專業的訓練,如“法語、德語、化學、物理和生物”以及“邏輯、倫理、歷史、政治經濟學,以及在議論文寫作和口語中使用英語”。這些課程并不取代或降低其他要求,而是作為滿足學位要求的選項而增加的,并且是為“認真和有抱負的學生,對某些研究有強烈興趣的學生”設計的。因此,選修制度為高等教育課程提供了一個機制,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學生需求和國家對勞動力的需求。
雖然提供多樣化的課程和學習內容是非常昂貴的,但選修課程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繼續為學生及其導師提供課程選擇的靈活性,從而提升學生畢業后適應勞動力需求的能力[21-22]。在目前的高等教育課程中,選修課程仍被認為是使學生和導師完成學業的最有效和必要的途徑。從艾略特首次宣稱以公共服務目的,為適應勞動需求做好準備,到伯杰龍(Bergeron)得出選修制度對本科生經驗至關重要的結論,選修制度繼續在高等教育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從而滿足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23]。
隨著世界各個領域沿著日益專業化和全球化的道路發展,學生教育經驗的靈活性也在相應提高。德納姆(Denham)強調了這一點:“簡單地說,隨著當前經濟、金融和政治趨勢的發展,如果畢業生沒有選擇國際關系、金融、政策和社會學的相關課程,將無法滿足21世紀工作場所的要求。”[24-26]國際上許多本科和研究生課程都有選修要求,這表明選修制度被廣泛采用,課程也在不斷進行相應的調整,以滿足21世紀對技能的要求[27-28]。
三、選修制度的啟示
(一)大學自主權和卓越教育家是推動改革的關鍵
“學院與大學之間的區別是:學院里的所有學生接受同樣的規定課程;大學里所有的學生可以學習許多不同的學科知識,學院是年輕人被送來學習并通過一串預定課程的地方;大學是年輕人去接受教育和幫助而進行科學追求的地方,大學應該使學生有機會接受普遍文化,大學通過其大師級的教授群吸引學生,通過擁有一些偉大人物而熠熠生輝。”[14]56選修制度的不斷完善,促進了哈佛大學的發展,同時推動了整個美國大學的轉型與發展。
選修制度在哈佛大學的完善和課程改革取得的成功及其深遠影響,有力地證明了大學具有一定自主權的重要性和教育家的關鍵作用。自由的學術狀態以及對于大學發展方向的深入思考,能夠讓大學真正發揮出自身的獨特價值,保證大學的課程改革能夠適應大學的發展與改革方向。
(二)關注學生公民意識,立足于國家發展
選修制度的成功還在于,將高等教育的目標和最終方向在學生和國家層面都給予了準確和合理的上位回答,將二者之間的關系和統一給出了明確的解讀。將“培養優秀公民”和“推進社會民主”作為高等教育發展的最重要的目標和特色。在經濟和文化日益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時代背景下,各個國家的教育目標已經從培養國家公民轉向世界公民的培養。各個國家學者對于世界公民的特征給出了八個特征,分別是:(1)作為全球社會的一員看待和處理問題的能力;(2)能夠與他人合作,并承擔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職責的能力;(3)理解、接受、欣賞和容忍文化差異的能力;(4)批判性和系統性的思考能力;(5)以非暴力方式解決沖突的意愿;(6)改變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以保護環境的意愿;(7)敏感和捍衛人權的能力(例如,婦女權利、少數民族等);(8)在地方、國家和國際各級參與政治的意愿和能力[29]。學生具有世界公民意識時,才能真正地意識到個人如何應對不同的挑戰,承擔起民族、國家和全球的責任,著眼于全球,著眼于未來,著眼于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和碰撞,以開放和長遠的眼光去認識世界、服務世界。
培養世界公民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就是高等教育課程的科學設置與實施。一方面需要保證專業課程的專業性和前沿性,讓課程內容跟時代接軌,融入前沿的科學技術知識與方法,具有開放性與現實敏感性。另一方面,注重課程的人文性。同時可以針對“我們生活的世界”,“全球化、貧窮、發展與貿易”,“全球治理”,“相互依存的世界的價值”和“世界公民”等內容和主題,設置專門的通識課程以培養學生的世界公民的意識,從而培養青年一代立足于國家和世界的,對人類、對社會、對自然的應該具有的天然使命感與責任感。
(三)著眼于國際視野,融合本土化特征
選修制度對于美國來講并非本土原創,其“選課自由”的思想起源于德國,但是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以及對于現代大學的影響,都是基于美國。
面對著18世紀德意志大學發生的嚴重衰退,哈勒大學、哥廷根大學先后進行了課程改革,歐洲最初的大學與教會息息相關,以教會的教條作為教育原則,但哈勒大學率先推行改革,奉行新的原則:采納近代哲學和近代科學,同時推行思想自由和教學自由。因此哈勒大學贏得了“學術自由的第一個發祥地”的美譽。哈勒大學將實用課程內容如馬術、擊劍、外語等納入教學體系;將文學院改為哲學院,同時將研究和教學建立在數學和物理等現代學科的基礎之上,開展自由研究與教學。在此之后,哥廷根大學將課程改革進一步深化,增加了地理學、外交學、科學和藝術等新興的人文和社會學科,同時法學院摒棄了教會法,設置了大量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能夠直接服務于國家內政外交的法律課程,如歐洲憲法、法律史和審判法等。學生可以依據自己的興趣和發展對課程進行選擇[30]。作為德國第二次大學改革運動的代表性標志,柏林大學自創立之日起就實行課程選修制,并且形成了與選修制相契合的教育教學思想與理論體系,從此,選修制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教學制度[31]。
美國高等教育在創辦后的百余年間,效仿英國,設置固定的課程和古典課程。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許多有識之士開始對這種課程體系以及設置方式產生懷疑和不滿。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斐遜首先提出美國大學要進行課程改革,實行選修制度,主張改變傳統的以古典文學為核心的、全部課程均為必修的課程結構,增加一些可以供學生自由選課的實用類課程,并宣稱:“學生可以自由上他們喜歡上的課程, 安排喜歡的活動,聽他們認為應該聽的講學。”[32]
在美國推行選修制的過程中,如果說杰斐遜起到了引進選修制的開啟作用,那么艾略特就具有讓選修制度在美國本土化之功。艾略特將選修制度的實施作為實現哈佛課程現代化的主要途徑之一,1872年到1897年期間,哈佛逐步取消了從四年級到一年級的所有的規定課程,僅剩一門修辭學作為一年級的規定課程。期間選修制度改革在哈佛取得了明顯的效果,新教師與新課程的數量同步增長。隨著改革的深入,選修制度的逐步落實,哈佛大學入學率的增長速度從曾經明顯低于其他學校的水平逐步到達19世紀90年代增長88.8%,幾乎高于同時期的其他任何院校的水平。顯而易見,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改革的落實,選修制度逐漸地顯示出其獨特的優越性和先進性。
從艾略特上任宣布在哈佛大學全面推行自由選修制度起,就將民主和自由作為大學發展的兩大核心特色,致力于打造具有獨特價值的現代的美國大學。從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將大學定義為“教授和研究所有人文科學和技能的學校”開始,美國就想要賦予它的所有學校一種美國特色。
美國的大學最初效仿英國大學,之后又先后借鑒了法國大學和德國大學,但不久之后在美國自身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中形成了擁有美國獨特價值的教育印記,將美國社會處處提倡和珍視的民主和自由的社會理念融入到美國教育中,結合美國的社會現實和時代發展趨勢,借助大學高度自治這一獨特優勢,形成了影響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教育改革體系。
大學的發展離不開其身處的社會環境、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民族文化氛圍等等,獨特的環境因素決定了不同國家不同大學的獨特價值追求,也反映了國家的歷史和人民的性格。正如亞伯拉罕·弗蘭克斯納(Abraham Flexner)所說的那樣,“歷經了幾個世紀,統一的大學模式從未由一個國家移植到另一個國家。”[33]教育改革一定要基于國家的歷史與各種環境因素的思考,充分吸收國際文明的精華,找到真正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印記,找到適合和屬于自身發展的教育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