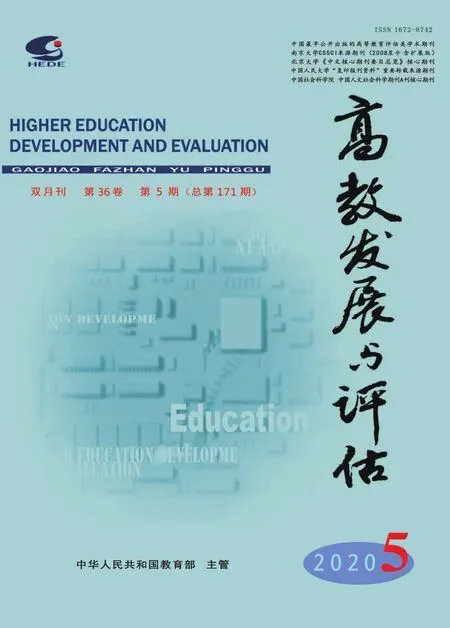大學觀承轉與通識教育旨趣
周 宏,董云川
(云南大學 高等教育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以“傳統(tǒng)的”與“現(xiàn)代的”為分野來看兩種教育觀,傳統(tǒng)的大學教育觀以“非工具論”為哲學基礎,將培養(yǎng)個體的整全人格作為總體育人目標,講求人文、社會、科技等各學科的均衡發(fā)展,并倚重實施通識教育來實現(xiàn);現(xiàn)代的大學教育觀以“工具論”為哲學基礎,定位在社會服務職能與培育學生的就業(yè)競爭力,課程體系追求技能、實作及直接效益、短程收益(1)觀點來自黃俊杰教授《21世紀大學理念的激蕩與通識教育的展望》一文。。
一、“傳統(tǒng)的“與“現(xiàn)代的“大學觀沖突分析
善于“型塑價值觀”的傳統(tǒng)大學觀與長于開發(fā)“學生專業(yè)能力”的現(xiàn)代大學觀之間,有理論上的緊張性,也有實踐中的動態(tài)平衡可能。求解二者“如何獲得動態(tài)平衡”至少應建立在對傳統(tǒng)大學觀與現(xiàn)代大學觀分歧的實質做進一步思考的基礎上。
首先,兩種大學觀對立的時空可能性。傳統(tǒng)大學所秉持的教育觀先于現(xiàn)代大學的教育觀而存在,傳統(tǒng)時代的大學觀無法與現(xiàn)代大學觀產生事實上的對峙;傳統(tǒng)大學觀與現(xiàn)代大學觀是大學理念發(fā)展在不同階段的具體表現(xiàn)形態(tài),并且“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概念具有相對性,“傳統(tǒng)”當其時即為現(xiàn)代,“現(xiàn)代”時過境遷則很可能轉為傳統(tǒng)。傳統(tǒng)大學觀與現(xiàn)代大學觀的分歧基于大學發(fā)展時間維度上的社會發(fā)展傳統(tǒng)性特征與現(xiàn)代性特征。而傳統(tǒng)大學并未處在以現(xiàn)代特征為內核的社會現(xiàn)實中,不具有現(xiàn)代大學的某些特質及由這些特質的結構及要素關系所決定的屬性,因而傳統(tǒng)大學的教育觀念不會且不必持有與現(xiàn)代大學教育觀念相一致的主張,自然也不會宣揚對現(xiàn)代大學教育觀的反對,二者之間本無所謂分歧。傳統(tǒng)大學觀與現(xiàn)代大學觀的分歧并非大學觀自身發(fā)展的歷時性樣態(tài)之間的沖突,而是共時性空間斷面上那些對大學教育持不同見解者之間的觀念分歧。
其次,兩種大學觀對立關系的真實性。即便兩種大學觀之間存在事實上的分歧,認定二者分歧過程中的錯位操作仍然使這一結論具有虛構性。二者的對立并非來自傳統(tǒng)大學觀“內在價值性”取向與現(xiàn)代教育觀“講求實用”的立場之間的抵牾,而是將一方合理內容理想化、另一方錯誤傾向極端化之后再進行錯位比較的結果。實際上,傳統(tǒng)大學觀“清致高雅”的格調與其自身“不切實際”的錯誤傾向互為對立面,現(xiàn)代大學觀“經世致用”的氣象與其自身“急功近利”的錯誤傾向互為對立面,但兩種大學觀正反四成分其他組合方式之間只存在螺旋結構中的對位或補位關系,卻并不構成真實的沖突、背反。將現(xiàn)代大學觀的“清致高雅”與現(xiàn)代大學觀的“急功近利”進行比較,或以現(xiàn)代大學觀的“經世致用”與傳統(tǒng)大學觀的“不切實際”相比較,當然很容易演繹出非此即彼、沖突對立的大學教育實踐主張。如此人為創(chuàng)設的分歧被刻意強化,高校辦學若盲目從所謂傳統(tǒng)大學觀與現(xiàn)代大學觀之間擇途而就,要么走上偏執(zhí)排他的單一路徑,要么采取毫無章法的混搭方式。
傳統(tǒng)大學觀與現(xiàn)代大學觀碰撞的外部動因在于:一方面,傳統(tǒng)大學觀賴以存在的社會格局及運行機制已經發(fā)生了變化;另一方面,促成現(xiàn)代大學觀產生和發(fā)揮影響作用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特性進一步彰顯,并于發(fā)展變革中向大學動態(tài)傳遞著促使大學發(fā)生相應變化的沖擊。傳統(tǒng)大學觀的依據(jù)之所以可以上溯到古希臘和中國儒家至圣先賢,也正是因其所依賴的社會土壤長期保持著較高的穩(wěn)定性,或者雖有變革但向大學的傳遞還沒有突破使其變革的臨界。而現(xiàn)代大學教育觀應運而生的時期,正值工業(yè)革命抵達科技時代的發(fā)展高峰,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翻天覆地的變革將大學推到時代潮涌的浪尖,使其明確受到來自社會變革的強烈波及并做出明顯反應。社會的發(fā)展變革是大學觀發(fā)展變化的外在根據(jù),也是推動兩種大學觀分歧的外部力量。
從內在方面來看,現(xiàn)代大學教育進一步改變了傳統(tǒng)大學精英教育定位下,與社會勞動特別是大眾勞動相疏離的狀況,形成了現(xiàn)代大學觀與現(xiàn)代社會生產生活樣式的耦合與聯(lián)動機制。首先,在現(xiàn)代大學觀的理念中,大學是“多元化巨型”的,被比作一個“變化無窮的城市”,與(僧侶居住的)村莊和(知識分子壟斷的)城鎮(zhèn)相比,“城市”更像文明的總和,隨著文明的演變,城市越來越多地成為文明的內在部分,越來越快地與周圍的城市互動[1]。現(xiàn)代大學在尋求自身發(fā)展和服務社會發(fā)展方面體現(xiàn)出主動性,現(xiàn)代教育觀很大程度上是在主動適應現(xiàn)代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其次,不同于傳統(tǒng)大學觀主要回顧過去的經驗,現(xiàn)代大學觀具有前瞻未來的特點,能夠積極適應社會變革,呼應社會發(fā)展對高等教育提出的人才需求。傳統(tǒng)教育也為社會培養(yǎng)人才,但僅著眼于精英階層的人才培養(yǎng),終究是有節(jié)制的,其所服務的群體、所發(fā)揮的社會作用也是限制性的。此外,從所處的社會領域來講,教育屬于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對于社會發(fā)展需要和人自身發(fā)展需要之間的文化關系,現(xiàn)代大學觀以發(fā)展了的人文主義精神視角呈現(xiàn)更強的包容性。
二、大學觀“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自洽
傳統(tǒng)大學觀重視價值性內容,也不乏實用的面向;現(xiàn)代大學觀側重效用,也體現(xiàn)著對價值的因應。傳統(tǒng)大學觀和現(xiàn)代大學觀分別具有各自的合理內核,都有對大學發(fā)展過程中的內在主體需要、外在客觀要求的體現(xiàn)和反映,隨著人類社會由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轉型,大學樣態(tài)也歷經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轉變。
傳統(tǒng)大學價值性取向的實用效應。究其根本,大學的起源包含著與其他組織分權以及促進社團內部成員協(xié)同的功用效果。作為大學初形的學院(universitas)是中世紀知識分子結成的社團,在性質上是“精神手工業(yè)者”的行會,與其他經營性手工業(yè)者的結社組織相類似,“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約束和引導主體的行為,使行為結果具有預期性,另一方面又保障主體權益不會受到其他主體的損害。”[2]歐洲大學初期三個主要學科是神學、法學和醫(yī)學,分別順應當時社會對牧師、律師、醫(yī)生的需求,具有很強的實用性;文科作為預科,尚且包含“提供有用訓練”使學生“適于承擔教會和世俗政府中的各種職業(yè)”的實用取向[3]。16世紀人文學科繁榮時期的語言、文學、藝術、倫理及哲學等學科,雖然并不直接具有對應社會現(xiàn)實需求的實用性,但人文學科在總體上代表世俗社會與神權抗爭,這恰恰是對當時最大社會現(xiàn)實做出了最高意義的功用性回應,并發(fā)揮了顯著效用。
現(xiàn)代大學功用職能的價值因應。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曾對早期工商業(yè)發(fā)展帶來的社會專業(yè)人才需求態(tài)度淡漠,結果是不斷增加的私立學校和教師填補了大學所陌生的實用學科教學,以及新科研機構的建立[4]。現(xiàn)代以來,大學作為社會有機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分工體系中承擔特定職責,產生相應功能,推動著人類社會的文明與進步,眾多著名大學紛紛把輸送人才、探索學術與服務社會融入辦學核心理念當中,自覺關注人類社會發(fā)展,積極推動國家和區(qū)域經濟產業(yè)結構、文化品質提升。大學有必要對社會現(xiàn)實的人才需要有所回應,并不意味著大學被迫替其他社會機構或組織發(fā)揮某種功用,而應該被視為社會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產生新的社會需求后為大學發(fā)展提出了新的依據(jù),大學由此豐富了自身的屬性。“大學不是達到特殊目的或者制造特殊結果的機器,它是人類活動的一種形式。”[5]傳統(tǒng)大學致力于探究高深學問,強調心智訓練和人格修養(yǎng),是與人類社會發(fā)展階段,與認識發(fā)展階段以及主要任務相對應的,大學觀如果始終排斥社會發(fā)展,排斥人的認識任務的豐富與發(fā)展,單純停留在高深學問、心智人格修養(yǎng)層面,那么大學反而成為單一職能、特定樣式或者局限性社會目的的工具。隨著社會發(fā)展進程的推進,大學著眼于更具普遍意義的人類福祉,投身于營建更美好的社會生活,大學的功能性和功利面正與人類(及人的主體性)需要一同閃現(xiàn)出價值的光芒。
大學觀念在分化中自洽。教育思想的形成和發(fā)展與時代和社會形勢有密切的關系,時代和社會的發(fā)展無疑是教育思想形成和發(fā)展的歷史背景。任何一種教育思想都是與某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科學技術及文化教育發(fā)展相適應的[6]。大學觀同樣不僅是時代和社會的產物,也是時代和社會發(fā)展進程本身的一部分,既反映時代的要求,又是當時主要社會潮流的一個方面。
“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大學’概念清晰、指代明確、論者與聽者均無理解岐義或異議。但今天的高等教育,己經在傳統(tǒng)大學的基礎上分別向‘高端’(研究型大學、頂尖大學)和‘低端’(社區(qū)院校、職業(yè)技術學院、短期大學等等)延伸,高等教育機構己經呈現(xiàn)出巨大的差異性。”[7]這種趨勢可以理解為大學在社會中自處樣態(tài)的變化,也可以解釋為大學內在價值的外化形式的發(fā)展。大學師生共同體最初通過以追求真理為目的的教學活動培養(yǎng)人,后來通過以發(fā)展學術為旨趣的科研活動提升人的認識,再到通過服務社會與科學研究的服務功能改善人類社會整體生活,時至今日進一步被寄望承擔起文化傳承、文化創(chuàng)新和文化引領的責任。
三、全人教育與專業(yè)培養(yǎng)的融通
全人教育源于傳統(tǒng)大學觀所秉持的古典教育哲學理念,培養(yǎng)“全人”是傳統(tǒng)大學觀的教育本質,中國古代“君子人格”培養(yǎng)與“全人”育人目標具有一致性。傳統(tǒng)樣態(tài)的“全人”教育理念試圖超脫具體歷史條件、假設在理想狀態(tài)中進行,要么基于宗教“原罪說”直接指向“神性”教育,要么假借自然主義賦予人之生命以潛能,憑借擬制“神性”,迂回通往“神性”教育。“全人”教育、君子教育均強調大學之根本在于人材培育,不同之處在于,“全人”教育主要是為“神”權謀,君子教育主要是為“王”權謀,都是既有神秘性又有實用性的。
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于美國的全人教育思潮傳承了“全人”教育理念的人文性和整體觀,體現(xiàn)了通識教育與傳統(tǒng)大學觀的結合。起初全人教育家更傾向于通過實現(xiàn)一次徹底的“范式”變革,喚醒人的自覺意識,不經其他周折地實現(xiàn)社會政治、經濟各領域的變革,并解決教育中的問題;80年代,在商政精英主導的強調教育對國家之責任的標準化運動沖擊下,全人教育開始著力于點滴教育改造,將課程、教學等領域納入視野。全人教育實踐在更廣闊地域的推廣和發(fā)揚,進一步豐富了它的內涵,秉持系統(tǒng)的生態(tài)世界觀,但在基本立場上仍然站在工業(yè)社會技術世界觀的對立面[8]。在技術的世界觀之下,人被視作一種需要進行嚴格的管教和馴化的對象,是代表著社會正統(tǒng)意見的教師按照一系列社會所要求的教學內容和教學過程來對其實施教育的對象,他們具有特定的可數(shù)字化計置的智能。而全人教育提出的人性假設是,每個人都有一種潛在的有待發(fā)掘的力量,學生是活生生的有機體,是一個充滿無限發(fā)展?jié)撃艿挠袡C體,教育的目的在于剌激和引導學生的自我發(fā)展。所有的孩子被認為都有發(fā)展成為“全人”的潛質。
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知識和信息傳播方式、技術和科學作用方式都發(fā)生了變化,通識教育的“全人”教育理念需要有所調整,在適應現(xiàn)實變化的基礎上,對大學的專業(yè)教育、社會的技術進步、人類營建美好生活的需求發(fā)揮價值引領和文化促動。而對于目前大學教育普遍存在過分注重專業(yè)教育、工具理性占主導的局面來說,專業(yè)教育有必要對當前社會發(fā)展、職業(yè)發(fā)展形勢有新的研判,對自身的功能有新的認識和定位。社會分工一經與科學技術結合,便加速了將產業(yè)結構與社會結構的發(fā)展與變革,也將大學人才培養(yǎng)置于專業(yè)勞動力片面化與綜合素質全面性的張力之中;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轉型,也愈益強化了社會對大學專業(yè)教育實用面的寄望,大學畢業(yè)生的從業(yè)能力成為全社會,尤其是學生本人及家庭的關切。然而,只具備狹隘專業(yè)知識與專業(yè)技能,而缺乏厚實綜合素養(yǎng)和自我發(fā)展能力,遠遠不足以勝任眾多知識密集型、創(chuàng)新導向的現(xiàn)代崗位對從業(yè)者的能力需求,社會持續(xù)發(fā)展要求職業(yè)人多元發(fā)展、個性鮮明,有自主學習能力和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能力,具備思想力、感受力、行動力均衡發(fā)展的特質。
按照愛因斯坦的觀點,僅僅用專業(yè)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專業(yè)教育可以使大學生成為有用的機器,但不足以使之為和諧發(fā)展的人。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并且產生熱烈的感情,是最基本的。大學教育必須能夠使學生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9]。實際上,只要那些有教養(yǎng)之人——他們耗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致力于那些精微而艱苦的知識研究——當他們愿意把自己的精力轉向甚至是最實際的實踐活動時,與那些未受這種教育之人他們很快會顯出自己的優(yōu)勢。因為受過培養(yǎng)的心智能給每一種工作或職業(yè)帶來力量,使我們變得更“有用”,使更多的人變得更“有用”。
“全人教育是指教育者首先要把學生作為一個人,一個主體性的人,一個有情感有智慧的人;同時,力求把他們培養(yǎng)成為一個具有與他們所受教育層次相稱的文化積淀與文化教養(yǎng)的人,一個具有與他們所在大學、所學系科(或專業(yè))相應的知識與視野并獲得必要的技能和能力訓練的人,一個在生理與心理、智力與非智力、情感與意向諸方面協(xié)調發(fā)展、具有較高綜合素質的人。”[10]“全人”是大學教育的育人目標,同時也應作為一個基本的立場和起點。大學的“詩心根植專業(yè)才有遠方,遠方必須自專業(yè)的腳下邁出第一步方可達致。離開專業(yè)基礎的通識是永遠不會有遠方的。”[11]阿什比強調,“走向文化的大路必須通過專精之門檻,由專精始可通達博文,否則浮光掠影,不流于膚淺者幾稀?”[12]正如懷特海所言,“我們的目標是,要塑造既有廣泛的文化修養(yǎng)又在某個特殊方面有專業(yè)知識的人才,他們的專業(yè)知識可以給他們進步、騰飛的基礎,而他們所具有的廣泛的文化,使他們有哲學般深邃,又有藝術般高雅。”[13]培養(yǎng)優(yōu)秀的職業(yè)人離不開通識教育取義“全人”的高瞻遠矚。
有學者以地球構造由內及外的地心、地幔、地表層次結構,比擬從專業(yè)核心課程到專業(yè)共同課程再到公共通識科目群的課程結構,強調專業(yè)知識的核心地位,認為沒有離開這一核心的抽象的、離散性的“博雅”知識系統(tǒng)[14]。今日應提倡的“通識”有必要基于專業(yè)學習、圍繞職業(yè)發(fā)展和面向社會需求。
通識課程的整體性。通識課程因沿傳統(tǒng)教育觀而重視世界整體性的思路,應吸納跨學科整合的觀點,打破學科界限,進行學科互動和滲透,拓展知識閾限與學術視野。正如美國一些著名大學的核心課程,開設的不是“法學概論”“經濟學原理”,而是“財富、權力、美德”“自我、文化、社會”(芝加哥大學),是“正義”“時間、空間和運動”“人性的概念”“地球的生命和歷史”(哈佛大學)等跨學科整合性科目[15]。通識課程不以提供全面性、多樣化的知識為目的,其所要奠定的知識基礎保留著與傳統(tǒng)大學觀一脈相承的理性主義整體觀取向。而時下一些高校通識課程逸樂、閑散的亂相則有悖于整體性原則,呈現(xiàn)出隨意性特征和無序狀態(tài),不但與“全人”價值取向毫不沾邊,甚至已經談不上確實意義的通識課程。
通識課程的引領性。在大學中,通識課程一般被定位為專業(yè)課程的基礎,基礎地位得到廣泛認可。整體性作為專業(yè)性的基礎,是客觀事實,但只是事實的一面。從通識教育的內容領域來看,需要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相互配合,各學科的交叉具有全面性,作為一種承載是具有基礎性的。但同時,這種交叉的內容必須具有一定的超越性,體現(xiàn)出超越于任何一門具體學科的特性。從通識課程的目標設定來看,較低學段的課程可能教給學生既有的學說、科學的真實性以及迄今尚無答案的科學問題;大學則應設法使學生認識到科學中尚未確定的內容以及它永無止境的性質[16]。從內容領域和課程目標來看,大學通識教育必須具有引領意義,否則將等同中學階段著重于資料積累的知識拓展教育,有失大學設置通識課程的必要價值。
大學通識教育與專業(yè)教育之間的關系,不僅呈現(xiàn)通識教育作為基礎的一面,從它對具體學科的超越性和無限性的引領來看,不僅為專業(yè)課程提供可供生長的給養(yǎng),更是在課程的結果端、在學生的素質結構中,為專業(yè)課程的效應增添無限性、拓展可能性。從學生專業(yè)發(fā)展來看,在專業(yè)工作的規(guī)范化、標準化程度逐步提高的情況下,個性品質、責任意識、思維方式、職業(yè)操守、職業(yè)心態(tài)等隱性素養(yǎng)的重要性和競爭力將越來越重要,“沒有精神和遠見的專家“將作為專業(yè)素質薄弱者出局。
四、結 語
人對自身主體性物用需要的滿足能力提升,社會組織的規(guī)模化和精細化程度提高、組織間關系復雜程度提高,人類探索客觀世界的能力提升,都強化了社會和個體對客觀世界施加影響的意圖與行動。在這種大環(huán)境下,通識教育處在專業(yè)至上、指標盛行、學習取向逸樂化、學術態(tài)度功利化等多重擠壓之下,此種困局不是個別大學或個別地區(qū)大學通識教育的困頓境遇,可以說是世界范圍內眾多大學的境遇。
通識教育與全部教育的真實關系是——有通識教育則有教育,無通識教育則無教育;專業(yè)教育與高等教育的關系是——有專業(yè)教育則有高等教育,無專業(yè)教育則無高等教育。如果說定位在“職業(yè)人”教育的大學教育是“半人”教育,那么排斥專業(yè)職業(yè)教育的全人教育,是培養(yǎng)“另一半”的人的教育,同樣是殘缺的。通識教育重要性的體現(xiàn),并不通過與專業(yè)教育的角力而得以體現(xiàn),二者并非零和游戲的關系,而是相互依存、互相成全的關系,無專業(yè)便無所謂通識,無通識也無所謂專業(yè)。通識教育有基礎性的一面,但它更高的價值則會在對專業(yè)教育的引領和托舉中得以展現(xiàn)。通識教育與專業(yè)教育融合的層次和水平,通識教育對專業(yè)教育的助力情況,便是通識教育自身價值在何種程度得以展現(xiàn)的表征。專業(yè)教育不能離開通識教育,否則大學教育將被稀釋為職業(yè)訓練,反而不及卓越的職業(yè)教育。
現(xiàn)有通識教育定義的表述普遍選擇“效益”路線,突出通識教育培養(yǎng)學生各種能力的目標定位和預期效果的做法,雖然存在謀求通識教育改善現(xiàn)實處境和爭取發(fā)展空間的合理成分,但在基本層面的工具論立場無疑與通識教育的內在價值主張之間存在明顯的張力。通識教育作為一個教育樣式,有必要避免兩個誤區(qū)。第一,通識教育不必追求與專業(yè)教育的形式平等。通識教育不是對專業(yè)教育的填空、補缺,二者屬于分層共處,而非對峙關系,不必時時急于與專業(yè)教育分庭抗禮,奔走呼吁謀求發(fā)展空間,將自己置身于弱者的境地,更不適合企圖造成自成一統(tǒng)的封閉體系,處處張貼醒目標簽以突出自身的獨立價值。第二,通識教育可能包羅萬象,但并不包打天下。秉持培養(yǎng)“全人”的通識教育尊崇各方面有機聯(lián)系的人類生活,在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的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全人”的生活理應包括職業(yè)生活,“全人“的能力結構理應包括為職業(yè)生活做準備的信息能力、職業(yè)道德直至終身學習的態(tài)度,“全人”的能力傾向理應包括適應適度的競爭環(huán)境與創(chuàng)新要求。全人教育呼吁重新認識生活的有機性,它只能通過正視業(yè)已形成的現(xiàn)代生活,引導合乎人生意義和社會發(fā)展的真實的生活,而不能通過屏蔽、阻斷某些社會現(xiàn)實來達成。從通識教育與學生個體生命成長相關聯(lián),與社會現(xiàn)實及人類生活相關聯(lián)的角度,通識教育不可能徹底擺脫“功利”性,畢竟生命不是抽象的,人類社會也不是抽象的,大學對個體生命和人類社會發(fā)揮的價值也不是抽象的。因此,回應現(xiàn)實的教育對象需要和社會發(fā)展需要,是傳統(tǒng)大學觀、“全人”取向的通識教育達至整體的人文關懷的必由之路,也是在現(xiàn)實的大學教育場域對專業(yè)教育充分發(fā)揮基礎作用和引領功能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