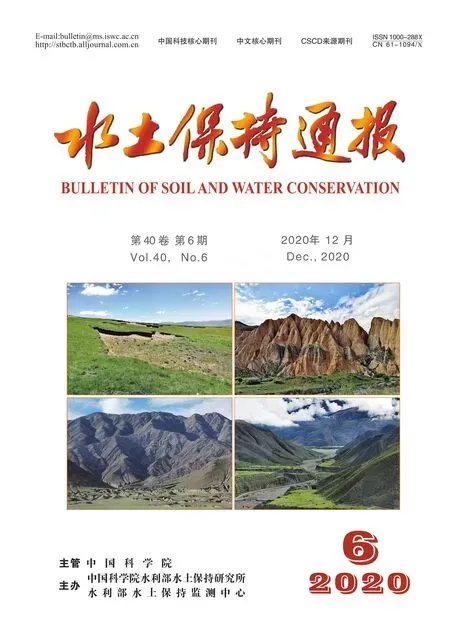1988-2018年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時空變化及其驅動力
高鵬文, 阿里木江·卡斯木,2, 趙永玉,圖爾蓀阿依·如孜, 趙禾苗, 哈力木拉提·阿布來提
(1.新疆師范大學 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 新疆 烏魯木齊 830054;2.新疆師范大學 絲綢之路經濟帶城鎮化發展研究中心, 新疆 烏魯木齊 830054)
綠洲是干旱區水系分布不均及空間降水量不平衡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特殊地理單元[1-3],因為土壤、濕度、地形等因素的共同影響下,綠洲成為干旱區內對生命系統承載力較高的,人類生產生活聚集地[4-6]。干旱區內的主要景觀類型是荒漠,而綠洲的出現改變了這種格局,故綠洲化與荒漠化是一個相互博弈的過程,為防范過渡荒漠化就必須研究綠洲形成的機理,綠洲擴展的方式及驅動力[7-10]。目前國內對于綠洲的研究多在石羊河流域[11]、黑河流域[12]、疏勒河流域[13-14]、艾比湖流域[15]、瑪納斯河流域[16]、和田河流域[17]等,由此可見綠洲大多發源于大河流域,其研究主要為土地利用變化[18-20]、荒漠化與綠洲化[21-22]、綠洲時空演變[23],植被覆蓋度的變化對于綠洲生態系統穩定作用明顯[25]。植被覆蓋度的反演研究對于區域內土壤、水文及生態有重要意義[26]。對于植被覆蓋度的研究國內外研究較為深入,也出現了大量研究方法[27],其中像元二分模型估算植被覆蓋度又是較為常用且有效的方法[28]。因此本文從干旱區綠洲大背景出發,利用像元二分模型計算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從而找尋干旱區哈密綠洲發展規律,分析內在驅動因素。哈密綠洲是干旱區內相對獨立的綠洲,因此沒有條件形成大片綠洲群,同時該地區為典型的溫帶大陸性氣候,夏季炎熱少雨,冬季寒冷干燥,僅有的哈密河也在21世紀初下游已經干涸,因此探討哈密綠洲的植被覆蓋度變化以此間接了解哈密綠洲生態環境狀況,從自然與人文兩個角度共同探尋哈密綠洲變化的內在驅動力,為該地區持續健康發展提供理論借鑒。
1 研究區概況
哈密綠洲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東部,也是內地省份進入新疆的第一片綠洲,屬于哈密市伊州區行政管轄。哈密綠洲南側為大片荒漠戈壁,北側為是東天山南部的洪積扇。因地處干旱區,屬于典型的溫帶大陸性干旱氣候。晝夜溫差大,最大日較差26.7 ℃,年均氣溫僅有9.8 ℃,年均降水量僅有33.8 mm,同時蒸發量卻高達3 300 mm,氣候干燥。哈密綠洲內有哈密河流經,但常年處于干涸狀態,主要水源由地表水(降水、降雪)和地下水(東天山冰川融化)兩部分提供。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及預處理
本研究數據主要為3部分: ①遙感影像數據。選取了1988,1998,2008年Landsat TM數據和2018年的Landsat OLI數據(https:∥www.usgs.gov/),獲取時間分別為7月24日,8月7日,7月29日及7月20日。再進行幾何校正、輻射定標、大氣校正等步驟消除大氣對于植被覆蓋度計算時的影響,再對其拼接裁剪,得到綠洲植被覆蓋度影像。 ②空間數據。從資源環境云平臺(http:∥www.resdc.cn/)獲取DEM、人口密度、GDP、溫度、降水和土地利用柵格數據。統一重采樣至30 m,重分類為5類。 ③基礎地理信息數據。從國家地理信息中心獲取1∶100萬的地理信息數據,選取道路及水系。先對獲取的道路與水系兩種矢量數據轉換坐標系,依據研究區圖裁剪需要的范圍,再對處理后數據做核密度分析。之后再轉柵格依據,同時重采樣至30 m,最后利用自然斷點法分成5類。
2.2 植被指數選擇
眾多學者對全球40多種植被指數進行了比較,高志海[29]綜合比較結果顯示歸一化植被指數(NDVI)與全球環境監測指數(GEMI)能夠反映民勤綠洲的總體情況,而盛莉[30]等人采用去氣溶膠植被指數(AFRI)代替NDVI,較為有效地排除了氣溶膠對植被覆蓋度提取的干擾,并取得了較好的結果,同時滑永春[31]等人通過試驗發現AFRIWIR2在干旱區內對于植被覆蓋度的提取效果好于AFRISWR1,因此本文選擇AFRISWIR2指數來提取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
ARVI=(NIR-RB)/(NIR+RB)
(1)
RB=red-γ(blue-red)
(2)
AFRISWIR2=(NIR-0.5WIR2)/
(NIR+0.5SWIR2)
(3)
式中:NRI,red,blue分別為Landsat影像近紅外、紅色、藍色波段的反射率; γ為大氣光路修訂系數,取值為1; SWIR2為TM及OLI影像的第7波段。
2.3 像元二分模型
采用像元二分模型估算植被覆蓋度,該模型也是較為簡單實用且被大量印證過得模型,其原理為:假定有植被覆蓋度與無植被覆蓋度的區域共為一個像元S,如全部覆蓋植被則表示Sveg,全部覆蓋土壤則表示Ssoil。由此可得植被覆蓋度公式:
S=Sveg+Ssoil
(4)
通過推到得出基于AFRISWIR2指數的植被覆蓋度公式:
(5)
式中:FVC為植被覆蓋度; AFRImax,AFRImin表示AFRISWIR2影像中純植被像元值與純裸地像元值。
理論上AFRImin值近似為0,但由實際地理環境影響,不同研究區內需依照實際情況進行取值[32-34]。圖1為哈密綠洲AFRISWIR2累計頻率,分別選擇累計頻率為10%與95%的值為AFRImin和AFRImax值[26]。

圖1 哈密綠洲去氣溶膠植被指數AFRISWIR2頻率直方圖與累計頻率
2.4 植被覆蓋度動態度
研究期內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不同等級面積動態變化,可以用動態度表示,具體為:
(6)
式中:T為研究時間段;Ds,De分別表示研究初期及末期植被覆蓋度面積。在本文表示為綠洲的擴張程度,K>0表示綠洲擴張,K<0表示綠洲萎縮,K的絕對值越大表示越劇烈。
2.5 植被覆蓋度分級
本文依據國家《土地利用現狀調查技術規程》《草場資源調查技術規范》《土壤侵蝕分類分級標準》及《中國荒漠化防治國家報告》,再結合朱震達等人[35]的研究,將哈密綠洲的植被覆蓋度分成5個等級,分別是極低植被覆蓋度(覆蓋度<10%)、低植被覆蓋度(覆蓋度10%~30%)、中植被覆蓋度(覆蓋度30%~50%)、中高植被覆蓋度(覆蓋度50%~70%)、高植被覆蓋度(覆蓋度70%~100%)。
2.6 地理探測器
地理探測器是用來度量地理現象及其潛在影響因子關系的空間分析模型,其不僅能較好的表達同一區域內的相似性和不同區域間的差異性,也可解釋自變量X對因變量Y的解釋強度[36]。
因子探測器可計算不同因子對生態質量時空變化分異性,以及探測其影響程度大小,計算公式為:
(7)
式中:N為研究區全部樣本數;σ2為整個區域Y值的離散方差;h為變量Y或因子X的分區,h=1,2,…,L;L表示分區數目;q為綠洲生態質量的空間異質性,值域范圍為[0,1],若分區是由自變量X生成的,則q值越大表示自變量X對屬性Y的解釋力越強,反之則越弱。
交互作用探測為判斷不同影響因子之間的交互作用,即評估因子X1和X2共同作用時是否會增加還是減弱對生境質量的解釋力,兩個因子之間的關系詳見表1—2。

表1 兩個自變量對因變量交互作用的類型
生態探測用于比較兩兩因子對生態質量的空間分布的影響是否具有有顯著的差異:
(8)
式中:NX1,NX2分別表示因子X1和X2的樣本數量; SSWX1,SSWX2分別表示由S和X1形成的分層的層內方差之和。

表2 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驅動因子
3 結果與分析
3.1 植被覆蓋度空間變化特征分析
本文利用4期影像計算哈密綠洲近30 a植被覆蓋度空間變化(圖2),并對其進行面積統計(表3)。由此可知4個時間段內極低覆蓋度面積占比都不足1%;低覆蓋度的面積占比都超過了50%,說明哈密綠洲總體上低植被覆蓋度占主要份額;中覆蓋度與中高覆蓋度從近18 a內呈現增長趨勢;高植被覆蓋度呈現先增加后減小的總體趨勢。 ①1988—1998年,極低覆蓋度增加了0.01 km2;而低覆蓋度的面積從1988年的1 150.64 km2降低到1998年的1 049.66 km2,降低了7.39%;中覆蓋度、中高覆蓋度及高覆蓋度面積占比分別增加了0.98%,2.24%和4.18%。同時從圖2的1988年植被覆蓋度中發現面積最大的低覆蓋度區域主要在哈密綠洲的西南部及東北部,且中覆蓋度、中高覆蓋度及高覆蓋度的區域沿西北—東南方向的條帶狀分布。

圖2 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時空變化

表3 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面積統計
從圖2的1998年的植被覆蓋度圖中可知,中覆蓋度、中高覆蓋度的分布區域相較于1988年沒有改變。而高覆蓋度變化區域變化明顯,主要集中在哈密綠洲的西北部及東南部。 ②1998—2008年,極低覆蓋度變化不明顯,低覆蓋度區域面積從1998年的1 049.66 km2降低到2008年的773.40 km2,降低了276.26 km2,降幅26.36%。中覆蓋度、中高覆蓋度及高度蓋度區域面積分別增加了79.34,51.54及152.32 km2。可知在該時間段內,低覆蓋度區域面積變化最大,從圖2的2008年植被覆蓋度發現,引起該變化的原因是在哈密綠洲的西南部新增了較大的綠洲;同時高覆蓋度區域從圖2的2008年植被覆蓋度中可知,主要分布在東部和西部。 ③2008—2018年,極低植被覆蓋度變化依舊不明顯,同時低植被覆蓋度在該段時間內也僅降低了2.94%,中植被覆蓋度與中高植被覆蓋度面積分別增加了23.91和65.47 km2,而高植被覆蓋度則首次下降,降幅3.61%。從圖2中可知,該段時間內,各植被覆蓋度等級變動較小,僅僅是小區域環境下的改動,綠洲增加的區域也僅在原有綠洲的周圍擴展,同時可以看到高植被覆蓋度的變化區域在綠洲北部接近天山南坡洪積平原前緣的區域。這說明近10 a哈密綠洲整體變動較為穩定,綠洲斑塊形狀趨于固定,變動也僅是從植被覆蓋度低的區域向植被覆蓋度高的變化。
3.2 綠洲動態度變化分析
經計算可知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動態度(圖3)1988—1998年,從極低覆蓋度到高覆蓋度呈現為先降低后增加的趨勢。1998—2008年,從極低覆蓋度到高覆蓋度表現為先減小后增加再減小再增加的波動過程。2008—2018年,從極低覆蓋度到高覆蓋度呈現出先增加后減小的趨勢。由此可知3個時間段內,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不同等級之間出現了3種不同方式的變化,其原因在于前10 a綠洲空間形態較為穩定,而這種穩定是由于總體面積不大,變化空間小;中間10 a間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不同等級之間面積變化最為劇烈,該過程拌隨著不同植被覆蓋度等級之間相互轉化;最近的10 a間,綠洲空間形態也較為穩定,而該穩定是因為總體面積擴大,現有綠洲基本框架基本形成所導致的。分析發現,3個時期內極低覆蓋度的動態度先增加后減少,但結合表1可知,3個時期內該等級的面積基本沒變;低覆蓋度區域面積的動態度均為負值,表明3個時期中低覆蓋度區域面積始終在減小,且降幅呈現為先增加后減小趨勢。起因在于前10 a內低覆蓋度區域面積減小較少,而在中間10 a內該區域面積變化最為劇烈,在近10 a變化較小;中覆蓋度區域面積動態度與中高覆蓋度區域在3個時期內變化一致,均為正向變化,表明面積都在增加,且增加幅度均表現為先增加后降低。但中高覆蓋度比中覆蓋度區域增幅大;高覆蓋度區域的動態度在前兩個時期內增速最大,但在近10 a內為負方向增長,表明高覆蓋度區域面積在近10 a降幅較大。

圖3 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動態度
3.3 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空間轉移分析
為探究哈密綠洲內部不同植被覆蓋度之間的相互轉化,及判斷哈密綠洲近30 a變化階段,本文對4期數據做植被覆蓋度轉移矩陣(表4—6)。從表4可知,1988—1998年低覆蓋度區域轉出到中覆蓋度、中高覆蓋度及高覆蓋度區域的面積分別為71.03,31.70及20.21 km2,轉出面積占比為10.68%。由此可知1988年低覆蓋度區域89.32%都轉入到1998年的低覆蓋度區域,也表明該時間段內低覆蓋度區域面積基本沒有轉變。中覆蓋度區域轉入低覆蓋度區域面積占比19%,轉入中高覆蓋度區域面積所占比例30%,轉入高覆蓋度區域面積所占比例17%,而沒有轉出的面積占比為33%。由此可知,中覆蓋度區域向覆蓋度更高的區域轉入比例47%,所以中覆蓋度區域在1988—1998年主要向更高的覆蓋度區域轉變。中高覆蓋度及高覆蓋度區域也主要是轉入到高覆蓋度區域內。因此總體上,在1988—1998年除低覆蓋度區域主要轉出區域為自身等級植被覆蓋度區域外,其他等級的植被覆蓋度區域均向比自身更高的區域轉變。但轉出的面積較小,不同植被覆蓋度等級之間的轉化不夠顯著,轉化強度較低。由表5可知,1998—2008年低覆蓋度的區域沒有轉出的面積有765.83 km2,占比73%,而轉入到中覆蓋度區域、中高覆蓋度及高覆蓋度的區域面積分別為135.48,67.87及80.13 km2,所占比例分別為12%,6%及7%。由此可知低覆蓋度區域在該時間段內變化最劇烈,轉出面積在各等級覆蓋度中最多。因此可說明哈密綠洲在該時間段內植被覆蓋度的變化主要是低覆蓋度區域向更高等級覆蓋度區域轉變,低覆蓋度區域成為哈密綠洲擴展的主要源地。從圖3的1998和2008年兩期植被覆蓋度圖中可以發現,低覆蓋度區域減少的區域集中在哈密綠洲的西南部區域。中覆蓋度區域及中高覆蓋度區域轉入到比自身高一個等級的面積占比也分別31%及55%。究其原因在于哈密綠洲中部的伊州區城區內的植被變化較為復雜,城區周圍的植被覆蓋度也變化較為活躍,因為在該時間段內哈密綠洲在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影響下農業及工業的大力發展。因此總體上在該時間段內,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總體是從低覆蓋度區域向更高覆蓋區域轉變。也正是這種不同覆蓋度等級之間的轉變,基本形成了現在哈密綠洲的框架。由此可認為1988—2008年是哈密綠洲快速擴展時期,是形成現在綠洲框架的關鍵時期。由表6可知,2008—2018年低植被覆蓋區域無轉入,轉出的區域僅占10%。中覆蓋度區域既向低覆蓋度區域轉變,也向高覆蓋度區域轉入,該等級轉出的區域占比60%,但主要轉出依舊是中覆蓋度區域。中高覆蓋度為變動的面積68.08 km2,轉入高覆蓋度、中覆蓋度及低覆蓋度的面積分別是31.93,44.33,10.14 km2。由此可知中高覆蓋度主要的變動還是該區域。高覆蓋度轉出高覆蓋度、中高覆蓋度、中覆蓋度的面積占比分別為46%,37%,10%。綜上所知,在2008—2018年內哈密綠洲的植被覆蓋度各等級都未發生較大規模的轉出入情況,所以改時間段內哈密綠洲總體擴展較為緩慢,即哈密綠洲空間格局并非在該時間段內形成,而是在2008年前已完成該過程,但已形成的綠洲內部各等級之間的轉化成為最劇烈的時期。

表4 哈密綠洲1988-1998年植被覆蓋度轉移矩陣km2

表5 哈密綠洲1998-2008年植被覆蓋度轉移矩陣km2

表6 哈密綠洲2008-2018植被覆蓋度轉移矩陣km2
4 驅動力分析
由因子探測的結果可知(表7),所選的8個生態因子均通過了p值小于0.05的顯著性檢驗。且不同因子的決定力q值普遍較高。q值從大到小排序依次為:土地利用>GDP>人口密度>降水>溫度>道路>水系>坡度。
由此可知土地利用變化是引起綠洲植被覆蓋度變化的第一影響因子,第二影響因素是人口密度與GDP,然后是溫度與降水,最后是水系及道路網絡的影響。表明干旱區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變化的主要驅動因素是土地利用類型。由于綠洲是基于人類活動在干旱區的產物,受自然因素如降水、氣溫、坡度等影響的同時,人類活動也對其產生更為深刻的影響。哈密綠洲發展過程受人口密度、道路等人工設施的建設影響較大。哈密綠洲內人口密度與GDP的貢獻率明顯高于溫度與降水,而土地利用類型是主導因子。自然因子與人類活動對于不同時間尺度上對綠洲演化起著不同的作用。表明在研究期內哈密綠洲,人為因素對植被覆蓋度狀況的影響遠高于自然因素。隨著西部大開發的實施,新疆城鎮發展迅速,經濟社會進程穩步加快,人類活動對地表影響日益深刻,由此造成綠洲植被覆蓋度變化劇烈。

表7 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的因子探測結果
從交互探測(表8)可知,坡度∩道路(0.209)、坡度∩河流(0.184)、道路∩溫度(0.465)和道路∩河流(0.417)(帶*)為非線性增強,其余為雙因子增強。而在因子探測中坡度(0.056)與道路(0.122)的解釋力最低,說明經過交互探測,坡度與道路對于綠洲植被覆蓋度的解釋力有大幅提升。其他雙因子增強按解釋力大小排序為:土地利用∩GDP(0.791)>土地利用∩人口(0.787)>土地利用∩降水(0.784)>土地利用∩溫度(0.752)>土地利用∩河流(0.687)>土地利用∩道路(0.685)>土地利用∩坡度(0.666),其他因子交互探測值均小于0.65。可知土地利用與其他因子交互探測后解釋力均大于原來單因子探測的結果,同時土地利用對于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有及其重要意義。
綜上分析說明不同類型的土地利用方式直接決定了該區域內綠洲植被覆蓋度,當然其他自然與人文因子對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有間接影響作用。生態探測(表8)可知,河流與坡度、河流與道路、溫度與道路以及道路與坡度,表現為無顯著差異,而其他因子之間的生態探測均表現出顯著差異。

表8 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的交互探測與生態探測結果
5 討 論
5.1 哈密綠洲擴展階段
綠洲擴展階段主要分為前中后期3個階段[37],前期主要是綠洲主體內部的填充,中期為向外拓展,后期為穩定擴展階段[38]。本文首次定義了哈密綠洲的發展階段,其中哈密綠洲在前期(1988—1998年)總體植被覆蓋度較低,且覆蓋度較好的區域都相對集中,不同等級的覆蓋度相互轉化的強度較低,屬于綠洲低強度穩定期[39];中期(1998—2008年)屬于極度擴張期,在該時期哈密綠洲面積增幅高達85%,同時不同等級的覆蓋度區域內相互轉化的強度較高,高覆蓋度及中高覆蓋度區域轉入的貢獻率最高的是低覆蓋度區域,同時由于該時期快速擴展,初步形成了哈密綠洲現在的基本框架[40];后期(2008—2018年)屬于高強度穩定期,在該時期內綠洲面積擴展較慢,但中覆蓋度、中高覆蓋度及高覆蓋度區域之間的相互轉移最為劇烈,該定義過程與劉亞文[5]對吐魯番綠洲、魯暉[41]對民勤綠洲、廖杰[42]對黑河綠洲階段劃分一致。
5.2 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影響因素
干旱區綠洲擴展主要表現為人工綠洲的擴展,對植被覆蓋度的分析可量化人工綠洲擴展[43]。植被覆蓋度變化影響因素的研究較多,在干旱區內不同區域影響因素差異較大,當綠洲內有徑流量較大的河流存在時,河流與鹽漬化的影響較大[44-45]。王耀斌等人[46]認為綠洲面積的波動受制于農業綠洲灌溉情況。當然河道變遷和水位變化是綠洲植被覆蓋度變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進入到哈密綠洲發展中期,哈密河水位降低明顯同時在其周圍的植被及作物減少。在綠洲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人為影響速率明顯強于自然影響速率[47]。本文從地理探測器交互探測得到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影響因素中人類活動的影響更大,而這一結果與劉亞文[5]對同屬東疆區域的吐魯番綠洲分析相同。本文也存在諸多不足之處,對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變化方向沒有實現定量化的度量。同時本文僅用一種中等分辨率遙感類型數據,今后對哈密綠洲研究中還需要加入多種數據源,并提高數據的空間分辨率,以此達到更加精細化的效果。
6 結 論
(1) 近30 a內,哈密綠洲總體上低植被覆蓋度占主要份額;中覆蓋度與中高覆蓋度從近18 a內呈現增長趨勢;高植被覆蓋度呈現先增加后減小的總體趨勢。
(2) 哈密綠洲從植被覆蓋度分析,(1988—1998年)屬于綠洲低強度穩定期;(1998—2008年)屬于極度擴張期,形成了現在哈密綠洲基本框架;(2008—2018年)屬于高強度穩定期。
(3) 土地利用類型變化是造成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變化的直接原因,同時在近30 a內,人為因素對哈密綠洲植被覆蓋度狀況的影響遠高于自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