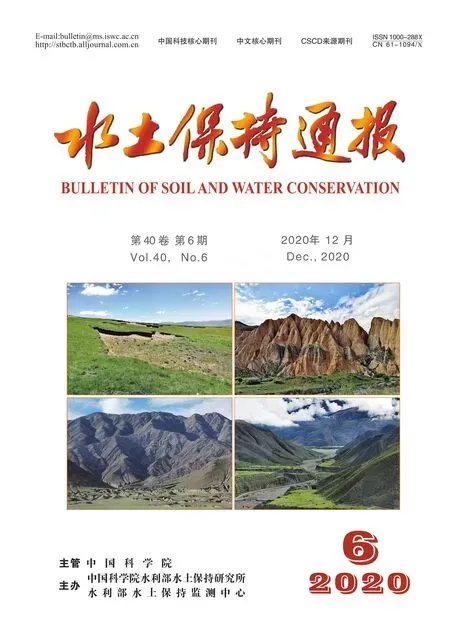1990-2018年東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及其驅動力
鄧信翠, 陳洋波
(中山大學 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 廣東 廣州 510275)
土地利用變化體現了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及影響,是全球變化研究的熱點問題。1995年,IGCP和IHDP聯合提出的“土地利用/覆被變化科學”研究計劃指出來了LUCC研究重點,推動了LUCC研究在全球范圍的發展[1]。土地利用變化驅動力是指影響土地利用目的和方式的自然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進行區域土地利用變化驅動力分析,是預測未來土地利用變化方向、優化土地利用方式、提高土地資源利用效率的基礎[2]。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采用土地利用驅動力模型[3]對區域土地利用變化及其驅動機制研究取得了較好的研究成果。Lambin[4]等對引起土地利用變化的原因進行了系統的闡述;Turne[5]等采用案例對比研究方法分析全球土地利用變化與環境變化的關系;Gobint[6]用回歸模型分析了影響農業土地利用變化的驅動力;史培軍[7]、擺萬奇[8]等采用回歸分析方法分析區域土地利用變化及驅動因素的關系;謝花林[9]、姜楠[10]等通過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了土地利用變化驅動力;賈科利[11]、李晨曦[12]等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區域土地利用變化的驅動機制。東江地處粵、港、澳三地交接處,是香港特區以及廣東省廣州東部、深圳、河源、惠州、東莞等地的主要供水水源。東江流域下游地區經濟發達,2017年東江流域GDP總量約占廣東省GDP的48%。經濟的快速發展驅使流域土地利用格局發生變化,影響流域生態環境質量和可持續發展。現有的關于東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驅動研究側重于分析東江子流域土地利用變化的驅動機制[13-14],土地利用演變分析的時效性和整體性不足。本研究以東江流域為研究區,選取土地利用動態度、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利用轉移矩陣,分析1990—2018年土地利用變化時空特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及灰色關聯分析法分析土地利用變化驅動機制,以期為優化流域土地利用方式、合理配置土地資源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東江發源于江西省尋烏縣的椏髻缽,流經龍川、東源、河源、紫金、惠陽、博羅、東莞等縣市在東莞石龍鎮流入珠江三角洲[15]。東江流域地處113°52′—115°52′E,22°38′—25°14′N,流域總面積為35 340 km2,干流全長562 km。地勢東北高,西南低。龍川縣以上流域為流域上游,龍川縣合河壩至觀音閣流域為流域中游,下游為觀音閣至入海口流域。流域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區,有明顯的干濕季,流域內多年平均降水量為1 500~2 400 mm,主要集中在4—9月,空間上分布上西南多,東北少,呈現由南到北遞減的趨勢;流域多年平均氣溫為20~22 ℃[16]。
1.2 數據來源
東江流域土地利用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提供的1990—2018年6個時相的土地利用現狀遙感監測數據,主要通過目視解譯Landsat遙感影像數據獲得,分辨率為1 km,利用ArcGIS軟件進行重分類將土地利用分為6類,影像裁剪得到東江流域1990—2018年土地利用數據。流域社會經濟數據來源于1990—2018年廣東省、江西省各市縣統計年鑒,從人口增長、經濟增長、社會富裕程度和農業發展4個方面選取14個社會經濟指標:總人口(X1)、非農業人口(X2)、地區生產總值(X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X4)、第一產業比例(X5)、第二產業比例(X6)、第三產業比例(X7)、社會固定資產投資(X8)、地方財政支出(X9)、地方財政收入(X10)、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1)、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X12)、糧食單產(X13)、農村機械總動力(X14)。
1.3 研究方法
1.3.1 土地利用動態度 區域土地利用數量變化速率可用土地利用動態度來表示[17-18]。其中,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是區域某種土地利用的面積在研究期間的變化速度,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是區域土地利用變化的整體變化速度。數學表達式為:
(1)
(2)
式中:K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Ua,Ub分別為研究初期、研究末期土地利用類型面積;T,t2-t1為時間間隔;LC為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 ΔLA(ij)為第i類土地轉變為非i類土地的絕對值; ΔLA(i,t1)為第i類土地在t1時期的面積。
1.3.2 土地利用程度 土地利用程度體現了區域土地利用的綜合水平和變化趨勢。樊玉山[19]等提出了土地利用綜合分析方法,將土地利用分為4級(表1),級數越高,土地利用受人類活動影響越大,在此基礎上計算流域土地利用程度綜合指數及土地利用程度變化率[20]。

表1 東江流域土地利用程度賦值表
1.3.3 土地利用轉移矩陣 土地利用轉移矩陣是土地利用變化分析常用的一種方法,以矩陣形式全面的反映研究區各類土地利用相互的轉移情況及土地利用結構變化特征[21]。本研究利用ArcGIS軟件對流域1990和2018年土地利用數據進行疊加分析,制作東江流域1990—2018年土地利用轉移矩陣。
1.3.4 土地利用變化驅動力分析 自然環境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是影響土地利用變化的主要驅動因素,自然因素制約了土地利用空間分布和開發利用程度,社會經濟因素則是土地利用結構變化的主要驅動力[22]。土地利用變化驅動力分析需要建立細致全面的指標體系,主成分分析法基本思路是降維,將驅動力因子中的冗余信息剔除,用較少的指標代替并表達出原來較多的信息[23]。灰色關聯分析通過計算驅動因子與各土地利用面積變化的關聯度,確定因子對土地利用變化的驅動作用的大小,關聯度越大,驅動作用也就越大,反之則越小,該方法有效的克服了單因子分析的假定性,與土地系統的復雜性相適應[24]。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東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社會經濟驅動機制;采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探索社會經濟驅動因子對各土地利用變化的驅動作用,由于未利用地面積較小,本研究不對未利用地變化驅動因子進行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土地利用結構變化分析
1990—2018年東江流域土地利用分布如附圖14所示。流域土地利用以林地和耕地為主,未利用地面積占比最小,1990—2018年土地利用結構變化主要表現為建設用地持續增加,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積逐年減少。1990年,流域林地面積占比為69.08%,林地在流域內分布較為廣泛,1990—2018年,林地面積共計減少了766.039 km2,面積減少主要發生在下游的深圳市和東莞市,至2018年林地面積占比為66.89%。耕地1990年面積占比為19.62%,2000—2005年期間,耕地面積急劇下降,面積占比減少了1.51%,2005年后耕地變化相對平緩,至2018年面積共計減少了1 171.25 km2,流域下游東莞市和深圳市耕地面積減少最為突出,耕地主要分布在流域下游的博羅縣、增城區、惠陽市和惠東縣,沿河流兩岸分布。草地1990年面積占比為3.35%,2018年為3.04%,面積變化較小,主要分布在中游紫金縣、東源縣和連平縣。1990年水域面積占比為4.41%,研究期內面積共計減少了44.749 km2,2018年面積占比為4.28%。1990—2018年,建設用地面積逐年增加,由1990年的1 225.31 km2增長至2018年的3 321.34 km2,面積及占比分別增加了2 096.03 km2和6.34%,2000—2005年期間,建設用地面積增幅最大,流域占比增加了2.46%,2005年后變化幅度減緩,面積增加主要發生在流域中、下游的深圳市、東莞市、惠陽市、增城區和源城區。未利用地在流域內面積占比較少,研究期間面積共計減少了2.3 km2,主要分布在下游東莞市。
2.2 土地利用速度變化
東江流域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以及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詳見表2。

表2 東江流域1990-2018年土地利用面積變化
從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來看,1990—2018年,建設用地土地動態度最大,地類變化速度最快,平均年變化速率為6.09%,其次是未利用地、耕地、草地、林地和水域,土地利用動態度分別為-2.49%,-0.61%,-0.34%,-0.11%和-0.10%。流域未利用地面積基數較小,研究期間面積變化速率較大;耕地、草地和林地的面積減少的變化速率較大,說明隨著流域社會經濟的發展,土地利用受人類活動影響較大。各類土地利用類型在2000—2005年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最大,這一階段土地利用面積變化速率最大。總體來看,1990—2018年流域土地利用變化速率呈先增加后減少趨勢。各類土地利用區域變化幅度差異明顯,草地與耕地區域變化趨勢一致,耕地在流域上游呈增加趨勢,中、下游呈減少趨勢,下游地類變化幅度最大;林地在各流域內均呈減少趨勢,變化幅度較小;水域變化趨勢與耕地相反,在流域上游呈減少趨勢,中、下游呈增加趨勢;建設用地在各子流域內均呈增加趨勢。
各土地利用變化速率呈先增加后減少趨勢,土地利用區域變化趨勢較一致,建設用地表現為:上游>下游>中游,其余土地利用均為:下游>上游>中游,且下游地類變化速率高于流域整體地類變化。1990—2018年,東江流域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先增加后降低,后期土地利用變化速度減緩。依據劉紀遠先生提出的土地利用動態特征劃分標準[25]:急劇變化型(21~24)、快速變化型(13~20)、緩慢變化型(4~12)和極緩慢變化型(0~3),東江流域1990—2018年期間的土地利用綜合動態度為9.75,各子流域分別為9.51,6.72和12.58,流域土地利用處于緩慢變化階段,仍處于較低水平。
2.3 土地利用程度分析
1990—2018年東江流域土地利用綜合指數詳見表3。由表3可知,1990—2018年,東江流域土地利用綜合指數處于中上游水平,土地利用綜合指數持續增加,土地利用綜合指數變化率為大于0,土地利用處于上升發展期。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流域土地利用集約化程度增加,土地利用結構不斷優化。其中,流域上、中游土地利用程度低于流域水平,下游高于流域水平,這可能是由于流域上、中游林地面積比例較大,建設用地面積較小。
2.4 土地利用類型轉化
結合東江流域土地利用轉移矩陣(表4)可知,1990—2018年,建設用地面積增加了2 096.04 km2,其中耕地轉入面積為1 042.85 km2,占到建設用地增加面積的49.75%,林地轉入面積為770.28 km2,占建設用地增加面積的36.75%,林地和耕地是建設用地增加的主要來源。耕地面積共計減少了1 171.25 km2,主要轉出方向為建設用地、水域和林地,凈轉出面積分別為1 042.85,87.70,60.04 km2;林地轉出面積為766.04 km2,主要轉向為建設用地和水域,凈轉出面積為770.28 km2,49.56 km2;草地轉出面積為114.75 km2,主要轉向為建設用地和耕地,凈轉出面積分別為17.88,97.31 km2。水域主要由耕地、林地和草地轉入,凈轉入面積分別為87.70,49.56和3.07 km2,1990—2018年,水域地類面積共計減少44.749 km2,主要轉為建設用地,凈轉出面積為185.54 km2;未利用地面積變化較小,其主要轉向為水域和林地。
對比區域土地利用轉移矩陣(表5),土地利用轉化差異較大。耕地轉化上,上游主要由林地轉入增加,中游和下游耕地主要轉為建設用地;林地轉化上,上游主要轉出方向為耕地,中游和下游則主要轉換為建設用地。草地轉化上,上游主要由林地轉入增加,中、下游主要向建設用地、林地和耕地轉出。水域轉化上,上游主要轉向為耕地,中游主要由林地轉入,下游水域增加來源為林地和耕地的轉入,主要轉出為建設用地;建設用地轉化上,各子流域建設用地面積增加主要來源于耕地和林地的轉入。

表3 東江流域1990-2018年土地利用綜合指數及變化率

表4 東江流域1990-2018年土地利用轉移矩陣 km2

表5 東江流域上、中、下游1990-2018年土地利用轉移矩陣 km2
2.5 驅動土地利用力分析
2.5.1 主成分分析 根據主成分提取條件: ①特征值>1; ②累計貢獻率>85%,提取出兩個主成分因子(貢獻率為95.287%)。第一主成分(貢獻率55.745%)與X3(地區生產總值),X4(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X7(第三產業比例),X8(社會固定資產投資),X9(地方財政支出),X10(地方財政收入),X1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2(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具有較強的正相關,與X6(第二產業比例)具有較強的負相關,這些因子主要與經濟發展水平與社會富裕程度有關,第一主成分主要表達了經濟增長和社會富裕程度的變化。第二主成分(貢獻率39.542%)與X1(總人口),X2(非農業人口),X13(糧食單產),X14(農村機械總動力)存在較強的正相關,與X5(第一產業比例)存在較強的負相關,主要反映了人口增長和農業發展。
根據因子得分矩陣,可得到提取的兩個主成分的表達式,以提取的主成分對應的方差貢獻率占總方差貢獻率的比例為權重,計算得到1990—2018年東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驅動力綜合得分:
F=(55.745F1+39.542F2)/95.287
(3)
式中:F1,F2分別為第一主成分、第二主成分表達式。
由圖1可知,東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綜合驅動力得分逐年增加,變化呈直線上升趨勢,其中1990—2005年土地利用變化綜合驅動力得分為負值,2005年后驅動力得分為正值,東江流域社會經濟驅動因素對土地利用變化影響逐漸增強。
綜合以上分析,本研究將影響東江流域1990—2018年土地利用變化的社會經濟驅動因子歸納為人口增長、經濟增長、社會富裕程度和農業發展。

圖1 東江流域1990-2018年驅動力綜合得分
2.5.2 灰色關聯分析 結合表6可知, ①耕地變化與X5(第一產業比例),X6(第二產業比例),X14(農村機械總動力),X12(農村居民人居純收入)以及X1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子有較高的關聯度,經濟增長特別是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是耕地變化的主要驅動力。 ②林地變化與X5(第一產業比例),X6(第二產業比例),X14(農村機械總動力),X12(農村居民人居純收入)以及X1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子關聯度較高,影響林地變化的驅動因子與耕地一致。 ③草地變化與X5(第一產業比例),X14(農村機械總動力),X6(第二產業比例),X12(農村居民人居純收入)及X1(總人口)有較高的關聯度。影響最大的是經濟增長中產業結構的調整,其次為農業發展、居民生活水平和人口增長。 ④對水域變化影響較大的因子為X12(農村居民人居純收入),X1(總人口),X1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X12(農村居民人居純收入)。居民生活水平和人口增長是主要驅動力。 ⑤對建設用地影響最大的因子為X1(總人口),其次為X2(非農業人口),X13(糧食單產)及X3(地區生產總值)。建設用地變化的主要驅動因子為人口增長、農業發展和經濟增長。總體來說,影響東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的驅動力因子依次為經濟增長、人口增長、社會富裕程度和農業發展,但各社會經濟驅動力并沒有明顯的主次之分。土地利用變化是一個復雜的演變過程,不同地類的影響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把所有驅動因素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對驅動因子有全面的認識,才能完整地揭示土地利用演變過程的驅動機制。
3 討論與結論
3.1 討 論
通過對東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分析可知,區域土地利用變化差異較大,土地利用處于緩慢變化階段,社會經濟發展對流域土地利用變化驅動作用逐漸增加,流域土地利用具有充裕的開發空間,特別是流域中上游地區,但流域土地利用開發過程會受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經濟活動等因素的影響。東江流域上游以山地丘陵為主,中游以丘陵和平原地貌為主,易發生水土流失、水旱災害等自然災害,地形和自然災害限制了土地資源的開發利用;流域下游以沖積平原為主,地勢平坦,土地易被開發利用。流域草地、林地集中分布在中上游地區,耕地和建設用地則主要分布在流域下游,流土地利用空間分布格局及開發利用程度表明了自然地理環境對土地利用的影響。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區域發展規劃差異等也是影響流域土地利用變化的主要因素,區域人口、GDP、城市化水平差異顯著,表現為:下游>中游>上游,人口、社會經濟的快速增長,更易促進非建設用地向建設用地轉化,城鎮化擴張越快,1990—2018年區域土地利用綜合水平與流域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較一致,表明了人口和社會經濟發展對土地利用結構的影響。政府決策方面,為保護東江源區生態環境,贛江政府2003年提出打造“臍橙基地”的產業定位,建設“水源涵養林”,實施以“青山綠水”為重點的生態工程。2005年,中游地區遭遇了百年一遇洪澇災害,政府推進了區域水源林和防護林的建設;此外,韶關市、河源市和梅州市為北部生態經濟發展區,限制了區域林地向其他地類的轉換。

表6 社會經濟驅動因子與土地利用關聯度
下游自改革開放以來,深圳和廣州經濟快速發展,并帶動了東莞市和惠州市的經濟發展,推動了下游地區城市化發展,與2000年之后建設用地面積快速增加、耕地面積急劇減少相呼應。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便捷的區位條件和完善的交通體系給東江流域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結合流域土地利用變化特點,本文提出以下區域發展策略:上游地區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應加強對林地的保護,減少城鎮建設對林地、耕地的影響;中游地區在推進城鎮化和工業化過程中,應提高土地利用集約化水平,減少無序擴張造成的土地資源浪費,加強對重要及敏感生態功能區的保護;下游城鎮化平較高,城市擴張帶來了建設用地供需矛盾突出、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用地比例低等問題,應推進城鎮、工礦和農村居民點整合,促進土地利用布局聚集,并加強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用地保護和生態環境建設。
3.2 結 論
(1) 東江流域土地利用主要以林地和耕地為主,未利用地所占比重最小。1990—2018年,建設用地面積持續增加,其余地類均呈減少趨勢。土地利用變化速率呈先增加后減少趨勢,2000—2005年土地利用變化速率最快;除建設用地外,地類變化速率表現為:下游>上游>中游,上、中、下游流域地類變化差異顯著。
(2) 1990—2018年,流域建設用地主要由耕地和林地轉入,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主要轉向均為建設用地。流域上游林地面積減少顯著,主要向耕地、草地轉化;中游林地、耕地、草地呈減少趨勢,主要轉為建設用地;下游耕地、林地、草地和水域主要向建設用地轉出。
(3) 經濟增長、人口增長、社會富裕程度和農業發展是東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主要的社會經濟驅動因子,驅動因子對流域土地利用變化驅動影響逐年增加。通過灰色關聯分析可知,社會經濟驅動因子對各土地利用變化的驅動作用不同,其中,經濟增長特別是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是影響耕地和林地的主要驅動力;人口增長和居民生活水平是草地和水域的主要驅動力;影響建設用地的因子主要為人口增長、農業發展和經濟增長。
(4)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流域土地利用結構不斷優化,土地利用集約化程度逐漸增加。1990—2018年流域土地利用綜合指數呈直線上升,土地利用綜合指數變化率為0.038,流域處于上升發展階段,土地資源不斷向經濟效益更高的土地利用類型轉變。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開發,未來流域內土地開發利用活動將更加頻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