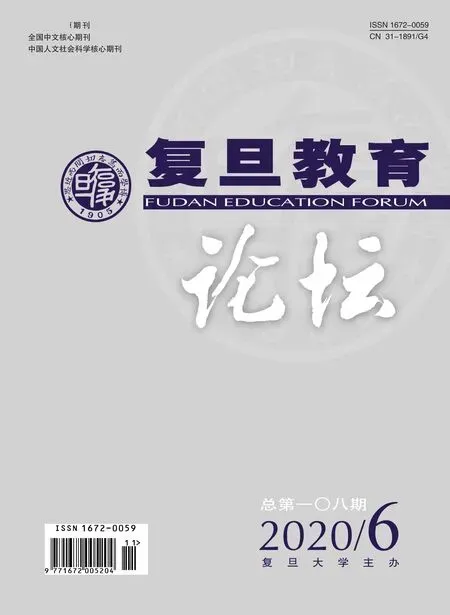澳大利亞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監管政策變遷的歷史沿革與特點分析
朱 浩
(湖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湖北黃石435002)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崛起,為私立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頗具爭議的新途徑,也加速了私立高等教育由一元體系向二元體系的轉變。我國于2017年9月1日正式實施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確立營利性民辦教育的合法性,這意味著民辦教育分類管理改革的國家頂層設計基本完成。但是,在實施環節仍然存在諸多操作性困境,從歷史演進的角度分析澳大利亞政府對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監管政策的變遷,有助于反思我國民辦教育分類管理制度實施過程中的問題。
澳大利亞高等教育體系與我國有著明顯的區別,提供高等教育的機構主要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科研和教學并重的綜合性大學或學院,這種類型以公立大學為主,僅有3 所私立大學;另一類是以教學為主的專門學科的非大學高等院校(NUHEPs),其組成結構更加復雜多元,既有政府所創辦的公立非大學高等院校,又有私人或慈善團體捐資創辦的非營利性私立非大學高等院校,也有教會創辦的各類學院,還有營利性教育集團或私人投資創辦的營利性私立非大學高等院校。目前,澳大利亞119 所非大學高等院校中有68 所屬于私立性質,這其中有65 所隸屬于不同的營利性教育集團。就澳大利亞私立高等教育機構而言,包括3 所私立大學和68 所私立非大學高等院校,它們都能提供高等學歷學位教育,但是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不能獲得政府提供的經常性公共資金。澳大利亞除了綜合性大學和非大學高等院校之外,還有提供高等職業教育的技術與繼續教育學院(TAFE),這類機構是在培訓機構(RTO)中注冊,并不屬于高等院校范疇,因此本研究并未將其納入研究范圍。
2018 年澳大利亞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TEQSA)發布的《高等教育機構統計報告》顯示,澳大利亞共有176 所通過認證注冊的高等教育機構,共計招收1,482,684 名學生。其中,43 所大學屬于“自行認證機構”(SAA),擁有較高的大學自治權,招生人數占到總招生人數的91%;133 所高等教育機構屬于“非自行認證機構”(Non-SAA),包括65 所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54所非營利性高等教育機構和14所高等技術與繼續教育機構。[1]澳大利亞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招生人數相對較少,但其增長速度非常快。2008 年私立高等教育的增長率達到20.8%,而公立大學僅為2.6%,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也從2000 年的5 所增長到2008 年的約150 所。[2]2011 年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增長到170 所,其后澳大利亞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對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進行審核,撤銷一批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注冊,少數機構自行關閉,大型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開展兼并收購,到2018年澳大利亞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減少了47 所。[3]雖然機構數量明顯下降,但是大型高等教育集團發展迅速,如卡普蘭高等教育集團、納維教育集團和IDP教育集團等全球頂尖教育服務機構。值得關注的是,羅瑞特亞洲教育集團(Laureate Education Asia)于2013 年在阿德雷德(Adelaide)中部投資創辦的澳大利亞托倫斯大學(TUA),是43 所澳大利亞大學中唯一的營利性私立大學。
二、澳大利亞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監管政策變遷的歷史分析
澳大利亞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與高等教育市場化進程有著密切的相關性,并在澳大利亞政府出臺私立高等教育政策的歷史變遷中漸次發展。這種變化與澳大利亞高等教育政策和民眾的教育選擇保持一致,同時,也代表著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博弈過程。
(一)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形成期的各方博弈:二戰后到1988年
1901 年頒布的《澳大利亞聯邦憲法》明確規定,教育的具體管理權歸于各州的教育行政部門。因此,在二戰之前,各州的高等教育機構很少獲得聯邦政府的資助,聯邦政府也無權干涉各州的具體教育事務。直至1944 年,澳大利亞政府發布沃克委員會提交的《沃克報告》,為聯邦政府參與各州教育事務提供了法理依據,聯邦政府通過財政資助的方式逐漸控制各州高等教育的領導權。1972 年,惠特拉姆政府采取取消大學學費、實行免費高等教育的教育政策,提供非競爭性聯邦政府助學金,[4]并宣布聯邦政府單獨承擔大學和高級教育學院的教育資助。從1974年開始,聯邦政府對大學的撥款占到學校辦學費用的90%。[5]這一階段澳大利亞私立高等教育的發展特征可以總結為由政府主導、國有化和去私立化,而聯邦政府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1975 年至1983 年弗雷澤自由黨-國家黨聯盟執政期間,澳大利亞聯邦的福利支出增加了46%,而其他社會性支出卻下降了27.5%。[6]從20世紀80 年代起,澳大利亞的公共政策價值取向從各種形式的國家干涉主義轉向更具活力的新自由主義,要求政府放松對教育的管制,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發揮私立教育的作用。這種轉變直接導致澳大利亞高等教育政策的變化,為私立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政策機遇。
1983 年,霍克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對于在高等教育領域是否發展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政府內部存在極大爭議,前后兩任就業、教育與培訓部部長蘇珊·瑞安(Susan Ryan)和約翰·道金斯(John Dawkins)持有不同的態度。蘇珊·瑞安堅決反對發展私立高等教育機構,認為這種機構僅是消耗聯邦公共資金,但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公立高等教育機構,甚至會對澳大利亞高等教育統一的高質量標準產生損害。[5]相比之下,約翰·道金斯并不將私立高等教育機構視為對現行高等教育體系的威脅,因為“在一個以廣泛和高質量的公共供給為主的高等教育制度下,私立高等教育需要大量的資本投資,收益很少甚至沒有回報,因為僅靠收費實際上不能平衡其辦學成本”[5]。20 世紀80 年代末到90 年代初,澳大利亞政府對待私立高等教育的政策導向從國家化和公立化轉向鼓勵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創辦來擴大高等教育經費來源,以滿足民眾不斷增加的高等教育需求,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發展的制度環境開始形成。1988 年,澳大利亞政府頒布《高等教育資助法案》,明確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合法地位,從國家層面的法律上賦予私立高等教育機構自主管理的權利。[7]
(二)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發展期的政策調整:1989年到1995年
1988 年,澳大利亞政府頒布《高等教育——一份政策聲明》,合并原有的高等教育雙軌體制,建立統一的國家高等教育體系,而私立高等教育機構也被納入其中。此時,在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法律文書中都將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稱為“其他機構”,“高等教育私人提供者”“私人提供者”“私立高等教育提供者”等稱呼交替使用來形容此類高等教育機構。[8]1989 年,聯邦政府出臺《高等教育貢獻計劃》(HECS),高等教育收費制度促使高等教育機構進入市場化發展階段,高等教育資助方式和政策環境發生巨大變化,為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1985 年,霍克政府正式實施對海外留學生全額收費制度,鼓勵大學用海外留學生的學費收入彌補辦學經費的不足,并允許公立大學與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開發市場化課程。在1987年頒布的《高等教育:政策討論稿》中首次提出教育是一種產業的觀點,要求高等教育機構拓寬辦學經費來源渠道。此時,聯邦政府對待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采取“權力下放”的政策,將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管理權歸于各州政府,而州政府通常僅要求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符合公司法的規定、通過州或者地區的課程認證即可創辦。因此,20 世紀80 年代末到21 世紀初,澳大利亞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沿著兩條路徑快速發展:
一條發展路徑是在州政府扶持下創辦高質量的非營利性私立大學。坐落于昆士蘭州黃金海岸的邦德大學是澳大利亞第一所私立大學,在澳大利亞邦德公司創始人亞倫·邦德(Alan Bond)和日本電子工業國際公司總裁高橋·原森(Harunori Takahashi)的共同倡議下,于1986年創建,并獲得昆士蘭州總理約翰·彼得森(John Beark Peterson)的大力支持。1987 年4 月9日,昆士蘭州議會通過《邦德大學法案》,確保邦德大學的合法地位和獨立性,邦德大學成為澳大利亞第一所非營利性私立大學,打破了公立大學一統天下的局面。之后,新南威爾士州和西澳大利亞州政府也出臺了鼓勵非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發展的政策。
另外一條發展路徑是與公立大學合作、承接學位課程或共同開發特定課程的混合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隨著海外學生逐年增加,公立大學的教育資源無法滿足其對特定課程的需求,例如英語、商業和經濟學等課程,部分公立大學將過剩的課程需求外包給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來完成,可以說這類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是滿足過剩需求的產物。1985 年,位于西澳大利亞的鹽池國際校園(WA)最早提議發展混合式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隨后澳大利亞商業和技術研究所(AIBT)以及國際管理研究中心(ICMS)開始承接公立大學的外包課程。[5]
企業投資高等教育的愿景和聯邦政府“自由放任”的政策導向為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提供了寬松的發展環境。但是,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教育質量低下問題以及盲目擴增低端私立商學院和預科學院的“爛蘋果”現象引發了澳大利亞社會各界的擔憂,呼吁聯邦政府出臺全國統一的教學規范與標準。1991 年,聯邦政府頒布《海外學生教育服務(教育提供方登記和財務規章)法》之后,出于維護國際聲譽和保護海外學生利益的考慮,要求各州和地方政府負責監督課程注冊,保障教育質量。另一方面,隨著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逐年增加,對于獲得政府財政補貼和統一認證的呼聲也越來越高。1991 年10 月,澳大利亞政府頒布《高等教育:90 年代的質量和多樣化》,要求建立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機制和高教機構之間的學分轉換系統,為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進一步發展奠定政策基礎。
(三)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監管體系形成期的質量保障:1996年到2009年
1996 年3 月11 日,自由黨的黨魁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在大選中獲勝,其為政舉措之一就是極力推行公共部門私有化改革,認為公共服務應該處于競爭的環境之中讓消費者進行選擇,而教育改革勢在必行。1997 年1 月,教育部長阿曼達·瓦恩斯通(Amanda Vanstone)上任之初就委任羅德里克·威斯特(Roderick West)組建教育研究委員會,對澳大利亞高等教育進行廣泛調研并提供政府咨詢報告,之后澳大利亞政府出臺了對高等教育市場化影響重大的政策文件——《大眾定制時代的澳大利亞高等教育》。[9]該文件著重探討聯邦政府對高等教育機構的撥款方式改革,從而提升高等教育機構的市場化水平和競爭力,提出發展成為“完全的經濟市場”,根本宗旨是提高聯邦政府撥款的使用效益。隨后,霍華德政府放開了高等教育機構自主設定學費的權力,加大了對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資助力度。2003 年,澳大利亞政府發布《我們的大學——支撐澳大利亞的未來》,提出兩種新型的聯邦助學貸款方式:一是面向公立高等院校和通過認證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中全額支付學費的學生提供“全額自費—高等教育貸款計劃”(FEEHELP);二是面向到海外接受學位教育的學生提供“海外學習—高等教育貸款計劃”(OS-HELP)。該改革方案在同年頒布的《高等教育支持法案》中得以實施,從而明確聯邦政府對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學生給予資助的基本政策。
隨著聯邦政府介入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澳大利亞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職能分化和多元化趨勢更為明顯。一方面,非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獲得來自聯邦政府的直接撥款。創建于1989 年12 月的澳大利亞圣母大學(UNDA)是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學,聯邦政府在1998年按照《高等教育資助法案》(HEFA)批準其與公立大學同樣擁有獲得聯邦直接撥款的權益,緊接著邦德大學也獲得同樣的權益。另一方面,公立大學的市場化傾向進一步推動混合式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隨著《高等教育貢獻計劃》的深入推行,聯邦政府不再對大學增加經常性撥款,而引進競爭性撥款方式,鼓勵高等院校自主尋求非政府資金來源,這進一步促進了公立大學與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合作。
在這一時期,澳大利亞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與資本市場聯姻,開展大量合并和收購活動,形成大型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集團,與此同時,國際資本也涌入澳大利亞教育市場。2004年12月,由悉尼商業與技術學院(SIBT)、墨爾本商業與技術學院(MIBT)、昆士蘭商業與技術學院(QIBT)、珀斯商業與技術學院(PEBT)、伊迪斯·考恩大學(ECU)和艾恩斯勃利商業與技術學院(EIBT)這6家小型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合并組建的IBT 教育集團在澳大利亞證券交易所(ASX)成功上市,成為澳大利亞第一家公開上市的大型營利性高等教育集團。[10]2007 年11 月,IBT 教育集團更名為納維教育集團(Navitas),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旗下擁有8 所營利性私立非大學高等院校。在澳大利亞國內資本涌入私立高等教育市場的同時,國際資本也開始進入該市場,進一步加劇澳大利亞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內部的整合與競爭。2006 年5 月,隸屬于《華盛頓郵報》旗下的卡普蘭教育集團(Kaplan Inc.)以5600萬澳元成功收購位于新南威爾士州的翠貝卡教育集團,之后進一步收購布拉德福德學院(Bradford College)和田莊商學院(Grange Business School),開啟國際資本收購澳大利亞本土教育集團的先例。從整體上看,澳大利亞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并購有利于形成規模經濟,進而提升高等教育行業品質和國際競爭力,也有利于澳大利亞政府對其進行監管。2003 年,《高等教育支持法案》將非營利性私立非大學高等院校納入聯邦政府直接資助的范圍,將營利性私立非大學高等院校的學生也納入“全額自費—高等教育貸款計劃”(FEE-HELP)的范圍,這一扶持政策極大地推動了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
2000 年3 月,澳大利亞文化、教育、培訓和青年事務部理事會設立了一個獨立的非營利性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機構——澳大利亞大學質量保障署(AUQA)。該機構定期對澳大利亞境內所有高等教育機構進行質量審核,將審核結果反饋給聯邦政府并對民眾發布審核報告,以此確保高等教育機構的教育質量、辦學聲譽以及政府財政資助。同年3月,澳大利亞文化、教育、培訓和青年事務部部長簽署《全國高等教育審批程序議定書》。在此之前,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評審和批準注冊都由各州政府自行進行,沒有統一的標準,實際執行情況也良莠不齊。《全國高等教育審批程序議定書》頒布之后,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準入門檻和教育質量明顯提升,通過審批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可以按照《高等教育支持法案》的規定獲得“全額自費—高等教育貸款計劃”的資助。從2005 年到2011 年的六年中,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獲得聯邦助學貸款資金的比例從2005 年的聯邦助學貸款總資金的9%增加到2009年的總資金的28%,在2009年之后,該比例保持相對穩定。[11]
(四)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監管體系完善期的政策變化:2010年至今
在2008年次貸危機的影響下,澳大利亞私立高等教育快速發展背后產生的問題漸次顯現,過分依賴國際生源、學生學業成就不理想、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之間的監督不協調等問題影響著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2010年,澳大利亞高等教育質量標準署對32所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其中包括20所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進行外部質量審計,包括機構治理、綜合戰略規劃和質量管理、跟蹤和改進績效機制、學生入學情況、政策執行的一致性、學生學業評估等八個指標,審計結果發現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教育質量和學術標準問題突出。[12]
2007 年,陸克文政府委任布拉德利教授(Denise Bradley)組建調查委員會對澳大利亞高等教育進行審查,并于2008 年發布了一份重要報告——《布拉德利評論》(The Bradley Review)。該報告為澳大利亞國內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擴展奠定基礎,并將發展目標設定為“到2020 年澳大利亞國內25 歲到34 歲的青年人擁有學士學位或以上的比例從2006 年的29%增加到40%”[13]。為實現這一總體目標,報告明確提出“未來高等教育行業的政策、監管和融資都必須考慮到通過私立部門所提供的高質量服務來發揮作用”[14],調查委員會建議聯邦政府成立全國統一的、獨立的國家監管機構負責所有類型高等教育機構的監管工作,實現澳大利亞高等教育體系的可持續發展。隨后,澳大利亞聯邦政府于2011 年頒布《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法案》,成立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TEQSA)。該機構具有更加充分的行政權,不僅對所注冊的高等教育機構具有教育質量的建議權,而且對未達標的高等教育機構可以撤銷注冊和課程認證申請,通過質量審核、專業認證和風險評估三方面來實現全方位保障高等教育機構的教育質量,并根據《高等教育標準框架》制定不同層次的統一認證標準,依據高等院校注冊認證的類別,對所有注冊的高等院校分別進行統一認證和分類評估。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正式納入國家統一認證的分類評估體系,也意味著對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管理權通過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從州政府正式過渡到聯邦政府手中。
自2011年成立以來,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對高等教育機構(尤其是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提出了更為嚴格的監管和認證要求。從2011 年到2017 年,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共計收到130份高等教育供應商的認證注冊申請,其中絕大多數是希望通過認證注冊為非自行認證的私立職業培訓學院,2016-2017 年度僅有8所新增機構通過認證注冊。[3]2011年到2018年澳大利亞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的統計報告顯示,澳大利亞私立高等教育的發展呈現機構數量逐年下降而入學人數逐年增加的矛盾現象。這種新現象之所以出現,原因可歸結為兩個主要方面。一方面,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更充分地利用在線學習模式吸引非全日制學生和海外留學生參與在線課程學習,通過線上課程發展離岸教育已經成為新增長點。僅在2014年,澳大利亞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招收在線方式學習的人數增加了20.4%,而傳統大學僅增加8.4%。[3]另一方面,澳大利亞公立大學與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形成深入合作的伙伴關系,合作范圍包括協助預備課程的教學任務、共享師資和校園設施、監督教育質量與學術標準、提供國際生生源以及確保雙方的經濟效益等。目前,納維教育集團與8 所公立大學建立了伙伴關系,攻讀學位教育的學生首先在納維教育集團旗下的高等教育機構完成一年制的預備課程學習,再到其合作的大學完成兩年的本科教育,獲得學士學位。這種合作模式每年為合作大學提供超過7500 萬澳元的辦學收入和超過3000 名生源,其中70%以上為國際生。[2]發展在線課程和公私合作辦學模式已經得到澳大利亞政府的政策支持,并在澳大利亞私立高等教育機構中普遍實施,也對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的監督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
三、澳大利亞政府對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監管的特點分析
澳大利亞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軌跡與其他國家具有諸多相似之處,尤其是公立高等教育占主導地位的國家,都經歷過從“排斥”或者說“邊緣化”到“被動接受”再到“標準化引領”的過程。我們在審視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相似性的同時,也可以認識到不同的地緣政治、區域經濟和傳統文化對私立高等教育發展起到不同的影響,以至于同處于新自由主義影響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亞政府對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監管方式具有其不同于歐美各國的獨特性。
(一)通過間接管理方式控制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逐利行為的度
澳大利亞的高等教育實踐已經充分證明,無論是“完全脫離經濟市場”模式,還是“完全經濟市場”模式都并不符合澳大利亞高等教育發展的實際需要,最理想的狀態是政府通過間接管理方式將高等教育市場化的發展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尤其是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是澳大利亞政府推動高等教育市場化和國際化的產物,辦學性質具有逐利性與公益性并存的特征,澳大利亞政府最終采用間接管理方式來引導其公益性和控制其逐利性。自2000 年澳大利亞政府設立澳大利亞大學質量保障署以來,以“質量標準驅動”為基礎的聯邦資助體系開始形成,澳大利亞政府利用非營利性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機構、聯邦資助經費以及競爭性撥款項目來引導和間接控制澳大利亞高校的發展,其中也包括對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引導。
2011年3月,澳大利亞政府頒布《高等教育標準框架》,進一步明確了高等教育提供者注冊標準、高等教育提供者分類標準、教育提供者課程認證標準以及學歷資格評定標準。[15]《高等教育標準框架》是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對高等教育提供者進行注冊評審和績效評價的重要政策參照,也是澳大利亞高等教育分類的標準,其分類標準是以學歷框架的不同層次來進行劃分,而不是以公立或私立的高校屬性進行分類,因此學術質量標準是按照同一層次內保持一致性的原則來進行評估。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對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從申請、評審、獲批再到課程認證有一套嚴格的質量標準和程序,對其教育質量的監管比對大學教育質量的監管更加嚴格,因為大多數私立非大學高等院校都屬于非自行認證機構。
澳大利亞高等教育資助政策已經形成包括聯邦資助政策、獎學金政策、學生助學貸款政策、捐贈政策以及稅收優惠等在內的相輔相成的政策體系,非營利性私立大學和其他非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與公立高等教育機構享有平等的權利,但是獲得政府資助的首要前提條件是取得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的注冊資格,以此來確保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教育質量。申請聯邦政府資助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必須與政府簽訂資助協議,確立任務書,公開財務與辦學成效信息以確保經費的使用效率,一旦發現私立高等院校舉辦者未能滿足資助的相關要求,聯邦政府有權根據實際情況削減或追回資助經費。澳大利亞2014-2015預算案規定,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想為本校學生提供聯邦資助項目的條件之一便是要公開學校的財務和辦學成效信息。[7]聯邦政府與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簽訂資助協議,制定嚴格規范的信息公開、經費審核和績效評估制度,不僅可以保證資助經費的投入成效,還可以防范非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以非營利之名行營利之實。
(二)通過誘致性制度強化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競爭與合作
鑒于澳大利亞教育管理體制的特殊性,聯邦政府采用強制性制度的運行方式通常難以在短時間內達到教育政策的預期效果,而采用誘致性制度來實現其目的。澳大利亞政府除了經常性撥款和基建撥款之外,還有種類繁多的競爭性資助項目。不同的資助項目有著不同的目的,有著嚴格的條件限制和申報資格,例如研究性資助項目、促進教育公平的資助項目和發展特定目標的資助項目等,實質上這些競爭性資助項目是政府向高校購買教育服務,以實現其發展目標。這些資助項目對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性質并沒有嚴格的限定,主要的限定條件是申請高校必須符合《高等教育標準框架》并且通過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的認定。競爭性資助方式有利于向優質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提供發展所需的經費支持,更重要的是可以引導和促進私立高等教育機構不斷提升教育質量和競爭能力,進而提升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公益性。
隨著澳大利亞政府鼓勵私立高等教育發展政策的實施,澳大利亞不僅擁有了像邦德大學和托倫斯大學這樣著名的私立大學,更發展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營利性高等教育集團,這些私立高等教育機構不僅與公立高校在某些領域產生競爭關系,更可以推動公立高等教育機構開展市場化運作。澳大利亞政府除了鼓勵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之間展開競爭,同樣也支持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通過深入合作來提升國際競爭力和加強社會服務。1994 年,伊迪斯考恩大學與納維教育集團旗下的珀斯工商技術學院簽署第一份合作協議,開啟了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深入合作的新模式。由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提供銜接課程和基礎課程、合作大學提供專業課程的聯合培養模式成為澳大利亞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合作的一種通行做法。
澳大利亞政府除了在制度上支持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開展合作,還根據需要設置各種專項經費項目來激勵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共同合作。例如,為擴大弱勢群體的大學入學機會,澳大利亞政府專門制定了“高等教育公私合作計劃”(HEPPP),提供專項財政資助激勵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參與特殊群體學生的預備課程教學。高等教育公私合作模式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利益共享和風險共擔,而是政府以資助項目的形式控制著私營部門可能出現的高額利潤,使得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共享合作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并確保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獲得相對長期、穩定的教育投資回報,形成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穩定的伙伴關系。
(三)通過分類資助引導私立高等教育機構質量優先發展
《高等教育支持法案》頒布之后,非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獲得申請聯邦資助項目的資格;《我們的大學——支撐澳大利亞的未來》發布之后,聯邦政府將符合資格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中的全額自費生納入高等教育貸款計劃。2016 年1 月,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教育預算案中第一次規定,在所有通過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認證的高等教育機構就讀高級文憑或副學士學位課程的本土學生都可以獲得聯邦直接財政資助,以擴大本土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換而言之,本土學生可以自由選擇不同的高等教育機構,而不受聯邦資助政策的限制。例如,在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就讀學位課程的本土學生與公立高校的學生一樣可以申請“高等教育成本分擔救助計劃”(HECS-HELP)“、學生服務及設備費用補助計劃”(SAHELP),這些資助項目原來僅提供給公立高校的學生。
2018 年澳大利亞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發布的《高等教育機構統計報告》顯示,非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辦學經費來源中,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直接撥款占54%,遠高于歐美國家政府對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撥款;國內外學生學費收入總和僅占18%,其中海外學生的學費收入占7%;非高等教育服務收入占5%,其中包括向海外學生提供英語專修課程(ELICOS)、職業教育與培訓(VET)以及學歷課程(Non-Award)等;其他收入占23%,包括捐贈收入、第三方服務收入和商業收入等。而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辦學經費來源中,國內外學生學費收入達到其總收入的61%,其中海外學生的學費收入占34%;非高等教育服務收入占24%;其他收入占15%;并未獲得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直接撥款。[1]從統計報告中可以發現,非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辦學經費最大的來源是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直接撥款,而學生學費收入還排在其他收入之后,由此可以看到澳大利亞政府鼓勵非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的政策傾向,并提供了公平的政策環境。同時,也可以發現澳大利亞非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對政府的依賴性較強,非高等教育服務項目收入來源最少,由此可以推斷此類教育服務主要是由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完成。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辦學經費來源中,雖然沒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撥款,但是實現了辦學經費來源的多元化,學生學費收入是最主要的辦學經費來源,同時非高等教育服務收入所占比例也很高,這與澳大利亞政府所提供的政府購買服務項目有著密切相關性。除此之外,在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就讀高等教育文憑課程的學生同樣有資格獲得政府的助學貸款。
隨著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快速發展和民眾對高等教育需求的不斷增長,澳大利亞政府高等教育資助政策中對公私立性質的區分和界限更加模糊,但是對于撥款經費的使用效率和效益要求更加嚴格。目前,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對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引導更趨明顯,無論是通過項目形式直接對非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進行撥款,還是通過鼓勵公私合作項目的形式間接資助營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都可以反映出澳大利亞政府對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財政資助政策正在從“機會公平”轉向“質量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