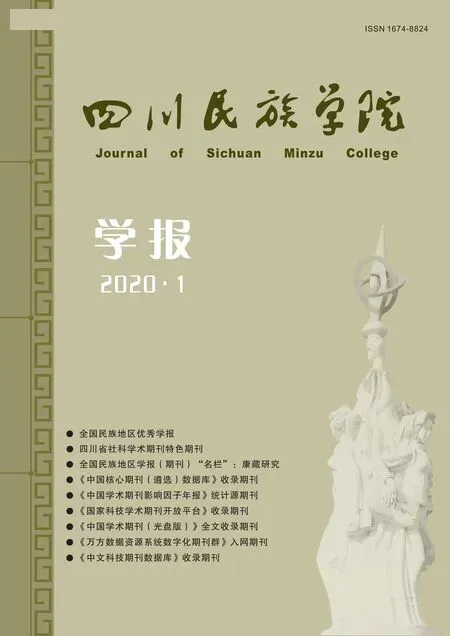碰撞與融合:民族習慣視野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司法適用
陳禹衡 尹 航
2018年10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事訴訟法》)的第三次修正,正式在制度層面上確認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但是對在民族地區如何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卻鮮有提及。在民族地區,其本身擁有的民族習慣對于司法審判有較大的影響,且民族習慣本身便體現出認罪認罰從寬的法律思維傳統,并且擁有一定的特色制度,因而認罪認罰制度在少數民族地區的適用應該結合民族習慣的背景,在民族習慣的助力下加快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推進的整體進程。
一、價值指引:認罪認罰從寬的民族習慣淵源
民族習慣對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推行,適用基礎在于兩者中的內容或者精神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在相當多的民族習慣中,雖然其文本內容本身不如同時期的成文制定法精密,但是其中體現了少數民族所特有的寬恕傳統,因而在價值指引層面,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精神內核可以在民族習慣中尋得蹤跡。
(一)布依族民族習慣中的認罪認罰從寬傳統
在云南布依族的民族習慣中,對于犯罪行為有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的文化傳統,對在其地域內的刑事犯罪根據犯罪類型的不同予以區分。一方面,對于觸犯神靈和宗教習慣類犯罪,其在民族習慣中采用的是完全不寬恕的情形,這是民族習慣受宗教傳統所影響而體現出的特征,早期的神靈崇拜與宗教祭祀便是民族習慣的來源,即使是在制定法所不制裁的領域內,民族習慣依舊扮演了制裁的角色。另一方面,對于行為人是出于過失而導致的犯罪行為,布依族民族習慣會采取較為寬緩的懲罰措施,并且在行為人認罪認罰之后甚至免除刑罰,按照布依族民族習慣,對于認罪認罰的行為人,一般是責令其賠禮道歉、賠償損失,若損害結果不是特別嚴重,甚至可以免于處罰,這和認罪認罰從寬的思想不謀而合。在布依族的民族習慣中,雖然透露出的認罪認罰從寬的思想是不完整的,但是其對于過失類犯罪所采用的認罪認罰從寬的傾向則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民族地區中的適用奠定了群眾基礎,在民族習慣已經體現出對認罪認罰者寬恕的前提之下,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擴展到其他類型的犯罪行為屬于在制定法體系內的自我進化。
(二)藏族民族習慣中認罪認罰從寬的傳統
藏區的刑事民族習慣迥異于其他地區的刑事民族習慣,典型的有賠命價、天罰等具有地域特色和宗教色彩的刑事民族習慣,而在此類民族習慣中,則流露出原始的“認罪認罰從寬”思想,雖然這種思想為罪刑法定原則所排斥,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其價值理念對制定法的滲透。藏族刑事民族習慣中認罪認罰從寬思想的集中體現是賠命價制度,當發生私人斗毆或者部落沖突引發傷害案或者人命案時,用經濟手段進行賠償而取代刑罰措施的行為,對藏區的司法環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本文不支持賠命價的適用,也并不贊同賠命價等同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觀點,兩種制度無論是理論基礎還是實施過程都有天壤之別,但不可否認的是賠命價中所蘊含的價值理念和認罪認罰從寬在某些程度上相契合。
在賠命價制度中,被告人通過賠償釋放了自己認罪認罰的善意,雖然在制定法的視角下,此案仍舊應該按照法定的程序進行,但是在藏族民族習慣的視野下,當事人“認罪認罰”便應該“從寬量刑”,這一觀念已經融入藏族的刑事民族習慣的觀念中。在藏區推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便可以依賴以“賠命價”為代表的刑事民族習慣中的理念來推動該項制度的落實,雖然兩者在立法理念上存在不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為了提高司法審判的效率、簡化訴訟程序、適時分流部分刑事案件的目的[2],但是在特定的場域下,雙方都達成了促進刑事審判的效率并且促進審判結果被接受的目的,因而在藏區推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可以依據其刑事民族習慣中的傳統理念加以推進。
二、罰的建構:民族習慣對認罪認罰從寬中“認罰”的變通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司法適用,除了認罪之外,離不開認罰所體現出的悔罪態度和損害補償,只有在認罰的基礎上才能結合認罪的事實進而從寬,本文采用“認罰的含義是指認法律的懲罰與財產上的懲罰”的觀點[3],在民族習慣盛行的民族地區,可以對財產罰進行變通適用,以期更好的司法適用效果。
(一)財產罰數量上遵從民族習慣傳統
對于認罰中財產罰的數量,適合按照民族習慣中的傳統進行恰當的變通,典型的如蒙古族民族習慣中的“賠九”習俗,在蒙古族民族習慣中,認為九是吉祥的數字,在很多場合都會適用九作為倍數,對損壞財物就應該“賠九”,蒙古的《衛拉特法典》則直接規定“把迷入的牲畜掃印上自家烙印的人,應罰牲畜九頭”[4]。有鑒于此,對于財產罰的數量,可以在總額不違反賠償標準的幅度內建議采用民族習慣中的數量習俗,既照顧到了被害人的利益,充分體現了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誠懇態度,同時也增加了賠償結果的可接受度。在此處的賠償不必拘泥于一般的形式,而是應該采用民族地區最能樂意接受的賠償數量。因此可以借鑒其地域內的民族習慣或者其所有的數字禁忌制定合理的財產數量標準,并且針對不同的民族地區進行調整。例如白族和水族認為6非常神圣,哈薩克族有罰7的習俗,俄羅斯族則因為宗教信仰對13尤為忌諱,雖然這里的數字本身并沒有涉及民族習慣中的刑罰,但是考慮到數字禁忌和民族習慣所擁有的共同的文化傳統背景,將其進行歸納適用。在認罪認罰中的財產罰中如果涉及物品,數量上依據習俗往往會取得更好的效果。
(二)財產罰物品種類上遵從民族習慣傳統
民族地區通行的民族習慣在刑罰措施上所具有的一大特征在于重實體物的刑罰而忽略標準財產的刑罰,這是由于民族地區缺乏法定的貨幣、崇尚以物易物、重視生產資料的文化背景所導致的,即使是在制定法占據絕對優勢的今天,在民族地區進行賠償時仍然會附帶有對生產資料作為實體物的賠償。在民族習慣的視野下,對于認罰不一定僅僅局限在財產的計量賠償,而是可以參照民族習慣對認罰物品的種類進行變通,采用此類變通模式有兩種好處:第一,照顧了民族地區人民的文化傳統和情感依賴,在民族地區對于生產資料的依賴是農耕地區難以理解的,某些情況下賠償馬、騾等牲畜可以更好地恢復被害人的生產,取得的收益更大,也更容易為被害人所接受。第二,民族習慣上處罰的物品的種類不僅僅是概括的說明,還包括物品的形態,諸如閹牛、犏牛等,尤其是當被害人生產資料遭受損失時,一般意義上的損失衡量可能并不能夠準確地反映物主的損失,而采用物品的精準對應則能夠最大限度地彌補損失,因而受到民族地區的群眾歡迎并被寫入民族習慣中。在認罰中的財產罰參考民族習慣的背景下,財產罰的結果顯得更具誠意、被害人更易接受、認罪認罰從寬的司法程序更容易推進,從而達到三方共贏的局面。
(三)法律罰不應該受到民族習慣的影響
雖然通過分析可以發現在民族習慣視野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似乎更容易推動司法程序的運行,但是在法律罰的層面,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能因為對效率的追求喪失對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則和公平正義原則的堅守。罪刑法定原則作為我國依法治國語境下的“宏大敘事”,本身便具有無可辯駁的優先效力,正如張明楷教授所認為的民族習慣雖然看似能代表民意,契合民主主義思想,但是一方面罪刑法定原則的基礎不止民主主義,同時我國的地域過大的實際導致民意難以統一。而且法律的預測可能性原理天然地排斥民族習慣[5]。有鑒于此,即使是在民族習慣的背景下,對于認罰中的“法律罰”,即實體上所規定的法律懲罰也不應該采用民族習慣中的刑罰。一方面,民族習慣中的刑罰多是具有殘酷性的刑罰措施,這些刑罰無疑是對生命權的踐踏,正如貝卡利亞所說“歷史上任何最新的酷刑都從未使決心侵犯社會的人們回心轉意”[6],所以民族習慣中的殘酷刑罰必然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所摒棄。另一方面,出于國家刑罰體系完整性的角度考量,對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也應該適用國家的法定刑作為基準,即使是在民族地區的法院,裁判量刑也應該根據國家的成文法,民族習慣只是推動成文法的適用。
三、 細化區分:習慣對認罪認罰從寬中“從寬”的影響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促使被告人認罪認罰的吸引力在于從寬,而正是從寬的結果同時倒推促使審判效率的提升,民族習慣對于量刑建議的參照和影響一直以來都存在,而民族習慣對量刑的影響理論基礎在于:第一,從責任層面觀察,當一種行為在制定法上被認為是犯罪而民族習慣上被認為是正當,便極有可能促使其責任程度的降低,而責任程度的降低表現在違法性的降低和有責性的降低,認定違法性的大小應該考慮犯罪方法的殘酷性、被害法益的大小等,同時也包括對法益和社會秩序的潛在威脅[7],而民族習慣上的認同則顯著降低了潛在威脅的程度,并從有責性上部分地阻卻了責任。第二,從違法性意識的角度考慮,當行為人所處的社會環境較為閉塞時,民族習慣所擁有的根深蒂固的影響對行為人的生活舉止影響頗大,因而不能夠將民族習慣和制定法的沖突壓力釋放于行為人一個人的身上,而是應該在量刑上予以削減。第三,從期待可能性角度考察,民族習慣所具有的“正當性”傳統使得行為人做出正確的判斷的期待可能性顯著降低,期待可能性在這里的影響程度固然不能達到刑罰存在有無的角度,但是對其量刑的影響作用應該予以正視。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對于民族習慣影響量刑的作用和角色應該予以承認并且加以正視。在民族地區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民族習慣的影響,而現階段對于從寬的幅度并沒有統一的定論,而是根據各地實際情況的不同而適用不同的從寬幅度,這也為民族習慣的影響作用的發揮提供了合適的場域。
現階段的從寬通常適用“3-2-1”階梯式減刑標準,而民族習慣可以在階梯式量刑的幅度內發揮作用,當行為人進行的某行為在民族習慣上并不違法而在成文法上構成違法時,在其認罪認罰之后,可以在通常情況下適用的減刑幅度內下降5%左右的量刑。這樣一方面從寬的幅度不是十分顯著,不會因為民族習慣因素的介入導致量刑幅度陡降,讓群眾產生民族習慣干預司法裁判結果的錯覺,即使是介入了民族習慣的因素,量刑幅度仍舊沒有突破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認罪時間因素對減刑的影響,因而在幅度內的適當減刑不僅不會損害司法的權威性反而會提高裁判結果的可接受度。另一方面,將民族習慣的因素納入從寬的量刑幅度中去,可以有效地削弱民族習慣和制定法之間的沖突,在民族習慣和制定法發生沖突的場域,一般情況下行為人處于制定法上的犯罪人卻同時是民族習慣上的受害者,為了使民憤最大限度地予以消解,在其中納入民族習慣的因素必然是有助于民憤最大限度地降低,因而適宜將其作為一種介入因素予以考量,將兩者間的狀態由角力轉至共生[8]。
四、 內在助力:長老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的作用
在民族習慣中涉及程序法方面的內容,不可忽視的一部分便是在民族習慣中長老的作用。長老在這里是一種概括性的稱謂,并且在不同民族習慣中稱呼迥異,但在現實的司法實踐中,民族地區的調解很大程度依賴長老。根據布朗族的數據顯示,2005年的布朗族老曼娥寨的糾紛調解調查中,多達60%通過當地特色的“高嘎滾(家族長)”進行調解,傾向于政府和法院調解的僅占4%[9]。可見長老在民族地區認罪認罰從寬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一)長老扮演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解釋助力者的角色
長老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扮演解釋者的角色,是基于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認罪應該確保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在其認罰的過程中,由于民族地區的被告人文化程度受限,因而在理解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上容易存在偏差,對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會理解為“誘供”制度,并且質疑司法的公信力,進而衍生出對認罪認罰后不適用從寬的擔憂,而此時長老解釋者的價值便得以發揮。第一,長老在當地具有極高的公信力,由其出面對被告人解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可以利用其宗族公信力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推行背書,能夠促使被告人及時做出符合自己意愿的選擇。第二,由長老出面進行解釋,和傳統的民族習慣的程序相似,當被告人看到自己所熟悉和相信的長老出面進行解釋甚至是勸導時,其內心對司法機關的抵觸會降低,從而傾向于認罪認罰。第三,長老具有語言解釋上的先天優勢,在對被告人進行解釋時用少數民族語言進行解釋易于使被告人理解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內容。
(二)長老扮演被告人權利保護者的助力角色
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對于被告人權利的保護,在民族習慣的視野下,長老的角色可以助力值班律師來對被告人的權利進行更為完善的保護。通常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第一,長老對被告人的幫助可以參與到量刑減輕意見的制定和商討中去,對于具體的量刑結果,可以將其熟知的民族習慣傳統和內容融入量刑意見中去,極具參考價值,在少數民族習慣的背景之下,融入民族習慣思維的量刑意見更易為少數民族群眾所接受并且更具教育意義,對于某些具有較深宗教信仰的被告人而言,此類量刑意見也更有利于其矯正。第二,長老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可以基于被告人文化水平的基礎上,在被告人的文化水平較低的情形下,和其進行溝通交流需要長老參與進行溝通交流。第三,長老在參與到認罪認罰從寬的過程中,對于被告人的心理狀態能夠及時掌握,在被告人認罪認罰后在其所在的宗族社會內部可以進行宣講,從而證明其已經改過自新,這無疑是有利于其改過自新,長老出面可以幫助其矯正后更好地融入宗族群體之內。
(三)長老扮演被害人權利保護助力者的角色
民族地區發生刑事案件,在很多情況下都是熟人間發生沖突,雙方都屬于一個社群內,擁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習慣背景,因而長老肩負起對被害人權利的保護義務。第一,長老可以從合適的角度和方式替被害人傳送其自身對于認罪認罰的被告人的反饋意見,將其作為一種量刑因素提供給司法機關考量,在被害人可能迫于宗族群體的壓力而不敢發聲之時,長老出面對被害人權利的保護則會激發被害人尋求公平正義的信心,維護司法公正。第二,在被害人不方便出面的情形下,長老可以替被害人對被告人的認罪認罰態度進行判斷,長老擁有豐富的經驗,在一個社會群體內,可以依據“品格證據”等綜合因素判斷,這種判斷方式也是“經驗法則和直覺判斷的運用”的一種新的變種[10]。第三,長老對被害人權利的保護的時間跨度可以不僅僅局限在認罪認罰從寬這一個司法流程內,其保護是全面而持久的,在宗族系統內部的熟人社會,長老所具有的權威效力可以有效地阻止同態復仇等情形的發生,可以最大限度地維護被害人的權利。
綜上所述,對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民族習慣視野下的運行,除了制度層面上的借鑒和參考,在人員參與層面也可以吸取民族地區推行刑事和解時的經驗,將長老等角色納入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發揮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對于長老角色的納入,不能混淆其助力者的角色定位,既要重視其作用,同時也不能對其角色定位過分拔高,更不能將其角色升格到決定認罪認罰從寬成立與否的地位,這無疑是將民族習慣中的長老仲裁程序和認罪認罰從寬程序混合,無疑與罪刑法定的大原則相違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民族習慣視野下的運行,不是用民族習慣來取代認罪認罰從寬的司法制度,諸如其中認罪的判斷方法,現階段應該采用更加科學的裁判方法,在不同法益之間予以取舍[11]。
結 語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推行和實施是刑事訴訟改革的重大措施,其從審判公正、裁判效率等多個方面推動刑事審判改革的進行。在民族地區,存在司法環境復雜、刑事審判執行難度大、裁判結果接受率低等情形,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推行,既有契合少數民族“輕刑寬恕”的傳統優勢,同時也面臨司法公信力受質疑、認罪后從寬程度兌現幅度存疑的憂慮。在這樣的背景下,將民族習慣中的精髓內容有限度地融合到認罪認罰從寬的司法程序中,可以促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避免民族地區人民的抵觸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