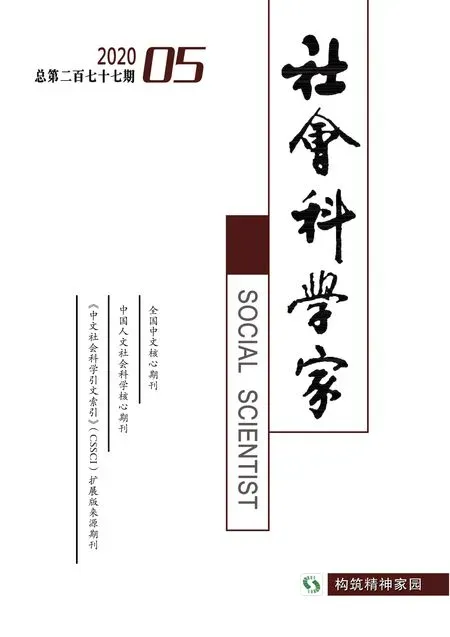通貫、通變與感通
——試論莊子氣論哲學“通”的思想
劉軍鵬,胡棟材
(1.濱州醫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 煙臺 264003;2.中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3)
《莊子》關于“氣”的討論共四十六處,涉及天人之際,內涵豐富及意義重要。①陳洪:《莊蝶之夢與渾沌之死——〈莊子〉“物化”“氣變”論解析》,《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黃柏青:《莊子的氣論及其哲學意義》,《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陳永杰:《〈莊子〉之“氣”辯》,《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尹江鋮:《莊子哲學實則氣學——兼論其理論盲點與理論困境》,《管子學刊》2018年第1期。學界既有的研究,集中表現為三類:一是梳釋莊子氣論思想面貌,注重探討《莊子》氣論的文本問題,同時涉及先秦道家、稷下道家或道教的氣論學說。二是在先秦思想視域下挖掘莊子氣論思想特色,結合相關出土文獻,探討莊子氣論與儒家氣論的關系,以至涉及莊子與張載、朱熹、王夫之等氣論思想關系。三是通過中西哲學比較語境或方法,致力于闡發莊子氣論在審美觀、身體觀、生態哲學及生命哲學等方面的現代意蘊。這些研究各有創獲,然而,從氣論哲學角度揭示莊子“通”的思想,闡發其通貫、通變及感通三義,仍付諸闕如。
一、通貫之義:“通天下一氣”
“氣”作為哲學范疇,在西周時就已出現。《國語·周語》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對此,伯陽父評價:“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這里已出現“天地之氣”概念及陰陽二氣說,并且以氣論通貫天道自然與王道政治。“天地之氣”及陰陽二氣的說法,既是對“云氣”、“六氣”等氣論的概括,同時也是某種超越。莊子“通天下一氣”說,對此有精要說明。
氣論并非道家的首創,而是春秋戰國時期比較流行的思想觀念。[2]“云氣”在《莊子》出現四次,內篇和外篇各兩次,雜篇不見。其中,三次表現為“乘云氣”,見諸《逍遙游》《齊物論》及《天運》,所指的對象分別是神人、至人和龍。在莊子的思想世界里,只有神人、至人和圣人才用“乘云氣”進行描繪,它們都是莊子所追求向往的人生境界,其所謂“至人無己”“圣人無功”“神人無名”。“云氣”在莊子語境中,既是流行變化的,又是創生不已的。“至人”“神人”及“圣人”,正因其隨順天地之氣而不造作,才能做到“乘云氣”。
一旦人違背物之本性,欲圖“有己”、“有功”、“有名”,其情形如《莊子·在宥》所言:“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云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如此一來,云氣、草木、日月都喪失了它們的精粹和自性,而被強以功利、人偽。莊子認為,這就根本談不上“至道”。透過“乘云氣”和“云氣不待族而雨”的比較,不難看到,莊子的“云氣”之辯,指向的正是順應“天地之氣”。與此類似,對“六氣”的言說也有同樣訴求。
《莊子》“六氣”說共兩處,最為人所知的是《逍遙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莊子此處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和前文所論“乘云氣,御飛龍”或“乘云氣,騎日月”,表面極為相似,細加體會,恐不盡然。一般認為,莊子講的“六氣”,就是《左傳·昭公元年》所說的額“陰陽風雨晦明”。郭慶藩認為,除此之外,還有一義,那就是莊子的“六氣”是指“六情”。如果再參證郭象的詮釋,或能更清楚莊子的深意。郭象說:“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游變化之途也。”[3]也就是說,“天地之正”和“六氣之辯”,都不僅僅是指萬物,同樣包括人在內。云氣之說與六氣之辯,都指向天地之氣的通貫。
此外,《莊子·庚桑楚》有關于“六者”的言說:“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蕩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此處“六者”,明確指人的“六情”即“容動色理氣意”。如果說“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是從總體上言明要實現一氣的通貫,那么,這里講的“四六之辯”,則是從具體方法上指明如何通貫人身之氣與天地之氣,以至達到虛明而無為無不為的境地。莊子的“六氣之辯”意指由自然之氣延伸的“六情”,即人與萬物之情感、情狀。“至人”“神人”及“圣人”,就是要實現對“六情”的辨明與超越。
在此基礎上,才能更好揭示莊子“通天下一氣”的通貫思想。《莊子·田子方》說:“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這就是說,萬物的統一性與多樣性,均根源于“一氣”的變化與通貫。氣化的根本特性就在于“通”與“變”,就在于對固定性、差異性及人為性的超越。盡管在莊子之前,已出現“一氣”或“天地之氣”的思想觀念,《大宗師》也提及“游乎天地之一氣”,但明確提出“通天下一氣”之說,并產生深遠的思想影響,邏輯上是從莊子開始的。
相較而言,“游乎天地之一氣”側重個體與自然的關系,“通天下一氣”強調氣化世界的整體性與超越性,后者包含社會管理及政治哲學意味。[4]從中國氣論傳統發展角度來看,后世儒家“盈天地間皆一氣”的氣論觀點,與莊子“游乎天地之一氣”及“通天下一氣”之說既有共通之處,又有細致區別,可形成比較。
二、通變之義:“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
《莊子》氣論哲學的通變之義,直接訴諸氣與身體的關聯性思考,其文本表現,多是通過寓言故事來言說。其中最著名一例,見于《至樂》的“鼓盆而歌”,“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生”“形”“氣”之有無變化,都指向身體的變化流行。所以,我身乃“是天地之委形”,生“是天地之委和”,性命“是天地之委順”。氣的聚散無定,物的變化不息,一切都在長流之中。反之,則“不通乎命”,身體的通變受到窒礙,性命之道無法實現。
在莊子的世界里,人之身體(形體)往往會被降格,因為,形體之于死生,被納入“氣”的維度而來感知、理解和詮釋,以此,莊子對“形”的言說,往往會被看成是荒誕。如《大宗師》描述的,“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于齊,肩高于頂,句贅指天。”《人間世》里面各種丑行怪狀之人,初看起來,實在難以接受和理解。“形”或“形化”在莊子哲學中強調的是身體的轉化。莊子正是要透過這種對“丑”的審視,來戳破人們對“形體”以及習以為常的觀念這層保護層的附著和依賴。由此,《齊物論》對“形”或“形體”進行深刻的反思:“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一有生命及形體,人就難以避免“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莊子是要取消掉身體生命,應該不是。正是基于“形”之“轉變”的考慮,莊子將“丑”納入審美的視野,在氣化世界中對待“死生”,并闡發了“蝴蝶”之喻。“蝴蝶”隨其形變,由丑而美,其生命形象是跳躍的,而生命本身又是易逝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莊子氣論哲學指向一種物化的心性之學。這種心性之學與后來宋明理學的心性哲學有所不同,它的主要面向身心性修養,以求達到“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通變境界。要深入了解莊子的物化心性之學,需要深入體認其氣論視域下的物化觀念。[5]
莊子感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他要使人通徹地體感到,所謂“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是自然而然之事,根本上不需要墜于恐懼的深淵,而是要“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大宗師),“相忘于江湖”即一種“游”的境地。而這種“游”之人,就是“圣人”。《莊子》并不難見“圣人夢”,其中屢言圣人,或以圣人為終極追求。《天下》說:“不離于宗,謂之天人;不離于精,謂之神人;不離于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于變化,謂之圣人。”《天運》說:“圣人者,達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無疑,圣人是莊子的追求。《莊子》屢言圣人,并不意味著他對現實血氣之人種種偏弊就視而不見。相反,莊子正是由于保持著這種圣人理學并堅定追求,所以他對人心性的觀照更是充滿洞見和關懷。
這一洞見與關懷,落實到他以“氣”為主的言說中,也是頗為可觀的。比如,對于人之身體、心性中負面性的“氣”,《莊子》有以下揭示:“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下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達生》)“人氣”“邪氣”和“忿滀之氣”,這三種“氣”,無疑都是有害于身體與心性修養的,它們在一定程度上都不過是人為之情感所生造出來的產物,所以,莊子一方面既講道“有情有信”(《大宗師》),另一方面堅持說要“無情”(《德充符》)、“不近人情”(《逍遙游》),卻又認為要像圣人那樣“達于情而遂于命”(《天運》)。[6]由此可知,莊子的思考是不欠周密性、全局性的,并非簡單的“囈語”。
莊子這種氣論思考,同時表現在他對身心之氣的注意。除了對有礙于修養心性的“氣”,莊子論述了一些積極意義的“氣”,如“神氣”(《天地》《田子方》)、“純氣”(《達生》)、“平氣”(《庚桑楚》)等,在此不一一例舉。要而言之,這些“氣”都是莊子主張要“養”要“守”的,不能遺忘或跌墜。所以,《達生》中這一段話就很有代表性:“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莊子始終強調要“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如此,才能“游乎萬物之終始”。這是莊子一再申說的,也是對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的繼承與發展。
簡言之,莊子氣論哲學的通變之義,就是要通物我之變、生死之變,從而“道通為一”[7]。這個意義上,“道通為一”的通變思想與“通天下一氣”通貫思想基本同義。
三、感通之義:“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
道氣關系是先秦道家思想的核心議題。《老子》論氣不多,道氣關系是其中特別重要的命題,最著名的論述是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此處,道氣關系的規定比較明確。“道”是宇宙的根源,萬物萬有的根本,“氣”則是“道”的體現與階梯。莊子基本繼承了老子道氣關系論,但也有新的發展,那就是強調氣的感通作用。
老子視“道”為宇宙本根的思想,在莊子這里有明確繼承。《莊子·大宗師》說:“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與老子道論相比,莊子將“道”與“天地”的關系做了進一步說明,強調了“道”的重要特質:“自本自根”和“生天生地”。即是說,道作為天地生成的根源,是萬物產生的條件,而其自身是無條件、無所待的。因此,所謂“太極”“六極”的存在,都以“道”為前提。后世儒學特別是宋明理學講太極道體,顯然批判地汲取了莊子道論思想。
更為重要的是,莊子承認道的根本地位,與此同時,氣變得更加顯豁起來。氣不僅成為溝通形上形下、宇宙人生的主體,還深具感通之義。在“通天下一氣”語境下,天地萬物通貫起來,人與自然一體感通,“道”有被擱置的傾向。抑或是說,在莊子這里,比老子更加明顯的是強調氣的“一體”意義上的流行變化與感通的觀念,“一氣”即是“道”。尤其是在《莊子》外雜篇,這一點更加明顯。
學界前賢對莊子哲學的道氣關系均有探討,認識到“氣”的重要性。比如,錢穆認為莊子哲學中的“一氣之”流行轉化,就是所謂道。曹礎基認為,氣是指道產生的作用。張松輝認為,在莊子的哲學中,道與氣是不同的事物,道是規律,氣屬于物質,如果只有道而沒有氣,萬物是不能的;反過來,如果只有氣而沒有道,萬物照樣無法出現。萬物之所以能夠產生、生長乃至死亡,是道與氣相互配合的結果。[8]劉笑敢指出,沒有道,莊子不成為莊子;沒有氣,莊子思想也缺少一個中間環節。[9]有關道氣關系問題認識上的混淆,原因在于沒有深刻把握莊子關于“一氣”的分殊意義,即作為通貫之義的氣、作為通變之義的氣和作為感通之義的氣。而且,“氣”在莊子道論的地位抬升,可能受到稷下學派尤其是稷下道家的影響,也可能與先秦儒家的感通思想有關。[10]
莊子關于道氣關系的創造性智慧,尤其是其感通之義的氣的思想,表現為《莊子·人間世》所提出的“聽之以氣”:“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這一段向來難解,確是理解莊子氣論哲學的關節點。一般意義是上,對于“聽”來說,“聲”是“聽”的直接對象,“耳”是“聽”的物質載體,“聽”受到“心”的控制或左右,“心”是“聽”的主體和主導。但是在“心齋”的語境中,莊子沒有談及“聲”的內容,而只是就“聽”本身進行思考。這遵從的是老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思想義旨。《莊子·齊物論》本身也有“人籟”“地籟”及“天籟”之說。[11]
在莊子看來,“聽”之道,在于由“聽到”達至“聽道”。如何能達至“聽道”?莊子闡發了“聽之以耳”“聽之以心”“聽之以氣”的三個層次。“聽之以心”的“心”指的是“血氣之心”,血氣意義上的“心”,無疑是“氣”的一種表現,“聽”的一個環節,而且還是有待超越的環節。“聽止于耳,心止于符”,從氣質意義上來說,“耳”和“心”都是判斷和滌除機制,“天地之氣”要進入人的身體,“耳”和“心”便要任關卡。關于“聽之以氣”,成玄英說:“如氣柔弱虛空,其心寂泊忘懷,方能應物。”[12]釋德清認為“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是“言心虛至極,以虛而待物。”[13]這些解釋不夠清楚,基本停留在老子哲學層面,未能揭示莊子氣論哲學感通意涵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在“聽”的活動中,莊子對“氣”的看重,無疑在于它是“虛而待物者也”。這樣的“氣”,成為溝通“物”(聽的對象與內容)與“道”(聽的主體與目的)的津梁。“聽之以氣”,是最接近于“聽道”的境界,因為“氣”也是感通天地與人身的樞紐。在“聽”的表現上,就體現為“虛”的狀態。這里的“虛”其實不難解釋,就是指一氣流行與感通。這樣一來,“聽”就接近于“道”。莊子“聽之以氣”的思想,在后世音樂、審美等方面有深刻影響。在道氣關系方面,亦不失為一個創造性觀點。這種道氣關系,對后世儒學理氣關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接引作用。
莊子“通天下一氣”“氣變而有形”及“聽之以氣”諸說,表現出一種獨特而又融合諸家的世界認知與人生追求。實質上,莊子氣論哲學是先秦氣論思想的一次雜糅與融合。[14]這一“通”的思想,內具通貫、通變及感通三義,與其他諸家思想多有會通之處。莊子氣論哲學所蘊含的“通”的思想特質,熔鑄并深刻影響了中國氣論傳統。委實如此,莊子氣論哲學關于“通”之“道”的本體論意義[15],值得進一步探索和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