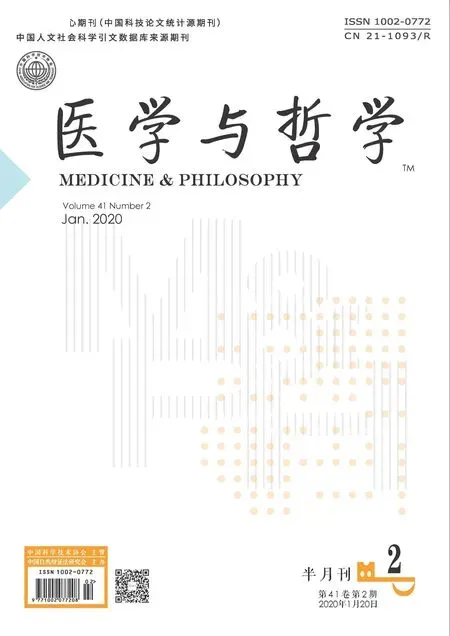基因組學研究免除具體知情同意的倫理挑戰與審查實踐*
康 輝 周偉莉 熊 茜 李 杏 萬 仟 侯 勇
隨著分析工具和方法的飛速進步,基因組測序的時間和經濟成本急劇下降[1],基因組學研究與臨床的結合愈加緊密,研究規模和范圍也大大擴展。這些研究推動了精準醫學時代醫學的進步,在科研倫理審查中的分量日漸增加。
基因組學研究所需的組織、細胞等遺傳材料采集方式一般較便捷,少量材料即可產生大量數據。常用研究材料和數據既可源于臨床診療活動廢棄的生物材料(血液、組織液、活檢組織、手術切除組織),也可來自唾液(含口腔上皮脫落細胞)、毛囊細胞甚至糞便(含腸道上皮脫落細胞)等資源提供者易于自行留樣的材料[2]。少數需特殊手段如切除手術、胚胎植入前篩查、羊水穿刺、腫瘤組織活檢才能獲得的,其采集一般與診療活動伴隨進行,且無需顯著多于診療所需。因此,資源提供者(受試者,含其監護人)留樣的順從性往往較高。但這種“順從留樣”實質未必等于“同意提供”。所獲取的同意形式上常體現為“入院告知書”或“診療告知書”的概括性條款,如“我院可能會使用少許標本進行醫學科學研究”或“我授權醫師對手術切除的組織進行處置”。這種告知難以使資源提供者充分知情,也未明示其應享有的選擇權和退出權。這樣的“同意”是否能被視為合格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值得商榷。研究者使用這樣采集留存的材料開展基因組學研究,需要倫理委員會逐項審慎考量,并共同承擔保護資源提供者權益的責任。
研究者如果不是計劃以具體知情同意(specific consent)方式收集和分析遺傳材料,而是使用以廣泛同意(broad consent)或一攬子同意(blanket consent)方式收集材料,倫理審查就涉及是否同意研究者免除再次知情同意的問題。
原國家衛計委2016年以第11號委主任令形式發布的《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以下簡稱“11號令”)第三十八條規定,需要再次簽署知情同意書的情形包括:“(二)利用過去用于診斷、治療的有身份標識的樣本進行研究的;(三)生物樣本數據庫中有身份標識的人體生物學樣本或者相關臨床病史資料,再次使用進行研究的。”第三十九條規定倫理委員會可以免除簽署知情同意書的條件是:“(一)利用可識別身份信息的人體材料或者數據進行研究,已無法找到該受試者,且研究項目不涉及個人隱私和商業利益的;(二)生物樣本捐獻者已經簽署了知情同意書,同意所捐獻樣本及相關信息可用于所有醫學研究的。”[3]可見,11號令規定的適用“已無法找到受試者”,或僅免除資源提供者再次具體的知情同意。
國際醫學科學組織理事會(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Medical Sciences,CIOMS)與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2016年共同修訂的《涉及人的健康相關研究國際倫理準則》第4版(以下簡稱“CIMOS 2016”)準則11對“研究者試圖使用過去收集和儲存的材料同時又沒有獲得捐贈者對數據未來研究的知情同意”提出免除知情同意的指導原則是:“(1)不免除知情同意,研究不可能或不可行;(2)研究具有重要社會價值;(3)研究對參與者或所在群體的風險不超過最小風險。”[4]與11號令的規定相比,CIOMS 2016免除知情同意的范圍似乎更廣。
審查實踐中,11號令和CIOMS 2016相關準則的適用應結合研究的具體情境進行。
1 基因組學研究申請免除知情同意的典型案例
對于基因組學研究,CIOMS 2016規定的條件(1)“不免除知情同意,研究不可能或不可行”實質為尋回資源提供者并獲取知情同意“不可能或不可行”,亦即11號令“無法找到該受試者”。如留存材料的身份標識不明,資源提供者自然難以通過常規途徑尋回。如果身份標識明確,則有可能有以下情況。
1.1 研究材料或信息具有身份標識但知情同意范圍未覆蓋研究范圍
案例1:某研究者欲以合作單位近年開展細胞保存服務時處理樣品所產生的棄置血漿(約40ml/人·份)為基底液,與腫瘤細胞系批量混合后研發腫瘤DNA液體活檢的標準品。然而細胞保存的知情同意書和服務協議,未考慮和提及醫療廢棄物的研究用途。研究者希望變“廢”為“寶”,申請免除知情同意匿名使用。倫理委員會認為細胞保存服務仍在有效期,要求研究者通過合作單位聯系服務對象征集知情同意。首輪征詢以電子郵件進行,回復率23%,已回復郵件中同意率達97%。研究者稱服務對象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可充分理解科研活動,已回復的同意率極高,未回復的視作默認同意或已“無法找到”,申請推進科研活動。倫理委員會認為已回復人群的高同意率不代表未回復人群的意愿,77%的未回復率不能忽視,服務有效期內“無法找到受試者”不成立。后倫理委員會委托合作單位隨機抽取部分對象電話調查,發現被調查者在完全了解研究內容后有相當比例明確表示不同意,之前不回復是對研究內容不了解或不愿被打擾。因此,倫理委員會的判斷得以證實,未通過免除知情同意申請。
“無法找到受試者”具有一定表面性。研究者往往以獲得的研究材料已編碼化為由聲稱“無法聯系”受試者。實際上,編碼記錄可以通過資源采集方回溯。倫理審查應深入剖析“無法聯系”的真實原因。“無法找到”的標準應設定為該材料初始采集機構所保留的聯系方式均告失效或研究時點明顯超出資源提供者期望生存期。
1.2 研究材料或信息已具有廣泛知情同意
包括CIOMS 2016在內的諸多指南和研究性文章認可,由于研究的確切內容往往未知,所以在樣本采集時不可能獲得具體的知情同意,采用廣泛的知情同意“可以接受”[3,5]。使用這些樣本應通過倫理審查機制對申請逐項把關,保護資源提供者。
案例2:2018年Cell的一項回顧性研究分析了無創產前基因檢測(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NIPT)2011年~2014年間產生的141 431例基因組大數據,產生大量科學發現。在該研究設計和倫理審查階段,倫理委員會檢視到知情同意書模板已注明“我同意在去掉個人信息后,檢測數據可供(經過倫理委員會批準的)研究參考”,即具有廣泛知情同意;由于NIPT數據測序深度(sequencing depth)平均不足0.1x(即個體基因組測序量不到全基因組的1/10),遠小于常規意義的全基因組測序(個人基因組測序深度已普遍達到30x~100x),該項申請定位為群體分析,不對個體特征進行深度挖掘,大數據分析的預期結果降低特定群體社會評價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同意研究者使用未聲明退出(opt-out)的數據,免除再次獲得知情同意。此外,因為國家規定檢測剩余標本、信息和資料的保存期限應不少于3年以備追溯復核,故研究者申請對隨機篩選的40例過期剩余復核樣本進行15x測序,驗證0.1x低深度數據分析方法有效性,且15x測序數據也不進行個體特征分析或公開發表。倫理委員會也予批準。該研究結果連同其研究范式在同行評議中得到廣泛認可[6-7]。
2 免除個人具體知情同意審查的倫理考量
CIOMS 2016免除個人具體知情同意審查的條件(2)“社會價值”的判定與其他研究的倫理審查程序無異,在此不予贅述。另一關鍵依據是條件(3),即研究對參與者或所在群體的風險不超過最小風險。
審查實踐中發現,某些知情同意書對研究風險的描述往往只詳細描述采樣風險,而對數據分析利用風險一筆帶過或者忽視,客觀上使受試者(資源提供者)未充分知情。倫理審查應把這兩種風險區分評估。如前文論證,如采樣風險被視作不超過最小風險[8],則數據分析利用風險應側重于分析結果潛在受益、隱私保護和意外發現等方面。
2.1 再次獲取知情同意對資源提供者的風險受益
案例3:某研究者與某市婦幼保健院合作,利用該院積存的400例0歲~5歲死亡兒童出生體檢干血片從基因組層面分析早夭因素。研究者以該研究對社會群體有利、對個體無害、再次知情同意操作困難為由申請直接開展研究。倫理委員會認為干血片作為死亡兒童留存的唯一遺傳材料,攜帶的遺傳學信息可被適齡父母(即理論上還擁有生育力的父母)用作二胎生育指導,一旦消耗不可再生,具有個體“稀缺性”,不應完全被視為廢棄物。雖然再次聯系有一定難度,但增加了資源提供者(適齡父母)的選擇機會,使其潛在受益大于風險。基于“有利”最大化原則,倫理委員會不同意研究者在不聯系父母(監護人)的情況下直接使用樣本,要求通過醫院嘗試再次獲取具體知情同意。在項目開展過程中,研究者逐漸認識到再次征求父母知情同意其實也平衡了研究者和合作醫院的責任風險。
2.2 遺傳信息隱私保護
生物醫學研究中研究對象編碼化或匿名化是公認的可保護受試者隱私的有效方法。但與其他個體識別性較弱的材料和信息不同,遺傳資源所攜帶的數據和公開數據庫比對后更易還原資源提供者的身份信息,甚至追蹤到其親屬。“千人基因組計劃”3名匿名志愿者的身份就曾由此被識別[9]。在我國已經出現遺傳歧視案例、“反遺傳歧視”立法還不健全的情形下,涉及基因組學研究的隱私保護應格外審慎,特別避免研究結果可能降低個體的社會評價[10]。
2.3 意外發現
案例4:某研究者推測NIPT檢測如果數據出現異常,部分原因可能是受檢者自身疾病(如腫瘤)的干擾,申請直接調取原始數據分析。該NIPT檢測剩余樣本和信息的科研用途也已獲得廣泛知情同意,但知情同意中并未預見和提及腫瘤。考慮到研究的預期發現明顯超出原檢測范圍,對資源提供者有重大影響,倫理委員會依據知情同意書中提及受檢者應接受必要的回訪,不同意研究者免除知情同意,要求研究者修改方案,與資源采集方合作借助醫學隨訪取得擬入組研究對象的再次具體知情同意。該研究后續確實揭示了孕期腫瘤與NIPT檢測數據異常的強關聯性,為孕期腫瘤的發現提供新的精準手段,也使得部分接受隨訪和再次知情同意征集的研究對象直接受益[11]。
如果倫理審查不考慮意外發現,輕易免除具體知情同意,都有可能減損資源提供者的權益:假如意外發現完全不反饋,那么資源提供者就喪失了相關的醫療機會;假如直接告知,那么資源提供者可能因為并沒有做好心理準備,會受到巨大的身心沖擊。這會將研究者和倫理審查機構都陷入尷尬甚至糾紛中。意外發現的結果是否反饋,基本原則是結果是否可靠、是否具有干預措施。美國醫學遺傳學與基因組學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Medical Genetics and Genomics,ACMG)的指南具體描述了遺傳咨詢需要告知資源提供者(受試者)的若干種意外發現,倫理審查可以參考[12]。
3 討論
世界醫學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WMA)2019年10月修訂的大會聲明(EthicalConsiderationsRegardingtheUseofGeneticsinHealthCare)指出,以基因組數據為核心的基因信息具有以下特點:(1)基因信息可以用于識別個體;(2)基因分析能夠大量產出個體的詳細信息;(3)基因分析可能產生額外發現(additional findings);(4)基因分析所得信息的充分含義尚不明確;(5)個體基因信息不可能完全匿名化,去身份識別的基因信息仍然可能被重識別;(6)基因數據蘊含的信息不僅牽涉受檢者,也影響與其有遺傳關系的個體;(7)個體基因檢測勢必需要醫生使用受檢者或與其有遺傳關系個體的醫療信息。因此,基因組學研究的倫理審查應有別于其他生物醫學觀察性研究的審查[13]。遺傳信息的個體特異性、終身伴隨性和族群相關性應成為影響倫理考量的核心要素[14-15]。
2019年7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規定獲得人類遺傳資源應尊重資源提供者的隱私,取得其事先知情同意,保護其合法權益。倫理委員會今后原則上不應受理和批準新采集遺傳資源完全免除知情同意的研究申請。使用過往留存樣本開展研究申請免除個人具體知情同意的,倫理審查應嚴格把握相關法規和指南設定的條件。
CIOMS 2016同時推薦了具體知情同意和廣泛知情同意都可用于生物材料及相關數據的收集、存儲和使用[4]。后者在綜合型生物樣本庫中的應用正逐漸擴大[16]。CIOMS 2016還指明,“廣泛知情同意的倫理可接受性有賴于適當的管理”。倫理審查并不能因為已有廣泛知情同意而削減研究者的責任義務,反而應強化對資源提供者權益的保護,增進和維護社會信任。
就基因組學研究而言,如果研究方案使用的測序數據量不大(深度較低或覆蓋度較小),僅涉及相關突變位點、突變頻率,可以酌情免除具體的知情同意。如果使用個體全基因組高深度數據,或深度分析個人特征,不建議免除。此外,審查還應考量遺傳材料的稀缺性、隱私保護和意外發現。一旦批準免除,需要定期跟蹤,不能“一免了之”。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和公眾隱私意識的廣泛增強,有條件地獲取再次知情同意是一種與廣泛知情同意相配套、增進資源提供者(受試者)對研究內容充分知情、強化資源提供者對個人遺傳信息進行有效控制的手段,應該越來越多被鼓勵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