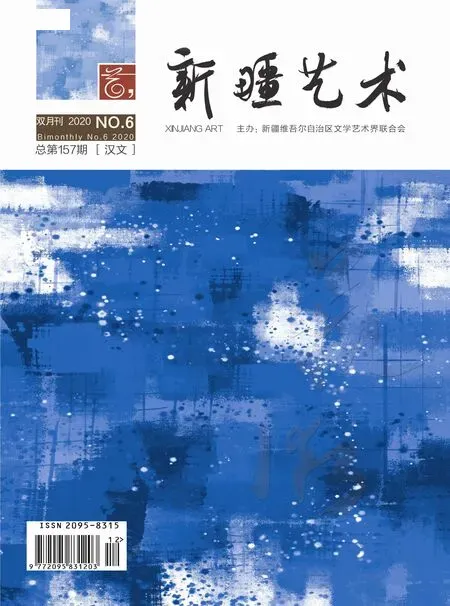陽光枝條上的殘夢
——讀李春海的版畫

李春海版畫作品
一
他被凍醒了。
他沒看到自己睫毛上的白霜,因為一睜眼它們就化了,像一群逃竄的白螞蟻,忽然就沒了。他對著白色的天花板,覺得那是一塊懸著的冰,隨時會塌下來。他覺得整個世界都被凍住了,包括他的手指、記憶、殘夢,連同他堆在墻角的畫和畫里的世界,都被凍住了。
那是北京,顯然是在冬天,2006 年的冬天,草場地附近的北皋藝術區,空曠的倉庫里,堆放著他和他的畫作。
那時間一些搞當代藝術的人把畫賣出了天價,把“觀念”搞成了神話,還有一些拍賣的謊言,讓一些魚目成功地變為珠子。那年月的藝術家、大師或自詡為天才的人很多,但和他都沒扯上關系。他沒有所謂的“觀念”,更沒有編織出什么精彩的故事,雖然他在北京,并且很認真地把三年的時光扔在了這里,但還是沒多少人知道他,不要說媒體,就是一些圈子也沒能進去,借用一句話就是:“你來晚了,棺材里已經有人了。”
二

李春海版畫作品
2009 年的某日,在烏魯木齊七坊街五樓的一間屋子里,陽光很好,他覺得腦子里的一些東西好像解凍了,在醒來,樓下是三三兩兩的車和人,拖著各自的影子在馬路上晃著,路邊坐著一個在陽光下打盹的狗,忽地一陣風過來,大地上的影子都被吹散了,然后一切都消失了,連同他的目光以及那個狗,都消失了。
世界就是這樣結束的,不是砰然一響,而是一聲嗚咽。——艾略特。
那些逃逸的時光,沒有色彩,也沒有形狀,用畫筆逮住它們,似乎很枉然。
不知道什么時候開始,他切開了一些記憶和夢想,制作了一幅幅時間的標本,他用刻刀解剖了時間,把過去和未來的殘肢與器官裝進木板里。這應該就是他的版畫。
讀他的畫有時會讓你進入一次思維的歷險,一次隱秘的感動。
一束光,從很黑的天空落下,黑色被割出一道口子。光的上方,是一個漏斗,光被裝在漏斗里,漏斗里的光所剩不多,眼看著就會被漏光。到那時間,世界會是什么樣子?因為完全的黑暗和完全的光明都會讓這個世界消失,這個世界說不定是需要陰影的,就如同人說不定是需要生命那樣。在光所抵達的地方,一個瘦長而癱軟的人,如同達利癱軟的“鐘表”,又讓人想起《馬拉之死》,一只求救的手伸向天空,想抓住的卻是另一只已經斷裂的手臂。
早晨,太陽躲在山梁的后頭,像一個準備出洞的老鼠,卻遲遲不敢出來,山梁沒有擋住陽光,陽光是一條條干裂的枝條,伸進天空,而另一些陽光,從山梁背后爬過來,是一條條爬行的樹根,向畫面的下方爬來。畫面的下方無疑就是土地了,土地被陽光的根須占領了,這些樹根的上面開始長樹,長出“禁果”,長出了一些衣不遮體的人,也長出了傳說和歷史。
一棵傾斜的樹杈上掛著一只空的皮手套,手套逐漸飽滿起來,手套沒能遮住手背的青筋暴起,所謂的五根手指,是五個“裝在套子里的人”。
這些不在戲劇、電影與小說里,也不是一行一行的詩句,而是一些凝固的瞬間,一些版畫——李春海的版畫。這些矛盾的、魔幻的、枯枝般質感的、充滿現實的苦澀的場景,讓人不自主地會想起一些隱藏于詩與哲學中的東西。似乎人人在其中都能找到了一根可供理解的繩索,但卻無法被人從思維的迷宮里救起。
三
版畫讓很多東西都簡單了,如同一黑一白的兩個音符,也能構成了一曲曲奇妙的樂音。在李春海的版畫里,我們卻能看到一種隱藏的色彩,在極具質感的造型里,膨脹而即將炸裂。
其實人人都有一種心靈的底色,在內心隱秘的角落里,被尋找。
在春海的畫里,有一條隱形的敘事鏈和屬于自己的藝術邏輯。
太陽,光線轉化為枯干的枝條,樹枝轉化為手臂,手臂捏著一個核桃,核桃的另一半被剝開,露出人腦和一張臉。
一條河流,被一根繩索攔腰捆扎,攔截的魚、扎系在繩子中的魚、逃離或漏網的人,同時出現在畫面里。
大地的裂隙里,藏著錯落的牙齒和舌頭,而深淵一樣的喉嚨,是通往另一時空的“蟲洞”。
這種形象的轉接,如同一幅幅動態的蒙太奇,卻發生在這靜態的二維畫面里。這種形象的推演,完成了一種悖論與錯誤,完成了對現實邏輯的游離與背叛,“錯誤”也在不斷地延伸與衍生。
藝術的魔力在于它是一種錯誤。玩藝術其實就是在玩錯誤,錯要錯得離譜,錯得無法無天,錯得讓正確無地自容。正確是可以重復的,而錯誤是無法復制的。思維的出軌有時候不一定就會翻車。春海的畫無疑是一次次的思維“出軌”。
在春海的繪畫中,包含著種種情感敘事,一幅畫中似乎就藏著一個故事,一組畫似乎又構成一種氛圍,一些氛圍又聚攏成星云,從而形成他自己的宇宙。

李春海版畫作品
這些畫里雖有一種蟄伏的語言,但他在觀眾面前,卻放下一架可抵達作品內核的吊橋,讓閱讀成為一種可能。
四
2020 年,整個地球似乎被一張口罩給蓋住了,世界只剩下半張臉了。被隱藏的半張臉里,藏著各種別人不知道的表情,也藏著一些荒誕,一些無法捉摸的事情。
一個著名博物館里的一幅名畫,一天下午,不知怎么就突然自燃起來,瞬間變為灰燼,畫框卻完好無損;在另一家博物館里,一張古老的畫,色彩瞬間脫落,沒有留下一絲痕跡。兩幅畫都是掛在展廳顯眼的位置,掛了很多年。現場都被很多人看見,但沒人找到客觀原因。因此有人基于科學的、準確的、靠譜的推測:這些畫是自我毀滅的,據說真正的藝術都有很強的自毀性。那兩幅畫自殺了!
很多個日子,他做著一個相同的夢:他畫里的人物,不知怎么都從畫布上跑了出來,他被某個聲音叫醒了,他從夢里出來,奇怪地看著自己筆下這些熟悉的東西,在進行一次集體越獄與叛逃,他喊著,讓他們回到畫布里去,沒人聽他的,他們擁出門去,四散著跑向野地,跑向泛著白光的冬天,一道冰雪的高墻推過來,他們都被埋了……
這時間,他醒了,殘夢很快散去。
外面沒有冰雪,只有雨水,他在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