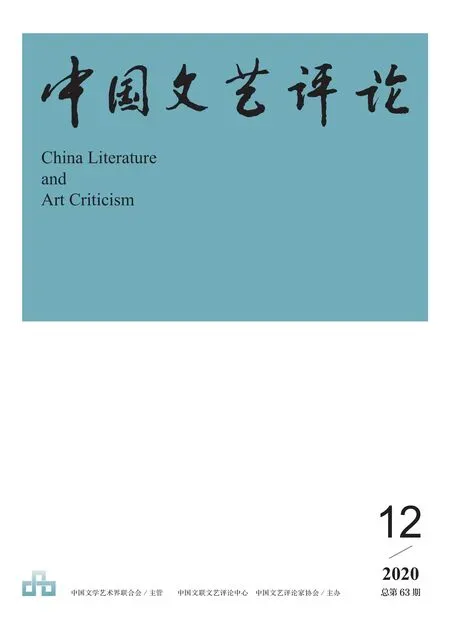王羲之與達?芬奇:兩個中西美術(shù)傳統(tǒng)的象征
[意]畢羅(Pietro De Laurentis)
一、我將王羲之與達?芬奇比較的緣起
我最早公開把王羲之和列奧那多?達?芬奇(簡 稱 達?芬 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作比較是2012年秋天在上海大學(xué)中國當(dāng)代文化研究中心做“書法與符號學(xué)”為主題的報告,在總結(jié)中國書法審美傳統(tǒng)時,我提醒聽眾,中國人眾所周知的《蘭亭序》和世界名畫《蒙娜麗莎》(意大利人平常叫做La Gioconda,約1503-1505年間)具有同等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分量。如果擱置書法與油畫的直接可比性和審美品第問題,這兩幅作品實際上都是各自審美傳統(tǒng)的象征。《蘭亭序》是中國和日本公認的書法傳統(tǒng)的象征,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所評的獎就命名為“中國書法蘭亭獎”。日本、韓國和東南亞一些國家也都有各自的“蘭亭筆會”組織。同樣,《蒙娜麗莎》可以說是近代以來西方最有名的一幅畫,是巴黎盧浮宮的游客最感興趣的作品,即便是文化水平較低的人也非常熟悉這幅畫。
當(dāng)然,這兩幅作品未必是王羲之和達?芬奇最成功的作品,但從社會和文化影響來說,《蘭亭序》和《蒙娜麗莎》可以說已經(jīng)成為各自作者的象征。二者的相似性可概括為:它們都既有濃厚的神秘感又對后代產(chǎn)生了長遠影響。
2019年春天,我在去中國參加“源流?時代:紹興論壇——王羲之與二王學(xué)的構(gòu)建”的國際研討會之前,為了讓我母親充分了解情況,我跟她說,我要到“中國的達?芬奇”的故鄉(xiāng)去參加以他的書藝為主題的重要學(xué)術(shù)活動。我為什么要這么說呢?因為至少在意大利人看來,說起天才,大部分人都會想到達?芬奇,意大利首都羅馬的機場就叫“達?芬奇國際機場”。雖然,西方美術(shù)傳統(tǒng)上偉大的藝術(shù)家很多,而且不少是意大利人,但是,就我個人喜愛而言,達?芬奇留下的作品雖不如同時期的大家豐富——長壽的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和夭亡的拉斐爾(Raffaello Sanzio,1483-1520)都是高產(chǎn)的藝術(shù)家,與達?芬奇并稱“文藝復(fù)興三杰”——但從藝術(shù)境界來講,達?芬奇要高于其他的畫家。
我偏愛達?芬奇也許和我母親有關(guān)。她從1977年當(dāng)全科醫(yī)生以來,診所墻上一直掛著達?芬奇關(guān)于人體解剖的素描版畫,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最早對一幅畫的清晰回憶,就是大概七八歲時母親給我看過《蒙娜麗莎》的照片,當(dāng)時她還問我:“你看看她的面容,她是不是在笑?”所以,一旦要給我媽媽介紹王羲之,我就會把東亞的“書法圣人”和西方的“藝術(shù)巨匠”聯(lián)系起來。后來,隨著我研究《集王圣教序》與王羲之逐漸深入,我發(fā)現(xiàn)了那次不經(jīng)意的比對并不缺乏證據(jù)。
首先,我在2019年下半年買到朱杰勤的《王羲之評傳》,這是1940年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這本書與1948年上海正中書局出版的沈子善《王羲之研究》都是中國最早研究王羲之的圖書。《王羲之評傳》的“引言”中有一段與我對比王羲之與達?芬奇非常接近的話:
以如此偉大之美術(shù)家,倘在海外文明諸國,則必有人為之創(chuàng)立紀(jì)念會矣,提倡王羲之獎金矣,為之舉行百年祭矣,而關(guān)于彼人之年譜列傳,尤多至不可勝數(shù),至少亦視之為拉飛耳(Raphael)、米克朗啟洛(Michelangelo)等儔,為人挦扯殆盡矣。[1]朱杰勤:《王羲之評傳》,長沙:商務(wù)印書館,1940年,第2頁。
雖然,這里并沒把達?芬奇與王羲之作比較,但是,朱氏同樣是把近代繪畫傳統(tǒng)精髓的兩個代表人物與“書圣”作了比較,可以說與我的比喻大同小異。《王羲之評傳》這個提法的目的是提醒更多的中國人意識到王羲之在藝術(shù)上的成就。在2020年的今天,我的目標(biāo)并不在于提醒中國大眾對王羲之應(yīng)該有如何程度的重視,而是提醒世界喜愛美術(shù)的人們,王羲之的藝術(shù)造詣等同于西方最經(jīng)典的藝術(shù)家。
實際上,西方學(xué)者喜仁龍(Osvald Sirén,1879-1966)也早在1933年出版的《中國早期繪畫史》(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ainting)序言里講到:“在中國的藝術(shù)長河中,沒有比王羲之更受歡迎的藝術(shù)家了”[2]“No artist in China has, as a matter of fact, become the object of a more universal admiration than Wang Xizhi.” Sirén, Osvald,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ainting, London: The Medici Society, 1933, p.3.。雖然,他講的是繪畫史而不是書法史,但是,他必須把王羲之放進去,說他是最受歡迎的,在中國是這樣,在日本也是這樣。這種極高的地位也只能讓我們聯(lián)想到西方美術(shù)傳統(tǒng)中同樣被視為巨人的達?芬奇、米開朗基羅等大家。
因此,雖然,王羲之與達?芬奇相距1150年之久,二人所處的歷史、文化與地理環(huán)境截然不同,但是,筆者認為,我們具體觀察兩者在藝術(shù)方面的造詣,還能找出一些共同點。
二、千古典范的《蘭亭序》和《蒙娜麗莎》
只要講《蘭亭序》,絕大部分受過中學(xué)教育的中國人都明白是指什么。它的藝術(shù)價值、文學(xué)和文化地位,中國人一定很清楚。
西方漢學(xué)雖沒有充分注意到《蘭亭序》的藝術(shù)價值,但傳統(tǒng)漢學(xué)研究畢竟是從中國文學(xué)遺產(chǎn)入手的,所以《蘭亭序》作為一篇文學(xué)作品,也早在1879年第一次被翻譯成西文。上海有一位叫晁德蒞(Angelo Zottoli,1826-1902)的意大利傳教士,在他的《中國文學(xué)教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里把《蘭亭序》翻譯成了拉丁文[1]Zottoli, Angelo, 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 Shanghai:Ex typographia missionis catholicae in orphanotrophio tou-se-we, 1879-1882, vol. 4, pp. 295-297.。當(dāng)時傳教士的官方語言是拉丁語,現(xiàn)在理論上還是,但基本上用的是各國的語言,不過,在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術(shù)領(lǐng)域一定要用拉丁文,19世紀(jì)尤其如此。中國文學(xué)的教科書中還收錄了《蘭亭序》,我覺得這已經(jīng)能夠讓我們意識到王羲之《蘭亭序》在書法和文學(xué)上的分量。現(xiàn)存的《蘭亭序》書跡不是原跡,而故宮博物院藏的兩個比較可靠的摹本都不一定是最能夠代表王羲之書風(fēng)的原作。王羲之《蘭亭序》的文本內(nèi)容的真相也是學(xué)術(shù)界爭論的一個熱點。無論如何,即便從初唐以來流傳的《蘭亭序》“神龍本”或元代才開始著錄的“張金界奴本”(通常所謂的“虞世南臨本”)都是可以質(zhì)疑的作品,但它們對其后的書法史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已經(jīng)成為王羲之書法的審美典范。
《蒙娜麗莎》實際上也不止一個版本,目前至少有四個版本(除了盧浮宮的版本以外,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藏品中有一幅被學(xué)者認為可能接近于達?芬奇早期設(shè)想的效果)。這并不奇怪。文藝復(fù)興時期的油畫和壁畫都需要先完成細致的草圖(意大利語叫cartone,即紙板的意思)然后通過上色再完善它,最終成為完整的“畫”。而達?芬奇非常注重草圖的前期工作的細節(jié),一般他畫一幅畫要比其他畫家慢很多(這點他與文藝復(fù)興高產(chǎn)畫家完全不同),甚至有學(xué)者認為他功夫主要是花在草圖上面。《蒙娜麗莎》的可疑性倒沒有《蘭亭序》那么大,除了肖像具體人物和完成年代還有一些爭論,沒有人懷疑它是達?芬奇的原作。而且,對于繪畫創(chuàng)作過程非常緩慢的達?芬奇來說,這幅肖像畫是其得意之作。他在翡冷翠、米蘭、羅馬都隨身帶著這幅畫,應(yīng)法蘭西國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ois I,1494-1547)之邀,在1517年搬到法國的時候,他把這幅畫與后來同樣也納入了巴黎盧浮宮的幾幅作品都帶到了法國。
雖然,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于《蘭亭序》墨跡和《晉書?王羲之傳》的文字的具體內(nèi)容和筆勢的具體形象爭論不休,但可以肯定的是,《蘭亭序》也是王羲之的得意之作。《世說新語?企羨》云:“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2]《晉書?王羲之傳》言辭略有不同:“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聞而甚喜”。。從這則記載可知,因為石崇(249-300)的《金谷詩序》的書法價值未曾有人贊美,王羲之關(guān)心的應(yīng)是《蘭亭序》的文學(xué)價值。遺憾的是,從現(xiàn)存資料來看,《蘭亭序》的書法意義只能從貞觀年間(627-649)編撰的《晉書》和褚遂良(596-658)整理的《右軍書目》兩種文獻來驗證,但那個年代離353年4月25日(永和九年三月三日)那次雅集已有300年之久。不過,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既然王羲之對這篇文章很滿意,無論是《世說新語》所載的“短本”《臨河敘》,還是《晉書?王羲之傳》記載的“長本”《蘭亭序》,王羲之在353年以后到去世的八年間絕對有過抄寫這篇文章的機會,所以我們不可以斷定沒有他親手書寫的《蘭亭序》真跡流傳于世。
王羲之與達?芬奇對各自作品的喜愛或許也是使《蘭亭序》和《蒙娜麗莎》越來越成為兩種不同的藝術(shù)傳統(tǒng)的象征的緣由。盧浮宮文物非常豐富,達?芬奇繪畫不只有《蒙娜麗莎》,但是參觀者對這幅畫的關(guān)注往往要超過其他的藝術(shù)品。《蘭亭序》也經(jīng)常被用來做書法史或書法作品圖書的封面,無疑是印刷版本最多的書法作品之一。甚至在中國書法史上,還有過以“蘭亭”來代稱書法的例子,其中一個例子即12世紀(jì)初的《蘭亭續(xù)帖》[1]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第五卷,武漢:湖北美術(shù)出版社,2002年,第10頁。。
三、兩位“世殊事異”的天才
任何現(xiàn)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天才也很少是孤零零地出現(xiàn)。孫過庭(約646-約690)在他的《書譜》(完成于687年)中說:“而東晉士大人,互相陶染。至于王、謝之族,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fēng)味”。大家可以看出,孫氏提出的解釋是王羲之、王獻之(344-386)、謝安(320-385)、郗愔(313-384)、庾翼(305-345)等豪門子弟之間有頻繁的交往。這是說,雖然王羲之是當(dāng)時絕對頂尖的人物,但是,他周圍的人在書法方面也都有一定的水平。這點正好與達?芬奇長大的地方翡冷翠,包括后來居住過的米蘭和羅馬很有相似之處:除了他以外,當(dāng)時還有非常多的藝術(shù)高手,除了上述的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以外,還有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約1415-1492)、布 拉 曼 特(Donato Bramante,1444-1514)、桑德羅?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 等精通多種手藝的巨匠。因此,王羲之與達?芬奇正好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充滿文藝氣息的時代和文化。故兩位天才具有重要的象征性。
可是我們也不可忽略他們之間的不同。第一,東晉時期的江南與意大利中北部的政治狀況全然不同。首先從地理版圖來看,王羲之曾經(jīng)活動過的今天的江蘇、湖北與浙江,比達?芬奇生活過的翡冷翠、米蘭與羅馬的意大利中北部要大幾倍:今天的托斯卡納、倫巴第和拉齊奧三個大區(qū)一共才62000平方公里,而僅江蘇省就有102000平方公里之多。
當(dāng)然,東晉時期中國南北分裂對立局面造成了江南社會不甚穩(wěn)定的情況——東晉與北方的后趙、前秦、前燕、北魏不斷發(fā)生戰(zhàn)爭,內(nèi)部君臣的陰謀斗爭與變亂也不少,如322年王敦(266-324)在武昌起義到371年桓溫(312-373)讓簡文帝即位。但是,這種局面與15世紀(jì)至16世紀(jì)的意大利中北部還不太一樣,因為意大利并沒有統(tǒng)一,而是包含各個獨立的都城與王國組成的半島(意大利真正意義上的統(tǒng)一始于獲取羅馬的1870年)。
第二,王羲之畢竟是貴族,屬于兩晉有相當(dāng)政治影響的瑯琊王氏家族,是標(biāo)準(zhǔn)的高門子弟。而達?芬奇只是地位較高的公證員之子,由于是婚外所生,一直沒得到父親的正式認可,所以無法走與父親同樣的道路,只能在低卑的工藝圈求個飯碗。這就是說,王羲之受的是當(dāng)時標(biāo)準(zhǔn)的貴族教育,是符合當(dāng)時知識分子標(biāo)準(zhǔn)形象的人物,而達?芬奇只能當(dāng)一個工匠——他自稱是“沒有文史知識的人”(omo sanza lettere)[1]米蘭安波羅修圖書館藏Codex Atlanticus《大西洋手稿》327背。實際上,所謂的“大西洋”是大地圖(atlas)的意思,與大西洋沒有任何關(guān)系。。這句話是他故意用夸張之語抱怨當(dāng)時高傲自大的文人瞧不起像他這樣不懂拉丁文的工匠。在達?芬奇看來,那些“文人”缺乏與自然界的直接溝通。達?芬奇腦子靈光,眼睛敏銳,手藝精巧,希望對自然科學(xué)各種現(xiàn)象做窮盡的研究,但因為他缺乏系統(tǒng)的知識訓(xùn)練,無法查閱古羅馬和古希臘的經(jīng)典著作,只能停留在一個敏銳畫家的寫實分析的狀態(tài)。他心里不把自己看作是畫家,卻自認為是個科學(xué)家。他不僅認為繪畫是科學(xué)的基礎(chǔ),而且還說繪畫的“神性可以把畫家的思想轉(zhuǎn)變成類似于神的思想”[2][意]歐金尼奧?加林:《中世紀(jì)與文藝復(fù)興》,李玉成、李進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2年,第323頁。。在達?芬奇看來,繪畫之所以高于雕塑是因為繪畫所付出的腦力多于體力[3][意]列奧那多?達?芬奇:《達?芬奇論繪畫》,戴逸編譯、朱龍華校,南寧: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第77頁。,這一點有學(xué)者認為他是在故意反駁以雕塑為主要表現(xiàn)手段的米開朗基羅,即他當(dāng)時的主要競爭對手[4]Antonio Forcellino, Leonardo: genio senza pace, Bari-Roma: Laterza, 2016, p. 297.。達?芬奇的繪畫創(chuàng)作一直以光學(xué)研究為基礎(chǔ),作好草圖底稿之后再用毛筆上色,操作時間非常緩慢。實際上他繪畫的真正功夫是花在草圖上的,所以16世紀(jì)初年逾50歲的達?芬奇已經(jīng)不太樂意用畫筆畫畫上色了,經(jīng)常由他畫室的弟子來完成他的底稿。
王羲之首先是個儒家思想環(huán)境培養(yǎng)的士大夫。他向往古代的隱逸之士,沒有在政壇上往上爬的渴望,但作為官員他必須考慮救世安民。從他種種書信和表奏都能看出他務(wù)實的做法和耿直的態(tài)度。我們在《晉書?王羲之傳》讀到的他擔(dān)憂百姓生活的記載,就是證明:
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振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晉書》卷八〇,第2097頁)
另外,王羲之認為“國家之安在于內(nèi)外和”(《晉書》卷八〇,第2094頁),所以他曾經(jīng)規(guī)勸好友殷浩(306-356)和謝萬(約321-361)不要北伐,不幸兩人并沒有聽取王羲之的建議,結(jié)果都以失敗告終。雖然王羲之曾任“護軍將軍”“右軍將軍”,人稱“王右軍”,卻沒有參與過任何戰(zhàn)爭,且極力阻止東晉的北伐戰(zhàn)爭。王羲之一直瞧不起同樣是士族出身的王述(303-368),后來王述成為他的上司,施加報復(fù),王羲之感到羞辱,終于在355年4月30日(永和十一年三月九日)辭官,并到父母墓前發(fā)誓不再做官,足以看出他耿直決絕的性格。

圖1 巨大弩-Ambrosiana-Codice-Atlantico-Codex-Atlanticus-f-149-recto
而達?芬奇則相反,他并不覺得與他的故鄉(xiāng)翡冷翠或曾經(jīng)待過的米蘭的政敵有實際合作關(guān)系是個多么嚴(yán)重的問題。他曾經(jīng)在1500年主動向占領(lǐng)米蘭的法蘭西人自薦,一點都不在意這背叛了自己居住過17年的城市。兩年以后的1502年夏天,達?芬奇還聯(lián)系殘暴的軍人切薩雷?波吉亞(Cesare Borgia,1475-1507)貢獻他的軍事知識,并沒有考慮波吉亞很可能把這些軍事知識用于侵略他的故鄉(xiāng)翡冷翠。1503年7月,波吉亞被打敗以后,達?芬奇還給奧斯曼帝國蘇丹巴耶濟德二世(Bayezid II,1447-1512)寫自薦信表示他有能力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建造一座橋。這封信的阿拉伯文版現(xiàn)藏于伊斯坦布爾托普卡匹皇宮(Top-Qapu Seraj,E 6184)。雖原稿已失,但法蘭西學(xué)會還存有這座橋的初步方案手稿(L.66 背)。達?芬奇出生后一年,即1453年時,信仰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帝國消滅了信仰基督教的東羅馬帝國(395-1453)。從信仰天主教的意大利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伊斯蘭教所謂“不信者”對歐洲產(chǎn)生最直接威脅的開始。但對達?芬奇來說,跟奧斯曼帝國合作并不是個問題。另外,與名實不符的“王右軍”正好相反,達?芬奇確實做出了許多跟軍事科技相關(guān)的方案,《大西洋手稿》收錄的“大火炮”(33正)、“翻墻機”(139正)和“巨大弩”(149正)等圖,同樣出于他超出凡俗的想象力(圖1)。
當(dāng)然,達?芬奇沒有具體的政治理想,主要考慮哪個元首給他發(fā)揮本事的機會,不等于說他沒有個性,從他與米開朗基羅的沖突可以看出他的個性和自信一定會讓他擺脫平凡工匠的命運。而王羲之對官員身份以外的生活還有許多寄托,他畢竟是玄學(xué)和清談風(fēng)氣大背景下的人物,對文學(xué)、音樂和書畫等能夠抒發(fā)情懷的藝術(shù)都有一定的了解,只是書法造詣特別突出而已。
四、高端藝術(shù)相通的三個因素
達?芬奇與王羲之,這兩位天才的個人背景雖截然不同,但作為兩種高端藝術(shù)的代表人物,精神追求與藝術(shù)生涯確有更多相同之處。
其一,與自然界的關(guān)系與情感。
關(guān)于王羲之最著名的一個典故是蘭亭雅集,而他寫的《蘭亭序》一文記述了那次“少長咸集”的“修禊”活動,通過曲水流觴等愜意高雅的交流,還形成了一番向往通達大自然真理的人文氛圍——如“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的著名對聯(lián)所總結(jié)的那樣。這些文人與大自然交際的層面主要是感性的文藝抒情與清談的哲學(xué)探討——甚至不能排斥道教與佛教打坐靜思等各種手段,當(dāng)然出發(fā)點與文藝復(fù)興時期達?芬奇等藝術(shù)家和科學(xué)家所探索的自然科學(xué)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但從個人與大自然的感應(yīng)關(guān)系來講,兩種態(tài)度未必有很大的不同。畢竟王羲之與達?芬奇都是師法大自然,只是所探究的“自然”的定義略有不同而已。王羲之是道教徒,經(jīng)常采藥服食,還跟僧人和佛教徒交往,明顯生活在充滿著形而上色彩的人文環(huán)境中。在《晉書?王羲之傳》中,王羲之自言如下:
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采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dāng)以樂死”。(《晉書》卷八〇,第2101頁)
達?芬奇則相反,他對宗教不感興趣,推崇科學(xué),研究光學(xué)、水力學(xué)、解剖學(xué)等。但如意大利著名的文藝復(fù)興研究專家歐金尼奧?加林(Eugenio Garin,1909-2004)總結(jié)的那樣,“達?芬奇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觀察者,用驚人的說服力審視自己的經(jīng)驗,但是,他并不總是能超越無系統(tǒng)的巫師實驗的進程”[1][意]歐金尼奧?加林:《中世紀(jì)與文藝復(fù)興》,李玉成、李進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2年,第329頁。。他雖提倡科學(xué),并認為數(shù)學(xué)是科學(xué)的基礎(chǔ),卻離不開帶有明顯神學(xué)迷信的中世紀(jì)舊學(xué),與伽利略?伽利萊(Galileo Galilei,1564-1642)的真正科學(xué)精神并不是同一個狀態(tài)[2]Antonio Forcellino, Leonardo: genio senza pace , Bari-Roma: Laterza, 2016, p. 235.。因此,我覺得這點未必與王羲之玄學(xué)清談追求欣賞大自然的感性相矛盾。
可以肯定的是,他們與自然界保持著緊密的關(guān)系,這對他們的藝術(shù)造詣無疑也起過相當(dāng)?shù)淖饔谩?/p>
其二,對個人生涯與時代的悲慨。
客觀地評價王羲之與達?芬奇的生平事跡,不得不承認他們的一生充滿著委屈、痛苦與無奈。王羲之不但對當(dāng)時的政壇有意見,而且對周圍的士大夫也有不滿。他是被趕出出生地瑯琊的北方貴族,又飽受疾患之苦,目睹周圍親友的不幸遭遇,縱觀他留下的書信,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他心里存在著不安之心。日本學(xué)者森野繁夫的《王羲之全書翰》在王羲之書信資料方面最具權(quán)威性。從書末附有《語句索引》可知,王羲之書信出現(xiàn)許多表示感慨的詞語,像“哀悼”“怨望”“畏愁”“禍毒”“悔悼”等(光“哀”字開頭的詞就有20個)[3]參見森野繁夫、佐藤利行:《王羲之全書翰》(增補改訂版),東京:白帝社,1996年,第4-19頁。。雖然,這些詞都屬于當(dāng)時文人書信的套語,但是,依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東晉士大夫的內(nèi)心世界。


圖2a、b 王羲之(左)、達芬奇(上)簽名

圖3 書譜52-61
同樣,達?芬奇一生雖不像王羲之晚年那樣疾病纏身,但一直擔(dān)憂父親不認可他,除了小時候與爺爺奶奶關(guān)系非常甜蜜以外,從沒有感受過家的溫暖,他一直都和學(xué)弟一起生活,沒有成家。另外,因為工作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拖延癥——一方面是他繪畫步驟緩慢,另一方面他的興趣過于雜亂,無法靜下心來完成作品——他也無法與當(dāng)時的藝術(shù)高手競爭。雖然眾人皆知達?芬奇精美絕倫的畫法,但藝術(shù)市場知道他一般都不會按時提交作品,同樣也很清楚他好多工程計劃是很難實現(xiàn)的。反而是他的年輕對手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不但讓訂購者對作品滿意,而且工期也相當(dāng)快,因此他們的收入往往要比達?芬奇高幾倍。
所幸這兩位天才在晚年都獲得了最終的安樂生活:王羲之52歲辭官以后,在浙東一帶享受了回歸自然的祥和瀟灑的六年時光;65歲的達?芬奇在1517年接受了法蘭西國王的邀請后,移居法國西北地區(qū)的昂布瓦斯。法蘭西國王弗朗索瓦一世安排他住在克洛呂塞城堡(Chateau du Clos Lucé)。在這里,達?芬奇很大的程度上回到他幼兒時代的綠色田園生活,與弟子們一起度過他奇特生活的最后三年。
王羲之與達?芬奇一生的失敗或殘缺,在他們留下的書信和筆記中都有詳細的記載,這也是時代的人文情懷和心理寄托的直接反映。
其三,得心應(yīng)手的美妙表現(xiàn)。
據(jù)達?芬奇發(fā)給米蘭君主路德維克?莫羅(Ludovico il Moro,1452-1508)的一封自薦介紹信(《大西洋手稿》1082正),他好像對自己文字書寫的美觀度不是很自信,因為這封信明顯是請了工整大方的專業(yè)書手來抄寫的。達?芬奇一般是從右到左的鏡像寫字,以左手為主右手為輔,所以他的筆記讀起來很費勁。他現(xiàn)存的唯一簽名是在米蘭國家檔案館藏的一張合同上。這是他與弟子在1483年4月25日在公證員面前所簽繪制《巖間圣母》的合同,行文是拉丁文,在頁腳達?芬奇簽署“Io Lionardo da Vinci”(我,列奧那多?達?芬奇)(圖2b),雖然在審美上無法與王羲之《得示帖》(日本皇家藏)署名“王羲之頓首”直接對比(圖2a),但是也并不缺乏自己的趣味。即便書寫對達?芬奇來說只是記錄思辨的語言而不具有書法的藝術(shù)性,然而我相信假如他讀到中國最鮮活精到的書法理論與實踐闡述——孫過庭《書譜》,尤其是第52-61行的內(nèi)容(圖3),他肯定會欣賞孫氏用自然界各種形象來描寫書法筆勢的詞語,像“懸針垂露”“奔雷墜石”“鴻飛獸駭”等說法。孫過庭明確告訴我們,這些都是跟書法的“姿”“態(tài)”“勢”和“形”有關(guān)系的說法。在孫過庭等中國古人看來,書法形態(tài)“同自然之妙有”,確實可以與自然界直接掛鉤。
同樣,達?芬奇所認識的自然界(包括人體在內(nèi))都是將繪畫天才的敏銳的觀察訴諸精巧手筆的結(jié)果。他畫出的各種素描并不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而是探究、分析與描寫自然界的產(chǎn)物,是通過他的思維和審美在畫面上展開再現(xiàn)的自然界,他在筆記中寫道:
畫家的心應(yīng)當(dāng)像一面鏡子,將自己轉(zhuǎn)化為對象的顏色,并如實攝進擺在面前所有物體的形象。應(yīng)該曉得,如果你不是一個能夠用藝術(shù)再現(xiàn)自然一切形態(tài)的多才多藝的能手,那么也就不是一位高明的畫家。[1][意]列奧那多?達?芬奇:《達?芬奇筆記》,杜莉編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年,第5頁。(法蘭西學(xué)會藏Ashburnham 《阿什伯納姆手稿》2背)
這與孫過庭將筆勢比成自然界的某種現(xiàn)象有一定的共同性。雖然,我們還不知道王羲之對書論的核心論點是什么,但是,從“甚有右軍法”[2]米芾:《書史》,盧輔圣編:《中國書畫全集》第一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1999年,第969頁。的孫過庭撰寫的《書譜》可以推論,王羲之應(yīng)該也認同書法與自然界的比擬。王羲之除了《蘭亭序》以外,沒有留下嚴(yán)格意義上的書法作品,但他當(dāng)時肯定有過追求“書法創(chuàng)作”的情景,應(yīng)該還留下過好多符合他審美要求的杰作,可是我們現(xiàn)在只能看到他的幾幅書信的摹本而已。與王羲之完全相反,我們尚能看到達?芬奇真正的作品,雖與同時代的名家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相比數(shù)量不算很多,但至少它們可以代表他的繪畫成就。
實際上,已有學(xué)者指出,體現(xiàn)達?芬奇藝術(shù)造詣絕對超越時代的是他的手稿。他在手稿涉及到的內(nèi)容非常廣泛——繪畫題材練習(xí)、解剖學(xué)、工程、水利、建筑等,直到現(xiàn)在,我們還會發(fā)現(xiàn),他把如此豐富多彩的“對象”都畫得那么精致,那么逼真,簡直令人敬佩不已。正如美國文藝復(fù)興藝術(shù)史專家伯納德?貝倫森(Bernard Berenson,1865-1959)以及歐金尼奧?加林所說的那樣,達?芬奇的素描,畫什么對象都會畫成美麗到極致的效果[3][意]歐金尼奧?加林:《中世紀(jì)與文藝復(fù)興》,李玉成、李進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2年,第195-196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素描當(dāng)成是照相和筆記。無疑是當(dāng)看到了什么令他注意的現(xiàn)象時,他即興把它畫出來,可以說是得心應(yīng)手最直接、最痛快的繪畫表現(xiàn)。這點跟王羲之書信其實非常相似。我們看不到王羲之當(dāng)時應(yīng)該寫得非常工整的《黃庭經(jīng)》等楷書作品的真跡,所以我們欣賞王羲之的書法,和欣賞達?芬奇手稿一樣,也只能依靠具有即興特征的書信摹本[4]達?芬奇現(xiàn)存的繪畫作品一共有27幅,分藏歐美幾所博物館和私人手里。手稿約4100張,裝成22本筆記書冊、3本圖稿合集和許多分散的獨立紙張。見Masters of Art: Leonardo da Vinci ,Hastings:Delphi Classics, 2014; Carmen Bambach , Un’eredità difficile: i disegni ed i manoscritti di Leonardo tra mito e documento, Firenze: Giunti, 2009.。達?芬奇淋漓盡致的線條與局部上色是他幾十年觀察事物和探究幾何學(xué)等功夫的自然結(jié)果。王羲之的生動活潑的筆勢也是他長期抄寫和撰寫各種文本修煉的自然結(jié)果。我想,這兩位天才的作品給我們的一種感覺是他們創(chuàng)作過程并沒有“辛苦”和“做作”。正好相反,他們都是把創(chuàng)作對象——無論是解剖人體還是敘述情景的漢字——自然而然體現(xiàn)在二維的紙面上。不過,因為它們是通曉大自然之形與神的偉大藝術(shù)家所作,充滿著一種超越二維平面的生命和活氣,在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的今天,依然向人類顯露造化之美。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得心應(yīng)手的創(chuàng)作境界實際上就是中國書法所謂“意在筆先”與“胸有成竹”的境界。
王羲之與達?芬奇各自的藝術(shù)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共同點。王羲之少年尚未發(fā)揮自己包括書法在內(nèi)的才能,到了一定年齡之后才達到了最高的境界,《晉書?王羲之傳》記載“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達?芬奇也有類似的情況。學(xué)者已經(jīng)指出,他第一幅獨立的繪畫作品是30歲以后所作——《圣母領(lǐng)報 》(Annunciazione,約1472-1475年 間 )(翡 冷翠烏菲茲美術(shù)館藏),其實尚未脫開安德烈?德爾?委羅基奧(Andrea del Verrocchio,約1435-1488)的影響,只有從1475年左右的《柏諾瓦的圣母》(Madonna Benois,圣彼得堡,埃爾米塔日博物館藏)才達到了自己畫風(fēng)的境界[1]Antonio Forcellino,Leonardo: genio senza pace ,Bari-Roma: Laterza, 2016, p. 88.。這正好跟王羲之書藝的成熟期很相似。他早年的作品《姨母帖》(遼寧省博物館藏)跟他50歲以后寫的《蘭亭序》與《喪亂帖》(日本皇家藏)一樣(圖4a、b),在風(fēng)格上有相當(dāng)?shù)牟煌M瑯樱_?芬奇的《抱銀鼠的女子》(Dama con l’ermellino,1488-1490年間,克拉科夫恰爾托雷斯基博物館藏)、《最后的晚餐》(Cenacolo,1498年,米蘭恩寵圣母堂藏)、《蒙娜麗莎》《施洗者圣約翰》(San Giovanni Battista,約1514年,盧浮宮藏)等大作也都是“暮年之作”。

圖4a、b 王羲之思維《姨母帖》《喪亂帖》
盡管民族與歷史背景各有不同,文化現(xiàn)象與藝術(shù)造詣或有差異,但對精致完美的追求是全世界都相同的。在今天的“地球村”里,東方西方所有民族皆知達?芬奇與文藝復(fù)興名家,但是只有遠東的中國、日本和韓國才了解王羲之與中國古代書法名家。這是歷史原因造成的。正如歐洲學(xué)者喜仁龍所總結(jié)的那樣:“如果我們不能在最偉大的中國書家的筆法中發(fā)現(xiàn)極精微的藝術(shù)品質(zhì),這可能是由于我們?nèi)狈ο胂罅蛯χ袊诵撵`的理解”[2]“If we are unable to discover such supremely artistic qualities in the brush-work of the great Chinese writers, this may be due to our lack of imagi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mind.” Sirén, Osvald,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ainting, London: The Medici Society, p. 3.。孫過庭《書譜》當(dāng)中還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話,將書法筆勢的豐富形態(tài)與文士形而上的探究精神直接聯(lián)系在一起。我相信,這句無疑是指王羲之等書法名家,但是同樣也可以概括西方巨匠達?芬奇:“好異尚奇之士,玩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得推移之奧賾”。
我相信,如果達?芬奇能夠觀摩中國古代書法杰作,也肯定能領(lǐng)會它的奧妙。畢竟,高端藝術(shù)的本質(zhì)是全世界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