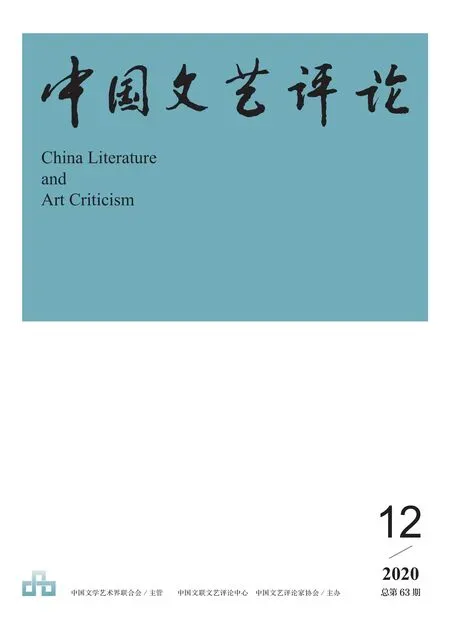歐洲美聲唱法的中國理路
——以應尚能的音樂實踐與理論探索為例
張紅霞
應尚能是我國近現代史上較早研究和介紹歐洲聲樂藝術的音樂家。他在聲樂演唱、理論、教學與創作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績,為中國音樂事業的發展貢獻了自身的力量。廖輔叔曾給予應尚能很高的評價:“像他這樣一位熱愛音樂藝術,熱愛教育事業的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歌唱家和教育家,在音樂人才還很貧乏的舊中國,應該算是難得的人才。”[1]廖輔叔:《關于應尚能先生二三事》,《音樂藝術》1985年第1期,第48頁。下文從若干方面對應尚能的成就與貢獻進行梳理與解讀。
一、應尚能的聲樂演唱與理論認知
美聲唱法在中國的發展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的西式學堂,隨著美聲唱法傳入中國,國內出現了一批按照歐美的發聲方法進行表演的演唱家。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聲樂在國內外聲樂教育家的培養下,有了一定的發展,出現了楊榮東、祁玉珍、周冠卿、沈湘、劉海皋、喻宜萱、周小燕、應尚能等一批演唱家。其中,應尚能是我國最早留學美國學習專業聲樂技法的歌唱家之一,并且是最早在國內舉辦個人獨唱音樂會的音樂家之一。1957年,在其從教26年之際,他在北京藝術師范學院舉辦了獨唱音樂會,演唱了多首意大利、德國歌曲與他創作的《植樹》《無衣》等曲目,這次音樂會是解放后北京首次舉行該類型的音樂會。應尚能留學美國歸來之初,主要以演唱外國作品為主。他在語言方面較為嚴格,能用意、德、法、英等文演唱,講究對語言與風格的精準把握,力求完美地再現作品的內在魅力。應尚能在演出過程中,特別講究與鋼琴伴奏的交相輝映,藝術歌曲的表演中尤其如此。為了兼顧不同聽眾的審美差異,應尚能認為要根據聽眾的不同來選擇作品。為此,他開始走中西融合的路線,借鑒中國的“咬字”規則演唱中外作品。“作為一位出色的男中音歌唱家,他在演唱中的聲音控制始終與音樂的發展層次和歌曲意境有機融會,聲情并茂而又注重藝術的整體表現。在體現出這些不同國家、不同時期、不同風格作品鮮明的藝術特征的同時,又共同賦予了應先生在演唱上樸實而有激情的特點。尤其是他對于舒伯特和黃自藝術歌曲近乎完美的詮釋,給現場聽眾留下了極其深刻、美好的印象,從而給他的演唱生涯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1]戴嘉枋:《應尚能音樂論著及作品選集》,長春:吉林音像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1頁。
應尚能在演唱時比較注重對作品時代背景、思想主題與情感的把握。在語言方面,他一直強調“咬字”的準確性。《國殤》是其在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創作的,音域從d1至g2,跨越11度,該曲具有悲壯與雄偉的色彩,鋼琴以八度伴奏織體來烘托氣氛,需要演唱與伴奏的配合完美契合。該類歌曲還有《吊吳淞》《無衣》等。
關于聲樂的理論認知,應尚能在《以字行腔》《再論以字行腔》《我的聲樂經驗》《聲樂概論》《聲樂的教與學》等文中有較為詳細的解讀。應尚能在教學過程中,依據自身的演唱實踐,并結合中國的發聲方法,總結出一套具有實踐可行性的經驗,其中《以字行腔》作為其遺稿,充分體現了他“民族化”探索道路的重要成果。該書詳細剖析了如何“以字行腔”,如何運用美聲唱好中國歌曲,如何將美聲與中國的文化與文字結合起來等問題。“一般說來,歌聲不能脫離字而抽象地存在……練唱應該從字入手”。[2]劉玲:《應尚能先生遺稿〈以字行腔〉》,《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2年第4期,第60頁。應尚能將美聲的發聲方法與“以字行腔”的演唱原則與規律結合,形成了一套教學體系。關于“字”與“聲”的差異性,應尚能認為“唱的字可能在音量上與講的字有程度的不同,在音域上則與講的字有范圍的不同”。對于咬字的理解,應尚能認為:“字頭、介母和字尾都是轉瞬即逝的部分,都不存在咬字問題,唯有字腹是非咬不可的。”[3]同上。
以字行腔貴在一個“咬”字。那么,如何練習咬字呢?應尚能認為應該從字在歌曲的位置加以強調,同時要區別說話與歌唱咬字的不同。應尚能從字與聲的關系來說明字的重要性,歌聲不能脫離字而單獨存在,有字必有聲,有聲未必成話。如果忽略字的存在,就會容易形成音包字的現象。練習咬字之前,需要明確歌唱中的字與平時說話的字是有區別的。“唱的字可能在音量上與講的字有程度的不同,在音域上有范圍的不同,唱時音高變化的幅度較大,這是明顯的區別。但根本性的區別應該在字的延長部分去尋找答案。”[1]應尚能:《以字行腔》,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年,第6頁。說話時,字與音是對應的,也就是一個音節代表一個字,屬于單音節的文字。但在演唱過程中則要復雜得多。應尚能認為:“唱歌時,字可能由一個到四個部分組成。這四個部分是:字頭、字腹、字尾和歸韻。字頭與字尾都是子音,字腹與歸韻都是母音。因此,子音有兩種形式出現,即字頭、字尾。母音則有三種形式,即介母、字腹、歸韻。”[2]同上,第7頁。在歌唱中究竟如何咬字?應尚能以“五音四呼”為切入點,從生理學的角度闡釋怎樣運用發聲器官來達到正確咬字的目的。“五音”指喉、舌、齒、牙、唇,應尚能認為子音是由五音等部位如何切斷或阻攔氣流而得的。“四呼”指開、齊、撮、合,不同的口型發出各異的母音,應尚能認為母音的發聲除口型之外,還應包括喉結在內的咽腔與口腔等。母音的改變,需要咽腔、口腔與口型等協調一致。
二、應尚能的教學經歷與作品創作
應尚能不僅是一位演唱家,在聲樂教育方面也多有建樹。他曾任教于國立音樂院、國立劇專、國立上海音專、華東師范大學、中國音樂學院等多所院校,是我國最早傳播西洋唱法的聲樂教育家之一。應尚能具備一位優秀聲樂教師所應有的技術與修養,既有精湛的演唱技巧與經驗,也有高尚的道德修養。他一生培養出眾多聲樂人才,如斯義桂、蔡紹序、謝紹曾等等,其中有諸多演唱家享譽國內外。
20世紀30年代,“土洋之爭”的爭論滲透到多個領域,在聲樂界也面臨這樣的困擾。針對“西洋唱法”“本土唱法”的兩種理念,爭論雙方都據理力爭。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雙方采取折中的辦法:“兩種唱法各有優長,又各有不足,不可能用一方取代另一方;惟有長期共存,互相學習,互相促進,才能使兩種唱法都得到發展和提高。”[3]李煥之:《當代中國音樂》,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第345頁。聲樂教學過程中,在曲目選擇時,應尚能雖以歐美藝術歌曲為主,但也積極探索用美聲的發聲方法來演唱蕭友梅、趙元任、黃自等人創作的中國曲目,在借鑒他人創作手法的同時,他自己也開始創作聲樂作品,并將這種嘗試應用到教學當中。
從1931年開始作品創作,應尚能就注重音樂創作的民族性表達,“將來的作品能否發揚我民族的精神?是不是我民族大時代的呼聲?能否代表我國家的文化?”[4]應尚能:《提倡國樂》,《應尚能音樂論著及作品選集》,長春:吉林音像出版社,2003年,第25頁。他提出的三個標準在今天看來也還是適用的。關于應尚能的創作特征,戴嘉枋曾評價:“他的音樂創作風格質樸流暢、情感凝練內蘊。音樂結構嚴謹而富有層次感。在音樂的旋律及和聲的運用上,他注重將歐洲古典藝術歌曲的表現手法,同曲調與民族語言的聲調、語勢及情感的結合,所以音樂不失其民族風格。”[1]戴嘉枋:《應尚能音樂論著及作品選集》,長春:吉林音像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2頁。筆者認為,可以將應尚能的教學經歷及作品創作分為三個時間段。
第一,初期階段。主要指應尚能在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教學期間,即在他學成歸國到抗日戰爭爆發之前,時間跨度為1931年至1937年。
1930年5月,應尚能從美國留學歸國,在黃自、蕭友梅的幫助下在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舉辦個人音樂會。這次音樂會引起當時中國音樂界的轟動,堪稱美聲唱法在中國傳播的先例。次年,他受聘于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除聲樂以外,他還教授視唱、合唱等課程。期間,應尚能認真教學,得到廣大師生的認可。他在該階段創作的作品主要有《梨花落》《我儂詞》《燕語》《寄所思》《吊吳淞》等。《我儂詞》是應尚能根據管道昇(趙孟頫的妻子)的同名詩詞來譜曲的,該詞是管道昇寫給趙孟頫的,表達了她對丈夫納妾一事的看法,用詞婉轉,將兩人比喻成泥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可以看出他們兩人的深厚情感。應尚能根據歌詞的音調和格律,遵循漢語四聲的特點,排除了演唱時倒字的現象,深化了“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意境。1932年1月28日,日本為了迫使南京國民政府答應其無禮要求,發動對上海中國守軍的進攻。全國人民對日本的侵略行為十分憤慨,文藝界也加入到聲討之中,音樂藝文社組織上海音專師生赴杭州舉行“鼓舞敵愾后援音樂會”,應尚能在音樂會上演唱了他創作的《吊吳淞》,緬懷在戰斗中犧牲的愛國將士。該歌曲是由韋瀚章作詞的一首藝術歌曲,結構簡單而精練,鋼琴伴奏與音樂旋律結合巧妙,情感變化豐富,體現出作者的愛國之心。應尚能在演唱時將歌詞、旋律仔細分析,注重音樂與伴奏的關系,將整首歌曲的感情、意義完整地表達出來。
第二,中期階段。主要是指應尚能在抗日戰爭爆發后到新中國成立之前,時間從1937年到1948年。1937年,應尚能在上海國立音專的聘期已到,并沒有被音專續聘,輾轉多地最終在重慶落腳,擔任國民政府音樂教育委員會委員一職并兼任秘書,后任社會組組長。應尚能主要做宣傳與音樂的普及工作,此地的工作和實踐成為他音樂事業的又一起點。在應尚能等一批有志青年的共同努力下,重慶成為戰時國統區的音樂教育中心。在這個階段,應尚能參與多種關于音樂的會議,“審核學校校歌”“音樂推廣人員訓練班”“搜集民歌”等決議就是在這些會議上形成的。期間,應尚能任實驗巡回歌詠團的團長兼指揮,帶領二十余人的歌詠團奔赴城鎮開展抗日宣傳。1940年他前往重慶青木關音樂院工作,任教務主任,為音樂院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應尚能在此階段的工作變動較大,先后又在江安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松林崗國立音樂分院、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滬江大學等院校工作。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最早在四川的璧山,是當時全國唯一的且較為完備的成人教育學院,在全國具有重要的影響力。應尚能被聘為聲樂教授,并主持藝術教育系的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后,重慶的許多大專院校逐漸搬遷到其他地區,國立社會教育學院也位列其中。在這個過程中,因經費的問題,無法及時建立新的校區,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在1946年9月搬往蘇州拙政園。后來,為了便于管理,其他校區的學生陸續搬遷到蘇州。作為該院的教師,應尚能隨學院一起前往蘇州任教,并在蘇州定居,為蘇州的音樂教育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該院音樂組匯聚了一批著名的音樂家,除了應尚能,還有聲樂家孫靜錄,作曲家劉雪庵、張定和,理論家錢仁康,鋼琴家洪琦,二胡演奏家陸修堂、黎松壽等。這樣的優秀教學團隊在當時是較為少見的。資料顯示,應尚能在1946年至1951年還曾在滬江大學(1951年滬江大學的音樂系并入華東師范大學,應尚能繼續任教并作為系主任主持工作)任教。重慶國立音樂院分院(后改名為“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于1946年搬至上海,應尚能擔任聲樂組主任。從時間上來看,應尚能在蘇州、上海兩地三校任教。雖然到處奔波,但應尚能依然能克服困難,為自己熱衷的音樂事業而奮斗。與滬江大學音樂系一樣,1951年蘇州國立社會教育學院藝術教育系被華東師范大學音樂系并入,應尚能在蘇州的音樂教學活動也隨著此次合并而結束。
在繼續自己的音樂教育工作的同時,應尚能的聲樂作品創作也沒有停滯,創作的作品包括獨唱、重唱、合唱、清唱劇與鋼琴曲等。《國殤》《破陣子》《炯炯丹心》《荊軻插曲》等作品表現了應尚能的愛國主義熱情。尤其是三幕清唱劇《荊軻插曲》中,荊軻為了深受災難的人民,懷著“殺盡天下奸雄,鏟除天下兇邪”的決心前往秦國,全曲以“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一慷慨悲壯的詩句結束,足見應尚能對身處危難之中的國家與人民的關切。
第三,后期階段。主要是指應尚能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的音樂實踐,時間從1949年到1973年。
1951年,應尚能擔任華東師范大學音樂系主任。音樂系在應尚能的影響下平穩發展,他的教學與行政工作得到大家的肯定與認可。“由于他對同事們在生活上處處關心,事事照顧,在工作上又愛才用才,放手信任地鼓勵教師們發揮自己的專長,他盡心竭力于教育事業。又因為他為人隨和,善于團結系里同仁,所以大家專心治學,合力工作,彼此相處得十分融洽。他把音樂系的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條。”[1]馬革順:《應尚能音樂論著及作品選集》,長春:吉林音像出版社,2003年,“序“,第1頁。1956年,華東師范大學的音樂系與北京師范大學音樂系合并成立北京藝術師范學院。應尚能前往北京藝術師范學院任教,同時受上海音樂學院的邀請擔任該院的聲樂教授。此時的應尚能為了祖國的教育事業,奔波于不同的院校,在北京、上海兩地任教。1964年他隨北京藝術師范學院一起進入中國音樂學院。
應尚能在該時期創作的作品形式多樣,如《歌唱和平的生活》《歌唱中國共產黨》《夜歌》《摘下果子香又甜》《告訴親愛的母親》等,既有歌頌勞動英雄的,也有描寫邊防戰士對祖國的思念的。《歌唱和平生活》《歌唱中國共產黨》兩首歌曲是應尚能為數不多的自己作詞的作品,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應尚能對中國共產黨的愛戴與擁護,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又有歡樂,又有和平,又有幸福”。
三、結語
應尚能作為吸收西洋唱法發展中國聲樂的先驅之一,強調民族語言的重要性,為中國的美聲唱法作出重要貢獻。此外,應尚能在創作方面也表現出不凡的能力,他創作的作品講究結構嚴謹,層次分明,和聲具有歐洲古典與浪漫的氣息,旋律兼具歐洲與東方的特點。他在教學與科研方面也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特別是“以字行腔”理論在教學中的實踐運用與理論升華,更是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遺產。作為一個具備國際視野的音樂家,應尚能從留學回國以來,一直致力于國內的音樂事業,“以他畢生的精力,探索著音樂報國的發展歷程;以他滿腔的熱忱,譜寫了平凡人生的華彩樂章。為了建立中國的聲樂藝術而付出的心血,正澆灌著當今百花齊放的樂壇”。[1]杜昀鵬:《歌唱之道:以字行腔——追憶應尚能的藝術人生及其藝術探索歷程》,《天津音樂學院學報(天籟)》2011年第4期,第26頁。期間雖歷經艱辛,但應尚能仍懷著樂觀的態度繼續前行,對中國聲樂事業的開拓奠定了基礎,為祖國的崛起與文化的繁榮作出自身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