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陶勇: 學醫是一種信仰, 它賜予我不平凡的前半生, 也將使我余生更加精彩
車翀 姚宇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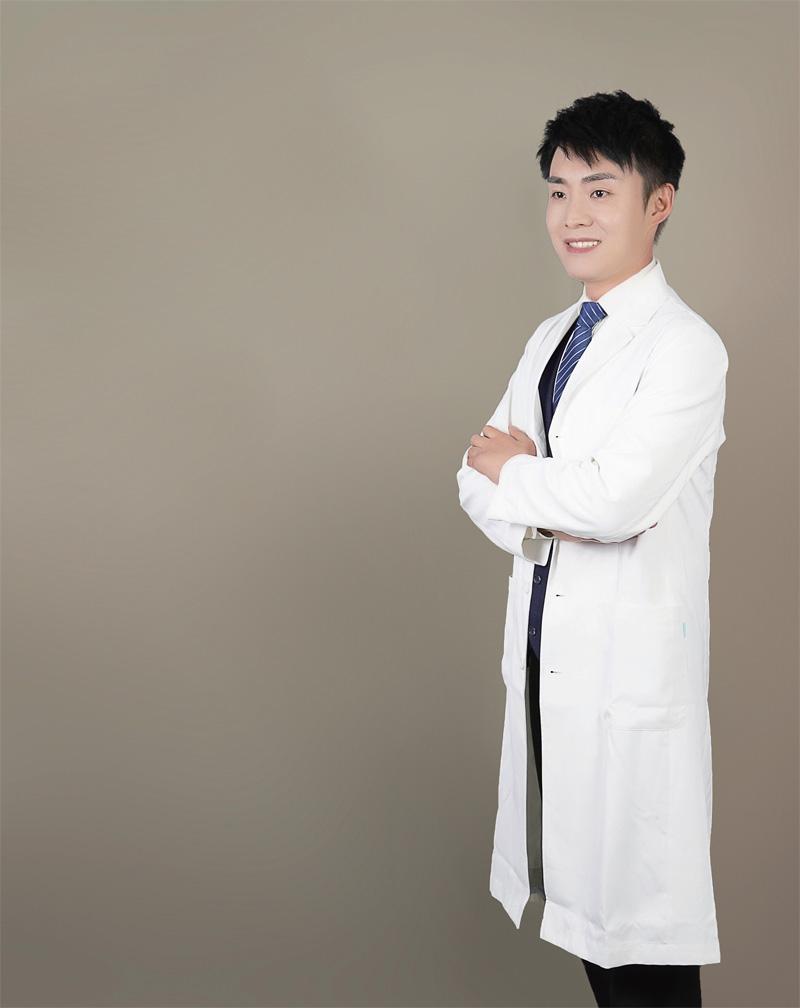
〇 陶勇:是傷者,但更是醫生
“很有意思,學了醫你就會覺得人體特別神奇。”聊起專業相關的內容時,陶勇的眼神突然明亮起來,“如果能治好疾病,就會覺得自己做的事很有價值。”
陶勇為何會選擇醫學,又為何選擇比較冷門的眼科專業,還得從他的童年說起。陶勇的家鄉在江西省南城縣,這里屬于我國沙眼高發的地區,當地許多人都因沙眼而飽受折磨,其中也包括他的母親。有一次,陶勇陪母親到南昌看病,當目睹醫生用針從母親眼中挑出一粒粒白色的結石,母親的痛苦得到緩解時,他便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名眼科醫生。
“擁有目標的人總是更容易成功一些。”立志成為眼科醫生的陶勇以高考省招生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部,師從名醫黎曉新教授。27歲博士畢業后,進入醫院工作的陶勇與讀書時一樣,仍舊滿懷著對醫學的敬仰和一顆鉆研之心。陶勇笑談道,自己常常向學生們發出靈魂拷問:“我怎么感覺不到你對醫學的熱愛?”在他看來,有些學生和年輕醫生對醫學的熱愛還遠遠不夠。醫學雖是一門專業,但更像是一種信仰,學醫、治病、救人都能讓熱愛醫學的人由衷地感到幸福。
“我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個人的臉龐。”這是從死神手中逃過一劫的陶醫生在微博中寫下的一句話,他告訴所有關心他的人,人生所經歷的黑暗時刻并不會讓他退縮和氣餒,光明從不會畏懼黑暗,而他也即將重新開啟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出院僅半個月,陶勇就已開始正常工作,處理醫院文件、參加視頻會議、指導學生的論文寫作等,一項都沒有耽誤,甚至在空閑之余還會思考醫院未來發展的相關事宜。陶勇曾在采訪節目中笑著表示,手部受傷意味著放棄過去的生活,重新開始一段新的生活,自己治病救人,也不一定要在手術臺上,做科研也是一種對醫學的貢獻。“醫學不能只有‘術來解決問題,它還得有‘道來探索對事物的認知。如果我對醫學的理解不能提高一個層次,我覺得就失去了當時學醫的初衷。”陶勇如是說,“我原本的想法就是減少自己的手術量,將重心轉到培養團隊上去,幫助更多年輕醫生去推動發展技術。”
“如果可以與自己和解,未來我一定能擁有美好和幸福;若未能與自己和解,我可能會生活在一片陰霾之中。”陶勇能夠如此坦然地面對人生轉折,無愧為一位“強者”。陶醫生擔心自己受傷會耽誤許多患者的治療,因此他希望自己的角色快些從“傷者”回到“醫者”,希望患者以后依舊可以認同他是位優秀的醫生,依舊會將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如今,陶勇已經回到自己熱愛的崗位,繼續為更多患者帶來光明。
〇 與葡萄膜炎抗爭的勇士
今年40歲的陶勇是北京朝陽醫院眼科的主任醫師,也是首都醫科大學的博士生導師、教授。他的專業是本就不屬于熱門的眼科,而主攻方向更是選擇了冷門中的冷門——葡萄膜炎研究。學醫從醫的十幾年間,他發表的SCI論文多達91篇,中文核心期刊論文62篇,還主持著多項國內外科研基金,陶勇成了國內少數主攻葡萄膜炎的眼科專家。
“葡萄膜炎”是個大家族,種類繁多,病因相當復雜,造成葡萄膜炎的病因可能是病毒,可能是細菌,也可能是惡性腫瘤,有一百多種可能原因。患有葡萄膜炎的患者大都屬于免疫力低下群體,常伴有很嚴重的并發癥,治療時稍不留神便會導致嚴重后果,輕則失明,重則失去生命。
如何及時找出病因?治療方案怎么選?很多時候,針對不同病因的治療方案不僅沒有辦法兼顧甚至截然相反,而稍有不慎就會導致失明,這也使得葡萄膜炎在致盲性眼病中“名列前茅”。而治療的難度之大,讓很多眼科醫生望而卻步,這卻讓陶勇激發了挑戰的勇氣。“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在陶醫生看來,醫學是神圣的,離不開醫者的不斷思考和勇于嘗試。疾病雖駭人,但更可怕的是無人愿意接近它,研究它,攻克它。患者需要治病,醫生就要千方百計將病治好,要挑戰別人治不好的病。陶勇面對復雜的病情和病因,就像是一位遇到復雜案件的偵探,爆發出十足的勇氣和熱情,抓住一個個線索抽絲剝繭,努力找到為患者保住視力的方法。陶勇這一干就是十數年,以患者為戰友,共同在復雜的致盲性疾病面前“作戰”,也積累下了海量的案例資料、分析經驗,這就像一個巨大的寶庫藏在他的“記憶宮殿”中,時至今日,陶勇早已成為我國葡萄膜炎領域數一數二的專家,許多患者從全國各地不遠千里來找他,“找到陶勇就有救了”在病友群中流傳,對許多患者而言,陶勇仿佛是他們握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葡萄膜炎的發病和復發機制未被破解,預防和治療的效果也很不理想,患者多為青壯年人群,其中包括一些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癌癥患者及腎移植患者,這種疾病已經引起了世界范圍內的廣泛重視。如何快速地找到葡萄膜炎的原因,是提高治療效果的一個關鍵,陶勇一直試圖做出一些“開創性的研究”。
陶勇眼中的“開創性研究”,既是戰勝疾病的未來之“道”,也是充滿魅力、吸引著他去挑戰的一條“勇士之路”,用于檢測葡萄膜炎的“眼內液檢測技術”算是他研究成果中的重要一項。葡萄膜炎的檢測以往以血液檢測為主,但檢查效率不高,現在通過抽取眼內約0.1毫升的液體進行檢測,就可以迅速鎖定病因。目前,全國已經有數萬名患者通過“眼內液檢測技術”快速確定了病因并得到治療,這項技術無疑為葡萄膜炎患者和經驗不足的年輕醫生帶來了極大便利。2020年2月,陶勇在ICU脫離危險后,單手打字,完成了《眼內液檢測的臨床應用》一書的最后章節。
由于“眼內液檢測技術”仍屬于一種微創檢測,不是陶醫生心中的完美檢測手段,他便又著手于“無創淚液檢測”的研究與開發,將自己大部分的精力與時間投入到科研事業中。
大多數醫生都明白葡萄膜炎領域的研究和工作有多困難,研究者太少,難度卻很大;陶勇也知道自己選擇的這條路并不好走,投入多,回報少。他笑著承認,許多時候自己為患者所顧慮的事情都是“吃力不討好”,有些患者不明白自己的病癥有多嚴重,也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但盡管如此,陶醫生沒有選擇退避,困難的事情總得有人做, 別人不想接的患者,他愿意接;別人做不了的手術,他可以做。

“學醫,不是讓我們成為一個會做手術的大夫就行,我們要學會思考,要嘗試做點別人沒做過的事情。”陶勇的目光溫柔而堅定。醫學生入學之前的宣誓詞中有這樣一段話:“我決心竭盡全力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維護醫術的圣潔和榮譽,救死扶傷,不辭艱辛,執著追求,為祖國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類身心健康奮斗終生。”陶勇用自己的行動,完美詮釋了一個醫者該有的樣子。
〇 醫者,仁愛之士也
在學術方面,陶醫生無疑是位出類拔萃的醫者,但與他精湛的專業技術相比,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那顆赤誠的醫者仁心。
陶勇出診時,患者們常常會一窩蜂地涌進診室,擠在他的辦公桌前,他不得不站起來維持秩序,一遍遍勸說患者按秩序排好隊,告訴他們這樣更能減少候診的時間,并保證給大家都看完。陶勇知道,許多前來就診的患者來自并不富裕的農村地區,不忍讓他們白跑,更不忍心讓他們白花“高昂”的掛號費。“我一般不限號,我的很多患者都是外地的,如果今天看不了,他們就要多花一天甚至幾天的房費住在北京,無形中增加了他們的負擔。”陶勇在接受采訪時,用最質樸的語言表達了對患者的關懷,他認為合格的醫者,不會想從窮人手中“撈錢”,因為過不了自己內心那一關。
有位患兒的母親在網上評價陶醫生時寫道:“孩子得了葡萄膜炎,排到號時已經九點鐘了,陶主任還沒有吃晚飯,一直在忙。為陶主任的敬業精神所感動。”為了多看一個患者,陶勇常常顧不上吃飯休息,甚至連喝水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當助手和護士們都已下班,陶勇也繼續加班為患者做完檢查,從早晨八點半一直工作到夜晚八九點,似乎已成為他的常態。
醫生的工作必然無法與“輕松”聯系在一起,陶勇幾乎每天都在滿負荷運轉,從周一到周五,專家門診、特需門診、會診都少不了他的身影;額外的時間里不僅要做科研,還要帶學生,醫院的各種會議也不能缺席,甚至周末也沒有休息時間。在陶勇的同事眼中,他每天都像臨上戰場的軍人,必須保持飽滿的精神,時刻準備面對一場焦頭爛額的“戰斗”。醫生從來就不是一個“正能量滿滿”的職業,他們每天與疾病打交道,見證無數的悲歡離合,也看透了人間的生死相隔。問起陶勇如何消除自己的“負能量”,他說患者給他的“感動”就是最好的良藥,來復查的患者帶來了自家老母雞下的雞蛋,被治愈的重癥患者帶來了自己網店里賣的衣服,保住視力的老奶奶帶來了自己親手納的鞋底……這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卻給了陶醫生莫大的支撐,讓他感到自己在治愈患者的同時,也成了“被患者治愈的醫生”。
如果幸福指數的滿分是 100分 ,你給自己打多少分?
陶醫生毫不猶豫地回答:“ 98 分。”
〇 醫生與患者 本不該有隔閡
很多人都擔心陶醫生在經歷“黑暗”之后會放棄醫療崗位,或者事后的他會以一種片面的視角來看待醫患關系,陶勇覺得這些擔憂實為多慮了。在陶勇看來,“醫生”與“患者”這兩個角色其實很難從本質上將他們分開,兩者本就該是一個整體,因為他們共同面對一個“敵人”,那就是疾病。陶醫生認為醫生與患者就如同一對“小兩口”,生活中難免遇到挫折坎坷,若兩人從一開始就不夠信任對方,各自藏有“小心思”的話,任何一點小坎坷都可能將這對“夫妻”拆散。醫生與患者亦是如此,倘若醫生從一開始就感受到患者對自己的不信任,那么就很難齊心協力戰勝病魔。
2020年11月2日的一則新聞,讓陶勇再次進入公眾視野之中。他與北京紅十字基金會共同發起成立的“彩虹志愿服務隊”服務項目正式啟動,34名來自社會各界的志愿者們組成了“光明天使”團隊,他們在醫院為患者提供導診、掛號、取藥等基礎服務,以及心理健康、知識科普等住院病房服務。
“我做過多年的志愿服務,到老少邊窮地區做白內障手術,那是醫院外的公益,但其實在醫院里,視障患者就診也需要關愛和照顧。”行醫將近20年的陶勇了解醫生的艱辛,也懂得患者的不易,成為患者之后的他,越發地體會到患者需要的不僅僅是針對疾病所做的治療,還有貼近內心的人文關懷。很多人感覺醫院是冷冰冰的,是充斥著消毒水味,是夾雜著疾病、病痛、細菌等負面詞匯的,陶勇希望通過“彩虹志愿服務行動”,可以讓患者們感受到溫暖,打通兩者之間的隔閡,讓醫院從此變得“光明”。
志愿者項目發起后,一位患兒的父親立馬報了名,陶醫生親切地稱呼他“天賜爸爸”,兩人已經相識11年了。當年,天賜爸爸帶著患眼部惡性腫瘤的天賜到北京找陶醫生尋求幫助,由于經濟原因,天賜晚上只能和爸爸一起睡在火車站,陶勇得知父子倆的情況后,曾多次幫助過他們。如今,天賜已經在老家的盲人學校讀六年級。
愛因斯坦說過,這個世界不存在黑暗,黑暗只是因為暫時缺少了光亮,只要我們用光亮填充黑暗,黑暗就會隨之消失。醫生猶如“光的傳遞者”,為患者帶去生命的希望,陶勇并不是唯一,他的經歷讓他成為“特殊”的那一個,但他恰恰也是中國千萬醫者的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