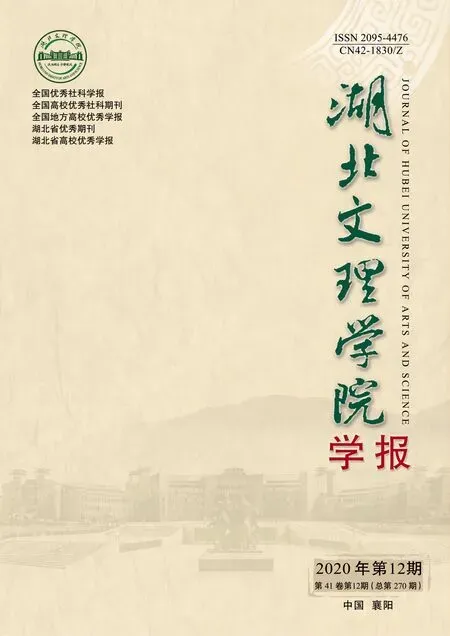基于“萬(wàn)物有靈”的精神救贖
——從《候鳥(niǎo)的勇敢》到《燉馬靴》
李翠青
(安徽大學(xué) 文學(xué)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東北大地以其特殊的文化風(fēng)貌在文學(xué)史的書寫中占據(jù)一席之地,從20世紀(jì)30年代的東北作家群來(lái)看,蕭紅懷著深沉的愛(ài)與痛,寫下了底層人民生與死的掙扎,蕭軍、端木蕻良等也都以自身體驗(yàn)傳達(dá)出對(duì)于東北大地的情感,當(dāng)代作家劉慶的《唇典》則專注于東北小鎮(zhèn)的人物和歷史,對(duì)東北地域文化進(jìn)行研究。遲子建生長(zhǎng)在東北的北極村,宗教文化的渲染賦予了她特殊的生活體驗(yàn),由此她筆下文字所展現(xiàn)出的是對(duì)于生命最原始的尊重。《候鳥(niǎo)的勇敢》和《燉馬靴》是作家表現(xiàn)人與自然信仰的新作,在自然信仰的影響之下,小說(shuō)中人與鳥(niǎo)、人與狼之間對(duì)于生命頑強(qiáng)守候的默契,也與作者一貫宣揚(yáng)的人道主義情懷相契合,人性在世俗的欲望之下不斷演變,唯有心存溫暖與善念,才可在俗世間舒適行走,實(shí)現(xiàn)精神救贖。
遲子建習(xí)慣以一種溫情的筆調(diào)表現(xiàn)東北大地人民的真實(shí)生存狀態(tài),自《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以來(lái),遲子建的中篇小說(shuō)以深厚感人的意蘊(yùn)在文壇占據(jù)重要地位。《候鳥(niǎo)的勇敢》在中國(guó)小說(shuō)學(xué)會(huì)2018年度中國(guó)小說(shuō)排行榜中居于中篇榜首,小說(shuō)從候鳥(niǎo)管護(hù)站展開(kāi),展現(xiàn)了瓦城的世俗百態(tài),揭露了東北小城社會(huì)的貧富差距與階級(jí)的不平等,并對(duì)人與自然的相處模式進(jìn)行了拷問(wèn)。而在2019年小說(shuō)排行榜中,遲子建的小說(shuō)《燉馬靴》獲得了短篇小說(shuō)榜之首,這個(gè)故事發(fā)生在抗戰(zhàn)年代,父親與瞎眼狼彼此之間相互幫扶成就了一段可貴的友誼。關(guān)注人性與自然是遲子建小說(shuō)的重要主題之一,作者尊重萬(wàn)物生靈,而從小說(shuō)中人物來(lái)看,從張黑臉到父親,他們都心懷善念,以深沉的悲憫情懷觀照自然,并始終踐行著生命平等如一的信念。
一、“萬(wàn)物有靈”的自然信仰
中國(guó)是一個(gè)有信仰的民族,對(duì)于宗教信徒而言,他們的信仰更甚,在生活中遵守教義,虔誠(chéng)地信奉神靈。縱觀不同宗教在我國(guó)歷史上的傳承與發(fā)展,儒、佛、道曾是中國(guó)人民的三大信仰和三大精神支柱,而在一些少數(shù)民族之中也有原始宗教的存在,我們所熟知的阿來(lái)小說(shuō)中對(duì)于苯教的描寫以及東北作家蕭紅筆下的薩滿教儀式的展現(xiàn),這些都是原始宗教的遺存,這些宗教信仰者聚居在偏遠(yuǎn)地帶,他們遠(yuǎn)離現(xiàn)代化的城市,依然保留著祖輩的信仰。遲子建居住在北極村,在祖國(guó)最北端的地區(qū)還遺留著少數(shù)民族的風(fēng)俗,作者長(zhǎng)期與當(dāng)?shù)氐亩鯗乜说让褡褰佑|,“這兩個(gè)少數(shù)民族信奉萬(wàn)物有靈;在他們眼里,花、石頭、樹(shù)木等都是有靈魂的”,[1]在這種觀念影響之下,遲子建也相信萬(wàn)物有靈,自然間有神靈,如果冒犯,便會(huì)有懲罰。這種對(duì)于生命普遍的敬畏與尊重也決定了作者的文學(xué)觀:在小說(shuō)中訴諸人道主義與悲憫情懷。
在小說(shuō)《候鳥(niǎo)的勇敢》中,張黑臉相信“萬(wàn)物有靈”是出于對(duì)自然的敬畏和信仰。張黑臉多年前入山林遇到了虎,在危難之際,一只有著巨大翅膀的鳥(niǎo)兒救了他,從此之后,他性情大變,不再貪戀世俗事,而融入了自然之中,并且擁有了神奇的能力:可以預(yù)見(jiàn)天氣變化。此時(shí)的張黑臉脫胎換骨之后失了人性的模樣,他喜歡有翅膀的動(dòng)物,并視它們?yōu)槎魅耍@樣的信仰使他六根清凈,一心與候鳥(niǎo)管護(hù)站的候鳥(niǎo)為伴。小說(shuō)的故事也是圍繞東方白鸛救助張黑臉,張黑臉救助東方白鸛這一個(gè)循環(huán)模式展開(kāi),最后它們共同留在了風(fēng)雪中。在周鐵牙把候鳥(niǎo)作為謀財(cái)工具時(shí),張黑臉卻把它們當(dāng)朋友、知己,在鳥(niǎo)兒受傷不能南飛之際,張黑臉虔誠(chéng)地祈禱,在對(duì)自然的感恩之下,張黑臉超越了人與獸之間的生理阻隔,他將候鳥(niǎo)看作神圣之物,相信“萬(wàn)物有靈”。
《燉馬靴》的背景是在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在人與敵手、人與動(dòng)物的矛盾下,“萬(wàn)物有靈”這一信仰表現(xiàn)了另一種姿態(tài)。故事主要聚焦于父親與瞎眼狼身上。人性與獸性之間有分別,不可以一概而論,人并非全是善良,而獸也有好惡之分,父親與狼都心存善念,因惺惺相惜的感恩之舉相互完成了心靈的溝通。父親在行軍過(guò)程中遇到了天生瞎眼的母狼,出于最本真的同情,父親給予了幫助,為它留骨頭,讓它解決最基本的生理上的饑餓。后來(lái)父親遭到日本兵伏擊,困在了山林,母狼的眼睛無(wú)法識(shí)人,但它憑借多年前的記憶仍然找到了需要救助的恩人。母狼懷孕后,那些狼崽不知所蹤,它們大多數(shù)像自己父親那樣嫌棄拋棄了母狼,但卻有一只小狼甘愿做母親的燈,照亮母親的生活,它感念母親,也懂得保護(hù)母親的恩人,在遲子建筆下,狼是有溫情的,通人性,在北方這個(gè)極寒之地,共同生存的生物之間有了惺惺相惜的感情,它們作為同一片土地上的生靈,擁有共同的信仰:對(duì)自然崇拜,敬畏生命。
二、精神救贖的別樣呈現(xiàn)
“阿多諾認(rèn)為,文字是人類最痛苦的回憶,藝術(shù)是一種‘救贖’,它一方面向人們敞開(kāi)了一個(gè)科學(xué)技術(shù)無(wú)法提供的關(guān)于生存意義的思考;另一方面又把人們帶回到‘本真’的領(lǐng)域,遭遇到自己的感性身體、欲望和情緒,這正是‘救贖’的意義所在”[2],遲子建對(duì)生活有著敏銳的感知能力,她將自身切實(shí)的情緒體驗(yàn)?zāi)毘蔀槠毡椤⑼ㄋ椎墓适虑楣?jié),因而往往從最不起眼的小事件中卻能挖掘出最世俗的社會(huì)病癥。遲子建在小說(shuō)《候鳥(niǎo)的勇敢》和《燉馬靴》中,將筆觸延伸到了兩個(gè)普通人身上,他們對(duì)萬(wàn)物懷有平等敬畏之心,在涉“罪”之時(shí),以別樣的方式寬慰精神世界從而救贖自身。
(一)除罪:自我懲戒
救贖思想來(lái)源于宗教,耶穌知曉人性之惡,將自己釘入十字架而換得信徒平安,贖盡污穢;佛教信條“救人一命勝造七級(jí)浮屠”以及好人升天堂、壞人入地獄的輪回之說(shuō),都是源于自我信仰范圍內(nèi)對(duì)所涉罪孽之事的懺悔心態(tài)。精神救贖便是要在認(rèn)識(shí)到思想罪惡之后進(jìn)行心靈洗滌,以此來(lái)超脫、升華怨念。
《候鳥(niǎo)的勇敢》中出現(xiàn)了階級(jí)地位相差甚遠(yuǎn)的兩種人:窮人和富人,也就是小說(shuō)所隱喻的留守人與候鳥(niǎo)人。窮人忙著賺錢而對(duì)自然發(fā)起進(jìn)攻,他們侵占、破壞自然,而富人居高位要職,則理所當(dāng)然地享受著職位所帶來(lái)的利益之便。張黑臉的潑皮女兒張闊說(shuō)得十分形象“采達(dá)子香運(yùn)往大城市,這是扶貧。大城市人看上去光鮮,可過(guò)得不痛快,精神空虛。這也是貧窮。他們沒(méi)養(yǎng)過(guò)這樣有生命力的野花。所以對(duì)達(dá)子香有需求。山里人撫慰了城市人的靈魂,是不是扶貧呢?”[3]78城里人從山里走出去過(guò)上了優(yōu)渥的生活,他們?cè)诤涞亩烊绾蝤B(niǎo)一般趕往南方的溫暖之地,而在夏天往返消暑。物欲滿足之后的他們開(kāi)始向往一種精神追求,“野花”“野生動(dòng)物”,這些帶“野”的生物以一種極其神秘的姿態(tài)與魅力吸引著他們的訴求,所以局長(zhǎng)愛(ài)吃野鴨,城里人也將山間的達(dá)子香視作珍寶。
如果說(shuō)城里人靠山里的野生之物來(lái)填補(bǔ)精神的空缺與貧窮,從而獲得天然的滿足感,那么張黑臉的回歸自然則是在反省后的一種徹頭徹尾的精神救贖。張黑臉原本是世俗之人,他在神鳥(niǎo)救助之后融進(jìn)了自然。他從前性格開(kāi)朗,桀驁不馴,“而現(xiàn)在話極少,呆板木訥,似乎誰(shuí)都可以對(duì)他發(fā)號(hào)施令”。[3]3張黑臉在失憶之后算是一個(gè)六根清凈之人,只懂得與候鳥(niǎo)為伴,不念世俗人情,而在遇上德秀師父之后則出現(xiàn)了精神上的波動(dòng)。張黑臉對(duì)德秀師父的感情出于本能的惻隱之心,而在這個(gè)相對(duì)封閉的場(chǎng)所,德秀師父的遭際讓他體現(xiàn)了世俗男人本應(yīng)有的擔(dān)當(dāng)與責(zé)任意識(shí):他想要給予溫暖,照顧這個(gè)命運(yùn)孤苦的女人。張黑臉和德秀師父在寺廟旁初嘗情欲禁果,寺廟是供奉神靈清凈神圣之所,因而他們想到的都是如何接受懲罰,可見(jiàn)都是深諳世俗倫理之人。“欲”是佛之大忌,卻是人之常情,按馬斯洛的需求層次來(lái)看,“自我實(shí)現(xiàn)需要的明顯的出現(xiàn)通常要依賴于前面所說(shuō)的生理、安全、愛(ài)和自尊需要的滿足,”[4]生理欲望處于所有欲望最下層,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而張黑臉和德秀師父的“禁忌”之戀卻無(wú)法逃脫內(nèi)心的懲戒。他們?nèi)找箲曰冢隙俗陨肀囟ㄗ呦驕缤龅慕Y(jié)局,小說(shuō)的最后部分,兩人在暴風(fēng)雪中為候鳥(niǎo)餞行,是懺悔的最終實(shí)現(xiàn)形式,“兩只在大自然中生死相依的鳥(niǎo)兒,沒(méi)有逃脫命運(yùn)的暴風(fēng)雪,而埋葬它們的兩個(gè)人,在獲得混沌幸福的時(shí)刻,卻找不到來(lái)時(shí)的路。”[3]202在茫茫大雪中空無(wú)一人,他們以天地間的一片純白實(shí)現(xiàn)自己的精神救贖。
(二)和解:承襲善念
張黑臉對(duì)于世俗生活的回避是通過(guò)改變?cè)械纳罘绞蕉鴮?shí)現(xiàn)的,他與德秀師父三次激情相擁之后祈求神靈對(duì)自身肉體進(jìn)行懲罰,以此來(lái)救贖精神苦痛。反觀小說(shuō)《燉馬靴》,在環(huán)境惡劣、生存艱難之時(shí)父親因懷有悲憫之心而自省,最終以溫和的方式拯救了自身。東北大地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賦予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赤膽忠心和鐵骨錚錚的勇氣,東三省作為抗日重要陣地自有其深厚的故事意蘊(yùn)。《燉馬靴》中父親在戰(zhàn)斗中不斷“燉”敵手的馬靴而存活下來(lái),父親是隊(duì)伍里負(fù)責(zé)做飯的戰(zhàn)士,他是抗戰(zhàn)隊(duì)伍中一個(gè)平凡的小人物,但在與敵國(guó)對(duì)陣之際,在鮮明的民族敵對(duì)意識(shí)之下,即使是小人物也有著強(qiáng)烈的愛(ài)國(guó)之心。在生與死,民族與階級(jí)的較量中,父親憑借老練的智慧取得了勝利,他拿到了戰(zhàn)利品——靴子,這無(wú)疑是給久戰(zhàn)后的父親提供了最得力的營(yíng)養(yǎng)供給。父親與張黑臉不同,張黑臉被救助之后儼然成了隱于世的人,精神歸于自然,而父親當(dāng)時(shí)身處艱難之地,作為一個(gè)正常人,他的首要選擇便是活下去。在這場(chǎng)生存斗爭(zhēng)中,敵手成了失敗者,但他在生命最后也沒(méi)有放棄戰(zhàn)士的尊嚴(yán),“他從未見(jiàn)過(guò)一個(gè)人的眼睛會(huì)在夜的飛雪中發(fā)出那樣強(qiáng)的光,銳利,絕望,又不甘”[5]16。父親與敵手的關(guān)系是對(duì)立的,而從生命的本能出發(fā),父親流露出了同情。年輕的士兵即使面對(duì)野狼啃食后死無(wú)全尸的惡果,仍然握緊士兵的志氣,這使得父親生出了敬畏之心,在敵手流血過(guò)多時(shí),父親用火來(lái)溫暖他的身體,讓他不至于在東北的大雪之夜里過(guò)于痛苦地離開(kāi),而這些源于父親精神震撼之后的悔意。那把三八式步騎槍,最終到了母親手里,這是對(duì)小戰(zhàn)士未完滿的婚姻人生的延續(xù),也是父親對(duì)死去敵手的深深緬懷。父親在后來(lái)的生命征途中找了救贖之道,那便是將善念傳承下去,他年復(fù)一年地傳頌這個(gè)故事,逐漸與內(nèi)心的矛盾和解,撫慰了精神上的歉疚。
父親對(duì)敵手懷有愧疚之情,在感懷中救贖自身,“父親每回講完燉馬靴的故事,總要仰天慨嘆一句:人吶,得想著給自己的后路留點(diǎn)骨頭!”[5]29而正因?yàn)楦赣H留下的“骨頭”,瞎眼狼免于餓死,而在多年后父親得到了它的保護(hù),最后拯救了自身,再次凸顯了父親對(duì)傳承善念這一抉擇的肯定。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不斷發(fā)展的今天,人們的物質(zhì)生活逐漸充裕起來(lái),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的我們很難切實(shí)體會(huì)到萬(wàn)物有靈,也無(wú)法想象人與獸之間存在的默契。精神上的懈怠也讓人們逐漸失去了同情與愛(ài)的本能,而當(dāng)下的人們把過(guò)去的故事視為漫談的傳說(shuō),口中充滿了輕視與嘲弄,浮躁社會(huì)之下更難體會(huì)善念的存在。而在抗戰(zhàn)勝利建國(guó)70周年后的今天,我們更要以過(guò)去英雄們艱苦卓絕精神滋養(yǎng)訓(xùn)誡自身,這些精神源于我們本能,卻在發(fā)展中不斷被湮滅,因此更因被喚起,來(lái)救贖我們快速發(fā)展的思想,體味人道主義關(guān)懷。
三、自然信仰下精神救贖的價(jià)值闡釋
(一)世俗生活的燭照
遲子建的小說(shuō)著眼于生活中的小人物,如傻子、進(jìn)城打工的夫妻以及魔術(shù)師等,而這些平凡人物身上有著萬(wàn)千人民的共性,真實(shí)顯現(xiàn)了社會(huì)生活百態(tài)。小說(shuō)應(yīng)當(dāng)反映現(xiàn)實(shí),按照生活的本來(lái)面目描寫現(xiàn)實(shí),這是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作品的基本要求。我們的民族不乏奮斗的歷史,專注英雄人物描寫的史詩(shī)性著作往往場(chǎng)面宏大、振奮人心,但在文學(xué)史中同樣需要一些作品來(lái)展現(xiàn)悲憫情懷與人道主義,而小說(shuō)中對(duì)于人性的書寫則使讀者獲得共情之時(shí)發(fā)揮感化效應(yīng)。“在世俗人道主義中,苦難敘事是啟蒙取向逐漸向世俗倫理取向和人性取向的演進(jìn),其人道主義思想專注于人的生存與自我確認(rèn)、人的生命意義與價(jià)值,展示人戰(zhàn)勝苦難、超越苦難而自我獲救的精神。”[6]遲子建從小人物出發(fā)而寫大歷史,將眼光投入到了當(dāng)今社會(huì)普遍存在的問(wèn)題之中,以東北地區(qū)的人性敘述作為一面澄澈的鏡子,來(lái)映照溫暖與悲情。
關(guān)注生態(tài)與自然是遲子建一直秉持的寫作原則,在近兩年的小說(shuō)《候鳥(niǎo)的勇敢》《燉馬靴》之中,作家再次剖析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guān)系,同時(shí)作家密切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對(duì)世俗人性的解讀也十分深刻。《候鳥(niǎo)的勇敢》中張黑臉的女兒張闊在父親變傻之后私吞其銀行卡,并驅(qū)趕父親去候鳥(niǎo)管護(hù)站做看守人來(lái)賺取錢財(cái),甚至不希望父親變聰明,好起來(lái)。周鐵牙雖為候鳥(niǎo)管護(hù)站隊(duì)長(zhǎng),卻視候鳥(niǎo)為賺錢籌碼,毫無(wú)愛(ài)心。官僚體系層層腐敗,官員憑借利益而使地位不斷穩(wěn)固,社會(huì)關(guān)系更是混亂,不論友情還是親情都要靠金錢來(lái)驅(qū)動(dòng)。窮人要變得富有,富人則要求更加富有,整個(gè)社會(huì)充斥著交易與虛偽,對(duì)于物欲的追求成了當(dāng)今人們的本性。小說(shuō)建構(gòu)了世俗社會(huì)之外的一處特殊場(chǎng)所——娘娘廟,在世人眼中廟里的師父神圣、可通靈,是“在夜里不用點(diǎn)燈的人”,這本是人們尋求清凈之地,不食人間污濁,周鐵牙、老葛卻在此處進(jìn)行著金錢利益的交易,德秀師父的前夫借著法會(huì)博取同情從而牟利,這些具有諷刺意味的無(wú)賴嘴臉進(jìn)一步映照出了世間人皆向利。瓦城人們?cè)诤诎档慕疱X交易中生活著,在集體無(wú)意識(shí)中他們失掉了善良的品格,作者將小城人民的生存狀態(tài)進(jìn)行了深度剖析,赤裸裸地展現(xiàn)了金錢驅(qū)使下靈魂失格、溫情喪失的狀態(tài),從而在極其真實(shí)的敘述沖擊下觸動(dòng)人們反思自身。
《燉馬靴》的故事發(fā)生在抗戰(zhàn)年代,與《候鳥(niǎo)的勇敢》相比,人物顯得單純而質(zhì)樸,小說(shuō)中沒(méi)有絕對(duì)的壞人,有的只是各自為國(guó)浴血奮戰(zhàn)的戰(zhàn)士,他們都用自己的鮮血守護(hù)了國(guó)家尊嚴(yán)。磨牙士兵因?yàn)橥砩夏パ烙绊憫?zhàn)友休息而被嫌棄,但在與敵人交戰(zhàn)之時(shí),他以一己之身投入熊熊戰(zhàn)火,為戰(zhàn)友爭(zhēng)取了生存的機(jī)遇,從而避免了全軍覆沒(méi)的慘象,那之后喑啞的磨牙聲成了父親回憶中最難忘的美音。在全民抗戰(zhàn)的那個(gè)年代里,戰(zhàn)士們單純懷有一顆熾熱的愛(ài)國(guó)之心,而欲望壓縮到了最基本的維度——生存。同樣可貴的是,在戰(zhàn)爭(zhēng)之外,戰(zhàn)士們懷著惺惺相惜的情感,對(duì)他人報(bào)以人道主義的關(guān)懷,他們的人格依然是完整的,心尚未被蒙塵,依然純凈、明澈,而正是這一純粹的情感才讓處于艱難條件下的民族得以勝利。
(二)現(xiàn)實(shí)附以“神話”的敘事體驗(yàn)
在與少數(shù)民族長(zhǎng)期生活的體驗(yàn)中,遲子建被“萬(wàn)物有靈”的信仰所浸染,尊重自然生靈,而幼時(shí)在長(zhǎng)輩敘述中所熟知的聊齋故事開(kāi)啟了遲子建的想象模式,因此在遲子建的小說(shuō)中會(huì)呈現(xiàn)出神話的因素。“在我眼里,能給生靈以關(guān)愛(ài),給大自然以生機(jī),給人以善良的神話是萬(wàn)古長(zhǎng)青的!”[7]遲子建對(duì)自然萬(wàn)物飽含溫情,作家信奉神話中的善念,堅(jiān)信諸類神話教義能夠驅(qū)使人們棄惡揚(yáng)善,并在實(shí)踐中懺悔自身。由此來(lái)看,神話故事的特殊效力也為精神救贖的實(shí)現(xiàn)開(kāi)辟了道路,神話故事中耳熟能詳?shù)奶焯门c煉獄的存在建構(gòu)出了生命在他界的延續(xù)狀態(tài),是對(duì)自身行為的救贖。遲子建小說(shuō)引入神話因素,賦予了小說(shuō)超驗(yàn)的神秘色彩,在現(xiàn)實(shí)與虛幻的對(duì)照中顯露人情冷暖。
小說(shuō)《候鳥(niǎo)的勇敢》中,故事主要圍繞候鳥(niǎo)管護(hù)站的張黑臉展開(kāi),各個(gè)情節(jié)獨(dú)立分散,同時(shí)又通過(guò)“候鳥(niǎo)”融為一體,將東北這一地區(qū)不同階層人物的生活狀態(tài)刻畫得淋漓盡致。小說(shuō)是對(duì)東北現(xiàn)實(shí)世俗生活的反映,其中也包括對(duì)生態(tài)問(wèn)題的關(guān)照,作者通過(guò)加入神鳥(niǎo)這一線索來(lái)對(duì)人們發(fā)出警示。“他眼前有一把巨大的羽毛傘,黑白色,傘柄是紅色的,是他此生見(jiàn)過(guò)的最華美大氣的一把傘。他仔細(xì)一看,原來(lái)是一只白身紅腿黑翅的大鳥(niǎo),站在他胸腹處,展開(kāi)雙翼為他遮雨。張黑臉說(shuō),他一直以為,自己是到了天堂”。[3]38東方白鸛從虎口救下了張黑臉,張黑臉因而成為了一個(gè)不問(wèn)世事的“鳥(niǎo)”迷。小說(shuō)的故事本是極度寫實(shí),而在張黑臉與東方白鸛的相處中,遲子建巧妙地設(shè)置了超乎常理的情節(jié),使小說(shuō)空間擴(kuò)大到了人性與神性的空間,凸顯了人與神鳥(niǎo)之間的溫情。沒(méi)有神話傳說(shuō)的民族部落雖然更為現(xiàn)代,但終究會(huì)因?yàn)槿狈ι衩囟@庸常。候鳥(niǎo)作為一個(gè)隱喻,在小說(shuō)中候鳥(niǎo)、留鳥(niǎo)與候鳥(niǎo)人、留守人是互相對(duì)應(yīng)的。候鳥(niǎo)冬天南飛,夏天返回,它們本來(lái)作為一種貪圖享受的存在而被人厭惡,但在一次疫情之中,傳聞中的候鳥(niǎo)殺死了驕奢淫逸的候鳥(niǎo)人,而在這時(shí)它們成了窮人口中正義的使者。當(dāng)厭棄的事物因?yàn)閭髀劦哪硞€(gè)符號(hào)而消失,人們?cè)诟杏X(jué)大快人心的同時(shí)必然十分感激那個(gè)符號(hào),并用虛無(wú)的傳說(shuō)包裝它。而候鳥(niǎo)這個(gè)在貪官相繼離世中出現(xiàn)的偶然因素,使得它具有靈性,人們開(kāi)始相信,候鳥(niǎo)是正義的使者,是不可侵犯的,而這是自我認(rèn)知加工的信仰,瓦城人們對(duì)于候鳥(niǎo)的信仰出于它殺伐果斷的正義身份,也是對(duì)神話故事中因果報(bào)應(yīng)的回應(yīng)。神鳥(niǎo)的現(xiàn)身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世界的人們有一種引導(dǎo)作用,推動(dòng)著故事人物去發(fā)現(xiàn)罪愆,同時(shí)對(duì)于張黑臉這個(gè)邊緣化的小人物,作者在純粹的現(xiàn)實(shí)世界之外給他提供了志趣相投的伙伴,消減了主人公的悲劇性。
《燉馬靴》的神話因素源于父親與狼之間超越物種的心靈互通,遲子建坦陳自己的文學(xué)觀曾經(jīng)受到小說(shuō)《聊齋志異》的影響,在聊齋這類小說(shuō)中,花妖狐怪、神鬼異類通常有著善良的品性,能夠與人成為知己,這些生物通人性,富有靈性,且有著優(yōu)良的道德觀念。瞎眼狼是深藏于東北山林的狼,在它缺乏食物瀕臨死亡之際,受到了父親這個(gè)人類的幫助,而等到父親遭遇困境之時(shí),它義不容辭地來(lái)保護(hù)自己的恩人,這是傳統(tǒng)志怪小說(shuō)里的報(bào)恩故事,有著神話與民間傳說(shuō)的成分。遲子建的小說(shuō)是一部描摹抗戰(zhàn)真實(shí)情節(jié)的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品,小說(shuō)中增加浪漫主義成分是使得小說(shuō)具有神秘色彩的點(diǎn)睛之筆。故事的主人公通過(guò)極具人道主義的施授而成功脫險(xiǎn),最后用自己的后半生來(lái)傳頌善念,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于自我的精神救贖,救贖過(guò)程的展開(kāi)也包含了神話這一因素的鋪墊,使得小說(shuō)的結(jié)局更具戲劇性。
(三)悲憫情懷的傳承
“文學(xué)既然是以人為對(duì)象,當(dāng)然非以人性為基礎(chǔ)不可,離開(kāi)了人性,不但很難引起人的興趣,而且也是人所無(wú)法理解的。不同時(shí)代,不同民族,不同階級(jí)所產(chǎn)生的偉大文學(xué)作品之所以能為全人類所愛(ài)好,其原因就是由于有普通人性作為共同的基礎(chǔ)。”[8]文學(xué)向來(lái)要求作家書寫人性,從最普遍的故事中揭示人性善惡,滿足受眾普遍的閱讀期待。從《霧月牛欄》《清水洗塵》到《額爾古納河右岸》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遲子建的小說(shuō)總能引起人的心頭一震,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共情,而這些源于作者對(duì)筆下人物細(xì)致入微的考察,將最真實(shí)的人性加以呈現(xiàn);而在最近兩部作品《候鳥(niǎo)的勇敢》和《燉馬靴》中,作家塑造了具有善念的兩個(gè)好人,他們對(duì)萬(wàn)物懷有悲憫之心,這是遲子建小說(shuō)人道主義情懷的再次延續(xù),由小說(shuō)人物帶動(dòng)來(lái)傳承悲憫情懷。
悲憫,是以一種充滿善意的方式對(duì)人性進(jìn)行問(wèn)候,它不是妥協(xié),而是對(duì)萬(wàn)事萬(wàn)物保持一種崇高的尊重。在小說(shuō)《候鳥(niǎo)的勇敢》之中,張黑臉對(duì)候鳥(niǎo)的愛(ài)護(hù)便是對(duì)悲憫情懷的生動(dòng)闡釋。張黑臉在候鳥(niǎo)受傷時(shí)給予悉心照料,對(duì)于候鳥(niǎo)的關(guān)懷超越了自己的孩子,張黑臉精神失常,卻比他人更懂倫常,甚至從人類道德關(guān)系出發(fā)來(lái)看待候鳥(niǎo)這對(duì)“夫妻”,當(dāng)蔣進(jìn)發(fā)開(kāi)玩笑要與候鳥(niǎo)同住時(shí),他鄭重其事地說(shuō):“那可不行,人家候鳥(niǎo)可都是一對(duì)一的夫妻,正是下蛋的時(shí)候,你摻和進(jìn)去,萬(wàn)一下個(gè)隔路的蛋,孵出來(lái)的東西,人不人,鳥(niǎo)不鳥(niǎo)的,那可咋辦?”[3]82-83候鳥(niǎo)尚且懂得一夫一妻制,而以莊如來(lái)為代表的官員卻在光明正大地養(yǎng)情人,人在進(jìn)化過(guò)程中以種族優(yōu)越性超越了其他生物,成為了這片土地的主宰,但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卻丟失了道德尊嚴(yán),最終不如山林間的鳥(niǎo)獸。常人都笑張黑臉傻,而張黑臉卻是懂得知恩圖報(bào),他尊敬、愛(ài)護(hù)候鳥(niǎo),當(dāng)他的恩人白鸛受傷不能南飛時(shí),他焦急萬(wàn)分“恩人哪,快些好吧……你受傷的這些日子,你老婆來(lái)看過(guò)你好幾回呢,她在門外召喚你,你聽(tīng)見(jiàn)了吧?”[3]162,當(dāng)東方白鸛的伴侶送走孩子后,又再次回到候鳥(niǎo)管護(hù)站,然而卻只看到大雪埋藏下兩只白鸛的尸體,在白鸛的引領(lǐng)之下,它們的孩子已經(jīng)安然抵達(dá)溫暖的南方,成為出色的候鳥(niǎo),來(lái)年便可以獨(dú)自飛回北方。樹(shù)森和德秀埋葬了他們,帶著犯戒后的懺悔意識(shí),這對(duì)可憐人也留在了暴風(fēng)雪中。瓦城人向往安逸的生活,然而小鎮(zhèn)人們也逐漸忘卻了原始的善念,張黑臉是心存善念的怪人,德秀師父是被生活傷害的可憐人,他們被瓦城的親人拋棄,卻仍懷著善念對(duì)待一群不相識(shí)的候鳥(niǎo),他們?cè)肌⒗铣桑雌饋?lái)落后于這個(gè)正在發(fā)展的社會(huì),但仍懷著永不腐朽的悲憫情懷。
小說(shuō)《燉馬靴》的主人公父親是一個(gè)善良的人,在艱難的抗戰(zhàn)時(shí)期仍然將自己的口糧分給瞎眼狼,在與敵手針?shù)h相對(duì)直至對(duì)方死亡時(shí),父親依然保留了內(nèi)心的善良,并在每年家族團(tuán)圓的小年夜將這個(gè)故事傳承下去,也將善念傳承下去。父親的子孫們有了自己的理想生活,他們忘卻艱苦,也不再觸碰內(nèi)心的悲憫,父親想要給子孫傳遞善念,留存“骨頭”,是對(duì)于善念的銘記,真善美并不是特存于古老傳統(tǒng)之中的美德,在當(dāng)今社會(huì),人性更具豐富雜亂,當(dāng)待人接物之時(shí)心存悲憫更顯得彌足珍貴。無(wú)論是張黑臉還是父親,他們都謹(jǐn)慎對(duì)待自己曾經(jīng)犯下的錯(cuò)誤,懺悔自己的行為,不論是尋求懲罰還是弘揚(yáng)善念,他們以別樣的方式最終實(shí)現(xiàn)了自己的精神救贖。
遲子建作為生長(zhǎng)在東北地區(qū)的作家,對(duì)于東北大地有著天然的熟悉,她認(rèn)同并尊重這里樸實(shí)古老的民風(fēng),在這個(gè)東北小鎮(zhèn),有著不同民族的人,他們有著神圣的信仰,相信“萬(wàn)物有靈”,遲子建根植于這塊土地,她將這種信仰灌注于作品之中,無(wú)論是張黑臉對(duì)于東方白鸛的純粹無(wú)比的感恩之舉,還是父親與瞎眼狼之間的惺惺相惜,都是對(duì)于自然生靈的淳樸的敬畏,他們懷著最原始的悲憫情懷,對(duì)同一片土地上的生靈施以援助之手,他們審視自身,用最虔誠(chéng)的態(tài)度來(lái)實(shí)現(xiàn)精神救贖,從而保存了善念。社會(huì)經(jīng)濟(jì)不斷發(fā)展,即使是身處邊遠(yuǎn)小城鎮(zhèn)的人們也爭(zhēng)相加入這個(gè)潮流中,追求金錢至上、崇尚物欲,富人越來(lái)越多,而惡行也隨之積攢,腐朽的氣息讓小城失去了原本的光彩,人性發(fā)生了變化,但仍有人頑固地堅(jiān)守善良之心,張黑臉埋葬了候鳥(niǎo),用最后的善舉換得了自己出走的機(jī)會(huì),留在了暴風(fēng)雪之中,父親則用自己上半輩子的經(jīng)驗(yàn)向后輩傳遞著生存智慧。遲子建看到了這座城市人心的崩壞,但作者仍然相信善念,小說(shuō)中灌注的悲憫情懷也是作者內(nèi)心的獨(dú)白,以善念對(duì)待萬(wàn)物生靈,在傳承善念過(guò)程中滌蕩?kù)`魂,實(shí)現(xiàn)精神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