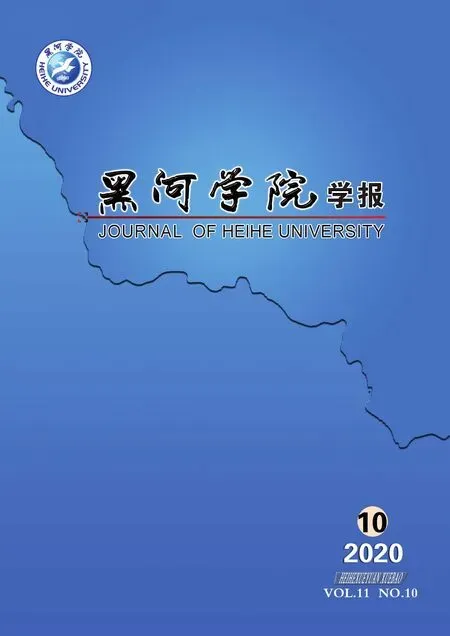以“社會劇”界定關漢卿公案戲
——從元雜劇《竇娥冤》談起
宗世龍
(安徽大學 藝術學院,安徽 合肥 230000)
在西方戲劇理論界,關于挪威劇作家易卜生劇作的爭論層出不窮,蕭伯納在《易卜生主義精華》一書中闡釋了“問題劇”的戲劇理念,認為“問題劇”這一戲劇類型的主要特征是將討論的技巧引進戲劇,讓“戲劇和討論實際上合二為一”,使社會問題可以在戲劇中得以自由表現[1],旨給觀眾倫理道德的教育,給人以理性的啟示。到20世紀中后期,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以“社會劇”的概念重新審視易卜生戲劇作品,并由“完整的人”這一概念剖析出易卜生劇作,發現易卜生是將現實社會凝結成特殊的戲劇情境,安排戲劇人物在戲劇情境中不斷地與社會發生碰撞,不斷追尋深邃與豐富的心靈世界,使觀眾跟隨戲劇人物逐步探微出真正作用于現實中人的本質原因,并旨在使觀眾通過情感與精神的共鳴,進而把握社會本質性內涵,而劇作中涉及到的社會問題的作用,僅旨在凝結出相應的戲劇情境。從而推翻了蕭伯納提出的“易卜生主義”這一帶有意識形態決定論的說法,將戲劇關注的視點從關注社會問題返回到關注人本身。
在相隔萬里的中國,同樣存在著以社會問題至上,忽略劇作家對社會與人本質性的探尋的現象。在中國,早期話劇階段是以“易卜生主義”為熱潮的創作熱、“十七年”間則以糾正意識形態為熱潮、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的革命樣板戲等都犯下了問題之上的錯誤,無論是戲劇創作者還是戲劇評論家都走向了問題劇的思維定式,從而忽略了戲劇是探尋人生存本質的藝術。現當代對于中國傳統戲曲的分析與評論,尤其是對于公案戲的探討,呈現出問題意識高于社會本質的傾向。以關漢卿劇作《竇娥冤》《魯齋郎》《蝴蝶夢》《緋衣夢》為代表的元代公案戲是元雜劇中重要的一支,其中《竇娥冤》在中國戲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縱觀現存的20余部元代公案戲劇本,其戲劇情境運動模式具有普遍性:因為某一社會問題形成對峙雙方,由貪官污吏武斷斷案造成冤案、錯案后,某一清正廉潔的官員突然降臨,并憑借其智慧使公平正義得以恢復。正是由于冤案得以平反,使得在解讀公案戲中出現了以呼喚意識形態上的清明政治的主流看法,而這一看法的實質是將公案戲中運用的社會問題作為戲劇的本質。雖然意識形態評論已不新鮮,但這無疑是以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論率先定義,進而將社會問題推向戲劇的本質。顯而易見這一研究方法脫離了戲劇文本的內核——對人的本質的探尋,無疑是舍本逐末、有失偏頗。
一、社會問題是否是元代公案戲的核心
最早將易卜生劇作界定為“問題劇”的戲劇家是英國的蕭伯納。1891年,蕭伯納發表了《易卜生主義精華》一文,這篇文章導致研究易卜生戲劇作品出現了錯誤傾向:“將易卜生主要看作是政治劇作家,評述社會和道德問題,他巧妙地把討論社會問題的機制引入劇作中。因此,在相當一個時期的觀眾心里,易卜生幾乎是社會和政治的變革者。”[2]將易卜生看作社會和政治的變革者最為著名的事件是《玩偶之家》上演后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劇中女主人公娜拉離家出走的關門聲使得新興起的女權運動者將易卜生奉為其發聲者,但易卜生面對這一評價說:“我沒有創作女主角,我只寫人和人的命運”。易卜生在塑造娜拉這一人物時并不是將其放置在認清夫妻關系后必須出走的前提之下,而是著眼于人類社會最為普遍的意義的個性解放,娜拉的出走是基于看清了海爾茂虛偽本質的戲劇情境下,依據人物追求自由與真實的性格特征引發的戲劇行動。所以,出走這一戲劇動作是應時、應勢而出,是符合其性格邏輯發展的。由此可見,易卜生不是以問題先行的模式進行戲劇創作的,而是將人物放置在特定的戲劇情境中產生出動機,動機的凝結促使戲劇行動的產生,人物性格與戲劇情境的相互碰撞使行動的產生具有合理性。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這樣評價:“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竇娥冤》、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3]王國維借鑒了西方戲劇中“意志”一詞給予《竇娥冤》《趙氏孤兒》兩部作品極高的評價。王國維的“意志說”先后受到叔本華與康德理論的影響,認為在“藝術虛構的生動世界中,一些奇特的人身上,能顯露自由意志、獨立人格的蹤跡。藝術人物非凡之處,是其僅憑一己之力,即能認準方向,排除萬難,冒著生命危險,捍衛人格,甘之如飴。”[4]這一觀點與西方傳統“意志說”不同,王國維并非將意志作為先驗實體植入給人物,而是將人物放置在“虛構的生動世界”中凝結出自由的意志、行動的動機,所以,王國維所指的“意志”應與中國當代戲劇理論家譚霈生提出的“戲劇情境論”中的“動機”概念同義。以情境論分析思考易卜生戲劇作品作為“社會劇”的戲劇類型的經驗,對再解析關漢卿創作的公案戲具有借鑒意義。
同以“社會問題劇”界定易卜生戲劇作品的誤區一致,對關漢卿筆下的公案戲的界定同樣走進了“問題先行”的誤區,以張庚、郭漢成編著的《中國戲曲通史》為例,兩位學者認為,關漢卿“是一個執著于現世的人,他是一個對于斗爭生活和人民充滿愛戀的人。崇高的理想,熾熱的感情,使他無法緘口不言,使他不能不高聲疾呼,起而戰斗,對黑暗的現實發出熱烈地抨擊。關漢卿的悲劇,就提出來元代最基本、最尖銳的社會矛盾——統治階級同廣大被壓迫人民的矛盾。《竇娥冤》《魯齋郎》《蝴蝶夢》,都一再選擇了重大的主題,從元代社會的各個側面反映了這個矛盾。”[5]兩位學者將關漢卿的人生經歷放置在元代社會大環境的背景下,在黑暗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關漢卿創作戲劇作品的實質是反映社會現實問題、呼喚社會改革。此種界定方式違背了戲劇是“人”藝術的永恒定義,退而將社會問題的解決標志為戲劇的目的,這無疑是不準確的。
以《竇娥冤》為例,在第一折中便出現了社會問題導致婆媳因立場不同出現的爭執,但這一社會普遍問題并不是將戲劇推動下去的核心動力,而是人物性格使然。劇作者在創作這一折時,先將戲劇情境設置為蔡婆婆的兒子去世,婆媳二人相依度日,蔡婆索要欠債不成反而被要挾,并將蔡婆婆與竇娥迥然不同的性格特征融入進戲劇情境中,使得在這一特定情境下,由于二人性格不同凝結出各自的動機,進而引發出爭吵的戲劇行動。
蔡婆婆受張驢兒父子的解救,無奈將二人帶回家中,失去夫君的竇娥起初以“況你年紀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了丈夫那”勸解蔡婆婆切勿被蒙騙丟了名節,但蔡婆婆懼于張驢兒父子不敢趕逐,竇娥心知斷不能留下張驢兒父子,堅持不能順從婆婆的意愿,所以凝結出定要趕走張驢兒父子的動機,于是竇娥在《后庭花》一曲中警戒婆婆若是應了婚事便是“可不道到中年萬事休,舊恩愛一筆勾,新夫妻兩意投,枉教人笑破口”,但婆婆此時執拗于自己的性命由張驢兒父子救下只得嫁與他,顧不得旁人笑話,使得竇娥在《青哥兒》中不得已以公公去世后留下的家產是足以使家庭維持下去為由提醒蔡婆婆“公公則落得干生受”,希望可以通過逝去的公公喚起婆婆的良知,但蔡婆婆固執到仍沒有理解竇娥的意思,使得竇娥在《寄生草》一段唱詞中已然表露出氣憤,“你待要笙歌引至畫堂前,我道這姻緣敢落在他人后”一句竇娥心中的悲憤全然爆發出來。不過蔡婆婆仍不知竇娥的心意,定要將張驢兒父子接入家中,并說出“事已至此,不若連你也招了女婿吧”一語,這一句使得竇娥的氣憤驟然上升到了極點,而后甩下一句“你要招你自招,我并然不要女婿”,無奈的是蔡婆婆還是將張驢兒父子帶入家中,拉開了竇娥悲劇命運的序幕。在第一折的戲劇情境中,通過竇娥與蔡婆婆的語言交鋒交代出了竇娥與婆婆、張驢兒父子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也可從中解析出竇娥的人物形象,在蔡婆婆起始與她說明張驢兒父子一事發展到婆婆執意將張驢兒父子帶入家中的情節發展中,竇娥對此事的態度反應不是單一靜止的,而是呈現出“溫柔勸說-設計暗示-憤然發怒-無奈接受”的發展趨勢。通過上文對于第一折戲劇情境的解析,可以發現這一情感態度的發展轉變是在戲劇情境的發展中得以逐一顯現,符合戲劇創作的基本邏輯。而且兒媳與婆婆的矛盾沖突是極其常見的,尤其在封建社會中婆媳沖突以媳婦做出讓步更是屢見不鮮,在這一戲劇情境中劇作者也正是運用了這一普遍化的社會現象賦予了劇本更貼近現實的生活氣息,在最具普遍意義的社會現象中將竇娥的人物形象初步塑造,為后文的情節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在第二折中關漢卿將社會問題進一步深化地凝結在戲劇情境中,即貪官惡吏對普通百姓的踐踏。張驢兒見竇娥遲遲不肯答應婚嫁一事,便向賽盧醫討來毒藥欲要毒死蔡婆婆,不料將自己的父親毒死,將竇娥逼上衙門。在這一戲劇情境中,竇娥孝順、堅持己見的性格特質得以延伸,在衙門面對已被張驢兒買通的官員,單純地以為這是自己的救命稻草將事情的發展經過稟明,但單純的竇娥沒有考慮到張驢兒已將太守桃杌買斷,無論竇娥如何陳情皆無力回天。雖然意志堅定的竇娥與張、桃為首的黑暗勢力糾纏不下,但黑暗勢力的魔爪緊緊抓住竇娥反抗的咽喉,“既然不是你,與我打那婆子”使得竇娥的人物命運發生了突轉,竇娥為了救下年邁的婆婆將污名認下,竇娥在這一戲劇情境中的戲劇行動最終選擇的契機發生在為救婆婆背下罪名,這樣關鍵性的時刻是竇娥人物命運的拐點,造成這一拐點出現的情節原因是以桃杌、張驢兒為首的貪官惡人出于個人利益而做出的迫害百姓的社會普遍問題,但這一問題的設置僅是戲劇情境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而竇娥在第一折中已表露出的孝順的特質使其在這一戲劇情境中必然凝結出解救與自己共同生活13年的蔡婆婆的情感動機,倘若竇娥的性格特點中缺少感恩與孝順的特質,竇娥的人物命運可能就有著別樣的發展進程。綜上可得出在第二折中關漢卿雖然也運用了社會問題推動情節發展,但同第一折類似,同樣只是戲劇情境的組成要素之一,而竇娥的個性與意志的選擇才是真正推動情節發展的根本動因。
最后來看《竇娥冤》一劇的重頭戲——法場誓言。第三折的戲劇情境延續了第二折中竇娥為了使蔡婆婆免于責打認下冤案,竇娥被押赴刑場,眾人齊聚刑場。在這一折中人物關系極為明晰且關聯性不強,蔡婆、監斬官、劊子手只是模糊在戲劇情境外圍的角色,主要展現的是竇娥在刑罰將至時的個人內心活動,關漢卿將內心活動轉化為唱詞,形成在場的“獨白”。竇娥在第二折“衙門冤案”中遭遇了衙門官員的不公平審判,內心已經知道在如此的社會中公平正義缺失、清明官吏缺位,自己的人生命運已經無法更改,所以,在第三折伊始,竇娥便高唱《正宮·端正好》《滾繡球》兩支:
《正宮·端正好》沒來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憲,叫聲屈動地驚天。頃刻間游魂先赴森羅殿,怎不將天地也生埋怨。
《滾繡球》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跖顏淵。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哎,只落得兩淚漣漣。
在這一折中的社會問題設置仍然延續了上一折的貪官惡吏對于平民百姓的戕害,但關漢卿在此將這種人與人的對立升華到人與天地間的矛盾對立,在這一對立關系中,人與人之間的階級矛盾、利益糾葛、愛情糾纏都淪為無足輕重的螻蟻。此外,在中國古典的道家思想中認為“道生一(德),一生二(天地),二生三(天地人),三生萬物。”所以,道德是天地人的根源,管轄與統帥著萬物的生滅,關漢卿筆下的竇娥站在生命逝去的法場質疑天地,實質上即為質疑天地人的最為本質的根源:“道”在道家思想中“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地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可見“道”在道家思想中具有社會公平的含義,竇娥質疑的“道”也就突破了天地萬物間道德的束縛,而是直指社會本質性問題——人是否生而平等。在社會劇的界定標準中追尋社會的本質是與展現人的普遍本質一致的,關漢卿在第三折將竇娥對于官員的質問轉變為對天地的吶喊體現出關漢卿“人本位”的哲學思想,劇本前兩折嵌入到戲劇情境的社會問題與現象,在竇娥與天地間的拷問下顯得無比弱小。但辯證的來看,正是由于在前兩折中關漢卿將社會真實存在的問題凝結入戲劇情境中,才使得在第三折中竇娥拷問天地的戲劇行動具備了合乎情理的邏輯性。綜上,劇作者在前兩折的情節鋪墊下在這一折盡顯天地思想,將最為普遍化但又最難回答的問題呈現于舞臺之上,同時,通過竇娥的奮力吶喊喚醒觀眾對于本質問題的思考與追尋。
阿瑟·米勒曾在《阿瑟·米勒論戲劇》中提出:“一出戲的深度和廣度是跟它所反映的人們的各種生活方式的深淺成正比。如果他對所有的人寫得越深透,即不是要么單寫他的主觀世界或要么單寫他的社會生活的話,其分量也就越重。”[6]這段話道出了關于“社會劇”中兩個層面的內容:社會生活與主觀世界。其中社會生活決定社會劇的基本屬性,主觀世界豐富了社會劇的藝術內涵[7]。通過對《竇娥冤》的分析可以得知,劇作者將社會問題凝結成的戲劇事件看作是戲劇情境的組成部分之一,而戲劇情境還包含了劇本當下的環境與人物關系,可知社會問題并非公案戲的絕對核心。在精心設置的戲劇情境下,將性格各異的人物放置于其中,凝結出了千差萬別的動機,在二者的合力作用下劇作者真正欲要探討的社會本質的問題躍然紙上,這一戲劇創作模式在其他三部公案戲《魯齋郎》《蝴蝶夢》《緋衣夢》中也有典型的展現。
二、“大團圓”結局對關漢卿公案戲界定的誤區
通過上文的解析可以發現,以“問題劇”思維研究關漢卿所作的公案戲存在著巨大的誤區,因此,得出關于公案戲的本質也是不全面、不合理的。后世學者在研究過程中出現的誤差應歸結于兩個方面:一是作品本身的復雜性;二是評論主體的復雜性。評論主體秉持特定戲劇觀念評價戲劇作品時,不免會出現對于戲劇作品本身理解的差異,且中國傳統戲曲的創作模式與劇本體制本就具有其獨特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現偏離戲劇本體的研究成果。就創作模式與劇本結構來講,大團圓結局模式最具普遍意義。
中國傳統戲曲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大團圓結局的模式,公案戲亦然。關漢卿在《竇娥冤》第四折中設置了極為動人的戲劇情節:考中功名、擔任要職的竇天章在各地巡回審查,竇娥的亡魂利用這一機會將案卷數次放到父親的眼前,竇天章決定徹查此案,竇娥亡魂與張驢兒等人當堂對質,最終還竇娥以清白。在《魯齋郎》中戲劇矛盾的解決方式是通過包拯智慧地修改文書斬首魯齋郎;《蝴蝶夢》中包拯作為清明官員通過睡夢中發生的蝴蝶事件給予主人公正義的翻案;在《緋衣夢》中錢大尹智勘閏香與慶安間的生死事件使二人最終喜結連理。通過梳理四部公案戲的情節線索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在黑暗的封建社會環境中普通人的性命如同草芥,階級鴻溝無法跨越,階級矛盾愈發不可調和,但劇作家在最后一折中設置清明官員的形象來恢復已破碎的正義。
現階段,對于出現大團圓結局的研究有三種說法。一是寄希望于封建王權實現自我完善,“恢復符合道德理想的社會秩序充滿了信心,堅信政治倫理和道德規范的治國功能。”[8]二是認為運用大團圓的方式“希望天下有道,善惡終有報;希望有人鋤強扶弱,為百姓撐腰;希望律法公正,保護弱者。”[9]以“機械將神”的方式試圖構建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三是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終于歡,始于離者終于合,始于困者終于亨”[10],提出的小說、戲劇應符合樂觀精神,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樂觀主義精神使得中國悲劇不同于西方悲劇“莊嚴敦肅”的風格,而呈現“苦樂交錯”的風格。綜合比較三種說法可發現,由王國維提出的觀點是建立在后人對于浩如煙海的戲曲文本進行的集中概括,可以得出關于中國戲曲最具普遍性的特點,即劇作家在民族精神的潛意識下做出的符合民族共性的結局選擇。因此,在悲劇意識方面,多數學者認為中國悲劇不如西方悲劇的原因也正在于劇作家約定俗成的潛意識創作習慣,倘若將公案戲的大團圓結局刪去,對于劇作本身的悲劇性是有增無減的,正是由于民族潛意識的作用,使用大量大團圓結局的模式使得刻意制作的美好沖淡了原本戲劇事件的悲劇色彩。也正由于這種虛妄的人造“美好結局”導致第二、三種觀點將具有民族潛意識的大團圓結局進行了過度闡釋,其理論基點是建立在將社會生活追求的本質性問題簡單理解為依靠“機械將神”或“賢明君主”的方式便可實現的基礎上,清官的形象是打破困頓現實世界的唯一武器,這一主旨的得出依舊源自將社會問題看作是元代公案戲劇作家追求表達的核心內容,單純地認為社會問題是戲劇作品的主旨,而沒有深入挖掘劇作家筆下人物身上的永恒人性與人的本質問題,這無疑是拋棄了“戲劇是人學”這一戲劇的根本特征,是典型問題劇的思維。
綜上所述,中國戲曲中大團圓的結局模式是導致問題劇思維出現的重要原因。在此筆者不欲判定此種結局模式與西方孰優孰劣,僅以戲劇應探討社會最具普遍性的本質性問題這一觀點,認為大團圓結局模式對于戲劇研究者探究中國古典戲曲是否存在西方意義上的悲劇作品以及在探討社會人類本質問題上產生了模糊對象與焦點不明的負面影響。
三、結語
以西方戲劇理論中“社會劇”的概念來界定關漢卿創作的四部公案戲,是建立在拋棄了作用于民族潛意識的傳統創作模式,即拋棄了大團圓結局帶來的美好假象。筆者認為,這四部作品的悲劇性戲劇情節都是圍繞著人類最為本質與普遍的問題,關漢卿的天地情懷與“人本位”的哲學思想造就了中國古典戲曲的社會劇類型。即使在無比黑暗的封建社會,戲劇也不應作為高臺教化的產物,應以其獨有的藝術特質成為蕓蕓眾生情感的聚集地,只有以人的感性生命為對象的戲劇作品,才能真正具有無限的藝術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