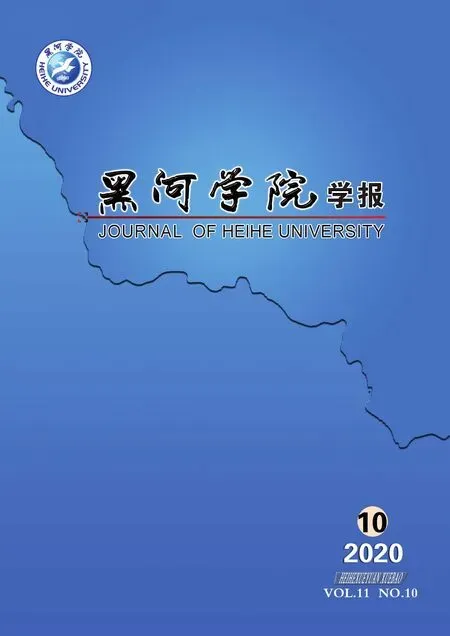文化地理與視覺互動
——論婁燁的都市空間轉向
李冠駿
(福州外語外貿學院 藝術與設計學院,福建 福州 350202)
總體來說,在婁燁建構的影像王國中,都市從未缺席。無論是其早期影片《周末情人》《蘇州河》,還是攝于21世紀之初的《紫蝴蝶》《春風沉醉的夜晚》,抑或近年來的《推拿》《風中有朵雨做的云》,在婁燁的影片中,都市以承載者、見證者,甚至窺視者參與敘事,外化著導演影像表達的沖動,同時,配合獨特的鏡語,傳遞著遭逢于都市叢林中的不同個體獨特的都市鄉愁。“電影中的城市,并不是現實中城市的簡單再現,而是一種想象和建構。”[1]誠然,被建構的城市作為一個特殊的意向,可由影片創作者肆意拼貼與堆砌,進而打上其鮮明的烙印。
婁燁早期的影片幾乎全部圍繞上海展開,上海作為一個充滿豐饒想象的都市空間,有著漫長的建構與書寫歷史。然而,不同于傳統海派主流敘事的兩個向度:“一個是左翼文化立場的階級敘事與都市人道主義批判,另一個是凸顯都市摩登景觀的現代性敘事。”[2]婁燁影像中的上海是縹緲的、含混的、不確定的,如夢一般游離于真實與幻想之間,仿若一個龐大的“召喚結構”,召喚著都市個體參與其中,用獨特的意識形態話語將其填滿。《周末情人》充滿叛逆的味道,改革開放的深入使物質逐漸豐裕,但年輕一代精神的焦慮卻日益凸顯,當表面的浮華與生活的真相形成對比,都市青年不再相信文化謊言,開始了反叛意味的景觀塑形。《蘇州河》中無論是都市形象還是人物糾葛都形成了相互補充的互文關系——在繁華/骯臟、虛假/真實的都市中所上演的“兩生花”的愛恨情仇。影像構筑的都市景觀具有傳奇性,所有一切真實記錄的畫面被一個個不確定的敘事元素逐一推翻,殘蝕著現代都市人群的情感信仰。《紫蝴蝶》更是把夢的迷離彰顯至極,導演雖選取了發生于1930年老上海的故事,卻巧妙地為這個“海上舊夢”置換了精神內核,表現出了被時代洪流扼喉的一代人的精神失衡。
從導演近幾年的影片來看,都市空間依舊是其敘事的主動力場,只不過敘事畛域卻開始產生位移,本文將以婁燁影片《浮城謎事》《推拿》《風中有朵雨做的云》(以下簡稱《風雨云》)為研究對象,以期探析其都市空間轉移后的新面向。
一、消解與重構——產生位移的都市美學
婁燁的早期影片,總是在試圖打破上海懷舊美學的樊籬。作為同質化的敘事空間,“老上海”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鏡像成為一代代年輕人競相追逐的夢。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的發展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但文化關照卻遠遠無法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基于此,年輕一代開始沉醉于懷舊美學彰顯的都市圖景。然而,當影像中五光十色的氣泡被戳破,粗鄙與殘酷的現實卻給了他們當頭一棒,鏡頭與現實的斷裂激起了年輕人的應激性反應,身體與思想上出現了跳脫秩序的反抗。《周末情人》就如實反映了年輕一代抗擊“文化泡沫”的過程,荷爾蒙的氣息也更好地表達了當下青年的文化偏執。《蘇州河》則與上海的歷史定位和發展脈絡息息相關。新中國成立后,上海曾一度被定義為工業型主導城市,為配合這一目標,一時間大量廠房林立。然而,伴隨著全球經濟的高速發展,上海也有了新的定位,鱗次櫛比的高樓逐漸取代了低矮的廠房,成為新的城市景觀。原來聚集在蘇州河兩岸的工廠成為待拆的、衰敗的空殼,靜默地封存著歷史的記憶。《蘇州河》的開場就赤裸裸地呈現了這一情景,攝影機如同眼睛一般掠過這些殘缺的軀殼,遍布的垃圾猶如歷史的碎片,四處逃竄,只留下岸邊游民空洞的想象。《紫蝴蝶》則直接在時代中拆解了懷舊敘事的“偽神話”,在思想與道德的批判中表現了一代人的精神迷失。
都市空間的轉移使得敘事美學產生了突圍與重構。當攝影機從上海轉移開來,彌散于影片中的懷舊氣質與歷史印痕則漸行漸遠。擺脫了歷史的壓抑,“當下”成為婁燁影片關注的重點。幾乎從《浮城謎事》起,其影片越發開始聚焦城市空間中極其普通的個體。不同于《蘇州河》中奇幻的美人魚以及《春風沉醉的夜晚》中的同性之愛,無論是《浮城謎事》《推拿》還是《風雨云》,雖然依舊有欲望、有糾葛,但導演摒棄了奇觀影像帶來的沖擊與刺激,用凝練的筆觸勾勒出都市普通個體失控的情緒表達,以及與現代文化洪流共生共存的悖論。《浮城謎事》以喬永照為中心,串聯起了與之相關的三段情感糾葛。影片有意弱化了都市男女的社會身份,取而代之地放大了他們的性別角色,便于強化認同感與代入感。生活的不平衡使人們產生了失重感,現實中的情感疏離使他們急迫地尋找同伴抱團取暖,以敵對現代性都市的冷漠。看上去,這似乎無關人們的社會性,是動物的本能欲望使然。然而,落腳于“人”的層面,道德與倫理的枷鎖又會使人們產生深深的負罪感,最終只能倉皇地逃離或被迫囿于原地。《風雨云》延續了這種影像書寫,所不同的是,影片中的都市個體被貼上了社會身份的標簽,無論是林慧、姜紫成,還是唐奕杰、楊家棟,他們或是事業有成的企業家,或是政府官員、警察,身份的標榜雖然使他們擁有了得以支配的權力,但最終一切還是煙消云散,他們成為時代演進與都市發展的注腳。《推拿》將鏡頭對準了盲人這一特殊群體,導演在影片中利用他們視覺的缺失巧妙地進行了視點置換——他們看不見彼此,他們對于外界是未知的,所以,他們自認為安全地肆意表達與宣泄著自己的情緒,但這一切卻通通暴露于觀眾視野之中,觀察者凝視著他們,正如凝視著在都市中裹足不前的自己。
二、文化與地理——時現時隱的景觀形態
“‘文化’通過時間作用于‘自然景觀’并且形成多種‘形式’的混合物(人口、房屋、生產、交往),這些形式的混合物結合起來就成為‘文化景觀’。文化景觀由自然景觀通過文化集團的作用形成。文化是動因,自然區域是媒介,文化景觀是結果。”[3]在文化地理學中,文化與空間、地點和景觀密不可分,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會催生出不同的可視的物質痕跡,而這種痕跡的形成依靠時間對自然環境的打磨。上文提到,歷史賦予了上海浮華與摩登的氣質,神秘與魅惑的物質景觀通過時代影像的表達,使年輕一代為之神往,然而,打破五光十色的都市鏡像,擁擠、無序的現實與庸庸碌碌的人群又使他們感到恐慌,于是,他們開始了一場對峙——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抵抗。由此,在婁燁的“上海空間”中,以反抗與逃離為題中之義的敘事動向逐層漸顯。離開了上海,婁燁的敘事空間依舊在南方的城市流轉。《浮城謎事》選擇了武漢作為故事展開的地點,《推拿》的故事則發生于南京,《風雨云》的攝影機聚焦在了廣州的一座待拆除的城中村。無需打破都市神話的光環,“地方感”成為導演敘事的焦點,進而在有意強調與弱化中完成主題傳遞。
“地點”所包含的意義相較于位置更加廣泛。“地點”是一個獨立的實體,通過所擁有的獨特的文化景觀標榜自身,同時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生活在其中的個體的經驗與理想具體化。《浮城謎事》在開場通過空鏡頭的方式展示了武漢的地標建筑——長江大橋,俯拍鏡頭漫不經心地在其上空掠過,卻可以使觀眾輕易地鎖定方位。《推拿》通過人物的對白,點明了沙宗琪推拿中心的所在地。在《風雨云》中,讓觀眾對于廣州感受最直觀的是人物所說的方言——粵語。作為三座經濟發展度與文化傳承度都較高的城市,武漢、南京與廣州都可以為都市個體提供完整與復雜的都市體驗感,但同時配合影片不同的表意,它們又各有側重。武漢時常云霧繚繞,少有放晴,正如《浮城謎事》的故事,層層推進,迷霧重重。南京厚重的文化感與內斂的氣質可以更好地襯托《推拿》中盲人群體的波瀾內心。廣州的開放度、包容度與風云變幻則與《風雨云》的敘事母題相互呼應、相輔相成。
導演在點明地理坐標的同時,也對片中具象的城市文化景觀進行了有意弱化。在這三部影片中,都市華美的外表被撕開,影像中不再出現都市中的經典地域,取而代之的是滿目瘡痍的街頭巷尾。淺景深鏡頭剝奪了城市空間的縱深感,由于壓縮而產生畸變的人或物處于前景,后景則是一片虛焦的模糊景象。《浮城謎事》中的罪惡,《推拿》中的焦灼,《風雨云》中的欲望,都被無限放大到了畫框之中,這些鮮活而又各異的都市體驗不正是生活在不同城池中的人們所正在經歷與體驗的嗎?導演模糊了地域特征是為了更好地使觀眾產生共情,普適的都市情感驅動人們反思自我,在快速發展的都市中探尋更深層次的精神地標。
三、瞥視與凝視——由表及里的視覺互動
德國理論家齊美爾在其代表作品《感官社會學》中強調了現代都市文化中視覺所處的支配地位。眼睛具有仿像功能,可以如實地記錄客觀現實。但雖然視覺是自然所賦予的,人們看待事物、感知世界的方式卻被文化化了。純粹的視覺觀感無法準確描述人們的生活體驗,所以,人們利用視覺/觸覺來感知與探索未知世界,對捕捉到的信息進行加工,形成個別化的經驗系統。人們對都市空間的探索亦如此,這點在婁燁的影片中表現尤甚。在婁燁的都市影像中,對底層空間的描摹與建構一直占據重要位置。在光怪陸離的城市之中,“被拋棄”的人群游離于浮華之外,對于他們來說,他們渴望融入城市,參與城市建設,彼此之間共享心得與體驗,但城市卻沒有在實質上真正接納他們。這就造成了他們與城市之間產生了疏離,從而在城市邊緣游蕩。當這一部分個體接納了自身并且無異議地認同了自己在城市中的處境,就會削弱行動力,采用假想的方式投身于城市建設,此時,眼睛就成為重新了解與探索都市空間的工具。婁燁的早期影片就體現出了視覺探索的重要性,無論是《周末情人》還是《蘇州河》,但在視覺互動中,奇觀性大于體驗性,加之都市個體的目光所及局限于“本邦”,所以,人們通過視覺探索都市空間,進而獲得都市體驗的表現不及后續影片顯著。在《浮城謎事》等三部影片中,導演采用了瞥視與凝視兩種方法探討了個體與都市的視覺互動,凸顯出人們的身份焦慮與情感困惑。
“瞥視”是一種瞬間現象,是最直接、最純粹的相互觀察,帶有一定的片面性,大多用于確定最初印象。“凝視”則是一種被延長了的觀看形式,是人們在城市中生活與體驗后,產生獨特體悟的方式。《浮城謎事》與《風雨云》的故事頗具相似之處,都有懸疑的兇殺案件與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影片中的人物大抵可以分為三類:施暴者/犯罪者、受害者、秩序維護者,同時施暴者與受害者又是可以相互轉換的,受害者基于過往經歷做出應激行為,成為施暴者。起初,受害者們都渴望在都市中擁有一段穩定的情感,這是他們基于“瞥視”所得的對于城市情感的想象。但城市內部權力分布不均,物質掌控兩極化,造成了人與人之間情感的疏離與冷漠,人們不再彼此信任,一段純潔的有溫度的感情成為奢念。所以,在“凝視”(體驗)過后,受害者由于情感困頓而逐漸封閉自己,偏離既定軌道,向施暴者轉變。而身為秩序維護者——警察,也同樣在情感羈絆中迷失自己,試圖在情與法的兩難中守護搖搖欲墜的規則。《推拿》則由觸覺代替了視覺,成為特殊群體探索都市空間,獲取都市體驗的方式。影片中大量搖鏡頭所形成的不規則構圖真實表現出盲人內心世界的無力以及對于城市生活的恐慌——他們由觸摸感知到的物體是否真實?這個城市又是否真正接納了他們?
從《周末情人》到《風雨云》,都市在婁燁的影像中歷經起伏,形成了不同類型的美學范式。無論是反抗式的奇觀影像,還是普適性的情感圖譜,都市空間的灰暗底色從未改變,偌大的城市時常讓人們感到恐慌,迷失方向。探析現代性都市的發展,婁燁從未止步。其影片提供的可借鑒的都市體驗,足夠讓人們寬慰,幫助人們從內心生出一種力量,抗擊虛空與浮躁的都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