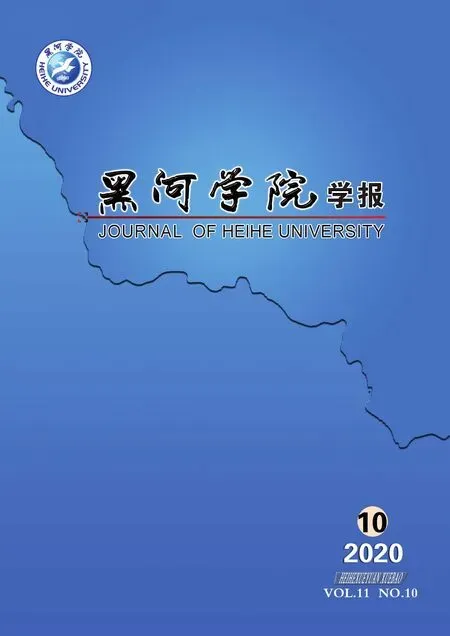石黑一雄小說的人文主義思想
李明慧
(大連財經學院 國際商學院,遼寧 大連 116000)
石黑一雄在面臨生存的壓力與各國文化之間的沖突,與個人人生價值無法實現等多重問題下,開始思考社會發展與人性,開闊的文化發展視角為石黑一雄在文學創作時提供更為冷靜的客觀思考方式。石黑一雄的小說不同主人公的視角下對人物的發展境遇與人性開展不同描述,反映了不同個體的生活尊嚴訴求,對社會發展文化發展進行了更為深刻的思考,反映出對人文主義最主要的思想。
一、人物個體生活尊嚴訴求
石黑一雄所描述的小說作品大多數為國際化視角,其作品主要內容描述為世界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類生存的狀況。在石黑一雄創作作品的初期,開始嘗試對普通人的生活描述,在社會發展背景下種種不可抗力性原因下的生存狀態。如石黑一雄的小說作品《長日留痕》,該作品的主人公為一名普通的英國管家,小說內容主要描述了英國管家個人悲劇式的生活經歷,將主人公的尊嚴與軟弱進行綜合性描述,同時也放棄了愛情和做人的權利。該小說作品的描述依據主要是老派英式紳士的文化與英國早期民族性格特點對于英國人物的性格影響等特點,該文章主要揭露了過去人民生活的保守觀念屬于較為悲慘的個人悲劇,從而對主人公的生活經歷進行描述反思,普通人在壓迫的社會中如何真正去生活,追求生活中的尊嚴。
從某種意義角度來分析,石黑一雄作品中的人物生活尊嚴訴求更多是對自身生活向往的描述,以及無法實現的目標與抱負[1]。作品《長日留痕》中的主人公為英國管家,在主人公所生活的英國社會被階級系統所籠罩,在較為壓迫的社會環境中去追求工作尊嚴,依然堅持有尊嚴的生活狀態。尊嚴對于人生價值來說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得到愛與尊嚴。但對于主人公來說,階級性的社會環境注定其自我尊嚴缺失嚴重,雖然小人物依然在努力地生活,去追求人生目標,試圖填平現實與理想之間的鴻溝,最大程度實現個人價值,兢兢業業完成工作。在小說的描述中使人物的生活更加有追求,描述更為充沛的人物性格,在生活中追求人格尊嚴。
《長日留痕》小說中主人公斯蒂文森對于個人尊嚴的主要定義為所處社會地位與職業,其認為只有取得一定的職位或社會地位才能得到他人尊重與尊嚴。斯蒂文森身為英國管家,為維持個人形象與尊嚴,生活與工作中極其克制個人情緒,將個人尊嚴依靠于建立對達靈頓公爵的盲目忠誠與對于公爵的命令無原則性遵從,對公爵的遵從是斯蒂文森個人尊嚴實現最主要的途徑。斯蒂文森在執行公爵命令時不會考慮其他各種想法與因素,只要完成對公爵的服務,其人生信念中只有公爵功成名就自己才能實現真正的價值,成為完美的人。
斯蒂文森對于公爵命令的盲目追求已經喪失了個人實際價值中的最基本尊嚴,與其追求實現尊嚴過程中具有極為相悖的理念差異。在英國社會階層中,斯蒂文森身為管家是不具備個人尊嚴的,一些達官貴人甚至會調戲斯蒂文森的工作,但在斯蒂文森的理念中,調戲也是工作尊嚴的表現,在過去社會階層概念影響下達官貴人的調戲為正常行為,其尊嚴獲取是行為是否符合當時階級社會的等級制度[2]。但若社會地位與個人尊嚴對等,以斯蒂文森為代表的英國管家等處于下層的群眾根本無法擁有全部的尊嚴,階級等級理念與個人尊嚴追求存在著嚴重的理念差異。斯蒂文森對于個人尊嚴的定位依托于公爵的個人發展,他在生活工作中盡力維護自己身為管家所具有的階級性尊嚴,幻想自己在工作過程中可以實現個人綜合價值,但在實際工作中,斯蒂文森對于達靈頓公爵的盲目尊崇與服務,會因公爵的錯誤形式使自身追求的精神價值徹底崩塌,為此斯蒂文森為盡力維護個人價值,將達靈頓公爵描述為紳士,同時也認為公爵所做出的對于社會發展是具有價值和意義的,自己也做出了相應的貢獻,營造極為虛假的個人尊嚴。
在石黑一雄的小說描述中,通過描述主人公的西部旅行來隱喻暗示個人思考,斯蒂文森的旅行過程也是個人價值與尊嚴相悖的精神旅途,斯蒂文森在職業發展中盡全力抹去錯誤價值觀,使得自己更為完美地發展,錯誤的觀念使得一生追求的尊嚴都無法真正實現。小說中對于尊嚴的描述是在社會發展階段中較為矛盾的兩種觀點:一種尊嚴內容是斯蒂文森對于尊嚴與職位相對等的關系,另一種概念則是尊嚴不僅僅是紳士所具有的,任何階層群眾都有擁有尊嚴的權利。無論社會地位、無論貧窮富貴,在人生發展中都具備追求尊嚴的權利,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思考,不同階層對于尊嚴的共同追求才是尊嚴的真正意義。斯蒂文森在旅行過程中的兩種尊嚴不斷做矛盾斗爭,但仍然未真正理解到個人尊嚴的實際意義。通過對斯蒂文森階層中小人物的描寫,石黑一雄對個人尊嚴的追求進行了一定描述,主人公對于尊嚴的追求更像是普通生活中一些人的實際生活狀態。雖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為追求尊嚴而努力著,但卻為了所謂的尊嚴,拋棄了人性中最美的價值,如親情、愛情與美好青春。在追求人生價值過程中,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在遵循個人道德底線的基礎上去追求個人尊嚴,在不斷的生活中豐富個人閱歷。石黑一雄的小說描述中并未完全否定斯蒂文森的人生尊嚴定義,真正的尊嚴追求是通過自身價值的實現,尊嚴也是職業與社會發展相互作用,不能以犧牲個人道德為代價。
二、小人物實現歷史責任的過程
石黑一雄在作品寫作中會構建一定時期的社會背景,建立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通過對小人物歷史責任的實現來構成小說整體結構。石黑一雄在寫作該類型作品時,對于精神等思想構成更多依托于小人物實現道德與承擔歷史責任,通過對小人物的描寫上升到一定高度的思考。石黑一雄小說作品《千萬別讓我走》,該作品以英國克隆技術為背景,營造了拯救與犧牲奉獻的精神世界。石黑一雄在小說的開頭描述克隆人凱西的看護員工作內容,表示凱西的恪盡職守。石黑一雄作品《長日留痕》中的管家斯蒂文森對于工作具有夸張的責任感,而作品中最為諷刺的表現是斯蒂文森對責任的追究最終被證實是錯誤的實現。理念的差異化與結局的戲劇化描述了以斯蒂文森小人物為代表的悲劇色彩,就如人類拼命地沖向所向往的天堂生活,但當大門真正關閉后卻發現自己身處地獄,具有極大的嘲諷意義[3]。《長日留痕》所表達的都是小人物對尊嚴的追求,《上海孤兒》是對虛無的空想主義追求,過于虛無縹緲的聲音,為小人物營造了美好的生活遐想,在受到烏托邦聲音的迷惑后,營造出美好的理想方向,從而激發小人物對所營造的假象的盲目狂熱追求。悲劇性的結尾是二戰后英國社會最為真實的人物寫照,在小人物的推動下,帶動了英國社會的歷史進程。
石黑一雄作品中的主人公班克斯為實現偵探的理想而努力,并通過偵破一系列案件而成功躋身英國的上層社會。在上層社會生活中,班克斯將個人發展與英國的興盛相連接,增強了自身的社會責任與歷史責任,班克斯認為自己是有價值的人物,但班克斯得到的是上層社會人對他的否定,使所有的自信全部崩塌,盡管偵破了一系列案件,但仍然是一個小人物,并無法真正實現偉大理想[4]。英國的機器文化已經滲透了社會各層次的發展,上流社會被賦予更為強烈的歷史責任,特別是西方帝國在開展歷史擴張階段,經過帝國主義對于侵略思想的大面積推廣,上流社會人物認為這是必須履行的意義,因此,英國的擴張行為已經潛移默化地影響了班克斯的思想,使其自認為自己肩負起了傳播英國文化與拯救世界的歷史責任,以班克斯為代表的主人公,為自己行為披上了更多的歷史色彩,將個人行為與歷史責任相結合,并以為必然。
盡管班克斯認為自己承擔了巨大的歷史責任感,但當真正回到英國時,仍然是一位基層中的小人物,而自身也未真正實現自我發展價值,將自己利益的獲得沉浸于英國帝國主義歷史責任成就感中,然而班克斯所承擔的所謂歷史責任實際只是英國帝國殖民侵略的內容,強大的歷史責任感并未提高班克斯在英國帝國中的地位,更多的小人物是帝國侵略的犧牲品。當自己奉為理想的精神已完全偏離初定目標,一切如泡沫般破碎。石黑一雄通過對班克斯的歷史責任實現的描述,對歷史進行片面性的批判,具有文化意義與價值。
三、后現代人類精神思考
石黑一雄作品更多是對人類價值的思考與探究。石黑一雄的小說描述大多數都圍繞主人公的情感思考,對主人公生存環境進行描述,更加注重小說內容與讀者之間的互動。石黑一雄在作品寫作時更加希望可以通過小說中的人物狀態對讀者產生一定的影響,思考后現代人類生活的生存意義與價值實現。石黑一雄在對人物描述時更能抓準人物的社會特性,通過不同階段人類的描寫,使得讀者可以在文章閱讀時得到更多性格上的帶入,有更多的共鳴[5]。讀者在閱讀文章時不但可以了解到書中主人公的社會經歷,更能對自身價值實現做出更多的思考。石黑一雄小說作品《無法安慰的人》更體現了后現代人類精神的思考,在該部作品中讀者閱讀文章時可以將任何地點做場景的確定,小說中的世界雖為想象世界,但作者通過細致描述與人物性格特點描述將讀者更容易代入到小說情境中,石黑一雄的小說不單純是故事內容,更注重的是對人類社會現象描述,從而更深入思考人類生存與價值的各種問題。
石黑一雄在寫作中已經認識到了現代社會人類精神價值危機,所以,在作品中通過以后現代描述手段為基礎,探討當下人類生活自我價值實現與體現人文關懷,在作品中更多描述的是對個人精神價值的追求與人性描述的體現。快速發展的社會與過于波動的經濟市場,使人們在生活中與工作中長期處于焦慮的狀態,利益化的生活已經成為人類的生存常態,在社會工作中更多的是追求,以最少的時間換取最大的經濟價值。時間的缺失與個人價值的無法實現,困擾著人們日常生活成為焦慮的狀態。石黑一雄在小說《無法安慰的人》中通過對于主人公的混亂的生活狀態描述日常繁忙的生活,使得讀者在閱讀時更能找到相似生活狀態。小說在對主人公進行展開描述時,多數是對自身內容的體現,瑞德到了陌生小城市,未有明確的工作計劃與日程表,對于任何事物無法進行準確的估計,無規律性的生活使得自己的生活狀態正在向奇怪的方向發展[6]。然而主人公瑞德的生活狀態似乎更符合當下人類的生存狀況,倉促的時間,做不完的工作,以及繁忙的事物已經成為人類焦慮最主要的問題,在工作中,生活中都無法得到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焦慮已經成為當代人生活的最主要情緒,雖然在追求人生價值中不斷努力,但是為此卻失去了體驗生命意義的機會。如故事里的主人公瑞德,雖然犧牲一切換來了舞臺演出的機會,但是禮堂中卻未有一位觀眾席,甚至都已經搬離了禮堂,雖然犧牲了全部,但卻未換來任何有意義的目標實現。
當代人經過繁忙生活后陷入無休止的重復循環中,石黑一雄在小說描述中采用了部分夸張的手法,表現了社會與人、人與人之間的價值,以荒誕的藝術形式向人們呼吁挽救精神價值的重要性,同時更注重的是對人類精神世界的思考。
四、結語
石黑一雄的小說不僅描述社會環境,更多是對人物的人生價值思考,反映個人主義思想。通過小說內容對小人物的描述,通過不同社會階級背景下的人物生活,展現當下人生存的困境。石黑一雄小說的主要目的是將讀者的目光脫離社會發展背景而去更加深刻地思考人物困境,從歷史發展與形式狀態轉變對人的關注。石黑一雄小說的主題有極大的影響,石黑一雄在小說描寫中去思考人類社會的發展價值與生命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