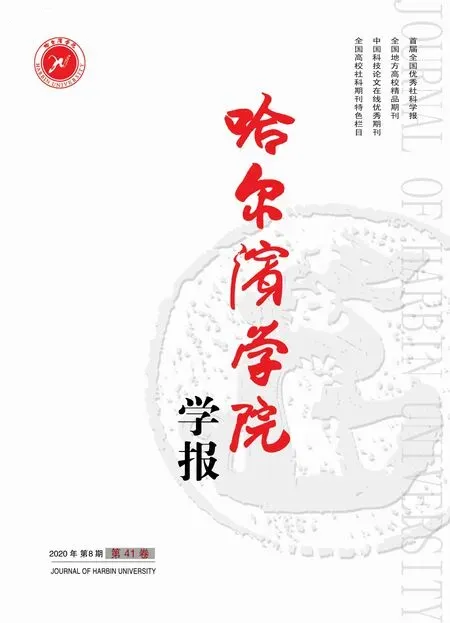近代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在華文化活動探析
王 瑞
(安徽大學 歷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19世紀40年代,西方列強用武力打開近代中國的大門,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中國的。丁韙良作為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1850年進入寧波傳教,他在寧波的十年中,不僅學會了官話和寧波方言,還自創了一套以羅馬拼音為基礎的拼音系統。“亞羅號事件”為丁韙良的北上提供了契機,他以列衛廉美國使團的中文秘書隨行,并參與了《中美天津條約》的簽訂。隨后擔任北京同文館總教習,于1872年8月創立近代第一份中文報刊——《中西聞見錄》;后擔任《尚賢堂(新學)月報》主編、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又輾轉武漢擔任湖廣仕學院總教習。學術界關于丁韙良的研究并不少,但關于他在中國的文化活動卻少有系統的梳理和評論。本文以中西方文化交融與沖突為切入點,整理了他在中國的系列文化活動,深入挖掘這些活動所體現的文化教育觀。
一、丁韙良在華前期進行的文化活動
(一)學習中文、研讀經典、編寫書籍
丁韙良來到中國的第一件事便是學習漢語。他在官話和寧波話老師的教導下具有了一定的漢語及方言基礎。除了利用學習漢語為媒介傳教外,他還系統研習中國傳統文化經典著作,如:《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尚書》《易經》《詩經》《春秋》《周禮》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構成元素進行大致了解,并把中國傳統文化與上帝加以融合,編寫了《天道溯原》,證明基督教和中國文化并不是完全相生相克的,為基督教的傳播提供理論依據。如引所言:“嘗思大道不限于邦國,至理可通與中外。如孔氏六經出于魯而遍行齊、魏、晉、楚諸邦,傳之后世。非獨重其人,重其言之衷于道也。”[1](P1)他肯定了孔氏六經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分析了傳統文化之所以根深蒂固的原因是“道”,接著利用中國的“開卷有益”說,闡明西書的益處,即“書之出于外國者,見所未見,愈有擴其胸懷。今是書出自西人之,而其道實非西人所創論”,以此來尋求中書與西書的共通之處。此外,該書還涉獵大量的關于基督教的內容,強調了基督教的優越性,如:“嘉慶年間,始遣使往教南洋,島夷其人,無文字無禮儀草服土舍尚力棄德好—嗜殺角勝即食敵人之肉祭神,以人為牲。往教者以西國文字按其土音作書設館,以教之福音以誨之。老幼貴賤聞之者,如聞喜報,即毀淫祠,從真神改土舍,易綿服,息爭—修人紀,自謂福音之道如天賜靈丹,我病既除,烏可秘而不傳,即遣人轉傳于他島。”[1](P46)其中,以印度、緬甸等國家的一些人皈依基督教為例,意在增強中國人對基督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從而爭取他們加入基督教。這也正說明此書很大程度上是為傳教活動而著,但客觀上也不乏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認識。
(二)擔任翻譯,參與中美外交
深厚的語言功底為丁韙良在“亞羅號事件”之后以美國使團中文秘書一職參與中美談判奠定了基礎,最終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其中,第二十九款規定:“耶穌基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為勸人行善,凡欲人施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傳教習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凌侮辱。凡有遵照教規安分傳習者,他人毋的騷擾。”[2](P95)該條款為西方傳教士提供了最初的法律人身保障。此內容為之后《北京條約》關于傳教士在中國的一些權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一直以來,丁韙良溫和的、傳統的傳教方式并未獲得中國人的認可,也未能取得明顯成效。而《中美天津條約》的簽訂似乎讓丁韙良看到轉機。如王立新所言:“然而這非但沒有消除反而刺激了傳教士借助武力獲取更多特權的欲望。”[3](P70)確實,丁韙良的北上之行感觸頗多,正如他所言:“北上之行使我關注大清國的北部,并覺得應該去那兒服務。”[4](P137)此后,他開始把文化生活的重心從寧波轉到北京。
二、丁韙良在華后期進行的文化活動
1860—1890年的中國處于初步自省的時代,洋務運動在這期間發酵并發展,丁韙良因時而變,抓住機遇,利用西方的科學技術及格物之術吸引更多中國人的目光。他北上之后,正是中國洋務運動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時候,《中西聞見錄》的刊發也免不了帶有迎合這場洋務運動的意味。丁韙良便利用報刊這種易于傳播的媒介,大力傳播西方科學技術。
1872年,丁韙良創立了近代中國第一份報刊——《中西聞見錄》。“《中西聞見錄》系仿照西國新聞紙而作,書中雜錄各國新聞近事,并講天文地理格物之學。”[5]《中西聞見錄》以介紹西方近代科技的方章為重點,另有雜記、寓言、詩歌、時政短評等文章及各國近事的新聞報道。其中,“各國近事”中有20余篇為丁韙良撰寫,涉及當時利國利民的一些科學技術,如對電報的介紹及后來電報在中國取得的良好反響;雜記也有多篇由他撰寫。此外,他還發表了20余篇關于格物之學的文章。
關于電報,丁韙良是這樣描述的:“始至五十年前始得電氣傳信一法,其超越舊制奚啻萬倍,在昔人見云中電光閃灼,常以比作事之神速,故從未有思及取而用之者……各國仍多用之,以其捷而且便也。”[6]可見,他思想中除了解決電報在應用中的問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給人民帶來了便捷。另外,他還就如何更加便捷使用電線提出了自己的想法,[7]并從電報使用過程中,讓中國人看到其玄妙之處,增強對電報的認同。從19世紀80年代,丁韙良最初介紹電報時中國官員的態度“……太神奇了,他們說道,但是我們在中國沒法用他,人們會偷走銅線的”,[8](P156)到1906年“中國的各個行省都布滿了電報線,巡撫和都督們都使用電報來進行聯絡,而不是用傳遞緩慢的書信,老百姓也喜歡用這種迅捷的方式來跟遙遠的成員互相交流,以及逐不出戶地跟遠方的商家解決生意上的問題。”[8](P156)從這個轉變來看,中國顯然已經開始接受傳教士竭力所宣揚的西方科學技術。
三、丁韙良在華文化活動體現的文化教育觀
(一)從極力否認到部分承認“西學中源說”
丁韙良來華之后對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有了系統的認識,并進行了刻苦的鉆研。在《中西聞見錄》中,他雖然積極借鑒中華傳統文化進行傳教,但他內心深處并不承認“西學中源說”。他在《中西聞見錄》里發表了大量的反對此觀點的文章。而在后來《漢學菁華》一書中,他則部分承認了此觀點,認為西方的柏拉圖和中國的孔子思想有共通之處,即孝道。他認為:“兩者不僅在討論的主題上是一致的,而且在名字上也有驚人的相似。”[9](P67)在科技上,他一直認為西方化學來源于中國的道教,道教的煉丹術催生了西方的化學,為當時西方科技對中國科技的實力碾壓提供了辯駁的依據。他認為,被廣泛應用于戰爭的火藥、應用于航海的指南針、羅盤,也是中國人發明的。對于數學和物理,丁韙良也肯定了中國的成就。對于哲學,他認為:“西方的不可知論流派對于他們來說聞所未聞。但即使在這一方面,中國人也比西方早了好幾個世紀。”[9](P18)可見,丁韙良并未否認在西方應用更為廣泛的技術是在中國萌芽和起源的事實,這給了西方人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看待中國及中國文化。此外,他還編寫了多部專著,《翰林集》《中國的覺醒》等都為他成為漢學家奠定了基礎,并讓更多西方人開始認識中國、了解中國,從而增強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
(二)對科舉制的客觀看法
丁韙良承認科舉制的優越性,認為科舉就是為國家選拔人才的一種機制,而最終通過科舉考試達到這種目的。此外,科舉制對人民的教育與政府的穩定會產生影響,因為競爭機制是科舉制的特點,既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懷才不遇而引起的騷亂,也可以增強階層流動,還可以制約皇權。對美國來說,他認為:“假如我們采取中國選拔人才的方法來為我們的國家政府選擇最優秀的人才,那么它對于我們的政府管理機構所帶來的有益影響絕不會小于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技藝發明。”[9](P207)他堅持認為:“它更符合我們自由政府的精神,因而可以期望它在這個國家結出比中國更甜美的果實。”[9](P219)另一方面,他認為科舉考試缺乏自然科學的內容,他把這歸咎于中國固守的傳統,他是這樣描述的:“在中國,文學高于一切,而科學則什么都不是。人們一生沉溺于文字,而不是實物;對于習得能力的培養要遠甚于對于創新能力的培養。”[9](P216)
四、結語
丁韙良在華的文化活動經歷了從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并極力促進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到利用報刊傳播西方的科學技術。他的多重身份引導他不得不做出一些改變。不能否認的是,傳教具有一定的侵略性,最起碼在文化上是不可避免的,雖然丁韙良一部分融合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但從根本上沒有改變宣傳基督教的本質,甚至還歪曲一些中國傳統文化來為傳教作鋪墊。但同時也正是丁韙良翻譯多篇西方著作,把西方先進的外交制度、法律、技術等引入中國,并把中國的傳統文化詳實地寫進自己的著作中,才得以讓西方人重新審視中國。丁韙良在向中國傳播西學、向西方傳播中學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促進了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也為現今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