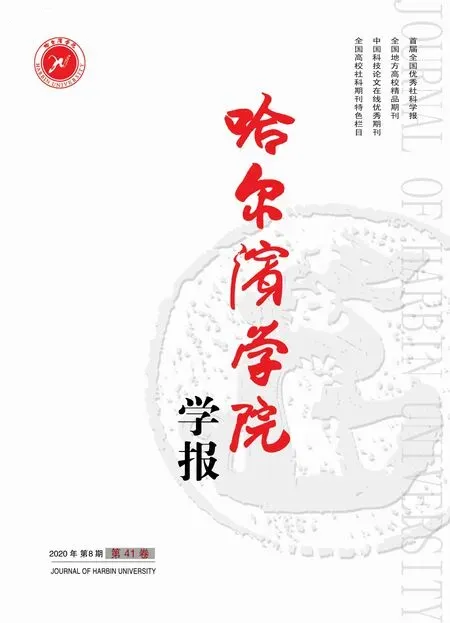現當代外國詩歌作品中的后現代性研究
——以鮑勃·迪倫為例
丁 艷,俞 靜
(1.合肥職業技術學院,安徽 合肥 238000;2.合肥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長期以來,鮑勃·迪倫作為民謠歌手、搖滾歌手活躍在流行文化領域,被人們所熟知。2016年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引發出大眾對音樂與文學的討論,當討論聲與爭議聲逐漸消失,鮑勃·迪倫詩歌作品的后現代意味開始散發出獨特的文學魅力,引導人們認識與理解文學與音樂的聯系。
一、鮑勃·迪倫詩歌思想的后現代性建構——矛盾與荒誕
鮑勃·迪倫深受后現代主義影響,其詩歌中不合情理、不合邏輯,充滿著沖突與矛盾的荒誕思維,蘊含著豐富的后現代性思想,有著巨大的感召力。
(一)荒誕與矛盾世界的構建
1.矛盾的構建
(1)沉默與激進。鮑勃·迪倫童年經歷戰爭的陰影,使其恐懼戰爭、厭惡戰爭,所以其詩歌中蘊含著反戰思想,如:《敲著天堂的大門》(Knocking on the door to heaven)、《答案在風中飄蕩》(The answer is floating in the wind)、《只是棋局里的一枚卒子》(Just a pawn in the game)等。[1]其中,《只是棋局里的一枚卒子》寫于1963年美國的一次種族隔離分子謀殺事件之后,鮑勃·迪倫在詩歌中將種族隔離分子(兇手)形容為“棋局里的一枚卒子”,諷刺兇手只不過是被人利用的工具。鮑勃·迪倫對戰爭的憎恨使他成為一個激進者、反抗者,但很快又收起自己的激進,轉向沉默與孤苦,在毒品與車禍的摧殘下面對人生的抉擇。[2]
(2)“預言家”與“平凡人”。1964年,鮑勃·迪倫發表了唱片《時代正在改變》(The times are changing),該唱片中最著名的是同名歌曲《時代正在改變》:“現在步伐遲緩者/將來必快速顯現/現在,領導者將在未來/因為,時代正在改變(節選)”,歌詞中暗含著大量預言,如:“步伐遲緩者將來必快速顯現”“到現在為止將成為過去”“領導者將在未來”等。這張專輯將他推上“時代代言人”的位置,并被稱為“預言家”。[3]
1968年,鮑勃·迪倫發布專輯《納什維爾天際線》(Nashville Skyline),同名歌曲《納什維爾天際線》用簡單、直接的言語表達了鮑勃·迪倫的自我回歸與平淡心境,“與你獨處”不僅是與愛人相處的快樂,也是鮑勃·迪倫對“時代代言人”這一標簽的“溫柔”抵抗。
從沉默與激進的矛盾、“預言家”與“平凡人”的矛盾來看,鮑勃·迪倫如同其他后現代派詩人一樣,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個體。[4]既可以成為“反戰代言人”“時代預言家”,又可以成為“平凡的沉默者”;既能在混亂的社會中保持激進與斗志,又能在時代浪潮中回歸平淡,這種矛盾性始終伴隨著鮑勃·迪倫的創作歷程,使他的詩歌散發出獨特的藝術魅力。
2.荒誕的構建
鮑勃·迪倫在詩歌中以荒誕、喧鬧、詭譎、光怪陸離的超現實主義場景增加詩歌的沖突性,利用隱喻與暗示構建詩歌的荒誕思維。[5]如《重訪61號公路》(Revisiting Highway 61)中的《荒蕪巷》(Desolation row):“他們販賣死刑犯的明信片/他們正在把護照變成褐色/美容院到處都是水手/馬戲團已經進入城市(節選)”,其中“絞刑明信片”暗指1920年三名在馬戲團工作的黑人因強奸白人少女而被民眾私下絞刑,行刑現場被印制成明星片銷售;“護照變成褐色”暗指美國官員的因公護照;“擠滿水手的美容院”諷刺美國男性的懦弱。[6]這一系列荒誕的象征與隱喻,突顯現實社會的“荒蕪”。
(二)否定與建設的對立
1.后現代主義的否定
(1)否定社會現狀。美國哲學家波林羅斯諾明確指出后現代時期的特征,即:冷漠無情與令人絕望。鮑勃·迪倫深受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其早期詩歌作品尤為明顯。如:《暴雨將至》(Heavy rain is coming)中,鮑勃·迪倫通過視覺與嗅覺描寫向讀者展現了當時社會的腐朽、黑暗和血腥,字里行間充滿了恐怖、陰郁和血腥,突顯其對當時社會現狀以及美好未來的否定。[7]
(2)對社會倫理的否定。鮑勃·迪倫認為,社會倫理的趨同性違背了人類最基礎的本能,即對自由的向往,所有社會倫理準則都是維護獨裁的工具。他在專輯《全數帶回家》(Take home all)中,將自己對當時美國社會倫理的否定顯露無遺,特別是歌曲《地下鄉愁藍調》(Underground township):“小心點,男孩/你無法逃脫/但是吸毒者、騙子/以及失敗者/在劇院里徘徊(節選)”,這里,鮑勃·迪倫營造出一個邪惡的人間,放眼望去盡是失敗者、騙子、吸毒者,社會倫理只不過是丑惡世態的“遮羞布”,每個人都在社會中迷失自我。
2.后現代主義的建設
經歷暴風雨般的反抗、批判、指責之后,鮑勃·迪倫逐漸認識到社會的變化與時代的進步,與過去全盤否定社會的自己告別,開始憧憬未來。這種思想上的轉變在詩歌中表現得尤為明顯。[8]如:《永遠年輕》(Forever Young),“愿上帝永遠保佑你并保護你/愿你實現你的所有愿望/愿你永遠為別人付出/愿你永遠年輕(節選)”。與以往詩歌的反抗與批判不同,《永遠年輕》是其與社會的和解,通過青春洋溢的情緒表達出對社會、對他人的期望、憧憬與祝福。[9]同時,也代表著鮑勃·迪倫的詩歌思想情緒從悲觀的破壞轉向了樂觀的建設。
(三)歷史感的喪失與內心的復雜
1.歷史感的喪失
鮑勃·迪倫在20世紀80年代期間的詩歌作品失去了對歷史厚度與深度的探尋,隨著商業目的增強,其詩歌的歷史意義逐漸喪失。1988年發行的專輯《妙境深處》(Deep in the wonderland),其中收錄的歌曲《一夜又一夜》(One night after another):“一夜又一夜,你像一個死人一樣倒在床上/一夜又一夜,我找到了另一瓶酒的家/夜以繼日,我想擺脫你/但是我做不到,這又有什么用/所以我只能整夜緊緊地擁抱你/一夜又一夜/一夜又一夜(節選)”,有迎合商業的意圖,全詩主題不明,思緒混亂,結尾倉促,缺少往日的深度與個性,與普通的情歌相差無幾。
2.內心的復雜
在鮑勃·迪倫的內心世界中,晦澀的意象與生命感慨一直都是其詩歌藝術的魅力所在。[10]如:《我要你》(I want you)中,鮑勃·迪倫通過“殮尸人的嘆息”“手搖風琴師的哭泣”“銀色薩克斯風的話語”等晦澀的意象象征愛情中的種種思緒,使詩歌中的愛情變得扭曲、乖張。又如收錄在《哦,仁慈》(Oh mercy)中的《穿黑大衣的男人》(Man in black coat),“六月以來,水面上一直冒濃煙/在高蹺的新月下,樹干被連根拔起/感受到這種脈沖、震顫和爆炸的力量/有人在外面毆打一匹死馬/她什么也沒說,什么也沒寫/她已經走了/和那個穿著黑大衣的男人(節選)”,這里,鮑勃·迪倫將自己置于愛情的對立面,通過奇妙的思維挖掘內心的情感世界,對詩歌語言的精雕細琢使他的詩歌更加難以理解。[11]此外,鮑勃·迪倫詩歌的另一大特征是對生命的感慨,1997年發行的專輯《被遺忘的時光》《Time Out of Mind》被稱為鮑勃·迪倫的回歸之作,經歷了社會變革與人生起伏的鮑勃·迪倫開始在詩歌中贊美生命、感慨生命。如:收錄于《被遺忘的時光》中的《高地》(Highlands),“陽光照在我身上/但這與過去不同/聚會結束了,越來越無話可說/我有新的眼睛/一切看起來都很遙遠/哦,天亮了,我的心在高地/在遠處的山上/有一條路可以到達那里,我會找到它/但是我的心已經在那里/現在就足夠了(節選)”,《高地》顯示出鮑勃·迪倫對當下社會的反向認知,一方面鮑勃·迪倫不再描述聚會上形形色色的人,而是關注聚會結束后的孤寂與落寞,但另一方面又高喊出“我的心在高地”,仿佛鮑勃·迪倫最后的“激進”與“怒吼”,表達出一位老人對生命的感慨,既蒼涼又火熱、既悲哀又光明。[12]
二、鮑勃·迪倫詩歌的藝術風格及其對于文學的意義
(一)鮑勃·迪倫詩歌的藝術風格
解構通常被視為西方文藝界后現代主義轉向的重要標志,鮑勃·迪倫詩歌作品也充滿著解構主義創作方式,即精神分裂式的語言表達、割裂式的語言表意與無解的設問。
1.精神分裂式的語言表達
在《重訪61號公路》中,鮑勃·迪倫重塑“垮掉的一代”,營造出魔幻、夸張和神秘的藍調音樂派對。[13]其中,《瘦男人歌謠》(Thin man singing)是精神分裂式的語言的代表作:“你出示門票/去看怪胎秀/怪胎聽見你講話/直徑奔向你/他說:‘成為一個畸形的人,你覺得怎么樣?’/你說:‘難以忍受’/當他遞向你一根骨頭”(節選),歌詞中充斥著這種毫無邏輯,前言不搭后語的語言表述。讀者很難理解什么是“怪胎秀”(freak show),怪胎為何要“遞向你一根骨頭”。但這是后現代文學作品的普遍特點之一,通過無情感、無邏輯和無因果關系的表達,使作品更加晦澀、難以捉摸,這符合鮑勃·迪倫厭惡讀者猜測詩作指向的態度。
2.割裂式的語言表意
割裂式的語言表意是指慣性語言符號組合的斷裂,也是對宏大敘事的解構。[14]如:收錄在《金發疊金發》(Blonde blonde)中的歌曲《絕對甜蜜的瑪麗》(Absolutely Sweet Marie),“你答應過的六匹白馬/最后都送進監獄/但是要成為法外之徒,你必須誠實面對(節選)”,其中“六匹白馬”、“監獄”之間前言不搭后語,存在慣性語言符號組合的斷裂,這種割裂式的語言表意方式將一連串人們習以為常的語言符號割裂,開創出一種新的表意符號,使鮑勃·迪倫的詩歌語言擺脫慣時性的束縛,表現出作者復雜的內心世界。[15]
3.無解的設問
1963年出版的專輯《自由不羈的鮑勃·迪倫》《The Freewheelin’Bob Dylan》使鮑勃·迪倫一舉成名,充分體現出其早期詩歌作品中的生命力,《在風中飄蕩》(Wandering in the wind)成為鮑勃·迪倫最著名的代表作:“一個人要走多少路?/才會稱他為人?/是的,一只白鴿必須飛過多少個海洋?/才可以在沙灘上安眠?/是的,大炮還要飛行多少次/才會被永遠禁止?/答案,朋友,在隨風飄揚/答案在風中飄蕩(節選)”,《在風中飄蕩》是美國民謠音樂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以精煉而又富有張力的設問與排比直擊人心。[16]在詩歌的“三連問”中,“人”與“白鴿”都是為后文做鋪墊的,鮑勃·迪倫真正要發問的是“大炮還要飛行多少次,才會被永遠禁止?”這正是當時美國青年的困擾與心結,代表著當時美國青年一代向國家、向社會的發問。然而鮑勃·迪倫在詩歌中并沒有回答,為讀者留下了“空白”,解構了設問與答案之間的聯系。
(二)鮑勃·迪倫詩歌對于文學的意義
2016年,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輿論一片嘩然。實際上,早在1996年鮑勃·迪倫首次入圍諾貝爾文學獎之時,質疑聲就如同浪潮一般涌來,文藝評論家站在“純文學”角度對鮑勃·迪倫詩歌評頭論足。但不可否認鮑勃·迪倫對文學多樣性做出的貢獻,他的詩歌打破了文學的邊界限制,促使詩歌文學的表達重獲大眾關注。[17]更為重要的是鮑勃·迪倫重新“修復”了文學與音樂的聯系,即“詩”與“歌”的融合,為大眾創造出新的藝術體驗。
20世紀50年代“垮掉的一代”代表詩人金斯伯格、加里·施耐德、杰克·凱魯亞克等人就已開始進行詩與歌的“試驗”。他們在書店舉辦詩歌朗誦活動,以爵士音樂為伴奏,運用大量簡短的元音節詞匯,并利用爵士音樂與詩的融合營造出神秘的氛圍。鮑勃·迪倫則沿襲這一詩與歌的嘗試,在民謠音樂中融入詩歌元素,并通過長期實踐完成詩與歌的磨合過程,使其音樂的詩性表達更加多元與完善。同時,鮑勃·迪倫以詩人的視角將政治、社會、宗教、戰爭等事件融入作品之中,極大地豐富了后現代文學的形式,加深了文學與音樂之間相互碰撞的思想深度。
從詩歌的演繹與發展角度分析,詩與歌本就相互融合、互為一體,鮑勃·迪倫詩歌的后現代性表達為音樂情感旨趣提供了新的方向,使音樂更加貼近詩性表達,貼近生命情感的共鳴。[18]鮑勃·迪倫詩歌對于現當代文學來說是一種回歸,使文學與音樂的交融與影響更加深刻,這便是鮑勃·迪倫詩歌對于文學的意義。
綜上所述,鮑勃·迪倫的詩歌中充滿了矛盾、荒誕和否定,同時也存在對社會的憧憬與對未來的期待,共同構建起鮑勃·迪倫詩歌思想的后現代性。并且,鮑勃·迪倫詩歌中精神分裂式的語言表達、割裂式的語言表意與無解的設問等藝術風格解構了慣性語言符號組合,使詩歌創作更加自由化、多元化,從而擺脫詩歌文學的邊界束縛,重新建立了詩與歌、文學與音樂之間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