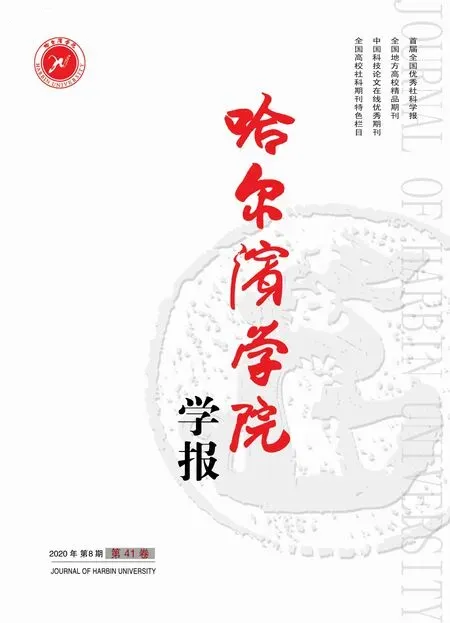《西游記》之創作動機及文學評價
潘 虹
(滁州城市職業學院,安徽 滁州 239099)
從創作動機的角度研究作家,再從作家的角度考察文學,可以打開文學研究的新局面。筆者在下文中對《西游記》的探究亦采用此法。
一、《西游記》的創作動機
(一)從結構檢視“刊西游記序”看《西游記》的創作動機
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距離明代雖然有數百年的歷史,但其留下的文學及非文學型態已根植于人心。這個故事的根據是百回本《西游記》,百回本《西游記》的出現不但促進了唐僧西天取經故事的發展,而且使人物與故事基本定型。據史料記載,早在萬歷二十年小說《西游記》就以百回本及章回體開始流傳,現典藏于臺灣和日本的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收錄了陳元之寫于“壬辰夏端四日”的《刊西游記序》,是目前發現的最早一部介紹《西游記》的刊物。[1]在早期學者的研究中,過多看重的是小說的有關信息和來源,很少有從小說的寫作結構來分析作者的寫作意圖。
陳元之的《刊西游記序》采用了序言公開化的公共特質,成為彰顯個人見解的代表之一,而淡化了序跋主要是以陳述成書概況的原始功能。這種寫序的方式,并非陳元之首創,《水滸傳》《三國演義》等長篇小說在流行初期也都是以序文的形式與主流文化對話或辯論。《三國演義》在序文中站在羽翼正史的立場上積極爭取自身的合法地位,而陳元之在序文中采用反向辯證的方式,讓讀者對現有的文學傳統進行再次反思,希望能夠以包容的態度接納小說,能夠對其中所蘊含的寓意理解透徹。為了更清晰地呈現陳元之的寫作意圖,現有具體引文: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譚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莊子曰:“道在尿溺。”善乎立言!是故“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若必以莊雅之言求之,則幾乎遺。……故聊為綴其軼敘敘之,不欲其志之盡湮,而使后之人有覽,得其意忘其言也。或曰:“此東野之語,非君子所志。以為史則非信,以為子則非倫,以言道則近誣。吾為吾子之辱。”余曰:“否!否!不然!子以為子之史皆信邪?子之子皆倫邪?子之子史皆中道邪?一有非信非倫,則子史之誣均。[2]
在這里,陳元之首先從道開始反思,將司馬遷與莊子的主張相結合作為小說立足于世的論述基礎。上文中的“或曰”即是對作者的猜測,雖然不是肯定的口吻,卻絲毫不影響小說的創作不凡這一觀點的體現。文中還以對話的形式質疑讀者的認知,抵制了外界的輿論沖擊。
陳元之在序中說,作者清楚地知道“道之言不可以入俗”與“濁世不可以莊語”的道理,是故意把故事寫得謬悠荒唐來吸引讀者的注意,這一看似反常的行文策略,應該是從讀者的反應中取得的經驗。從這一角度檢視陳元之序文發現,其不僅肩負著推廣的使命,也引發讀者深思并以寬容的態度接受這類創作模式。
從序文的結構看,陳元之將小說的出版信息以“綴段式”的寫法穿插其中,可見,小說的來歷并非是其寫作重點,他是想將《西游記》這一嶄新的創作風格呈現給讀者。為了順應當時的出版主流,必須在小說的言說上進行創新,以讓讀者接納,因此也就使得陳元之的這篇序文形成了較少的文字介紹出版歷程,將更多篇幅用于對小說進行回護辯駁的結構。[3]
(二)從孫悟空形象的塑造看《西游記》的創作動機
在吳承恩創作《西游記》之前,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就早已流傳民間,但吳承恩的《西游記》并非民間流傳故事的簡單拼湊。吳承恩在創作中對民間流傳的故事進行了大量的改造。《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是較為完備和最早記錄《西游記》中故事的作品,吳承恩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猴行者的白衣秀才形象進行了重新改造,塑造了滿腔熱血和充滿熱情的孫悟空形象。猴行者是為了修成正果而主動幫助和尚西天取經的虔誠的佛教形象,而孫悟空則是崇尚自由、傲骨嶙峋的形象。[4]
有學者曾經說過:“未能滿足的愿望,是幻想產生的動力,每一個幻想包含著一個愿望的實現,并且使不滿意的現實好轉。”吳承恩在《西游記》中也存在兩個未達成的愿望,一是未能實現長生不老的愿望,二是未能實現個體生命價值的愿望。
首先是善生。《西游記》中,作者創作的石猴出世是對新生命的誕生的極力贊美,對石猴誕生的背景的細致描寫,字里行間刻畫出歡騰激越的畫面。第四回,從孫悟空不滿于被封為小官弼馬溫,到被稱為齊天大圣的滿足,體現了孫悟空自身的價值。但這只是玉帝為了天庭的安全而對其的安撫,實際上并不重視它。以至于蟠桃盛會對孫悟空招待不周,使得孫悟空意識到齊天大圣的稱號只是一個騙局,從而偷吃仙丹,大鬧天宮,反抗玉帝對自己的不平等待遇。孫悟空的遭遇也反映了吳承恩早年懷才而不被重用的現實。[5]
其次是惡死。吳承恩意識到死亡是一種悲哀,向往著能成為神仙,與天地、山川同壽。他在創作《西游記》時已經六七十歲,可謂是老之將至,與其筆下的孫悟空年齡階段十分相似,因此,他將一生的憤怒記錄在猴王身上,讓孫悟空跨越千山萬水,歷經磨難,尋求長生不老的秘方。孫悟空在求學歸來的路上遇見閻王爺前來勾魂而進入幽冥界,將自己連同整個猴族都從生死簿上劃掉,也因此被如來套上緊箍咒壓到五行山下,必須等到西天取經的唐僧將他帶出。在取經途中,豬八戒、沙和尚都有過放棄的念頭,唯獨孫悟空一心只想與唐僧前往西天求取真經,可見,孫悟空的態度之堅決。孫悟空一路降妖除魔,最終取得真經,被如來佛祖封為斗戰勝佛,實現了自身的價值。這是一種至高的境界,達到了忘我的狀態。[6]
二、《西游記》的文學評價
學界普遍認為百回本的《西游記》系統較為復雜,難以厘清。目前在金陵世德堂本后,其底本作品為世德堂系統。《西游記》的問世,受到民間的歡迎,被很多書商翻刻,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在小說界形成了一股流行風。《西游記》的版本各式各樣,小說內容生動有趣,與神魔小說在短期內同時出現,體現了《西游記》在神魔小說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當時神魔小說快速發展,據統計,現存已知作品就有19種之多。
《西游記》問世后,人們對其評價較多,正反不一,但負面批評占絕大多數。如:(1)今是書之編,無過欲泄憤一時,取快千載,……亦借秦為諭,以警后世奸雄,不過勸懲來世,戒叱兇頑爾。其視《西游》《西洋》《北游》《華光》等傳不根諸說遠矣。(佚名《新刻續編三國志引》,萬歷三十七年,1609)(2)放模外史,引用方言,編輯成書,揚榷故實。……有《三國志》之森嚴,《水滸傳》之奇變,無《西游記》之謔虐,《金瓶梅》之褻淫。(煙霞外史《韓湘子敘》,天啟三年,1623)(3)《西游》《水滸》皆小說之崇閎者也,然《西游》近荒唐之說,而皆流俗之談;《水滸》一游俠之事,而皆無狀之行,其于世教人心,移風易俗,俄頃神化,何居而得與《破迷正俗演義》相軒輊也。(朱之蕃《三教開迷演義敘》,約萬歷四十年—天啟四年間)(4)是書動關政務,半系章疏,故不學《水滸》之組織世態,不效《西游》之布置幻景,不習《金瓶梅》之閨情,不祖《三國》諸志之機詐。(崢霄館主人《斥奸書凡例》第四則,崇禎元年,1628)(5)小說原多,每限于句繁語贅,節目混牽。若《三國》語句深摯質樸,無有倫比,至《西游》《金瓶梅》,專工虛妄,且妖艷靡曼之語,聒人耳目,在賢者,知探其用意;用筆不肖者,只看其妖仙冶蕩,是醒世之書,反為酣嘻之具矣(戲筆主人“忠烈傳序”,署年當為假托,疑在明末)。[7]
綜上可見,通過批判暢銷名作來提升自己的地位,在當時也十分常見。雖然《西游記》不是唯一一部受到批評和攻擊的小說,但卻成為不同類型或不同時期小說的共同評判對象,這不單單是商業因素所致,同時,也反映了時人對于《西游記》的某種認知和共識。
對于這類小說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虛妄幻景、荒誕不經與妖艷靡曼方面。自《西游記》面世就受到了來自各方的評判,當時的歷史演義小說正處于巔峰,大量的以“按鑒”創作的演義作品,如:《新刻考訂按鑒通俗演義全像三國志傳》(天啟三年間黃正甫所刻)、《新刻按鑒演義全像大宋中興岳王傳》(萬歷間書林余氏三臺館所刻)、《按鑒演義帝王御世有夏志傳》(崇禎年間題鐘惺編輯)、《新鐫玉茗堂批評按鑒參補出像南宋志傳》(硏石山樵訂正)、《新刻按鑒編纂開辟衍繹通俗志傳》(鐘伯敬原評),都將“按鑒”兩字印于作品封面處或題名處。這些小說都強調其資治通鑒的價值,發揚鑒古知今的致用原則,同時,鄙視那些虛誕幻妄或無益于民生的怪異作品。[8]
當然,還有一些學者對《西游記》是持肯定態度的。睡鄉居士評論說:“《西游》一記,怪誕不經,讀者皆知其謬;然據其所載,師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動止,試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摹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則正以幻中有真,乃為傳神阿堵。”(崇禎五年,1632)而幔亭過客則站在宗教立場表達了對小說的認同,并對《西游記》中描繪的文筆進行了贊美:“余謂三教已括于一部,能讀是書者,于其變化橫生之處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道不洽?而必問玄機于玉柜,探禪蘊于龍藏,乃始有得于心也哉?至于文章之妙,《西游》《水滸》實并馳中原。今日雕空鑿影,畫脂鏤冰,嘔心瀝血,斷數莖髭而不得驚人只字者,何如此書駕虛游刃,洋洋灑灑數百萬言,而不復一境,不離本宗;日見聞之,厭飫不起;日誦讀之,穎悟自開也!故閑居之士不可一日無此書。”(崇禎年間)
筆者認為,對于《西游記》的批判,不論負面還是正面,都體現了學術思想層面的糾紛與糾葛,雖然在目前這一觀點并未有明確的證據證實。但值得肯定的是,《西游記》在明代萬歷年間,其影響力不僅體現在娛樂方面,而且其中隱藏的諸多的政治哲理,也受到人們的喜愛,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喜愛。
三、結語
由于虛與實、奇與正兩股勢力的存在,使得原本以歷史演義為主體的通俗市場變得多元化,出現了神魔系列小說,之后,又出現了人情或世情小說,打破了原有的演義小說的框架。《西游記》作為四大奇書之一,具有較高的文學成就,為通俗小說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