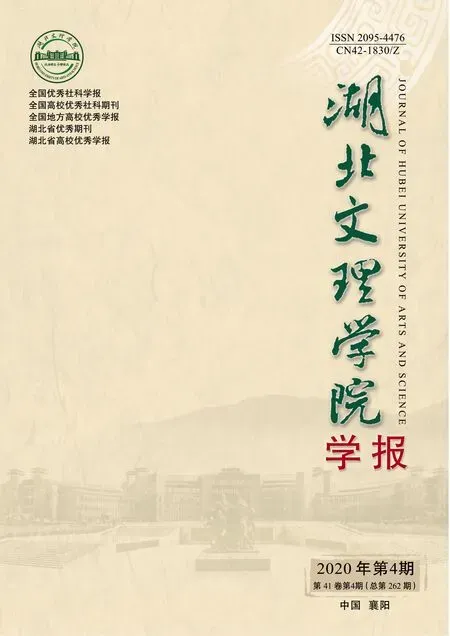仙桃方言“和”類連詞“兩個”的語法化動因
高志明
(湖北文理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湖北 襄陽 441053)
“兩”是一個基數詞,與“個”組成數量詞,為數量結構,檢索北大語料庫,我們發現南北朝時期漢語文獻出現“兩個”作為數量結構的用法:
(1)如一具牛,兩個月秋耕,計得小畝三頃。
(賈思勰《齊民要術》)
(2)從臺西下坂行五六里,近谷有文殊與維摩對談處,兩個大巖相對高起,一南一北,高各三丈許,巖上皆平,皆有大石座。
(日·釋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3)我見兩個泥牛斗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
(釋慧印,校訂《筠州洞山悟本禪師語錄》)
(4)從來巡繞四邊,忽逢兩個神仙。眉上冬天出柳,頰中旱地生蓮。
(張鷟《游仙窟》)
(5)六師自道無般比,化出兩個黃頭鬼。
(潘重規,編《敦煌變文集新書》)
(6)雪峰往福州卓庵,過沙汰后,忽有兩個納僧來禮拜和尚。
(靜筠禪師《祖堂集》)
這些數量結構基本做定語,限定“兩個”后面的名詞(名詞性結構)。現代漢語普通話層面,“兩個”出現語義虛化痕跡,“兩個”開始向數量模糊的少數義變化,意義虛化為概數,語用功能表示約指數量較少。
(7)幫我找兩個男生來搬教材。
(8)你說你書法好,你寫兩個字我看看。
這里的“兩個”語義并不明確實指雙數“兩個”,而是具有模糊指數意味:小于、等于或者大于兩個(但不會大于四個五個)的數量,即此類“兩個”的語義識別比較模糊,“一個、兩個或三個”都在說話人的意指之中。
在漢語西南官話區,我們還觀察到“兩個”有進一步虛化為連詞和介詞的現象。自郭忠首次報道西南官話武天片中的天門方言“兩個”具有連詞和介詞語法功能[1],賴先剛報道在四川話中“兩個”也有此類用法[2]121。儲澤祥報道湖南慈利通津鋪話“兩個”具有連詞用法[3];儲澤祥進一步探討在西南官話區,“兩個”作并列連詞的用法及其類型學意義[4]。陶伏平在儲澤祥基礎上,補充討論了“兩個”作為介詞的用法[5]。陳凌發現了贛方言中的“兩個”亦有類似現象[6]。鄉賢江藍生指出了仙桃方言“兩個”的逆語法化特征[7]。我們感興趣的是:作為體詞的數量結構“兩個”虛化為連詞和介詞的動因和機制是什么?它能否再進一步虛化?這也是上述研究沒有詳細展開的地方。
我們以西南官話武天片的仙桃方言為例,試著探討“兩個”的虛化問題。
一、仙桃方言中兩個的虛化途徑
(一)數量結構——復指虛化
數量結構做定語是“兩個”的起初用法,這在仙桃方言中還廣泛存在:
(9)他有兩個壇子(女兒)。
(10)他讀了兩個五年級才考上初中。
(11)他家兩個狗子都被人偷了。
“個”作為量詞,應用范圍比普通話要寬泛很多。仙桃方言量詞系統并不發達,對事物衡量相對模糊隨意,只要說話人覺得不好量指的事物都可以用“基數詞+個”來稱謂。
仙桃方言中,“兩個”由基數虛化為模糊概數的語義也比較明顯:
(12)我說兩個話你聽。
(13)你兄弟被人欺負了,快叫兩個人來幫忙。
(14)我手上沒得一兩個錢,做什么生意?
數量結構“兩個”在仙桃方言中還廣泛用作同位短語,對其前述復數主語予以復指強調,表意出現初步虛化:
(15)你們兄弟兩個合伙起來欺負我!
(16)她們妯娌兩個很和睦。
(17)爺父子兩個上街去了。
(18)我跟奶奶兩個一起去的。
(19)小王和老李兩個到武漢出差了。
其實,“兩個”作為賓語或主語的雙數復指標記,其虛化痕跡在北宋已現:
(20)好仁者與惡不仁者本無優劣,只是他兩個資質如此。好仁底人,是個溫柔寬厚底資質。
(黎靖德《朱子語類》)
(21)我當時要個不惜身命底人。直至如今無人稱得老僧意。你兩個吐露個消息看。僧擬議。
(釋賾藏《古尊宿語錄》)
(22)郭排軍,前者我好意留你吃酒,你卻歸來說與郡王,壞了我兩個的好事。
(南宋·佚名《話本選集·碾玉觀音》)
(23)哥嫂兩個忍氣吞聲,前后俱收拾停當。
(宋元·佚名《話本選集·快嘴李翠蓮記》)
(24)有些法度,房上生出那草,養住那水,好生流不下來,只約漏了。你兩個小廝慢慢的上去,把那房上草來,一根一根拔的干凈著。
(元·佚名《樸通事》)
(25)你打水去。我兩個牽馬去。
(元·佚名《老乞大新釋》)
(26)曉得兩邊說話多有情,就做不成媒,還好私下牽合他兩個,賺主大錢。
(明·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
復數標記“們”起源比較滯后,此處“你兩個”“他兩個”“我兩個”中的“我、你、他”都指復數,“兩個”為復指,與“我、你、他”共同構成賓語或主語,兩個與“我、你、他”連用,對“我”“你”“他”的指代語義實施強調的語用功能。
(二)復指虛化——連詞
不同于動詞的“動→介→連”常規語法化順序,仙桃方言“兩個”呈現逆語法化的虛化路徑[7],即由數量結構虛化為連詞和介詞。我們覺得江先生講得有道理,但和類連詞“兩個”不應是由數量結構直接虛化而來,應該是由同位短語復指虛化后再次虛化,過渡為表并列的連詞:
(27)我兩個隔壁的幺爺一路來的。
(28)你兩個小孩子吵什么架?
(29)三班要兩個五班比賽打籃球。
(30)我們隊的牛兩個四隊的牛打起來了。
(31)你把鋤頭兩個梿枷一起拿來。
(三)連詞——介詞
“兩個”由連詞繼續虛化為伴隨介詞,細分為有生方向介詞、比較介詞和關涉介詞三類[8]:
(32)兩個人家老年人吵架,有啥了不起!(有生方向介詞)
(33)他夜里才回來,什么都沒兩個我講,就睡了。(有生方向介詞)
(34)她的身材兩(個)你差不多。(比較介詞)
(35)她的臉色兩個紙一樣白。(比較介詞)
(36)你怎么兩個她談戀愛?(關涉介詞)
(37)我兩個他將了盤軍。(關涉介詞)
(四)弱化——脫落
以上幾種虛化在仙桃方言共時系統中同時存在。實時口語交際中,當“兩個”虛化為復指短語和表概數語義時,“兩”的調值弱化為21,“個”類似詞綴,也須輕讀。“兩個”連讀,語速較快,音步合并為一個音步。當“兩個”進一步虛化為介詞后,“兩個”的“兩”讀音較重,“個”讀音輕化,口語交際中“個”還有進一步輕化現象:“個”在口語交際中常被省去——脫落了。這種語音脫落現象是兩個語法化不斷深入的形式標記,吳福祥也認可“兩個”虛化途徑中,音韻上發生銷蝕,“兩個”省縮為“兩”。這說明“兩個”的虛化軌跡是:數量結構>復指短語>連詞>介詞。
二、仙桃方言“兩個”的虛化動因
(一)省力原則
省力原則是語言交際和語言演變的重要動力。“兩個”起初語義表雙數,后又作復指短語,當“兩個”前面的名詞或代詞從語義上已為說話雙方共知為雙數信息,則再增加“兩個”數量結構表復指,顯得多余,特別是當“兩個”前面的結構為“X跟Y”“X和Y”等形式時,語義表達上更顯得像疊床架屋,語言的省力原則迫使說話人省略“跟”“和”“同”“連”等并列連詞標記,連詞省略,語義表達完整,但XY之間勢必需要音步停延以區別“X跟Y”的關系。音步停延使連詞省略的省力性打折扣,于是將“兩個”前置,放于XY之間,形成“X兩個Y”的并列結構,進而再由作為表偕同功能的兩個虛化為介詞“兩個”,由于省力原則,“個”進一步脫落,形成“X兩Y”模式,如:
(38A)不要把我和她兩個放在一起,我和她兩個搞不來。
(38a)不要把我兩她放在一起,我兩她搞不來。
A句兩個小句都有復指短語,“兩個”復指與連詞“和”疊用,顯得多余和拖沓,省力原則迫使說話者將數量結構“兩個”與連詞“和”壓縮在一起,用“兩個”這一個形式予以合并表達。進而再根據連詞“和”“跟”“同”的單音節形式予以類推,將量詞“個”省略,形成只用“兩”連接前后名詞或代詞的a句。
(39B)誰要是再欺負我們家小明,我連他家大人兩個一起打。
(39b)誰要是再欺負我們家小明,我兩他家大人一起打。
B句介詞“連”與“兩個”在句中同時運用,“連”語義指向包含惹事小孩及大人,與“兩個”語義疊合,顯得冗余。說話者借助省力原則將二者合并用“兩個”表達,同時類推機制使得說話者將“個”也省略,單說一個“兩”,與單音節介詞“連”的用法一致。
又如:我跟他兩個在那兒吵起來了[2]122。也可說成:我兩個他吵起來了。意思不變,表意更簡潔。再如:
(40C)你岔(約)他下,和他兩個一起去。
(40c)你岔(約)他下,兩(個)他一起去。
(二)語用重復
彭曉輝報道湘語祁東話“兩個”表雙數,“兩個”前可以用單數人物名詞、代詞及稱謂語。[9]仙桃方言中“兩個”作為復指,前面一般用雙數名詞,不能用單數人物名詞、代詞。即“兩個”前面是雙數名詞,后面接“兩個”亦表雙數概念。“兩個”對前后銜接的雙數名詞或代詞實施語義強調的語用功能。
(41)你們兄弟兩個合伙起來欺負我!
(42)她們妯娌兩個很和睦。
(43)爺父子兩個上街去了。
(44)我跟奶奶兩個一起去的。
(45)小王和老李兩個到武漢出差了。
賴先剛在分析四川話“我跟他兩個在那兒吵起來了。”時,認為“兩個”在句中不作任何結構,語義顯得多余,相當于助詞。我們也覺得,仙桃方言“兩個”在句中屬復指語義,但表意虛化,僅表示強調語用功能,“兩個”省略不影響表意。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兩個作為復指虛化,在實時交際活動中,語音痕跡為:說話人說“兩個”時語速較快,發音較數量詞“兩個”要輕,跟模糊概數“兩個”的讀音差不離。這說明,表語用重復的復指代詞“兩個”在句子中的語義值已被降為可有可無,不用再承擔更多的句子語義屬性,僅僅對前后銜接的實義代詞或名詞起語用強調作用,語用重復跟省力原則共同作用,推動“兩個”進一步虛化,“兩個”或將慢慢詞匯化,虛化成為補足音節的襯詞。
(三)句法位置及句法功能變化
劉堅認為,語法化或者是因句法位置、組合功能的變化而導致實詞語義虛化;或者是詞義的變化引起句法位置、組合功能的變化而使得實詞虛化。[10]數量結構“兩個”表雙數,其句法位置常緊跟在名詞或代詞前,用作主語、賓語或定語。但如果名詞或代詞前插入領屬或限定成分,則“兩個”的語義及句法功能發生變化。如:
(46)我的兩個嫂子//這兩個壇子鬼//兩個狗子
“兩個”后面插入新的限定成分,變成:
(47)兩個我的嫂子//兩個我的壇子鬼//兩個老王家的狗子
仙桃方言“兩個”在(47)中不能說;或者說(47)中的三個句子不能單說,需要跟其他語言形式組合構成上下文語境,此時“兩個”語義不再表示數量,而是表示偕同義的連詞或者介詞。
也就是說,表雙數合并的數量結構“兩個”因轉喻及語用功能變化,“兩個”句法位置與句法功能發生變化,要么出現在前后名詞或代詞中間,起連接作用,和前后成分共同做句子成分,共同承擔語法功能,不再獨處于名代詞前,獨立承擔語法功能。要么雖跟在名詞代詞前,但這二者常常置于動詞謂語前作狀語,表示性質或方式等狀中關系。因句法位置發生由實而虛變化,導致句法功能順應其變化而出現虛化,語用頻率增量遂使得“兩個”慢慢虛化。
(四)人際功能互動及變化
江藍生認為,“兩個”詞義與功能的虛化,源于在話語交流過程中,說話人為加強表達的明晰性而主觀增添句子成分、引起句子結構改變引起的。[7]我們也覺得,“兩個”虛化過程中,人際互動及其功能變化是重要動因之一。“兩個”最初表雙數概念,作為數量結構帶名詞或代詞,用作主語、賓語或定語。這三類句法成分表明“兩個”同時具有描寫和客觀指示性,這兩種功能屬性使得“兩個”在句法層面生成語篇功能;在話語主體層面看,說話者與聽話者雙方都將“兩個”人或物的互動作為意義浮現的心理理據,即話語交際涉及的兩個人或物會在言語中或言語后發生諸如合并、銜接、跟從或附屬等言語行為。也就是說,“兩個”因語境作用而發生轉喻可能,話語雙方將客觀性的雙數指稱呈現轉喻為主觀性的指涉關系敘述:銜接-跟從-附屬。套用韓禮德三大功能說,我們認為,語用化(人際互動及其功能變化)是語法化的一個動因,即“兩個”在功能上呈現概念功能>語篇功能>人際功能的虛化軌跡。漢語介詞常常是某些動詞的語法化完成的,“兩個”雖然是數量結構,但“兩個”虛化為介詞,“兩個”也具有普通介詞一樣的動作意味。如:我兩個你去。我們調查中發現說話人常伴有搭肩膀或招手動作。表明“兩個”在言語交際中隱含有人際功能:
(48)你岔(相約)他下,兩(個)他一起去。
(五)語義演變
“兩個”的語義演變有三種情況:第一是虛化。“兩個”位于已知雙數名詞代詞之后,表復指,表義功能虛化,在句中可省略,不影響句意(如上述)。第二是功能化。復指短語“兩個”在句中語義虛化,因轉喻機制導致“兩個”語義所指及句法功能再度發生虛化和演變,由表示計量的雙數向連詞“和”、介詞“和”“跟”等功能語義演變;伴隨所指演變的,就是其句法位置和句法功能變化。數量結構“兩個”通常位于單個體詞性結構前表限定,復指虛化后,位于雙數名詞后表示語用強調,“兩個”作連詞,則需放在兩個體詞性結構之間。語法的變化強化了語義所指的心理事實,“兩個”的語義遂逐漸虛化出介詞和連詞:和、跟意義。如:
(49)華子和平娃兩個星期天回來吃飯。(“兩個”表復指)—→華子兩個平娃星期天回來吃飯。(“兩個”為連詞)
第三是模糊化。“兩個”數量結構中,“兩”語義具有模糊性,《漢語大詞典》“兩”義項之一:表示不定數,多與“一”或“三”前后連用,義為少量。
(50)撥弦三兩聲。
(白居易《琵琶行》)
(51)竹外桃花三兩枝。
(蘇軾《惠崇春江晚景》)
(52)兩三點雨山前。
(辛棄疾《西江月》)
(53)三言兩語
(54)請王書記代表我們講兩句話。
(55)估計一兩點鐘到。
(56)兩豁子他就把氣打足了。
仙桃方言“兩個”語義也有模糊概指義,也是由表實義的數量發生語義演變,由確指雙數、“兩個”變成概指數量少。
(57)我說兩個話你聽。
(58)你兄弟被人欺負了,快叫兩個人來幫忙。
(59)我手上沒得一兩個錢,做什么生意?
三、仙桃方言“兩個”的虛化機制
江藍生認為,仙桃方言“兩個”演變的直接誘因是口語交際過程中同位短語“我兩個”中的隱含項被顯現造成的。[7]但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實時口語交際中,仙桃方言“你兩個”“我兩個”“他兩個”中的單數人稱很少表復數概念,“兩個”作同位結構時前面一般搭配復數主語。仙桃方言“兩個”作為同位短語表復指概念的表意功能已經虛化,省略之不影響表意,應該是數量結構“兩個”的初步虛化(詳見前述)。我們以為,“兩個”的虛化機制不應該是概念浮現,而主要體現為轉喻機制和重新分析。
(一)轉喻機制
轉喻認知是仙桃方言“兩個”虛化的重要機制之一。認知語言學認為,語法規則的演變、詞義的引申以及詞匯的豐富往往是由話語主體的某種認知規律所驅動的。“兩個”在虛化軌跡中,受制于多種轉喻機制。
1.“兩個”初始是數量結構其認知特征包括:兩個事物、并列、組合、整體計數。語用環境下,“兩個”可以由組合并列轉喻前后銜接:
(60)你兩個你哥哥抬籮筐。
(61)做飯洗衣兩個他都在行。
因前后銜接,共同作為,施事需要動作偕同,于是“兩個”又增加“偕同”轉喻意義:你岔(相約)他下,兩(個)他一起去。偕同做某事,總有一方為主一方為從,主從通過比較產生,于是“兩個”又增加“比較”的轉喻義:
(62)她的身材兩(個)你差不多。
(63)她的臉色兩個紙一樣白。
有比較必然需要比較對象,在此基礎上“兩個”又增加了“對象”的轉喻義:
(64)兩個人家老年人吵架,有啥了不起!
(65)你怎么兩個她談戀愛?
(66)他夜里才回來,什么都沒兩個我講,就睡了。
2.“兩個”有數量并列義,事物并列在數量上至少滿足兩個因此,“兩個”在實時話語交際中就具有了“數量少”的轉喻義了。又由于數量少,一眼就可看出,不需要精確計算就能得到結果,于是“兩個”就有了表“概指數量少”的轉喻義了:
(67)我說兩個話你聽。
(68)你兄弟被人欺負了,快叫兩個人來幫忙。
(69)我手上沒得一兩個錢,做什么生意?
(二)重新分析
語言的演變說到底是一種規則的演變,由實詞“兩個”的虛化軌跡:聯合結構復指虛化——多義概指語義虛化——語法虛化連詞——語法虛化介詞,發現重新分析也是促使“兩個”發生虛化的重要機制。
(70)我有(兩個)哥哥。
(71)(兩個)嫂子
(72)(我)兩個(哥哥)星期天一定回來。
(73)你怎么[兩個](嫂子)談戀愛?
當名量結構“兩個哥哥”與代詞“我”搭配,進入句72中,“兩個哥哥”與其他成分發生重組,結構須重新分析為:“兩個”起連接作用,連接名詞與代詞共同作主語。“兩個”虛化為附屬結構,不作句子實義成分。句73中,“兩個”數量結構不再跟“嫂子”構成定中關系,而是作介詞,與“嫂子”結合,重新分析為狀中結構共同在句中作狀語。雖然說重新分析是“兩個”虛化現象的句中結果,但經過重新分析,“兩個”作為一種新的結構規則進入語言系統,從而增強了“兩個”的合法化身份,促使“兩個”虛化為連詞及介詞的語用頻率大為增加,“兩個”虛化遂具有較顯著的類型學意義[3]159,“兩個”的逆語法化現象“很值得繼續研究”[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