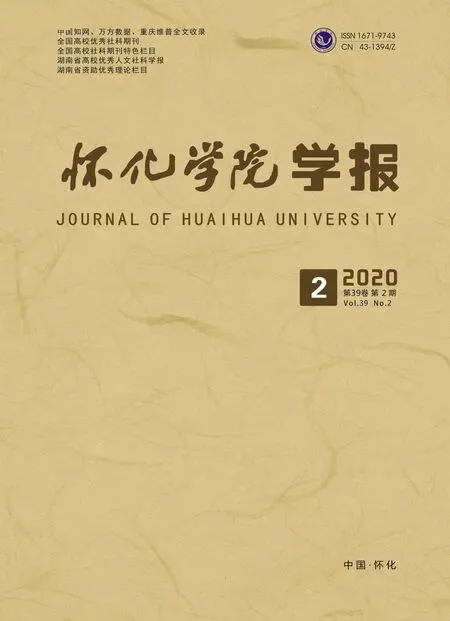《瘋癲亞當》三部曲的動物倫理思想
鄭婷婷
(福建師范大學協和學院,福建福州350117)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被譽為加拿大文學女王,獲得過世界文壇眾多重量級大獎。阿特伍德十分關注加拿大的民族、女性、人權、自然的現狀與發展,通過文學作品對濫用科技引發的一系列生態災難表示擔憂,是一位極具人文關懷和社會責任感的作家。《瘋癲亞當》三部曲,也稱為末世三部曲,包括出版于2003年的《羚羊與秧雞》、2009年的《洪水之年》和2013年的《瘋癲亞當》三部小說。阿特伍德為讀者描述了一個被科學技術摧毀的未來世界里人類幸存者帶領著一個新物種艱難前行的故事,表現了對人類現實的嚴肅思考以及對人類未來命運的擔憂。在三部曲中,動物成為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動物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動物,而是科學技術、消費社會的產物。例如,專為人體器官移植設計的轉基因豬,沒有眼睛沒有大腦只有嘴巴的雞肉球,狼犬獸、魔發羊、獅羊、浣鼬等都是基因工程的產物。科技天才秧雞還創造了理想人類“秧雞人”。這個新物種在一場“無水的洪水”瘟疫后取代人類在地球上生活。阿特伍德通過生態預警小說警示人類無視自然規律、濫用生物技術導致的生態倫理危機,并提出面對這樣的未來,人類應該用什么樣的態度處理人與動物之間的關系。本文以《瘋癲亞當》三部曲為研究對象,以動物倫理為研究視角,挖掘小說中不同的動物倫理思想,反思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系,揭示深遠的生態內涵。
一、人性與動物性二元對立
西方人對待動物的態度主要源于猶太教和古希臘文化兩個傳統。《圣經·創世記》宣稱,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類,只有人類有靈魂,上帝希望人類管理和支配其他的動物。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人與動物之間建立了一個嚴格的等級制度,“植物就是為了動物的緣故而存在的,而其他動物又是為了人的緣故而存在……大自然是為了人的緣故而創造了所有的動物”[1]23,動物低于人類,人類可以隨意利用和處置動物。法國哲學家笛卡爾提出“動物是機器”“無機的自然界是機械的,有機的植物界也是機械的,連動物界都是機械的”[2]27,認為動物與時鐘一樣無法享受快樂、體驗痛苦或其他感覺。亞里士多德、笛卡爾是動物機器論的主要代表人物,都認為動物沒有理性,不具有道德地位,對人類只有工具價值,人類對動物不負有道德義務。動物機器論具有廣泛的影響力。隨著工業革命的深入,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否定了自己的動物性,夸大了人性中的理性,將人性與動物性對立起來。《瘋癲亞當》三部曲中動物大滅絕現象以及大院精英和廢市民眾對動物的態度體現了人性與動物性的二元對立。
(一)大院與基因動物
小說里的未來世界被一群資金雄厚的高科技生物大公司控制,各大公司建立了自己的大院,大院里住的全都是科技精英,他們崇尚科學技術。為了滿足人類的消費需求或滿足科學幻想,科技精英們熱衷于創造動物,他們覺得“創造一種動物是如此的有趣,它讓你覺得你像是個上帝”[3]53。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需求,科技精英們致力于發掘動物的新用途,利用生物基因技術將動物改造得面目全非,并用基因動物進行實驗。吉米的父親是奧根農場的基因研究專家,負責開發器官豬項目——專為人體器官移植設計的轉基因豬。器官豬體內長著可以移植給人類的組織器官,“一只器官豬身上一次長五六個腎”[3]24,這使得器官移植操作起來簡單廉價多了,而且可以避免排異反應。科技的運用劃分了人與動物的等級。在經濟利益面前,基因動物淪為商品和機器,對人類只有工具價值。
吉米長大后,受好友秧雞邀請參觀沃特森·克里克學院最新的研究項目——雞肉球,“一個像大皮球的物件……里面伸出二十根肉質粗管,每根管子末端各有一個球狀物在生長,一個生長單位可以長十二份”[3]209。雞肉球被去除了眼睛、大腦等與消化吸收無關的器官,只留下所謂的嘴巴,其實就是倒入營養素的口。雞肉球生長速度驚人,并根據人類不同的需求,兩周內長出雞胸脯、雞腿肉等不同產品,這樣的生物怪物迅速壟斷了肉食品市場,緩解了人類的消費需求。小說中人類按照自己意愿改造的自然物種很多。例如,浣鼬、浣熊和臭鼬的結合體,沒有浣熊的攻擊性,沒有臭鼬的臭味,乖巧可愛,是完美的寵物選擇;狼犬獸,外表像狗一樣可愛,見了人尾巴搖個不停,可一旦去拍它,便將人的手一口咬下。
阿特伍德看到人類濫用生物技術隨心所欲地改造物種,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如果我是上帝,我會很不安。他創造了一切,并且認為這一切都是美好的。但現在人們正在這件藝術品上到處胡亂涂改。”[4]429創造這些異化動物的內在驅動力是人類的消費需求,異化動物喪失了自然賦予它們的動物性,使動物呈現出物化的狀態,喪失了動物生命的尊嚴。
(二)廢市與珍稀動物
小說里的廢市是下層民眾生活的地方,治安混亂,破敗不堪;民眾自私冷漠,爾虞我詐,生活在貧困無助中。廢市民眾貪圖享樂,倒賣珍稀動物的皮革,以食用珍稀動物為樂。托比租住的房間樓下就是一家以稀有動物的毛皮做原料的高檔女裝作坊。顧客們以穿著的毛皮大衣作為炫富的資本,因此希望動物毛皮是貨真價實的;而服裝店為了滿足顧客的需求,在密室里現殺現賣。“他們在柜臺上出售萬圣節的道具服……轉身回到密室熏制獸皮……偶爾還會聽見動物的咆哮和哀號……他們剝皮的畜肉統統賣給一家名叫‘生珍’的美食連鎖餐廳……但是在私人宴會廳里,你可以吃到瀕臨絕種的動物。”[5]32-33
遺跡公園北面邊界處的停車場舉辦了一場“生命之樹”自然物材交易會,吸引了很多趕時髦的上層人士。“上帝的園丁”攤位邊上有很多披著厚重昂貴皮革的闊佬富婆路過,讓瑞恩好奇的是“穿戴這些皮具的人對另一個生命的皮膚緊貼著自己的肌膚有何感覺”[5]145,然而闊佬富婆們卻表現出不以為然的表情,反正動物又不是他們殺的,何必浪費動物的毛皮呢!
本該與人類和諧共生的珍稀動物成為商品,被殘忍殺害,血肉成為人類的盤中餐,皮毛成為人類炫富的資本,滿足了上層階級的時尚需求,生命的尊嚴被踐踏。
二、人性與動物性的統一
傳統的動物倫理思想將人的人性與動物性二元對立起來,語言、理性、道德成為區別兩者的判斷標準,對理性的崇拜推高了人性,貶低了動物性。人類和動物的基因排序有極高的相似性。人類是由動物進化來的。由于本能的需要,人類仍然擁有自然性,我們稱為動物性,如食欲、性欲等一般動物性行為。
阿特伍德認為,動物性是人性的基礎,人是人性和動物性的統一體。“亞當第一”在布道時重申了人類的靈長類血統,即使傲慢的人類無法接受這一事實,但人類的胃口、欲望和情緒都具有靈長類的本性,這是無法否認的,科學證明了這一點,DNA使人類與動物緊緊相連。在贊美詩中,“亞當第一”請求上帝去除人類心中的驕傲,警告人類謹記動物內在,不要以動物性為恥辱。阿特伍德指出,“我們所懷有的種種信念和想法,到了其他動物那里就成了與生俱來的本能”[5]240。
性欲是人類內在的動物性。小說提到了吉米和秧雞無法控制自己的性沖動,與女性性交以滿足自己的生理需求。“喜福多”藥片表面上是為了解決人類縱欲的后顧之憂而研發出來的。這種藥不僅可以抵抗性病,提高性欲,還具有控制生育、延長青春的功效。“喜福多”給人類帶來高質量的性生活,又是一種安全可靠的節育產品,因此,一經問世就炙手可熱。正因為如此,秧雞在設計新人類的時候將性設計成不再受到荷爾蒙和沖動的驅使,而是一種機械性的交配行為。食欲也是人類內在的動物性。“無水的洪水”爆發后,人類滅絕,吉米帶領秧雞人在一片廢墟中覓食,還得警惕四周器官豬、狼犬獸這些基因動物的攻擊。面對饑餓,人類的文明與理性原則毫無意義,生存才是最基本的需求。吉米身上更多體現出人性中的動物性,而秧雞是理性工具的代表,他們對待動物的態度截然不同。吉米小時候看到焚燒動物,不斷地問父親焚燒動物的原因。父親告訴他這些動物被感染了,吉米為無法拯救動物而感到內疚。雖然奧根農場承諾器官豬死后不會被做成腌肉或香腸,但在肉類稀缺的背景下,豬肉制成的各種食物仍然頻繁出現在員工餐廳的菜單上。吃飯的時候,大家會開玩笑說又吃器官豬餡餅了。吉米食不下咽,因為他認為器官豬是和他一樣的生物。吉米視動物為伙伴,對變異動物表示同情,認為人對動物負有責任;而秧雞視動物為實驗品,根據消費需求像機器零件一樣對動物進行重組。阿特伍德選擇吉米帶領“秧雞人”在新世界重生說明了他認為人類最本質的特征是動物性,人類應該尊重動物權利,保持人與動物和諧共生的關系。
三、反思人類與動物的關系
18世紀英國哲學家邊沁從人的角度論證動物的倫理地位,認為動物能感受痛苦,人類對動物負有直接義務。20世紀上半葉,德國哲學家阿爾貝特·施韋澤在《文化與倫理》中提出了敬畏生命倫理,即不僅要敬畏人的生命,而且要敬畏動物和植物的生命,生命沒有高低和貴賤之分。美國生態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中提出了大地倫理學說,即大地是由土壤、水、植物和動物等組成的相互依賴的生態共同體,人類是這個共同體的一員。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球環境污染,生態環境不斷惡化,各種自然災害頻發,人類開始重新審視人與自然、人與動物之間的關系。彼得·辛格在邊沁功利主義基礎上提出了動物解放論——所有動物一律平等,認為動物是有感知力的,進一步論證人應該增加動物的利益,把道德關懷從人類擴展到動物。辛格關于動物解放的觀點集中在《動物解放》一書中,這本書被稱為“動物保護運動的圣經”。后來,美國動物權利理論研究專家湯姆·雷根出版了《動物權利的理由》,提出了另一個概念——動物的權利。雷根認為,動物也有意識和情緒,與人類一樣都是生命的主體,具有自身所固有的價值,與人類一樣具有道德權利。西方動物倫理思想遞進式的發展體現了人類道德的進步和文明的提升。20世紀70年代,環境倫理體系逐漸成熟,動物倫理成為環境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阿特伍德的動物倫理思想是通過小說中的環保宗教組織“上帝的園丁”表現出來的。“上帝的園丁”有自己的圣人、宗教節日和教義,批判人性與動物性二元對立,倡導動物與人類和諧共生的生態倫理思想。基于洪水之后上帝與所有生物立約,“上帝的園丁”認為“動物不是毫無感覺的物體,也不是切碎的肉塊”[5]93。動物和人類一樣擁有對生命的平等權利,動物不為人類而存在,它們擁有屬于自己的固有價值和權利。“上帝的園丁”有許多宗教節日是以動物的名稱命名的,如鼴鼠日,通過慶祝鼴鼠節,引起人類對動物界邊緣物種的重視;四月魚節,借此呼吁人類對海洋動物的關愛;狡蛇節,借蛇的智慧,希望人類認識到動物性是人性的基礎,順應自然本能,遵循自然規律。園丁們遵循自然的生活方式,平時吃素食,養殖蜜蜂,培植菌類,用蛆蟲療傷。皮拉是“上帝的園丁”的成員,養殖蜜蜂和培植菌菇是她的專長,并把本領授予托比。皮拉說:“你永遠可以向蜜蜂傾訴你的煩惱。”[5]102皮拉死后,托比常與蜜蜂對話,視蜜蜂為朋友,認為蜜蜂有靈性,是連接生者與死者、往返于現在與未來的信使。“亞當第一”在布道中慶祝鼴鼠節,慶祝地底下的生活,贊美了被人們輕視的不受歡迎的存在。人們很容易輕視那些邊緣的物種,覺得他們可有可無。但事實是,離開它們人類將無法生存。“亞當第一”列舉了眉毛蟲、鉤蟲、陰虱、蜱蟲這些不受歡迎的存在,它們以自己獨有的方式執行著任務。腐尸甲蟲和細菌將腐爛的肉體分解,回歸自然,滋養萬物。如果沒有蚯蚓、線蟲、螞蟻不停地翻弄土壤,大地就會變成像水泥一樣雜亂堅硬,生物將要滅絕。“想想蛆蟲和各種霉菌的抗菌特性,想想蜜蜂釀造的蜂蜜,還有蜘蛛結成的網,對傷口的止血特別有效”[5]166,這些是大自然為各種疾病準備的解藥。“亞當第一”認為各個物種對地球貢獻著自己的力量,肯定了不同物種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人類和其他物種都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人與動物是互為主體的關系,是共生的關系。
加拿大特有的自然地貌以及阿特伍德童年經常跟隨身為生物學家的父親叢林旅行的經歷,使得阿特伍德創作的作品蘊含著豐富的動物倫理思想,折射出作家的動物觀,并加深了作品的生態內涵。人類為了追求經濟利益,加劇了動物的商業性捕殺,許多物種瀕臨滅絕,破壞了生態平衡,不利于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作為生態預警小說,《瘋癲亞當》三部曲意在揭示人類對動物滅絕的漠視、對生物科技力量的過度崇拜和濫用以及貪圖享受、唯利是圖。三部曲并非科幻小說。阿特伍德創造了一個與現實生活近乎平行的另一個世界,深入挖掘了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系,警示人類必須認識到自己人性與動物性的統一以及人與自然與生態系統的統一,同時預警盲目崇拜科技導致的生態倫理危機,批判大院和廢市體現的人性與動物性二元對立的思想,并通過環保宗教組織“上帝的園丁”表達人與動物同為生命主體、人與動物共生、人性與動物性統一的生態倫理思想。阿特伍德通過三部曲小說呼吁人類關注動物的生存狀況,反對虐待和捕殺動物,倡議客觀平等地對待一切動物,構建理想的動物倫理思想,促進人與動物、人與自然和諧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