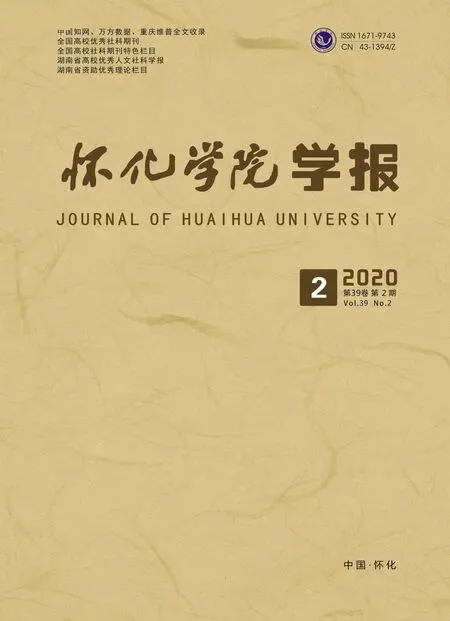小說《漫水》方言寫作特點及其效果分析
周福雄, 粟鳳華
(1.懷化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湖南懷化418008;2.懷化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文理綜合學院,湖南懷化418005)
榮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的《漫水》[1]是一部極具影響力的鄉村題材的中篇小說。《漫水》作為王躍文鄉村敘事的轉型之作,其成功在于以一種回歸的姿態,實現了對沈從文等湘籍作家“泛”方言寫作傳統的繼承與開拓[2]。小說通過獨具特色的方言寫作和一種寧靜恬淡的敘述方式,塑造了許多個性鮮活的人物形象,勾勒出一幅悠然閑適的鄉村圖景,自然呈現了“鄉村的美好傳統”,同時也很好地展示了文學作品創作中方言寫作的巨大優越性。當然,由于方言存在的地域性特點,方言寫作也必然存在局限性。因此,通過對小說《漫水》的分析,探究其方言寫作的特點和效果,對進一步開展方言寫作及其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漫水》方言寫作特點
在小說《漫水》中,作者一改過去官場小說的寫作方式,采用了地道的漫水方言進行寫作。小說中各式各樣、獨具特色的漫水方言用語,使得整篇小說呈現出濃郁的地方色彩,給讀者帶來了意蘊濃厚的地方民俗文化生活體驗。小說的方言寫作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方言詞語大量使用
《漫水》語言中的方言詞語隨處可見,比比皆是,其中,尤以方言名詞、方言動詞和方言形容詞數量最為豐富。而且,由于表達的需要,部分方言詞語的使用頻率也非常高。
1.方言名詞
相對于其它詞性的方言詞語,《漫水》中的方言名詞數量無疑是最多的。這不僅是因為小說中涉及的事物眾多,而且很多都需要用方言來指稱。比較突出的有以下三類:
第一類,人名稱謂類。最具特色的是以下幾種:
前綴“老”加其他語素構成的稱謂語及其衍生稱謂語,如老弟(弟弟)、老娘(母親)、老爹(父親)、慧老弟(弟弟)、老弟母(弟弟的妻子)等。
青少年男性姓名中區別性的單字加“坨”構成的稱謂語,如旺坨、發坨、強坨、金坨等,都是長輩對晚輩或同輩之間對青少年男性的昵稱。
丈夫姓名中區別性的單字加“娘娘”構成的稱謂語,表示“奶奶”的意思,體現了漫水以男為尊的傳統觀念,如余娘娘、慧娘娘等,是晚輩對長輩的尊稱。
丈夫的名加“阿娘”構成的稱謂語,如有慧阿娘、有余阿娘等,是對同輩男性妻子的稱呼,同樣體現了漫水人以男為尊的傳統觀念。因為是對同輩的稱呼,因而稱謂語前面加上了既顯得平等、親切,又具有區別作用的“有慧”“有余”等男性姓名中完整的“名”。與上一類稱謂語“余娘娘”“慧娘娘”不同,因為是晚輩對長輩的尊稱,當然不能直呼其名,喚作“有余娘娘”“有慧娘娘”自然就有失體統了。
其他稱謂語。如崽(兒子)、伢兒子(小孩子)、女人家(女人)、后生家(青年男子)、糧子(軍人)、猛子(很大膽的人)等。
第二類,植物動物類。
如貓兒刺、老鼠刺、樅樹(馬尾松)、樅茅(樅樹葉)、樅菌(一種食用菌)、早禾郎(蟬)、狗娘(母狗)、蛐蛐(蟋蟀)、老鼠子(老鼠)等。
第三類,其他類名詞。
指時間處所的,如日里(白天)、山窩堂(山里的洼地)、灶屋(廚房)、地場坪(屋前的坪地) 等;
指食品餐飲的,如點心飯(中飯)、財頭肉(豬頭肉)、血湯肉(用新鮮豬血、腸油、里脊肉做的湯)、團年飯(除夕團圓飯) 等;
指其他事物的,如零星錢(零錢)、遠路話(外地話)、爛話(挑撥離間的壞話)、雙雙話(含沙射影的話)、直話(耿直實在的話)、補巴(補丁)、老屋、千年屋、老木、壽木(棺材)、日頭(太陽)、洞眼(小洞)、腦殼(腦袋)、肉皮(皮膚)、眼珠子(眼珠)、窗格子(窗格)等。
“崽”是湘語親屬稱謂語中一大特色,可以看作湘語的一個核心特征詞[3]。同時,以上的多個“子”尾名詞,都充分體現了該小說湘方言寫作的特點。
2.方言動詞
《漫水》中的方言動詞也較多。這不僅在于漫水方言中存在諸多與普通話詞語同義的方言動詞,而且,由于各地存在的不同民俗文化生活,漫水人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形成了一些普通話中并不存在對應詞語的方言動詞。
第一類,普通話中存在同義詞語的方言動詞,如聽(聞)、落(下)、過(嫁)、樹(建)、怕丑(害羞)、出窯(分娩)、曉得(知道)、撲黑(偷襲)等。但在小說中,因為表達效果的巨大差異,這些詞語并不宜被普通話詞語所替換。如(文中所有例句都來自小說《漫水》):
(1)漫水人的年飯弄得早,中午邊上就聽得家家臘肉香了。
(2)大肚婆都掐著手指算日子,猜哪個先出窯。
第二類,普通話中不存在同義詞語的方言動詞。如虎(瞪大眼睛,露出兇相)、燂(在火上來回移動進行短暫燒烤)、擔腳(做腳力活)、跟腳(小孩跟著大人不愿離開)、出燈(正月初三開始舞龍燈)、做酒(舉辦宴席)等。如:
(3)我過去不爭氣,放排、拉纖、擔腳,幾個辛苦錢,都花在堂板行了。
(4)漫水正月初三開始舞龍燈,叫做出燈。
3.方言形容詞
《漫水》的語言不僅體現了鮮明的方言寫作特點,而且非常淳樸、簡練,具有很強的口語化特點,因而,形容詞等修飾、限制性詞語的使用自然比名詞和動詞要少。
第一類,性質形容詞,如靈空(聰明)、里手(內行)、霸蠻(堅韌執拗)、靈泛(腦子反應快)等。
第二類,狀態形容詞,如烏青烏青(非常綠)、筆陡(非常陡峭)、麻眼(天色變暗)、油光水亮(光亮潤澤)、白亮亮(銀白發亮很有光澤)、亮晃晃(光線好很清晰)等。如:
(5)你胃口再怎么不好,霸蠻米湯都要喝幾口。
(6)有人記得她的頭發,梳了個油光水亮的髻子,髻子上別了個白亮亮的銀簪。
4.其他方言詞語
除了以上三類方言詞語,小說中也出現了少量其他詞類的方言詞語,如方言代詞“哪個(誰)”、方言量詞“條(只)”“餐(頓)”、方言介詞“把(用)”、方言語氣詞“哩(呢)”等。如:
(7)有人發現自家的甘蔗或橘子被偷了,多會叫罵幾句,哪個也不會當真。
(8)另外,你捉條雞送去。
(9) 有慧說:“昨天夜里,老子打了綠干部一餐!”
(10) 余公公懶得回答,只說:“你把眼睛看吧。”
(11) 有人笑話說:“余公公怪哩,菜種得老遠,花種在屋前屋后!”
(二)方言慣用語獨具特色
慣用語是口語中短小成型的習用短語,往往作為語句中的構成成分,言簡意賅,生動形象,能起到一般語言達不到的表達效果。在《漫水》中,無論是作者陳述還是人物對話,都時常會蹦出這樣的慣用語來,如果再配之以湘方言的語音、語調,則人物情態瞬間躍然紙上。如講冤枉話(說人壞話,造謠生事)、擺龍門陣(聊天)、找梯子落地(找臺階下)、嘴巴不上路(說話不中聽)、不進油鹽(聽不進建議和勸告)、卷喇叭筒(要抽煙時臨時用小塊方形紙卷成喇叭狀,里面塞進煙絲制成草煙)、不得信(沒有感覺到任何征兆)、嘴巴上長了塊牛麻牝(咒罵別人嘴巴不干凈說壞話)、把嘴巴撕齊耳朵邊(咒罵別人說壞話,要撕爛其嘴巴)等。
(12)有余自己找梯子落地,說:“不信,我去捉個蛐蛐來!”
(13)有慧阿娘白了男人家一眼,說:“你嘴巴不上路!”
(14) 你愛聽就聽,不進油鹽也沒辦法。你想想吧,我要炒菜去了。
(15)老木開始上漆,慧娘娘說:“不得信就落雨了!再多晴幾日就好了。”
(16)有慧嘿嘿笑著,說:“他媽媽的,哪個喊他嘴巴上長了塊牛麻牝?”
顯然,漫水方言中的慣用語,對于漫水人而言(當然也包括作者)幾乎是信手拈來,而且已經完全成為他們日常口語表達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自然帶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
(三)方言諺語豐富生動
諺語來源于人們對生活的長期觀察,是對客觀事物的認知及其規律的總結,因而往往形式通俗,結構固定,含義雋永。《漫水》中的諺語數量眾多,含義豐富,地方特色鮮明。從語義角度可以將《漫水》中的方言諺語大致歸為以下幾類:
1.事理認知類。如:
(17)俗話說,討死萬人嫌!
(18)懶人自有懶人福。
(19) 人死如燈滅。
(20)從良的婊子賽仙女。
(21)人正不怕影子歪。
(22)肥水不落外人田!
(23) 好鑼不要重敲,好鼓不經重錘!高人莫攀,矮人莫踩!
(24) 老話講得好,吃不窮,用不窮,盤算不到一世窮。
2.農事氣象類。如:
(25)雷打冬,牛欄空。
(26)喜鵲叫,風調雨順!
(27) 人勤地不懶!
3.生活知識類。如:
(28)蟲老一日,人老一年。人一世,蟲一生。
(29)山上打野豬,見者有份!
(30)邊出日頭邊落雨,東海龍王過滿女。
(31)俗話說,木匠看凳腳,瓦匠看瓦角。
(32)泥匠看墻角,裁縫看針腳。
(33)看女要看娘,看屋要看梁。
(34)二十五,推豆腐;二十六,熏臘肉;二十七,獻雄雞;二十八,打糍粑;二十九,樣樣有;三十夜,炮仗射!
毫無疑問,小說中大量使用的諺語都是漫水及其他湘方言區人們生活經驗和智慧的結晶。它們不僅生動展示了湘西農村人們生產生活及文化民俗的特點,而且,諺語中“日頭”“落雨”“滿女”“糍粑”“炮仗”等方言詞語的使用也很好地體現了湘方言特點。當然,這些諺語的使用也讓小說語言更加豐富而生動,方言寫作特點也更得以突顯。
二、《漫水》方言寫作的效果分析
《漫水》描繪出來的鄉土世界充滿了詩意與溫情,始終彌漫著淳樸、自然且毫無雕琢痕跡的鄉土民俗與人情人性之美,這無疑都極大提升了小說的審美效果和對讀者的吸引力。究其根源,小說運用的方言寫作策略是形成這一效果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方言寫作不可避免地會給廣大讀者帶來閱讀上的障礙,或多或少影響著讀者對作品的理解和欣賞。同時,書面語言中方言語音、語調的缺失,也大大削弱了小說語言的表現力,從而導致了方言寫作中難以避免的局限性。具體分析如下:
(一)積極效果
1.構建了詩意醇美的鄉村世界
方言匯集了大批生動有趣的民間用語,包括方言詞語、諺語、慣用語、民謠、故事傳說等。因此,《漫水》中的方言寫作自然為作者構建一個原生態的醇美的鄉土世界提供了最生動、最豐富的材料。同時,小說中大量至簡而不加雕琢的生活化語言風格與方言詞語、慣用語、諺語的特點完全融為一體。因此,這種簡約樸實的生活化語言與各式各樣浸潤著泥土氣息、特色鮮明的方言詞語、慣用語、諺語共同勾勒出一個個鄉土氣息十足的民俗活動場景和鄉村故事,立刻就在所有讀者面前構建了一個詩意醇美的鄉村世界。如:
(35)伢兒們踩高腳,放炮仗,滿村子瘋。女兒家踢毽子,小辮子在后腦殼上一跳一跳的。
(36)撿大菌子過癮,吃還是小菌子好吃。就像捉泥鰍,捉喜歡捉大的,吃喜歡吃小的。
這些句子幾乎就是漫水人日常交談中最平常的生活語言,無需雕琢修飾,脫口而出,但寥寥數語,卻意蘊甚濃。句(35) 用白描的方式,通過多個方言詞語的使用,生動描繪了過年時孩子們盡情玩樂、村子里一派歡樂祥和的節日氛圍;句(36) 通過直白的總結式的話語折射出了漫水人們生活的樸實與自得,以及從簡單的生活中獲得的快意和滿足。
2.塑造了鮮活豐滿的人物形象
作為一部鄉村題材的小說,通過方言對話來塑造小說的人物形象,自然是小說創作者的最佳選擇。而且,用方言進行寫作更貼近小說人物真實的生活狀態,更能充分展現人物的性格,從而塑造出鮮活豐滿的人物形象。如:
(37) 喊了半日,余公公感覺不對數,拿手摸摸慧娘娘的額頭,再摸摸她的鼻孔。“老弟母,你莫愒我啊!”余公公虎地站起來,反手朝強坨扇了一耳光過去,“你娘都冰冷了,你這個畜生!”
(38) 秋玉婆更是起了高腔,朝有余阿娘拍手跺腳的:“我講她,你也幫腔?曉得你倆共穿一條褲子!你們樣樣是打伙的,屋打伙住,兒打伙養!……”
句(37) 生動描述了余公公在臥病幾天后登門看望慧娘娘,卻意外發現慧娘娘已經去世的情形,從“摸額頭、鼻孔”以及自言自語“你莫愒我啊!”我們分明感受到了余公公對慧娘娘貼心的關懷,以及那種發自內心深處的擔心和后怕。緊接著,余公公突然“虎地站起來,反手一耳光”以及怒罵強坨“你娘都冰冷了,你這個畜生!”又讓我們從老人迅猛的行為和怒斥中瞬間感覺到了這位老人內心無比的憤怒和悲痛。句(38)則通過“起了高腔”“拍手跺腳”以及后面含沙射影的詈罵語,非常生動地刻畫了秋玉婆在“相罵”時那種潑辣蠻橫、尖酸刻薄的農村婦女形象。
3.形成了樸實生動的敘事語言
寫家鄉的人和事,用家鄉的方言進行寫作自然比普通話具有更強的塑造力和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在創作中,作者可以充分發掘自己的靈感,調動所有情感和潛能,輕松找尋到最鮮活、最生動的言語進行敘事,從而很好地還原鄉村生活的本真,形成方言寫作獨特的審美效果,自然也大大增強了小說語言的感染力。如:
(39)偷甘蔗也有手藝,用腳踩著甘蔗蔸子,悶在土里掰斷,不會有清脆的響聲。
(40) 有余見她立起來了,也不望她的臉,只瞟著她的腿腳,輕聲道:“好鑼不要重敲,好鼓不經重捶!高人莫攀,矮人莫踩!”
句(39) 通過方言口語的表達方式,原汁原味地再現了鄉村孩子們“偷甘蔗”的手藝和場景,形神兼備,不僅細膩地體現了孩子們的調皮與狡黠,更突出反映了漫水的鄉村世界里人們生活的情趣與溫馨。句(40) 中,睿智的長者余公公通過幾句形式整齊、含義深刻的方言諺語,不僅巧妙告誡了秋玉婆謹慎做人的道理,也讓小說的語言更加樸實生動,韻味十足。相反,如果放棄方言寫作方式,改為普通話創作,我們不難想象,其中的韻味必定大打折扣。這正如作者所說:“我并不是刻意為之,鄉村生活決定了文字本來的面目。”[4]
(二)局限性分析
方言是局部地區的人們使用的語言,它并不具備全民性。在文學創作中,用方言進行寫作,在產生諸多積極效果的同時,其存在的局限性也是難以避免的。
首先,方言詞語、慣用語、諺語等方言用語必然給廣大非該方言區讀者帶來諸多閱讀理解方面的障礙,繼而影響讀者對作品的主觀評價。在《漫水》中,雖然大多數方言用語讀者能夠理解,而且作者對其中部分方言用語也進行了解釋,但作者并沒有也不可能對所有方言用語都逐一進行說明。或許在作者看來,部分方言用語并不需要進行解釋,甚至部分方言詞語、慣用語、諺語真無法用普通話來準確說明。這就必然使讀者在閱讀中留下一些疑惑。如“山坎坎”“山窩堂”到底是怎樣的地勢,“擔腳”“麻眼”“不得信”是什么意思,也許一些讀者能夠連蒙帶猜,大概理解,部分讀者就只能望“言”興嘆了。
其次,在用方言寫作的文學作品中,為了盡可能減少由于方言用語給讀者帶來的閱讀障礙,作者必然會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去解決,如直接在敘述中解釋、前后同義反復、利用對話巧妙解釋等。在《漫水》中使用得最多的方法就是直接在敘述中進行解釋,如“漫水這地方,爺爺就是公公。”“漫水人說男女私通,叫做搞網絆。”“老屋就是棺材,也是漫水的叫法。還叫千年屋,也叫老木,或壽木。”通過插入這種直白的解釋,陌生的方言得以被讀者理解和接受。但大量注釋的存在不僅阻隔了讀者的思緒和感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讀者閱讀時的效率和流暢度。
最后,用方言寫作的作品,對于那些熟悉該方言的讀者而言,在閱讀時很容易喚起最真實的感受,從而引發讀者強烈的共鳴,因而在閱讀中自是妙趣橫生。如《漫水》中使用的辰溆片湘方言正是筆者使用的方言,讀到這些耳熟能詳的方言用語,那些熟悉的方言語音、語調總是自覺而迅速地從腦海中蹦出來,然后驀地轉化為無比生動的畫面,讓人忍不住拍案叫絕!如“你要是亂說,我把你嘴巴撕齊耳朵邊!”“不得信就落雨了!”那種辰溆片方言區說話人特有的語音、語調和脫口而出的順溜、自然的神情,非該方言區的讀者在文字中一定是無法感受到的。我們不得不承認,用方言閱讀和用普通話閱讀的感受相差了十萬八千里——沒有了方言的語音和語調,這些方言用語幾乎就失去了靈魂!因此,用方言寫作的作品,對于那些完全不了解該方言的讀者而言,因缺少了方言語音、語調的依托,確是一種無法彌補的缺憾,自然也就成了方言寫作中難以克服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