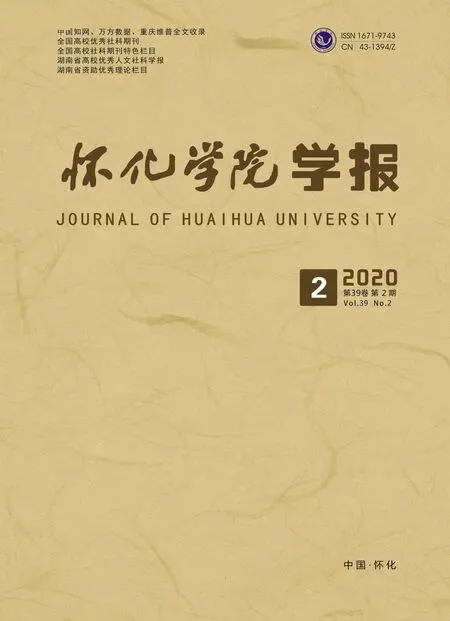巫道文化與當代湘西文學的悲劇意識
彭繼媛
(吉首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湖南吉首416000)
湘西是一個保留著濃厚巫文化色彩并具有明顯地域性特征的地方,有學者這樣寫道:“由于歷史上道家文化與巫文化互相滲透,使得湘西文化既保留了特有的文化特質,也染上了道家色彩,這種道家色彩以一種集體無意識方式積淀沈從文的內心,使沈從文的創作表現出了道家文化意蘊。”[1]而我以為,追隨著前輩作家沈從文的寫作傳統,蔡測海、黃光耀等當代湘西作家的創作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表現出了道家文化意蘊。在湘西,巫的命運是悲劇性的,不僅在歷史上被強勢的漢文化所驅逐,近現代以來也被現代化轉型的社會擠壓到邊緣甚至地下。作為湘西文化圖騰巫的這種悲劇性命運與道家悲劇意識的結合,深深地刻印在當代湘西作家的情緒意識中,使得他們以不同的書寫姿態表達著這個區域中的人們所固有的悲憫情懷和憂患意識,所以當代湘西作家在思想意識特征上繼承與弘揚了傳統湘西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鑒于沈從文開啟了當代湘西文學的傳統,本文將沈從文的作品納入研究視野,并從巫風浸潤的悲劇人生、異化生存的悲劇人生、欲望下的悲劇命運三個方面分析當代湘西文學中巫道文化所蘊含的悲劇意識。
一、巫風浸潤的悲劇人生
在民族發展中,有學者這樣說:“巫或覡,占據了與眾不同的社會地位,成為人界與神界之間的媒介,同時也是神意的轉達者。所以他們的意見,就被看做神的旨意。神意和命令必須通過他們的傳譯才能下達于凡人。因此,巫師具有特殊身份,在早期社會中擁有崇高的地位,是集團首領、政治首領、文化的創造者和知識、技能的擁有者和傳播者。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巫師的地位卻每況愈下。從漢代起,原來神圣崇高的巫術業已被視為‘賤業’……巫士多出身貧賤。至封建社會中晚期,巫師更成了罪惡的代名詞。”[2]在當代湘西文學作品中,巫、巫師或視為常人的身份,或置于神圣的位置,或遭遇了走下神壇的悲劇命運,而深受巫風影響的湘西人也不可避免遭受了悲劇的命運。正如有學者這樣說:“在理性之光無法照耀到的角落,人對鬼神世界的冥想、對同類的防范、巫師人神一體的迷狂、祭祀鬼神的狂歡,帶來了非理性狂熱下釀造的悲劇。”[3]
沈從文在《湘西》中介紹和評價了留存于湘西的巫術如放蠱、趕尸、落洞等,他在《月下小景》《鳳子》 《神巫之愛》等篇目中描寫的神巫形象,是把巫作為一個普通的神的使者來描繪的,巫和普通人一樣都有喜怒哀樂、生老病死。如沈從文《秋》與《病》中五明的干爹就是這樣一個巫師,他在行巫儀式前后與主人拉家常,說笑話,熱心撮合五明與阿黑等等都是極為普通的人生場景。當然沈從文也在《貴生》 《阿金》 《雪晴》等作品中展現了鄉下人迷信巫術的不利方面,使得其小說充滿了迷信的宿命感與悲劇意識。《貴生》中的貴生,因為忌諱“金鳳八字斤兩重、克夫”,錯失了金鳳;《阿金》中的阿金同樣迷信于“寡婦克夫”的說法;《雪晴》中的鄉下人其迷信被人為的禮教利用,最終導致罪惡與悲劇。
沈從文之后的第二、三代當代湘西作家如孫健忠、田瑛、田特平、黃光耀等無不在作品中書寫著巫文化帶給他們的影響,比起前輩他們一方面書寫湘西人信神崇巫的思想,另一方面也關注巫師及其深受巫文化影響的湘西人在現代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悲劇命運。孫健忠作品中可較多地見到他對巫術、祭神、占卜的描寫。如《城角》中只因私塾老師說剛生下的嬰兒來日不是王爺就是將相,導致眾多的山民前來拜神。《啊,罌粟花》中大嘴媒婆因天上的流星活活拆散一對鴛鴦,造成一個獨守青燈、精神受到摧殘;一個傷痕累累被迫遠走他鄉的現實悲劇。蔡測海《船的隕落》中老土司面對老裁縫,帶著法器,為其超度亡魂。侯自佳《古鎮棄兒》中,醫治人們心靈的傷口,不是請醫生打針上藥,而往往是通過“燒香燒紙”“磕頭作揖”去拜求命運之神——算命先生和看相師父,似乎只有他們才有仙丹靈方。田瑛在其作品中描寫巫術、祭神、占卜,書寫巫師在現代社會的悲劇命運及其深受巫文化影響的湘西人的悲劇命運,在當代湘西作家中很突出。他曾說,“老家自古巫風盛行,除了趕尸,還有輪回轉世一說”[4]。在《龍脈》中父親意識到自己將要離開人世,告訴兒子如何預卜兇吉征兆,如何解夢,如何避邪,如何祭祖如何敬神……等等。如果說在《龍脈》中巫的崇高位置是毫無疑問的,那么在《活巖》中看似死胎的嬰兒活了,香爐逃脫劫數,重新得到安置,可以說巫的崇高位置開始坍塌,只是維持著它暫時至尊的地位。《早期的嫁穡》中母權的喪失也意味著巫的至上位置已經喪失。同樣在《綿綿的山藤》中泥菩薩被捏成了齏粉。《遠山的耕耘》中巫的命運已經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至高無上的巫師最后落得自殺的結局,雖然終究又活過來卻也只能過著行尸走肉的日子。而在《山的圖騰》中巫的崇高位置已經被新的神所替代:“此神并非泥塑,亦非木雕,而是一張彩色的紙像,鑲嵌在一個鏡框里,懸空而掛,占據了大半邊倉壁。那神從容地作微笑狀,望著他,讓人有一種沐浴在陽光下或春雨中的感覺。神的目光具有奇跡般的輻射效果,無論你怎樣變換視角,都能感受到他的普照。”[5]在新的時代,人們已經找到了代替巫師位置的具體的“神”。而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田瑛在《沉棺》中書寫了深受巫文化影響的湘西人難以跳脫巫的約束,轉而用毀滅的方式表示反抗所產生的撼人靈魂的悲劇性。在這個故事中駝子的自我活葬,人們心安理得地安葬活人、把有異相的嬰兒丟到河里,上演著一場場殺人不見血的悲劇,這不得不讓人深思巫作為一種精神的束縛所帶來的巨大荒謬性。苦心積慮的駝子怎么也想不到他精心策劃的自我犧牲會功虧一簣,而故事結尾算命先生對其雙生孫子的命運八字的預測更凸顯了故事的悲劇性。同樣田耳在《掰月亮砸人》中反思巫蠱盛行的民風下湘西窮鄉村姑桑女的悲劇命運。黃光耀、于懷岸分別用長篇小說《土司王朝》 《巫師簡史》來關注巫師的命運沉浮。黃光耀《土司王朝》中的梯瑪難逃悲劇的命運,雖然梯瑪天賜在容美境內人人敬畏,像神一樣供奉著,但作為人生命中最可貴的親情、愛情等愿望均被壓抑或剝奪,其內心是痛苦的。于懷岸《巫師簡史》中一代代巫師被塑造為承載著神意但卻是“向死而生”的人,末代巫師趙天國在他完全喪失巫師的法力后也就失去了神的眷顧,最終他為了貓莊族人的生存失去自己的生命。此外黃光耀《白河》 《虎圖騰》等作品也關注巫師的悲劇命運。
生活在湘西地區的人們信仰多神崇拜,對神巫敬畏,人們的一切活動,都或多或少地蘊藏著敬神驅鬼的巫文化成分。人們通過神巫進行各種祭祀活動、施行巫術和虔誠地祈禱來表達自己的愿望,以期得到與神的對話,得到神的庇護和恩賜,從而讓自己生活得更好。直至近現代生活在湘西地區的民族仍然“信鬼成俗,相沿至今”,這里的人們用各種各樣的節日來迎接心目中的神,通過祭祀、還儺等儀式重復著古老的傳統。沈從文、孫健忠、黃青松、田特平、于懷岸等作品中還可以看到神圣的巫術。但“五四運動”以來,隨著對科學理性的崇尚,對重塑國民健全性格的迫切愿望,巫和巫術一度被視為鬼神迷信。在具有了現代科學意識的作家看來,“鬼神之說”是生產落后、科學不發達的結果,是一種愚昧的思想。正如新文學倡導人之一的陳獨秀說過:“今之風水、算命、卜卦、畫符、念咒、扶乩、煉丹、運氣、望氣、求雨、祈晴、迎神、說鬼,種種邪僻之事,橫行國中,實學不興,民智日僿,皆此一系學說之為害也。”所以,要“去邪說,正人心”[6]。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當代湘西作家作品中無處不在的巫文化就變成了一種無形的精神枷鎖,進而對人性產生了極大的傷害。其中田瑛以多個作品書寫了巫師怎樣一步步從至尊的地位到被拉下神壇的過程。其《沉棺》中駝子對命運詛咒所作的反抗更顯其命運悲劇的深刻,這種對愚昧山民深受巫風蠱惑的反思有著與沈從文同樣的憂患意識。與沈從文不同的是,田瑛、黃光耀、于懷岸等開始書寫巫師在新時期的悲劇命運,曾經在邊遠的湘西延續了千余年的巫文化在“科學”“民主”等現代觀念面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二、異化生存的悲劇人生
“人為物役”“心與形化”常常用來指代老莊時代異化的悲劇人生,在這個時代人性被扭曲,“人”作為個體存在常常被社會異己力量所吞噬……在對這種異化現象的深刻認識中,莊子感到極大憤慨與深深的悲哀。而在當代湘西社會,雖然地處偏僻,但現代文明的入侵和席卷全國的政治運動對人性的摧殘,同樣極大地觸動了當代湘西作家的心扉。沈從文、孫健忠、蔡測海、吳雪惱、侯自佳、田瑛、吳國恩、黃光耀、于懷岸、張心平等作家的一大批作品表現出對人的關懷和憐憫,流露出深刻的悲劇意識。
沈從文論及自己的作品時,曾說人們照例會為其作品的樸實、清新而感動,而往往忽略了其文字背后隱伏的悲痛。以此來觀照沈從文的作品,其不動聲色看似淡然的敘述在表現人精神的扭曲所導致的異化的人生方面是令人震撼的。如《丈夫》中的丈夫為了生存竟然把年輕的妻子送到小河的妓船上去做“生意”。《上城里來的人》中的農婦認為軍隊強奸婦女是常事,不必害怕,農婦表面看似漠然其實蘊藏著難以述說的苦難,她的態度既是對軍隊和當權者變相的反抗,也是她面對殘酷的現實處境無可奈何的表現,其性格靈魂上的變形和扭曲可見一斑。如果說沈從文都市題材的小說大多是揭露教授、紳士、大學生等所謂社會精英種種異化的人生,那么沈從文在《邊城》等湘西題材的小說中所表現的那種來自鄉村淳樸自然的人性也在逐漸泯滅,由此可知生活在社會多重壓榨下的人們,不僅在經濟上陷入生活的泥沼,而且靈魂上毫無尊嚴可言。此后第二、三代湘西當代作家繼續關注特定歷史階段中湘西人異化的生存困境。孫健忠《留在記憶里的故事》中老實、勤勞的來順阿公和他活潑、善良、年輕的孫女幺姑都在大躍進運動中死去。蔡測海《激情被你耗盡》中勤勞、善良、用情至深的“我”,抱著最淳樸的愿望憧憬著與馬六的幸福生活,可生活卻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外界的干擾,雖然“我”最后撿得了一條命,但卻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這種來自外界的生存壓力帶給人的日常生活乃至精神的摧殘是不言而喻的。吳雪惱《長竹筍的時節》中奴秀和玉杰兩表兄弟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因饑餓悄悄逃到貴州做鋸匠,日子艱難還要承擔著被公社抓回去定大罪的風險。侯自佳《翌日,將是一個溫馨和煦的晴天》中的曹世萬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所有知識分子的縮影,惡勢力肆意的攻擊和誣陷摧垮了他的肉體和精神。吳國恩《尋找詩人夏天》中“我”的父親作為一位歌手,在苗鄉本擁有與巫師同樣尊貴的地位,卻因唱歌被關到牢里三年,而工作隊的成員詩人夏天也因與父親志趣上情投意合,時刻被監視。田瑛《風聲》中人們守著公社的糧食,“大公無私”地看著“我”的妹妹被餓死。黃光耀《白河》中的大隊支書何詩光憑借手中的權力處處刁難“我”的父親田大年,當“我”奶奶揭穿他后,他多次污蔑奶奶并導致奶奶瘋癲。張心平《張蒲扇趣事》中的張蒲扇根據張家灣地勢高、熱得遲、冷得早的實際情況改變了種雙季稻的計劃,雖然當年張家灣獲得豐收,但張蒲扇一夜之間變成了反革命。吳雪惱《哥哥》中尚未成年的弟弟,為了革命不惜與家人劃清界限,等媽媽的問題得到平反后,他又自私地瞞著家人去頂替媽媽的職位,弟弟在異常的年代所表現出來的人性異化是觸目驚心的。由此可見,盡管老莊時代和當下的湘西社會相距甚遠,但生存在不同時期的人們卻都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異化人生,陷入了人生的悲劇泥濘。秉承著道家對人生存的悲憫意識,當代湘西作家對極權政治下普通民眾的生存給予了深沉的關注。
走過了動蕩歲月,尤其隨著與外部世界交流的日益加強,異于農耕時代全新的現代生活模式和現代思維方式逐步打破了湘西的鄉村生活,對城市文明和商業化的過度追逐所導致的“道德淪喪”現象日益增多,人的異化現象也越來越明顯,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淳樸牧歌情調正逐步遭到破壞。事實上大家熟知的沈從文所創造的文學湘西是他構筑的烏托邦世界,而其理想世界的載體《邊城》中眾人對要“碾坊”還是要“渡船”的不同選擇已可見商業文明對湘西人影響的端倪。孫健忠小說在再現原始的同時,也再現了城市文明對人性的腐蝕,最為普遍的是在城市文明的快速進程中,滋生了一些唯利是圖的現象。如其《乘風而去》中馮老大辛辛苦苦用心血雕刻出來的東西,只因他不愿意變賣成金錢,被兒子兒媳們砍得粉碎。蔡測海《黑手》呈現的是一個充斥著謊言的鄉村世界,自覺憋屈的男人可以不分青紅皂白捂死妻子和孩子,并合裝一口木頭匣子;在烈日炙烤下白發父親希望英俊少年兒子記起臥冰求鯉、割股救父那一類故事,充滿著現代社會的異化人性又遺留著傳統思想的痼疾。田瑛《金貓》中金錢對人心的蠱惑所呈現的異化更是令人震驚,故事中的王為了留住金貓竟可以將自己的兒子送給愛吃人肉的惡霸,因為金子在他意識里比生命更為重要。但最終王因為金貓讓兒子喪失了性命,自己也丟了命。黃光耀《硅化木》中從父親開始挖硅化木到父親跳進泥坑試圖讓淤泥掩埋自己,鄉村淳樸、善良的民風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是由金錢、物欲和權勢交織的冷漠殘酷的鄉村世界。而“我”在質疑父親行為方式的意義時,“我”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卻也沒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標,“我”無力面對父親的厚重希望。現代人在異化的生存環境中艱難生存,上演著一出出人生的悲劇。吳國恩《給一只狗命名》中企業家蠻子占有了小雄的妻子杏花,原以為血氣方剛的小雄和杏花的哥哥順子會和蠻子有一場惡戰,但蠻子卻僅憑年薪十二萬的職位就收買了小雄和順子,尊嚴在金錢面前顯得不值一提。現代社會中,城市建設的步伐加快了對鄉村的侵蝕,影響著他們農耕的生活方式,他們在城市和鄉村之間艱難抉擇。吳國恩《泥腿根子和他的土地》中,根子和他的舅舅根發老人拼命護著自己的耕地,哭過鬧過但耕地最終沒有留住,根子被拘留了,老人一氣之下患病去世。最后根子忍痛賣掉了耕牛,當根子再次進城看到他喜歡的女人妮為了生計已經委身于另一個男人,他蹲在地上嗚咽起來。失去了土地,農民就失去了自己生存的根,失去了自己的家園。從根子的哭聲中可以體味出根子的無奈、茫然、孤獨和絕望,他將被迫離開故土,走向陌生的城市,而城市對他來說一切都顯得那么遙不可測,充滿著太多的不定和恐懼。田耳也多在生活的喧囂與熱鬧的表象中去表現個體的艱辛與無奈。在《衣缽》中,李可雖然大學畢業,但仍然無法走入城市,不得不回到鄉村跟著父親學做道士,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于懷岸《別問我是誰》中“別問我是誰”隱含了進入都市的鄉村弱勢群體的普遍生存狀態,而沒有名字的主人公4號,作為一個符號暗示了進城的人們在城市中生存艱難、沒有身份、找不到歸屬的困境。
地處偏遠山區的湘西,終難抵擋城市文明的影響。當代湘西作家展示人們在現代文明加速發展、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產生的精神空虛、信仰危機、道德弱化、人情冷漠等現象,表達作家們對社會對人生的思索。可以說當代湘西作家作品中對人的關懷充滿著憂患意識和焦慮感,其中所浸透著的深刻的悲劇意識與莊子悲劇情懷是一脈相承的。
三、欲望下的悲劇命運
道家直言不諱地對欲望提出批評,這在我國古代各類文化思想體系中是比較突出的。《老子》曾說道:“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即強調人自身的過度欲望造成了人生的悲劇。當代湘西作家作品中林林總總的人物,為了滿足自身的某些過度欲望,踐踏道德底線,放棄做人的尊嚴,甘做金錢的俘虜等,因此不可避免地品嘗由此帶來的種種苦果。
無論是在沈從文的鄉土小說還是都市小說中,我們都能看到過度的欲望所導致的人性的畸變或悲劇的命運。《丈夫》中可以看到鄉民在外界的誘惑下漸漸變得物欲化、功利化,盡管鄉民的自尊在侮辱中最后得以覺醒。而他書寫的都市社會的人往往因為金錢或權勢過著無聊庸俗、紙醉金迷的生活,甚至連愛情在此都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錢交易。《紳士的太太們》中這些紳士的太太們沉湎于肉欲游戲,荒淫腐朽,猶如行尸走肉。《某夫婦》中,紳士和其太太為了騙取錢財互相出賣對方,夫妻之間的感情因為金錢的誘惑蕩然無存。由此可見,沈從文極力表現都市現代文明中因物欲、情欲的膨脹所帶來的道德的喪失、生命力的萎靡、人性的異化。沈從文之后的第二、三代湘西作家同樣繼承了沈從文對人之欲望下悲劇命運的思考。孫健忠《舍巴日》中的寶明、寶光逐漸變成了物質的工具和奴隸。蔡測海《激情被你耗盡》中從外地逃荒來的外鄉人王胡子,因其貪婪之心最終招致了殺身之禍。《家族企盼》中的水生因過度縱欲最后被眾人“像丟一頭死牛一樣被丟進了天坑”。于懷岸《白夜》中貓莊無業游民黃鱔,因為自己的非分之想被鋒利的斧頭砍掉了腦袋。向啟軍《南方》中陳小狗是個好色之徒,他的死亡宣告了性狂歡背后的毀滅。黃光耀《絕唱》中的秦庭之與不同女人的愛恨情仇最終導致了他割腕的悲慘人生。努力嘎巴(田愛民) 《鸚鵡》中的年輕車工放縱了自己的肉欲,一次次將自己推向了精神的沼澤地。而田耳在《氮肥廠》 《拍磚手老柴》《合槽》 《被猜死的人》對人之過度的欲望所招致的悲劇人生書寫極為深刻。如《拍磚手老柴》中因金錢誘惑陰差陽錯當上了拍磚手的老柴,先是老婆被他拍死了,最后將這磚拍到了自己的頭上。《合槽》中的鄉下老漢為了炫耀自己的電動假牙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還落得因丟了假牙,變形的臉只得用木楔子撐起的悲劇。而《被猜死的人》中,生活在敬老院中的梁瞎子對物質和金錢過度的欲望以及他對老人們魔咒般的控制,讓陷入絕境的老人們合伙結束了他的性命,欲望膨脹下的梁瞎子所表現出的人性的貪婪、無恥、丑惡,實在發人深省。
在道家文化思想領域里,人因為自身過度的欲望導致了諸多的人生悲劇。而當代社會,金錢至上、物欲橫流,人性、人道主義這道亮麗的風景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踐踏。人欲念的增強,造成了新一輪的人性扭曲及生命悲劇。當代湘西作家例如孫健忠、吳雪惱、吳國恩等從政治、現實處境等思考人的悲劇命運時,另有當代湘西作家如向啟軍、黃光耀、田耳、于懷岸、努力嘎巴(田愛民)等書寫著欲望下的悲劇人生,展現作家主體的悲觀情緒和無奈心態,充滿著道家式的傷感與絕望。
如果說“由于悲劇意識在當代文學中的回歸,……道家悲劇意識綿延悠長使得當代文學彌漫著整體的悲涼”[7],那么當代湘西作家作品作為當代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同樣深受道家悲劇意識的影響。事實上,巫文化和道家文化也是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這正如有學者說:“古代巫文化,與其他文化一樣,在歷史的進程中,都要受到當代文化潮流的影響,并從中吸取養分,不斷地新陳代謝。由于歷史上統治階級以正統的立場對巫術與‘淫祀’加以禁絕,使巫教的生存變得十分艱難,于是,巫教(巫法)開始尋求出路,首先就是與道教靠攏,使民間也認同它們同屬于道教。由此巫道逐漸產生新的結合,在民間形成既巫既道、內巫外道之‘道法二門’形態。”[8]而這種“在民間形成既巫既道、內巫外道之‘道法二門’形態”更是為理解當代湘西文化具備“內巫外道”或“既巫既道”的形態提供了一種可能。有學者還這樣具體指出:“鄉土文學與道家文化的連接在于遍布鄉村大地的民間道教信仰,它以內在的生活觀念或外在的巫風民俗構成鄉土文學的一道風景線。”[9]“巫風民俗不僅呈現了鄉土道教的集體無意識心理,而且還成就了鄉土文學的地方色彩或‘異域情調’。”[9]以此來觀照當代湘西文學,秉承沈從文所開啟的湘西文學傳統,當代湘西作家無論是遠離家鄉漂泊在外的田瑛等,還是安然默守如畫家鄉的向啟軍、努力嘎巴(田愛民)等,作為生于斯長于斯的湘西人,他們無一例外都在深情地關注著哺育他們、滋養他們的這片熱土。他們無不深受這塊熱土上濃郁的巫文化的影響,其文學書寫中充滿著浪漫氣息、靈異的想象,這樣一種與生俱來、深入骨髓的對巫文化的崇拜和迷信所導致的神秘癲狂甚至可能是一種無形的精神束縛,使得他們的書寫充滿了別樣的“異域風情”,也預示了其生命書寫存在著難以言說也難以消弭的悲劇色彩。由上可知,當代湘西作品中,巫作為一個“人”的存在其本身的悲劇命運,巫文化所表現出的對生命存在無法預料的未來的隱憂和傷痛,恰恰與質疑壓抑、異化人性的道家文化對個體“人”的生存命運的極大關懷和深深憂患不謀而合,巫文化與道家文化在當代湘西文學中相互融合的狀態由此顯見。而在對生命存在熱切的關懷中,我們發現難以逃離的異化人生往往使得當代湘西作家有著深深的憂患意識,并為之悲憫。這種傷痛和隱憂來源于他們與生活的外在環境和人的自身因素之間所構成的多重悖謬關系所作的深沉思考。值得驚喜并為之感嘆的是如同主流文學中的作家一樣,深受巫道悲劇意識影響的當代湘西作家面對現實的困境他們勇敢地應對,其文學書寫在保持自身特色、繼承與弘揚湘西傳統地域文化、人文精神的基礎上,也表現出向當代中國文學主流挺進的發展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