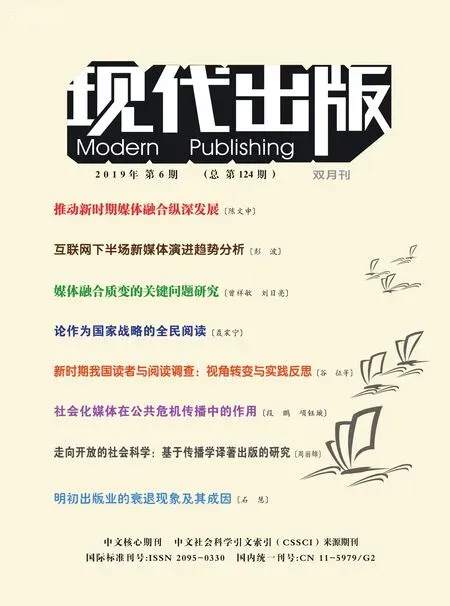走向開放的社會科學:基于傳播學譯著出版的研究
2020-01-14 02:20:28周麗錦
現代出版
2019年6期
◎ 周麗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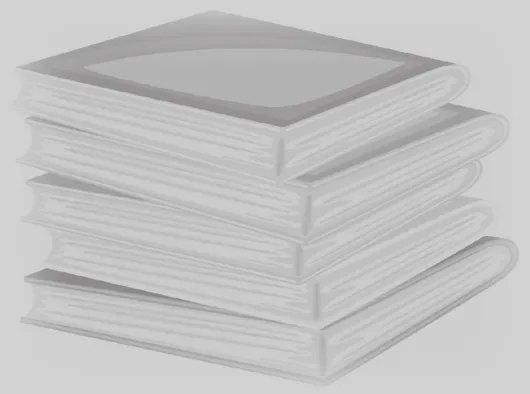
自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通過了新的研究生學科專業(yè)目錄,新聞傳播學被認定為一級學科以來,這一學科尤其是傳播學便進入了發(fā)展的快車道,各種資源和人才不斷匯入,各類成果層出不窮。在圖書出版領域,除了國內學者的專著和教材大量出版外,傳播學譯著的海量涌現成為引人注目的現象。正如有學者注意到的:“進入21世紀以來,在各種硬件條件的支持下,大批西文傳播學專著與教材被系統(tǒng)地譯介進中國……譯叢已經在中國新聞傳播人才培養(yǎng)和學術研究方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
本文考察了2000—2018年國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qū),下同)出版的理論傳播學譯著,形成了包括351種譯著的樣本庫。這351種傳播學譯著中的313種被納入各類譯叢,占總數的89.2%。這一現象表明,傳播學譯著很少出版單行本,譯叢因此具有了研究價值。傳播學譯著所屬譯叢的特征是什么?出版社為何青睞譯叢這一出版形式?傳播學譯著的發(fā)展趨勢是什么等,都是本文要考察的問題。
一、傳播學譯著所屬譯叢的特征
根據本研究的統(tǒng)計,從2000年到2018年,國內共出版了傳播學譯叢109種。通過具體考察可見,這一階段傳播學譯著所屬的譯叢具有如下特點:
第一,譯叢名稱中“文化”“社會”這兩個詞出現的頻率較高。這一階段傳播學譯著所屬的譯叢,除了會使用最為常見的“傳播”“新聞”“新聞傳播”“新聞與傳播”“媒介”“媒體”等詞為譯叢命名,還大量使用了“文化”和“社會”這兩個詞,具體見表1。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國德育(2022年12期)2022-08-22 06:16:18
浙江樹人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4期)2022-08-15 10:58:48
湖北教育·綜合資訊(2022年4期)2022-05-06 22:54:06
金橋(2022年2期)2022-03-02 05:42:50
金橋(2022年1期)2022-02-12 01:37:04
華北理工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1年3期)2021-07-03 09:06:34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18年9期)2018-10-16 06:30:16
軍事文摘·科學少年(2017年4期)2017-06-20 23:29:09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6年2期)2016-05-04 04:18:29
雕塑(2000年1期)2000-06-21 15:13:24